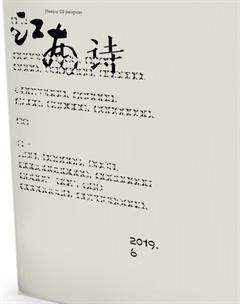斷裂后的銜接
謝魯渤
年輕時寫過幾年詩,中斷了多年之后,最近幾年又開始寫了一些。當初是怎么起的頭,為什么會中斷,現在何以又重操舊業,都沒有多想過。過去的不想也罷,但這幾年的寫詩是一種什么樣的動因和形態,其實就擺在那里,對自己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不用多想。大致上可以借用兩句話來表述,一是不知不覺已到了老年,這是詩人張曙光的句子。沒錯,不知不覺。套用到自己身上就是,在不知不覺到來的老年寫詩,亦可謂不知不覺。二是當我老了的時候,詩歌會來找我。想不起是在哪里看到的,印象中好像還是聶魯達所言,不敢確定,但也不妨籍以自嘲。在相信自己確實不知不覺到了老年時,聽到了詩的敲門聲,這無疑是件有趣的事,繼而重新寫詩,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了。
既然是不知不覺,且因詩歌來找我而為,我的一時興起的寫詩想必還難以具備作為一個詩人的鮮明特點(假如每個詩人都應該有其鮮明特點的話)。事實上我也知道自己已經寫下的許多作品是不值一提的,“我掂量過你,詩人啊,而且覺得你無足輕重。”圣-瓊.佩斯的話,完全可以自認是對我說的。年輕時寫的詩后來出過一個集子,書名《日落回家》,有點關門的意思,以為從此不再出門了,現在又回到街上,環境和風景都變了,得先找找路。斷裂后的銜接,哪怕沒踩到點子上也是可以想見的。
不久前在一個飯局上,詩人孫昌建給我看了一份復印件,是我的早已忘得一干二凈的兩首詩,標題為《紅日永遠照西湖》。昌建是從哪里翻找出來,打算派什么用場,當時沒來得及問他。期間我手頭上正在寫的一首詩叫做《神經痛后遺癥》。起因是去年冬天得了帶狀皰疹,治療后癥狀消失但腿部疼痛一直持續,被大夫定性為后遺神經痛。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感覺新奇,想都沒想,就拿它來寫詩了,顯示出了我隨意性的一面,但寫了幾句就擱置了,如同布羅茨基所言,“一首詩開了頭,詩人并不知道這首詩怎樣結束。”我把這事說給昌建聽,他隨口給了個標題黨句式:從《紅日永遠照西湖》到《神經痛后遺癥》。雖說是句玩笑,倒讓我心頭一亮,一個“到”字,提示了我此番銜接的基點,而“痛”這個詞,應該就是我所以要將斷裂的兩端去做銜接的一個與神經相關的因素。
如此說來,《神經痛后遺癥》也許不會是令人滿意的一首詩,但肯定是于自己有意味的一個象征。不知不覺就到了老年也好,所謂老了的時候詩歌會來找我也罷,無非都是表面的說辭,斷裂后的銜接,其實是我個人的意識形態,通俗一點說,也是神經痛后遺癥在“作祟”。
意識形態這個詞很容易被認為是政治用語,我年輕時寫詩也是很忌諱的,不愿受其影響和牽制。有幾年好讀董橋,見過他的一篇《藏書和意識形態》,認為在馬克思寫成《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之前,由法國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十九世紀初葉造出的這個詞,是指“思想概念”的一種科學,“要人家看出自己癖好和偏見的根源”。后曾一度失傳,經馬克思重新使用,“這個字的意義好像就越來越廣了,運用范圍包括概念、理想、信仰、感情、價值觀、宗教、政治哲學乃至道德標準等等”。董文想說的意識形態,關乎文人的藏書癖好,著眼在藏書家難以自釋的“偏愛”意識,我取的也是這個意思,覺得這一點與我老來熱衷斷裂后的銜接,且并不在意其結果的“形態”,可謂是一拍即合。
在斷裂的兩端,分別只有三、四年的時間。前一個三四年,飽滿、熱情、匆匆忙忙,衣袋里揣一支筆,一個小本子,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寫,寫的比想的多,一下子就被當作詩人了。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是個合集,出版社編輯拿我和集中另一位詩人比較時,說他的詩一句句看,似乎都不知所云,但整篇的意思一目了然;我的詩一句句看則明明白白,但整篇的意思卻令人費解。這是我至今還能記得的,關于自己在詩歌寫作上唯一給人留下的印象,雖僅為一家之言,但對于后一個三四年與詩歌的復合,具有一種讓我不得不經常停下來想一想的制約力。
“詩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詩歌中得到反映,這是藝術的規律,也是人生的一條規律。”(聶魯達)我想我這后一個三四年的寫詩,應該也是脫離不了這個規律的,并且既然處于銜接期,與前一個三四年,一定帶有某種相似性,哪怕只是一點點痕跡。從年輕到老邁,生活的內容與方式無疑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骨子里的形態還是會表現在詩歌中。“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自然,只有有個性和感情的人才會知道要逃避這種東西是什么意義。”(艾略特)如果說我現在的寫詩有什么比較費點心思的地方,我想大概與這個說法相對接近。
詩歌的浪漫主義想象和對現實生活的觀照,在我的“意識形態”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前者偏向過去,后者自然得自于當下。都說老來易懷舊,那是一種從積淀中提煉的行為,和董橋筆下藏書家的癖好似有異曲同工之妙。按董的說法,其意識形態的基本涵義,還是指一個人對習俗風尚的尊重,日積月累,習以為常,知其然而不愿知其所以然,結果就說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了。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很浪漫主義的,富有象征意味。而現實關照恐怕會相對困難些,取自于當下生活的有感而發,見仁見智、莫可一是,但我信奉謝默斯·希尼的話:“與我們自己爭辯的是詩歌,與他人爭辯的是修辭。在直面當下的諸多事件之時,過多的意志較之于處理的手段,往往會扭曲我寫作進程中的節奏感。”
我在2000年夏天有過一次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邀請的肖爾布拉克之行,同行者中的白樺、舒婷、雷抒雁都是著名詩人。和雷同住一個房間時聽他談詩歌的傳統問題,說每個詩人頂多只是傳統導向中的某個小環節。當時因為中斷寫詩已久,沒怎么往心里去,現在復習功課,發現這說法應該來自西班牙的阿萊克桑得雷:“詩與藝術總是特別需要傳統,在傳統中,每個作家頂多只代表在導向表達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他的基本任務是他運用不同的隱喻,把燃燒的火炬傳給熱烈奮進的下一代。”我不敢說自己過去和現在的詩歌寫作是否夠得上這個“小環節”,是否能接近這個“基本任務”,但是在閱讀與練習的過程中,對于前輩和同輩,乃至后輩“在傳統中”的表現,我是格外心儀的,試圖從他們“不同的隱喻”中反觀自身。
以上所說的這些,稱為創作談是不免有些牽強的,它顯而易見的只能說是幾點隨想,缺少深思熟慮的那種格局和深度,但它與我銜接之作的詩歌應該還是相稱的,只是不知道自己的這個寫作還能延續多久,是否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好在有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話擺在那里,“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也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