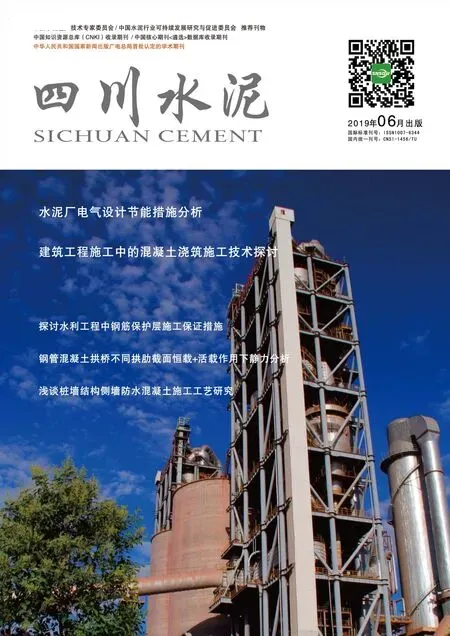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居住建筑文化關聯初探
——以“長脊短檐”為例
黃源媛
(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 重慶 400045)
0 前言
在歷史上,東南亞同時受到中、印兩大古老文化的夾擊,而其固有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又賦予它以明顯的個性。東南亞這種特殊的文化構成也反映在建筑上,從而培養出獨具特色的東南亞建筑文化。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居住建筑也從東南亞地區固有的文化中汲取了不少養分。同時,由于民族遷移的雙向性,居住在東南亞地區的許多民族都不同程度與我國西南地區部分少數民族有著某些關聯。
1 “長脊短檐”象征與實用意義
屋脊長于屋檐、正脊兩端略向上翹起的“長脊短檐”的屋頂形式是東南亞傳統民族民居的又一主要特色,這種長脊短檐的倒梯形屋頂形式實際上是將懸山頂的脊檁延長所致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屋頂形式既滿足使用功能需求又具有審美意義。“長脊短檐”普遍存在于干欄建筑,兩端屋脊搞搞翹起使人聯想到牛角、船等物件。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與東山文化崇尚船的形象有關②,常見于東南亞“船”形住屋,屋脊長于屋身,項脊向內收與邊柱銜接,山墻下各有一塊小檐板代表船首船尾,裝飾牛角、鳥等吉利圖案。
但從技術實現的最優化角度可以做出另一種解釋:為了避免雨水打濕山墻,人們將屋脊向兩邊加長,長脊短檐是節約材料減輕自重和獲得最大遮蔽面積的最佳中間點(如圖6),東南亞傳統居住建筑有兩種入口設置方式,即“正面入口”和“山面入口”,其中“山面入口”較為古老,在這種情況下,“長脊短檐”形式所具備的防雨優點可以得到充分發揮,這樣一種庇護作用還在景頗族住宅中得以證明:人們常利用屋脊的延伸部分設置門廊,由于面積較大屋脊伸出也較長,但是后門使用率低需遮蔽范圍小所以屋脊長度較短也不需要承脊柱
屋脊兩端稍稍翹起是為了中和抵御向下的重力趨勢,減小屋脊下塌的趨勢。“長脊短檐”形式的防雨效果不如在山面加設的披檐,于是就出現了“長脊短檐”與山面披檐相結合的形式,由于設置了山面披檐,“長脊短檐”的形式就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向其本來面目——懸山頂回歸,最后演變成為新的屋頂形式歇山屋頂(圖1)。這個過程反映建筑形式從簡單到復雜的演化,而這種演化又是基于使用要求的滿足上的,象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一些少數民族文化里面演化成了船、鳥、牛角等說法,但這些文化象征意義都是需要技術形態的支撐的。


圖1.屋頂“長脊短檐”形式演變過程[1]
2 “長脊短檐”是中國古代干欄式建筑的主要特點之一
具有長脊短檐特征的干欄建筑不僅在東南亞,在中國甚至日本都廣有分布,即使今天,我國云南盈江一帶的景頗族仍然在建造這種建筑。早在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家就有提出:“屋脊長于屋檐和兩端略向上翹起的正脊,為古代干欄建筑的主要特點之一”。在廣州出土的漢代陶屋中就發現長脊短檐的痕跡。貴州赫章可樂漢墓出土的干欄陶屋,屋脊也是微向上翹的,盡管沒有直接表現出長脊短檐,但也殘存著早期形式的一些痕跡。將已有研究綜合分析,發現“長脊短檐”這種形式至少在長江以南地區曾存在,而這一地區也正是中國古代干欄建筑分布密集地區,因而說“長脊短檐”是中國古代干欄建筑的特征之一,并且其傳播至東南亞的路徑與干欄式建筑傳入東南亞的路線大致相同,這也是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在建筑上的文化關聯之一。
3 結語
通過以屋頂為例的對東南亞傳統居住建筑主要特征的研究,發現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與東南亞地區在干欄建筑中均出現“長脊短檐”,并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保留著一些早期特征。由于這些地區“跨國境而居”,受到兩種或多種文化的夾擊,跨境民族有著不同于非跨境民族的特點,而民族遷徙可以促使民族學背景的總體特征發生較大的變化,在不同民族雜居地區,比較進步的民族建筑形式常常成為其他民族模仿的對象。在這種不斷地相互學習和模仿過程中,建筑才得以保持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進而演化為一種共同文化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