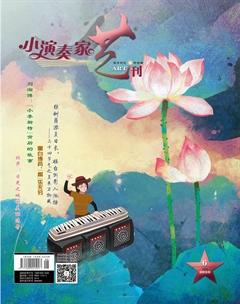黑白博弈,“棋”樂無窮
槑槑
琴、棋、書、畫是我國古代四大才藝,其中棋指圍棋,它伴隨著儒釋道思想和其他文化藝術(shù)融貫于綿綿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
在小小的一方棋盤上,帝王看到了山河疆土,軍事家看到了金戈鐵馬,詩人看到了錦詞麗句,樵夫看到了草木山石,農(nóng)婦看到了柴米油鹽……人間百相,紛繁世態(tài),人生玄機,皆暗藏于黑白棋子之中。
一盤棋,有妙手,有臭招,有“天外飛仙,一招制勝”,也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但更多的時候是黑可下,白亦不錯,貌似模棱兩可,而這正是圍棋的玄妙之處,也是人生的中庸之道——行棋有規(guī),落子有道,棋行天下,大道至簡。
圍棋作為博弈的一種,在中國歷史久遠,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揚雄的《方言》都把“弈”解釋為圍棋,孔子也在《論語》中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真正給圍棋崇高釋義的是班固,在傳世的《弈旨》中,班固首先把圍棋與靠擲骰子論輸贏的博戲區(qū)別開來,認為博戲的勝負多半出于偶然和僥幸,圍棋則不然,不僅體現(xiàn)智力,甚至體現(xiàn)道德,不僅是對自然的模仿,也是對人事的擬議,他說:“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quán),下有戰(zhàn)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關(guān)于圍棋的形制,他說:“局必方正,象則地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除此之外,班固還對下棋者的精神狀態(tài)給予了肯定性的描述,說當一個人沉酣于圍棋時,“至于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zhì)之《詩》《書》,《關(guān)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yǎng)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靜泊自守以道意。”意思是說人下棋時的沉迷狀態(tài)可以媲美孔子說的“好學自得”、“發(fā)憤忘憂”,下棋產(chǎn)生的情感體驗合乎儒家的詩教精神,而圍棋給人帶來的心智與身體合二為一的狀態(tài)可以修身養(yǎng)性,達到陰陽調(diào)和、剛?cè)岵o為默識、清靜自守。把圍棋與天地之象、神明之德、圣人之度聯(lián)系起來,班固稱得上始作俑者,后來者大體延續(xù)了他的思路。
到秦漢時期,圍棋也成為培養(yǎng)軍事人才的重要工具。東漢的馬融在《圍棋賦》中就將圍棋視為小戰(zhàn)場,把下圍棋當作用兵作戰(zhàn),說:“三尺之局兮,為戰(zhàn)斗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古代許多著名軍事家如三國時的曹操、孫策、陸遜等,都是疆場和棋盤這大小兩個戰(zhàn)場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除了以詩賦著稱于世外,也是一個圍棋專家,據(jù)說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對圍棋之盤式、著法等了然于胸,能將觀過的棋局重新擺出而不錯一子。
南北朝時期,由于玄學的興起,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為榮,因而弈風更盛,下圍棋也被稱為“手談”。上層統(tǒng)治者無不雅好弈棋,他們以棋設(shè)官,建立棋品制度,對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與棋藝相當?shù)牡燃墸敃r的棋藝分為九品,《南史·柳惲傳》載:“梁武帝好弈,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見當時棋類活動之普遍。此外,日本圍棋分為“九段”也源于此。
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新標志。所謂棋待詔,就是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yè)棋手。當時供奉內(nèi)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棋手中嚴格挑選出來的,他們都具有較高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唐德宗時的王叔文、唐宣宗時的顧師言等。棋待詔制度的實行不但擴大了圍棋的影響范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這種制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xù)了五百余年,對中國圍棋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明清兩代,圍棋流派紛起,棋藝水平迅速提高。清代的梁魏今、程蘭如、范西屏、施襄夏被稱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棋風奇巧多變,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為浙江海寧人,人稱“海昌二妙”,據(jù)說施襄夏和范西屏曾對弈于當湖,經(jīng)過10局交戰(zhàn),勝負相當,從此成為流傳千古的一段佳話。
圍棋不僅是一項體育運動,還是深受大眾喜愛的一種棋盤游戲,其中所蘊含的豐富文化是華夏文明的重要體現(xiàn)。如今,圍棋運動已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中國、韓國、日本最為興盛。
一首雋永含蓄的言志之詩
圍棋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態(tài)和高雅的娛樂形式,自古以來就與文學有著深厚的淵源。歷史上,圍棋興盛的時期也是詩人輩出的時期,有許多詩人都對圍棋情有獨鐘,如王勃、王維、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陸游、王安石、蘇東坡等。
“山僧對棋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白居易的這首《池上二絕》再現(xiàn)了兩位僧人對弈竹林的畫面,全詩淡化了棋盤上的爭斗,將殺氣化為了一種清幽之境:和煦的陽光映照著這片竹林,卻看不到人的影子,唯有對弈落子的聲音傳來,意境悠遠。
棋癡王安石寫了許多詠棋詩,其中一首寫道:“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zhàn)罷兩奩分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他將圍棋看作一種消遣工具,對弈時經(jīng)常隨手而下,因此勝局不多,但他不以為意。
詩人杜牧在《重送絕句》中寫道:“絕藝如君天下少,閑人似我世間無。別后竹窗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詩中的“吳圖”便指棋譜,這首詩生動地描繪了一名癡迷圍棋者在風雪之夜借著昏暗的燈光照譜擺棋的情景,可以說是別有一番情趣。
除此以外,自稱棋藝不佳的宋代詞人蘇東坡在觀看他人對弈時,由于被圍棋的意境所陶醉,曾寫下“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詩句,一直被世人所推崇。可見,蘇軾雖然棋藝不高,卻體會到了圍棋之外的樂趣,與其說他喜愛下棋,倒不如說他喜愛的是“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的意境,他還曾與黃庭堅合作過一副對聯(lián):“松下圍棋,松子忽隨棋子落;柳邊垂釣,柳絲常伴釣絲懸。”這也說明蘇軾把圍棋看成忘憂消慮、調(diào)節(jié)情緒、怡情養(yǎng)性的手段。
在眾多詠贊圍棋的詩句中,杜甫的“楚江巫峽半云雨,清簟疏簾看弈棋”、歐陽修的“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文天祥的“夜靜不收棋局,日高猶臥紗廚”等都是流傳至今的佳句,而在這些數(shù)不勝數(shù)的圍棋詩中,最長的一首當屬宋代邵雍所寫的《觀棋大吟》,這首詩竟然長達360句,共有1800字,這樣的長詩在詩歌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有人說圍棋是一首永遠也寫不完的詩。這些與圍棋相關(guān)的文學作品,不但從各種角度精心描繪和贊美了圍棋,還從不同側(cè)面解讀了圍棋與文化、圍棋與人生的關(guān)系,可謂是我國文學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一顆專注技藝的匠人之心
圍棋棋子分為黑、白兩色,黑子181個,白子180個,棋子呈圓形。相比日本常用兩面凸的棋子,我國一般使用一面平、一面凸的棋子,其中云南所產(chǎn)的云子歷來為弈者所青睞,迄今已有五百余年的歷史。
用圓頭鐵棒輕輕沾上經(jīng)高溫熔化的原料,向下翻轉(zhuǎn)滴棒,將熔料滴到細長的鐵板上,待熔料形成圓潤赤透、大小如一的棋子時,快速向上翻轉(zhuǎn)滴棒收料……云南圍棋廠的劉廷舉已將這套動作重復了25年。在云子的制作過程中,滴子是極為重要的一步,學會滴子不難,但想要滴出一顆好棋子則需要數(shù)年的磨煉。
云子,這一在元明清三代被皇家宮廷、高僧名士奉為珍品的棋子,歷經(jīng)數(shù)載,配方及工藝幾經(jīng)失傳,直至上世紀70年代,云南圍棋廠的匠人們通過對幾粒遺留民間的老云子不斷試驗分析,終于復原了傳統(tǒng)生產(chǎn)工藝,云子方才再現(xiàn)人間。
劉廷舉是云南圍棋廠里滴子的老師傅,從進入圍棋廠起,他便守著窯爐日復一日地修煉技藝,想通過自己的手藝讓這些棋子靈動起來。
在劉廷舉來到圍棋廠前的幾年間,老廠長何華封醞釀并發(fā)動了一場關(guān)于圍棋生產(chǎn)的變革,這位老人窮盡畢生,只希望云子能更加盡善盡美地呈現(xiàn)出來能將昔日的輝煌延續(xù)下去。
在一間簡陋的生產(chǎn)車間里,劉廷舉開始了一天的工作:調(diào)好控溫表,以適宜的火候保證熔煉原料的恒定,反復摩擦擺放棋子的鐵板,再把鐵板放在窯口加熱,這樣棋子的底部才能更加平滑。接下來便是長達8小時的滴子工作,劉廷舉如古人那樣靜坐爐前,“長鐵蘸其汗,滴以成棋”。窯爐里的溫度高達1200攝氏度,站在爐邊,熱浪撲面而來,即使是夏天,劉廷舉身邊的風扇也在呼呼吹著,身著短袖的他,臉上滿是涔涔細汗。
在劉廷舉看來,想要滴好一顆棋子,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隨著時間的累積熟能生巧。他說:“我每天最多能滴6000多顆棋子,廢品率不會超過5%,但有一點至關(guān)重要,滴子的時候要心無雜念,如果心里有包袱,做的棋子就不好,廢品率就高。”
據(jù)說滴棋人的性格能融入棋子當中,心情煩躁或生氣,做出的棋子便是一顆“不高興的棋”,不是有氣泡,就是不圓潤。這也是新學徒最難跨過的一道坎,很多來圍棋廠學習的年輕人第一個月做得還不錯,到第二個月往往因急于求成、沉不下心而生產(chǎn)出大量殘次品。因此,如果不能摒除內(nèi)心的雜念,就沒辦法勝任這份工作。
制作一顆至臻至美的云子,滴子只是開始。剛成型的云子在8小時自然降溫后,還要經(jīng)歷打磨、清洗、分揀等12道工序。在分揀車間,工人熟練地將不合格的廢品挑出來,再用卡尺測量每顆棋子,誤差不能超過0.5毫米。每個環(huán)節(jié)每名工人都得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因此純手工制作一顆棋子一般需要三四天。
“手工制作的棋子薄而光滑,手感很好,因為難度高也更珍貴。”劉廷舉拿起一顆黑子說道。陽光照射下,原本烏黑雅致的棋子變得晶瑩通透,泛出碧玉光澤,或許是因為融入了匠人的心性,云子透著一種沉靜儒雅之美。做了25年云子,劉廷舉身上早已沒有了初學者的浮躁,取而代之的是持久的耐心與深長的情意,一如他拿起云子時的沉默不語、眉眼彎彎。
一種懷素抱樸的人生之思
金庸先生是出了名的圍棋迷,他的小說中不乏圍棋的蹤影,比如《笑傲江湖》中梅莊四友的老二黑白子就是個棋癡;《碧血劍》中寫蘇東坡棋力不堪,引入“勝固欣然敗亦喜”的說法;《天龍八部》中有一場著名的珍瓏棋局,這盤棋決定了虛竹的命運,也左右了小說的走向。金庸先生曾寫過一篇《圍棋五得》,文中說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訓,得心悟,得天壽。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歡下圍棋的人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楸枰相對,幾個鐘頭一句話不說也能心意相通,友誼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金庸與沈君山、林海峰、陳祖德、郝克強都是通過下圍棋結(jié)交的,友誼甚篤。金庸還有幾位日本朋友,他們語言不通,只能用漢字筆談,卻也因下棋而成為朋友。日本棋界流傳著一句話:“下圍棋的沒有壞人。”這句話雖不免有自我標榜之嫌,但圍棋公平至極,沒有半點投機取巧的機會,只要有半分不誠實,立刻就會被發(fā)覺。可以說,每一局棋都在不知不覺地對人進行道德教化。
圍棋是嚴謹?shù)乃季S鍛煉和推理鍛煉,有人稱其為“頭腦體操”。現(xiàn)代醫(yī)學保健理論很注重心理衛(wèi)生,注重保持頭腦的功能,因為人體一切器官的運作都是靠頭腦指揮的。有些人年老后體力衰退,但頭腦仍然敏捷,往往得享高壽,這便是下圍棋可得天壽的理論根據(jù)。我國當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亞賢、過旭初、過惕生等都年壽甚高,足為明證。王子晏老先生年過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日本業(yè)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記不清自己的年齡,弈棋卻仍然鋒銳凌厲,因為頭腦清晰,演講起來既風趣又有條理。
得教訓與得心悟是最難了解的,尤其是得心悟,當是“五得”之精義。唐玄宗時期的圍棋國手王積薪傳下來的“圍棋十訣”,至今在日本仍被視為圍棋原則的典范。十訣的第一訣是“不得貪勝”。下棋是為了爭勝負,不求勝又下什么棋?但過分求勝而近于貪,往往會落敗。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既要求勝,又不貪勝,如果能把握此中關(guān)鍵,棋力便會大大提高。吳清源先生常說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氣和、不以為意,境界方高。然我輩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過有此了解,雖達不到這樣的境界,時刻在念,庶幾近焉。
確實,圍棋是極其簡單樸素的,卻又深邃復雜、充滿玄機;圍棋是黑白分明、精確嚴密的,卻又不可思議,可以無限引申;圍棋是最自由、最少規(guī)定性的,但系統(tǒng)聯(lián)動,每一步都關(guān)乎大體,關(guān)乎生死。它似乎有著傳統(tǒng)中國文化與思想所特有的審美氣質(zhì)與詩性品格:通靈圓融、無為有為、圣俗一體、道器合一,看似子虛烏有,又似乎囊括萬象,似乎只是一種單純的符號和結(jié)構(gòu),又似乎可以表現(xiàn)人世間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