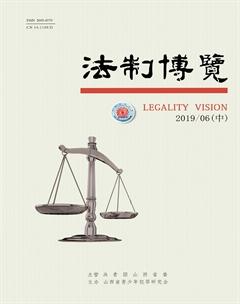協(xié)同創(chuàng)新方式下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及利益分配機制
摘 要:在當前這個科技興國,知識強國的時代,協(xié)同創(chuàng)新顯得尤為重要。自“2011計劃”以來,我國涌現(xiàn)出一批批產(chǎn)學研協(xié)同創(chuàng)新聯(lián)盟,由企業(yè)、高校、科研機構(gòu)及政府等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智力成果,卻也因此引發(fā)了各個創(chuàng)新主體因投入與利益分配不匹配而導致的問題,即知識產(chǎn)權(quán)如何共享,利益分配方式,等問題亟待解決。
關鍵詞:協(xié)同創(chuàng)新;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利益分配;權(quán)利保障
中圖分類號:F204;F27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17-0144-02
作者簡介:石浩鑫(1995-),男,甘肅慶陽人,西北師范大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協(xié)同創(chuàng)新基礎理論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一)協(xié)同創(chuàng)新理論現(xiàn)狀
創(chuàng)新,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靈魂。通過不斷的創(chuàng)新,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國家競爭力增強。美籍奧地利經(jīng)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在其著作《經(jīng)濟發(fā)展理論》中首次提出“創(chuàng)新”概念,認為創(chuàng)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即執(zhí)行新的組合。德國教授赫爾曼·哈肯認為協(xié)同是各元素間的相干能力,其性質(zhì)是在整體運行中各元素的合作、協(xié)調(diào)。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哈肯又提出了協(xié)同學理論:在整體系統(tǒng)內(nèi)部,各子系統(tǒng)相互配合、相互協(xié)調(diào),諸多相關力量聚集為一個核心性的總力量,達到超越原單個功能相加總和的強大的新功能,從而產(chǎn)生1+1>2的協(xié)同效應。[1]
到目前為止,國內(nèi)關于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幾個方向:①區(qū)域協(xié)同創(chuàng)新運行機制研究。為促進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提高創(chuàng)新競爭能力,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的轉(zhuǎn)化;[2]②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合作創(chuàng)新的意義、政府政策支持、資源配置、人才培養(yǎng)、問題破解。③多視角、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各個國家急需的戰(zhàn)略性問題、科學技術(shù)尖端領域的前瞻性問題和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公益性問題進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究。比如:鄒曉東、陳艾華的“面向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跨學科研究體系”張瑜的“基于產(chǎn)學研創(chuàng)新聯(lián)盟的網(wǎng)絡型協(xié)作機理研究”邵云飛、何偉及劉磊合著的“高校協(xié)同創(chuàng)新機制與人才培養(yǎng)培養(yǎng)模式研究”等一系列著作。
(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必然性
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科技人才的培養(yǎng)都離不開科技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戰(zhàn)略地位越來越重要,現(xiàn)實需求越來越迫切。隨著環(huán)境復雜性的增強,全球化的發(fā)展,當代創(chuàng)新模式已突破傳統(tǒng)的線性和鏈式模式,呈現(xiàn)出非線性、多角色、網(wǎng)絡化和開放性的特征,并逐步演變成以多元主體協(xié)同互動為基礎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chuàng)新能力特別是科技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日益成為當前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是評價一個區(qū)域乃至一個國家經(jīng)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世界經(jīng)濟論壇指出,競爭力是一個集合,決定著一個經(jīng)濟體生產(chǎn)力水平的各種制度、政策和因素,更富有競爭力的國家將有可能在中長期獲得更為迅速的發(fā)展。WEF將全球競爭力指數(shù)作為其主要的競爭力指標,認為世界各國處于不同的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即要素驅(qū)動、效率驅(qū)動和創(chuàng)新驅(qū)動。在發(fā)布的《2011—2012全球競爭力報告》中,WEF指出,中國仍處在效率驅(qū)動型發(fā)展階段,而美國等一些發(fā)達國家已處在創(chuàng)新驅(qū)動。所以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我國科技界目前新的重大任務。
二、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
知識經(jīng)濟時代,知識技能顯得尤為重要,經(jīng)濟時代的“大爆炸”可以稱之為“腦力風暴”。在Polanyni提出隱性知識之后,知識被分為顯性知識和隱形知識。通常人們對顯性知識有比較直觀的認識,如課堂傳授的知識、著作等。Polanyni認為隱形知識是個人技能的基礎,人們可以從教科書中學習各種知識卻無法講他們串聯(lián)起來形成隱形知識。而這里所說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中的“知識”指的就是“隱形知識”[3]。
知識產(chǎn)權(quán),源于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曾一度被中國大陸學者翻譯為“智力成果權(quán)”“智力財產(chǎn)權(quán)”,而在中國臺灣地區(qū),更被直接翻譯為“智慧財產(chǎn)權(quán)”。1986年《民法通則》首次使用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概念,從此以后,“知識產(chǎn)權(quán)”一詞就成為中國學術(shù)界規(guī)范術(shù)語。①“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法律解釋:由于我國沒有統(tǒng)一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所以對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概念缺乏嚴格意義的法律解釋,即便是在我國已經(jīng)加入的有關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即1967年在斯德哥爾摩簽訂的《成立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公約》簡稱WIPO公約和1964年烏拉回合談判達成的《與貿(mào)易有關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定》中,也只是以列舉的方式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范圍進行了界定。因而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概念的把握主要來自于學者們的學理解釋。②“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學理解釋:國內(nèi)學者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界定大多采用歸納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種是將“知識產(chǎn)權(quán)”定義為“人們就其智力創(chuàng)作的成果依法享有的專有權(quán)利”[4],另一種也是更通用的一種則認為除了“智力成果”以外,知識產(chǎn)權(quán)還包括“工商業(yè)標記”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5]由此可見,定義“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關鍵,在于確定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客體范圍。[6]
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從理論上來講,是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即高校、企業(yè)、科研機構(gòu)及政府等在合作共同開發(fā)的科研項目中,對于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而取得的所有權(quán)、使用權(quán)、薪資及獎金等各種利益的共同享有。但是在客觀操作中,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知識產(chǎn)權(quán)并不是被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主體完全共享,技術(shù)成果所產(chǎn)生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所有人應該是提供技術(shù)研發(fā)的一方主體所有,其他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只有使用權(quán)。所以在共享過程當中存在很多問題。知識產(chǎn)權(quán)大致分為三類:①在著作權(quán)當中,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第13條的規(guī)定:兩人以上合作創(chuàng)作的作品,著作權(quán)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沒有參加創(chuàng)作的人,不能成為合作作者。第11條:著作權(quán)屬于作者,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創(chuàng)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chuàng)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視為作者。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根據(jù)以上兩個法律條文,在著作權(quán)當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中的企業(yè)只有在其自己主持,自己承擔責任的時候才能視為著作權(quán)人。在這種情況下,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之間一定有一個雙方或多方合同,以便于成果的共享,至于如何約定成果分享,利益分配等具體性問題根據(jù)創(chuàng)新主體之間的約定。②在專利權(quán)當中,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八條的規(guī)定,合作完成的知識成果雙方都可以申請專利,申請專利的個人或者單位是專利權(quán)人,其他主體可以免費使用,這一情況是不同于著作權(quán)中的規(guī)定的。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對于其所享有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轉(zhuǎn)化率是比較低的,企業(yè)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獲取利益,而高校美名其曰擁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卻無法將其轉(zhuǎn)化成即得利益。
三、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中協(xié)同主體間利益分配問題及解決方式
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人、財、物的一種集合,集合各種優(yōu)勢攻堅同一科研難題,在整個過程中,前期的合作創(chuàng)新過程是比較明了的,到了后期的智力成果分配上存在著一些矛盾。
(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中利益分配的問題
1.創(chuàng)新主體之間簽訂合同約定不明確,在糾紛發(fā)生后無法依據(jù)其做出裁判。在當前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的背景下,各區(qū)域政府大力支持產(chǎn)學研協(xié)同創(chuàng)新科研項目,企業(yè)和科研機構(gòu)為了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積極形成協(xié)同創(chuàng)新聯(lián)盟,所以只是針對前期協(xié)同創(chuàng)新問題做出了具體的約定,但是問題的核心在于知識成果共享的利益分配,創(chuàng)新主體間本就依托利益建立起協(xié)同關系,所以最后的利益分配約定不明,無疑是導致創(chuàng)新進展緩慢、協(xié)同關系解除及引起糾紛的根本因素。
2.因創(chuàng)新成果而形成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所有者不明確。在我國協(xié)同創(chuàng)新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的普遍做法中,所有者是進行投資以期獲得利益的企業(yè),簡單來說就是投資者。其實對于這種合作知識成果的所有者,法律有規(guī)定。著作權(quán)中,一般作者是權(quán)利人,未參與創(chuàng)新過程的人不是權(quán)利人,除非法人或者企業(yè)主持或者受其意志支配的,企業(yè)或者其他組織才能成為著作權(quán)人。在專利權(quán)和商標權(quán)當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共同擁有所有權(quán),具體就是有關專利法和商標法當中所規(guī)定的合作完成知識成果的權(quán)利享有,法律所規(guī)定的獨占使用、排他使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讓等的具體規(guī)定。也就是說,法律所規(guī)定的權(quán)利所有與實際應用中是有出入的。
3.創(chuàng)新主體參與度相差大,不能確定后期利益分配占比。知識產(chǎn)權(quán)創(chuàng)新過程中,企業(yè)與擁有人才資源的科研機構(gòu)、高校簽訂合作創(chuàng)新合同,約定企業(yè)給予創(chuàng)新過程中資金等的支持,或者約定知識成果產(chǎn)出后,企業(yè)將知識成果商業(yè)化、產(chǎn)業(yè)化,前提是享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所以并不是所有創(chuàng)新主體都對知識成果產(chǎn)出有重要貢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所作的貢獻并不同,有些甚至并沒有參與,那么究竟如何進行利益分配?
(二)如何解決知識產(chǎn)權(quán)共享中的利益分配問題
1.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為了聚集不同方向的人、財、物,凝聚力量,提高效率,以達到1+1>2的效果,所以不同的創(chuàng)新主體要提供自己的優(yōu)勢,匯集人、財、物。另外,知識成果產(chǎn)生之后,面臨的是權(quán)益的分配,如何分配,分配標準,分配多少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在達成協(xié)同創(chuàng)新協(xié)議時寫入合同,達到合同權(quán)利義務明了,矛盾糾紛解決方式清晰,促進各方協(xié)同創(chuàng)新效率提高,協(xié)作創(chuàng)新聯(lián)盟的穩(wěn)定。
2.明確創(chuàng)新成果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所有者,依據(jù)意思自治原則,合同有約定按照合同約定,合同沒有約定,依照前文提到的法律規(guī)定確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所有者。一般情況下,知識成果主要是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發(fā)揮主要作用而產(chǎn)出的,則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所有人就應該是高校或科研機構(gòu),企業(yè)僅擁有使用權(quán)。高校或科研機構(gòu)作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所有人去管理和應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但不能對企業(yè)的權(quán)益造成影響。當高校與科研機構(gòu)作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所有者時,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應當恰當管理知識產(chǎn)權(quán),避免其因管理而發(fā)生問題;在研發(fā)過程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的商業(yè)秘密也應當由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管理保護。當企業(yè)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所有者時,企業(yè)也應當嚴格管控知識產(chǎn)權(quán),并給其他創(chuàng)新主體經(jīng)濟補償。對于其他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主體,可享有一定的權(quán)利。
[ 參 考 文 獻 ]
[1]鄒曉東,陳艾華.面向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跨學科研究體系[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2]杜玉霞.區(qū)域科技協(xié)同創(chuàng)新信息服務平臺的理論界定——以鹽城市區(qū)為例[J].農(nóng)業(yè)圖書情報學刊,2018(03).
[3]韓經(jīng)綸.知識共享于風險防范[M].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4]鄭成思.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5.
[5]劉春田.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6.
[6]劉國濤,馬鳳玲.知識產(chǎn)權(quán)戰(zhàn)略學[M].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