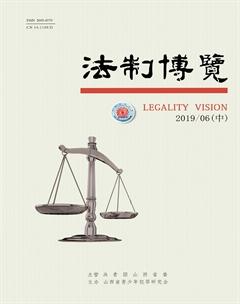論違約金的功能定位與協調
摘 要:我國理論界對違約金制度的功能定位尚有爭議。應將賠償功能作為違約金制度的核心,以體現我國違約金制度對于立法目的和司法觀點的合理承繼;而對于違約金所具有的懲罰與擔保功能,則可以通過違約定金制度的優勢得以發揮,從而更好地協調違約金與違約定金制度之間的關系,形成更為清晰的法律適用體系。
關鍵詞:違約金;違約定金;功能定位;賠償功能;懲罰與擔保功能
中圖分類號:D92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17-0081-03
作者簡介:閆可為(1995-),吉林四平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民商法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對于違約金制度的功能,學界存在多種不同的觀點。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違約金二分法學說認為,違約金分為賠償性與懲罰性兩種,且兼具兩種功能。賠償性違約金是法定的,而懲罰性違約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①第114條中沒有體現,需要依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才能得以適用;②而擔保功能單一學說認為,擔保功能應為違約金的單一屬性,因為“懲罰性違約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違約金,而“賠償性違約金”不屬于違約金的范疇。③
上述兩種觀點的差異巨大且各具代表性,其根本差別源于對“違約金”意思自治范圍的理解不同:在二分法學說之下,一般認為違約金是對損害賠償額的預定,只有在當事人的特別約定之下才可成為對違約行為的額外懲罰;而在擔保單一屬性學說之下,違約金則是對違約行為的意定額外給付。在不同的理解之下,違約金制度的定位得不到明晰,這對制度的適用產生一定的阻礙。因此,要解決違約金制度的法律適用問題,首先得明確制度的核心功能所在。
一、賠償功能:違約金的核心功能
從法律解釋的角度,《合同法》第114條所規定的違約金應當是指以賠償功能為主的違約金。④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內容往往不夠明確,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對違約金條款的性質沒有作出明確約定,裁判者則將其推定為賠償性違約金,這完全符合“以賠償性違約金為原則,以懲罰性違約金為例外”的精神。⑤例如在翟某某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拆遷安置補償糾紛案⑥中,當事人在拆遷協議中約定了這樣的違約金條款:“若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違約,除將44.4平方米的門市無償地給付乙方外,另賠償翟某某違約金50萬元”,此案當事人對違約金條款的性質沒有作出明確約定,故裁判將其推定為賠償性違約金,并以違約金酌減規則為依據,對過分高于損失的數額不予支持。現今,違約金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被默認為以賠償性功能為主的制度,學理上這種觀點也明顯居多。
但是,即使如此,學界還是在不斷地探討違約金制度的主要功能所在,并提出了眾多不同角度的新觀點,這不禁讓我們反思,探尋違約金之核心功能的實際意義是什么?諸多學者致力于考察比較法上的違約金制度,由此探求違約金制度的功能與含義,但是,比較法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應是服務于淺層的認知和盲目的比較,應當認識到的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度背后,更為復雜的是其制度沿革的歷史和社會生態的特定狀況,這是由不同民族和地區的文化、社會生態、法律體系構建而成的,在此之上形成了一套自成一體的法律制度。反觀我國的違約金歷史,從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開始,違約金制度的構建就朝著賠償性功能傾斜,隨之,在合同法的制定過程中,賠償性功能也成為了違約金制度構建的主要方向:“不論早先的試擬稿還是后來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草案都曾明確規定,約定的違約金視為違約的損失賠償。正式通過和頒布的合同法雖然刪去了這一句,但貫徹了損害賠償的功能”。⑦經過立法后幾十年來的司法實踐,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違約金制度。現今,在以解釋和優化本土制度為目的而進行制度優化時,必須關注和尊重我國違約金制度的歷史和發展脈絡。
二、懲罰和擔保功能:違約金的輔功能
以擔保功能作為違約金制度核心的觀點認為,所謂“懲罰性違約金”,就是以擔保功能為主的違約金制度,而損害賠償功能只能作為其輔助功能。⑧由此應當建構具有選擇性競合關系的違約金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若二者針對的利益并非同一,則當事人可累加主張;反之,則不可累加主張,債權人得擇一行使。當違約金約定的數額高于損害賠償額時,應將違約金限于實際損失數額內,與此同時,損害賠償請求權并不因債權人選擇違約金請求權而喪失,債權人仍可主張超出違約金的損害賠償,只是需要依據法定程序證明其損害;當違約金約定數額低于實際損失數額時,當事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⑨
我們知道,當兩種請求權出現競合時,當事人可擇一行使。從請求權行使的角度來看,主張擔保性為違約金核心功能的觀點與主張為懲罰性的觀點基本無異。筆者對其觀點提出一些思考:當違約金請求權的數額高于其實際損失時,當事人可以擇一行使請求權,其既可以選擇違約金請求權,也可以選擇損害賠償請求權;但若將違約金請求權的范圍限于實際損失的范圍,這不但限制了當事人的意思自由,還會使兩種不同的請求權相互混淆,實為不妥。此外,現有司法實踐中很少出現請求違約金酌增的案例,因而,這一設想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是缺乏堅實的司法實踐基礎。
上述觀點還認為,若將違約金的核心功能定位于賠償性,其將不再具有實質意義上的限制違約金數額的功能,這種做法也將過分地限制當事人的意思自由。筆者認為,雖然《合同法》已經較為全面地貫徹了意思自治原則,但意思自治總是有限度的,絕對的意思自治是不存在的。在違約金的意思自治問題上,無論是以賠償功能為主還是以懲罰、擔保功能為核心的違約金條款,都將受到民法中公平原則的裁量和限制,實際損失也終將成為案件裁量的參照標準。因此,不應僅以限制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由,從而否定以賠償功能為核心的違約金制度的合理性。
無論是以學理的角度,還是以司法實踐作為參照,違約金應當明確堅持以賠償功能為核心,而懲罰和擔保功能只應當成為其輔助功能。
三、違約定金的功能:與違約金的關系
違約定金是指在交付或接受定金以后,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履行主合同,都應按照定金罰則予以制裁的制度。違約定金與違約金相似,其皆具有擔保功能和懲罰性功能。
定金制度作為債的擔保方式,其具有擔保功能。我國《擔保法》第89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向對方給付定金作為債權的擔保”,在學理上,定金也被列舉為債權的擔保方式之一。
定金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懲罰功能。許多學者提出,定金與違約金的關系十分密切,并認為兩者的性質是基本相同的:胡長清曾指出,“違約定金者,即于付定金人履行其債務時,受定金人得沒收其定金之定金也。此種定金有強制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效力,與違約金同。”⑩史尚寬也認為,“此種定金,與違約金同,同樣有間接的強制契約履行之效力。”○11上述學者之所以將違約金與定金制度論作相仿,是由于將“懲罰性違約金”默認為與之比較的對象。可以看出,違約定金具有強制債務履行的效力,也具有與違約金相似的懲罰功能,其相當于預付形式的違約金,與違約金的懲罰性和擔保性功能大體一致。
但是,在我國當前的法律框架中,違約定金的功能卻被限定為賠償屬性。其一,違約定金與違約金請求權屬于選擇性競合的關系,這體現在《合同法》第116條:“當事人既約定違約金,又約定定金的,一方違約時,對方可以選擇適用違約金或者定金條款”;其二,違約金與違約定金在司法實踐中皆被認為是對損害賠償額的預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12第91條也明確指出,定金的數額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之20%。也就是說,在司法實踐當中,違約定金制度始終發揮著損害賠償額之預定的功能,其填補損害之價值與賠償性違約金幾乎無異。
由此可見,在上述法律框架下,違約定金受到損害賠償數額的限制,其自身本應具有的擔保和懲罰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
四、與違約定金制度的功能協調
《合同法》第116條確立了違約金與定金的擇一適用規則,并為司法實踐所廣泛遵循。其之所以將違約金與定金請求權劃為競合之等別,一方面是出于避免雙重獲利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兩項請求權皆具有填補損失的功能。
但應當認識到的是,在實踐中,從當事人對制度的選擇角度來看,違約定金與違約金制度分屬不同的功能,且各具不同的責任承擔機制:違約定金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屬于實踐性合同,且具有更強的擔保屬性,僅有書面約定卻并未實際交付定金的,定金合同不成立,而一旦合同得以成立,則產生雙方合意之履約擔保;與此相對的是,懲罰性違約金并不具有如此嚴苛的合同成立條件,也沒有提前交付一定金額作為雙向擔保的機制。因此,作為一種單向的違約規制,其雖也具有一定的擔保效果,但尚不能與違約定金所呈現出的擔保功能相提并論。
除此之外,在實際交易中,當事人在進行制度選擇之時,亦會考慮到定金制度自身存在的“懲罰”特性:其一,違約定金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前提;其二,違約定金以“罰則”冠名,明顯帶有懲罰色彩;其三,定金合同的實踐性能夠充分體現意思自治原則,且定金所具有的雙向擔保屬性也始終有利于公平原則在民事活動中的貫徹。因而,在以賠償功能為核心的違約金制度下,違約定金所具有的懲罰性功能和機制是得天獨厚的。對于當事人來說,定金的賠償功能只是其輔助功能,而擔保和懲罰的意味則更為突出和明顯。
對此,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違約定金與違約金制度的功能不同,二者不應互為損失填補的替代;從體系的角度來講,若將兩種制度皆定位于損害賠償額的預定,則會使二者產生趨同性和可替代性,從而造成混淆。因此,應當關注到違約定金的制度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并發揮其懲罰和擔保功能。于此,筆者不妨提出一種新的進路:
第一,堅持以賠償功能為核心的違約金制度。應當將《合同法》第114條所規定的違約金解釋為賠償性違約金,明確違約金制度的賠償性功能定位,這不僅體現了對立法文義的遵從,也符合當前司法實踐的規律和現狀。
第二,將違約金的懲罰和擔保功能賦予至違約定金制度之上。目前,違約金制度以賠償功能為主,并扮演著損害賠償額之預定的角色,但對于其懲罰和擔保功能,在實踐中則很難得以充分發揮。反映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當中,一般來說,認定“懲罰性違約金”的情形往往較少,而大部分的違約金條款都會被認定為“賠償性違約金”,究其原因,則是由違約金自身的適用特點決定的:違約金是一種單向的責任機制,合同雙方對于懲罰數額往往持有差別化的考量,因而最終呈現出的責任約定必然具有妥協的意味。在公平原則的規制下,若以懲罰為目的的意思自治內容不夠明確,平等民事主體間的責任還應當以損失填補為主。
既然如此,能否適當借助違約定金制度的優勢以彌補現有違約金制度的不足?與違約金相比,違約定金既能夠體現對自由合意的尊重,也可以保證約定的公平性:通常來說,在訂立違約定金合同之時,考慮到定金罰則的適用,雙方一般不會夸大損失的預期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來講,雙向擔保機制能夠讓違約定金的約定保持公平和理智,違約責任的懲罰性也能夠在合理的幅度內得以體現。筆者認為,可以將違約金的懲罰和擔保功能賦予違約定金制度,允許當事人以約定懲罰性違約定金的形式督促合同的履行,以擔保合同目的的實現。
第三,適當放寬違約定金的約定限額。當事人在約定違約定金時,往往無法準確預估主合同違約所造成的實際損失,故違約定金的約定數額常以主合同標的為參照。依照現行法律規定,主合同標的之20%是違約定金的約定上限。不可否認的是,法律應當對意思自治下的違約責任予以一定程度的規制,這不僅是民法中公平原則的要求,也是禁止不當獲利精神的體現;但事實上,合同違約后的損失填補作用是有限的,應當允許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當高于預期損失的賠償數額,以保證被違約方的利益有回復到原始狀態的可能,對此,筆者建議將違約定金的約定限額適當放寬,使違約定金制度的懲罰性質和擔保價值予以充分體現。
在此基礎上,當事人仍可依據《合同法》第116條,選擇行使違約金請求權或違約定金請求權。當違約定金或違約金約定數額可覆蓋實際損失時,當事人可擇一行使;若二者約定數額皆低于實際損失時,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對違約金數額予以增加。但是,對于同時請求適用違約金和違約定金的,出于公平原則和避免雙重獲利的考量,不應予以支持。
五、結論
應當堅持以賠償功能為核心的違約金制度,將違約金的懲罰和擔保功能賦予至違約定金制度之上,與此同時,適當放寬違約定金的約定限額,以充分發揮違約定金所具有的制度優勢,這不失為一種可供參考的進路。
[ 注 釋 ]
①以下簡稱為《合同法》.
②韓世遠.違約金的理論爭議與實踐問題[J].仲裁講壇,2009(1).
③王洪亮.違約金功能定位的反思[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2).
④曾有觀點認為《合同法》第114條第3款規定的是懲罰性違約金,但新進觀點則認為其仍為對遲延履行損害賠償的預定,并非為懲罰性違約金,持有新進觀點的學者為韓世遠.
⑤韓世遠.違約金的理論爭議與實踐問題[J].仲裁講壇,2009年第68輯.
⑥(2014)邯市民二終字第253號.
⑦韓強.違約金擔保功能的異化與回歸——以對違約金類型的考察為中心[J].法學研究,2015(3).
⑧王洪亮.違約金功能定位的反思[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2).
⑨王洪亮.違約金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關系[J].法學,2013(5).
⑩胡長清.中國民法債編總論[M].商務印書館,1994:359.
○11史尚寬.債法總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493.
○12以下簡稱《擔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