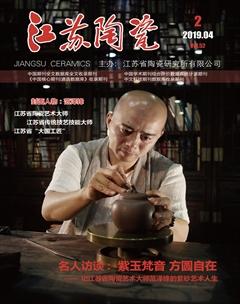踏莎行難天趣橫生
吳偉華
2005年,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聯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共同舉辦了“書·畫·印·壺:陳曼生的藝術”展覽研討會。這次展欄公開了陳曼生關于書·畫·印·壺4項近百件藏品,對研究陳曼生以及了解當時的社會風尚文化藝術產生了相當積極的作用。與會者不禁都會產生思考,為什么陳曼生能夠在紫砂的歷史上產生這么大的吸引力,他遺留下來的東西,百年以后來看依然很有味道。
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陳曼生所代表的是當時文人的一種生活狀態,金石書畫的藝術觀是從外界接受訊息以后的一種折射,這種折射在通過造型、顏色、工藝、銘文、陶刻等等種種痕跡表現出來,形成一種“天趣”,這種趣味性以當時人的視角來看是無法取代的,因為這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結合日常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生活中的趣味,沒有這種生活方式就沒有這種趣味,這是現代人如何摹古也無法企及的,所以當下復古、摹古的作品永遠只能接近而無法超越,因為這就是“陳曼生”等等古人的生活,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的現代人,不可能存在比他們更多的生活感受,自然也就無法在自己的作品上創造出超越這種感受的情感。
所謂“天趣”就是天然的趣味,而“天然”二字是我們意識中誕生的,本不存在的一種基于我們人的評價,生活中的天趣即是生活中的感觸,以此為主題創作的作品就必然要有自身基于生活的理解,基于生活的情感,作品“天趣壺”(見圖1)便是以生活為題所進行的一次嘗試。
1 ?作品“天趣壺”的造型
說起紫砂作品的造型首先就要談它的工藝,造型是基于工藝才能夠誕生的,在作品“天趣壺”上,壺面的線條與傳統紫砂壺一直強調的飽滿圓潤似乎完全相反,其壺身的曲線向內凹曲,四條棱線筋骨顯露,唯有壺底的轉折看起來圓潤飽滿,壺面與壺底結合到一起,形成了一個長S型,但在視覺上卻顯得較為平和舒緩,大片開闊的壺面給人一種“滑”的感受,間接地體現出紫砂的“光”、“素”、“潤”,這樣的壺身對于展現紫砂本身的材質美無疑是有利的。在具體拍打泥片成型的時候,要采用與傳統塑造“腹鼓”壺身相反的手法,讓力道內斂收縮,而不是向外擴張,最終將壺面上的“力”凝聚于壺身下部,仿佛緊扣的彈簧,厚積薄發。
壺面之上采用了無肩的設計,壺口內藏,方蓋整個壓于口面,蓋面平整,以方邊隆起形成階梯狀,具有較強的層次感,在此之上塑鏤空壺鈕,鈕中空如水滴,鈕似指圈又似壽桃,抽象的形態給人多種不同的聯想,但結合壺蓋、壺口以及紫砂壺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特性,很容易便能想到這是在描述一粒即將落入水面的水滴,漣漪以及反光正折射出好看的光圈,這一切自然生趣猶如在電影中截取的某一幀畫面,雖是定格但卻充滿了后續的動感。
2 ?作品“天趣壺”的意蘊內涵
紫砂壺上所寄托的情感首先是創作者的情感,而創作者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這也正是紫砂壺本身時代感的由來,但藝術創作者并不是單純的情感宣泄,而是有所選擇的精煉,要在一把壺上表現出想要呈現的一面,作品“天趣壺”的主題是自然的趣味,但形體卻并非是自然誕生,也不是模仿的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事物,而是創作者的憑空捏造,這一點與創作的主題無疑是有所沖突的,所以在形體與內涵的表現上,就需要一定的抽象化,盡量地少表述一些內容,虛化形體與輪廓本身的存在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一種思維的引導,通過較為現代感的形體節奏從視覺上引導思想情感,往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種種事物進行聯想,從而造成時空變幻的錯覺,引發情感上的共鳴。
3 ?結 ?語
紫砂壺新的形態的創作既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又是一件復雜的事情,重要的并非是根據茶壺的結構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形體輪廓,而是要將創作者的情感、意蘊、文化素質等元素,合理地賦予這一形態,如何更好地讓人能夠理解、讓人想象,這才是真正屬于藝術創作的領域,同時也是紫砂壺藝創作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