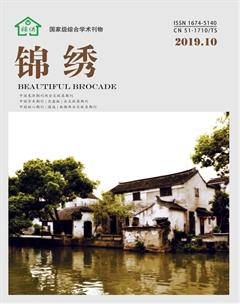關于新型電信詐騙未遂的次數認定的研究
王夢宇
摘 要:使用網絡群呼系統實施電信詐騙作為新型犯罪手段,在數字化進程發展迅猛的當今社會愈演愈烈。與傳統電信詐騙手段相比,其犯罪行為的實施更為復雜,危害的波及范圍更為廣泛。在犯罪行為的實施,主觀犯意的表達等方面,與傳統詐騙有較大差別。本文以趙某等人特大電信詐騙案為例,主要討論關于新型電信詐騙未遂的定罪問題。
關鍵詞:新型電信詐騙;犯罪未遂;定罪
一.案情概述
2018年12月27日開始,根據公安機關長時間的偵查結果鎖定的特大電信詐騙案的犯罪窩點被逐一攻破,各犯罪嫌疑人紛紛落網,使之長達半年以上的電信詐騙犯罪告一段落。
該犯罪集團以犯罪嫌疑人趙某為領導者和組織者,組織、構建、發展下線人員利用網絡群呼系統共同實施電信詐騙行為,構建起分工明確,層級分明的一線、二線、三線犯罪窩點。該組織使用群呼系統將通過軟件設置的詐騙語音包發送給臺灣各地區的居民。若被害人接通,則會接入該組織的一線話務員窩點,一線人員謊稱其醫保卡等遭盜用,可以幫被害人轉接報警,被害人若信以為真并按照語音指示操作,則會被轉接至該組織二線人員,即冒充警察的人員。在冒充警察的人員謊稱有人利用被害人身份參與犯罪活動后,以調查為名收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并以送達傳票被害人未到庭為由,對被害人實施羈押,被害人會聲稱未收到傳票并否認參與犯罪活動,此時,二線冒充警察的人員便與被害人交涉,告知被害人其可以幫助接通檢察官,以此移交至三線冒充檢察官的人員。三線冒充檢察官的人員會提出可以不對被害人實施羈押,但是需要扣押其財產,直至犯罪調查結束,以此來騙取被害人轉賬或者現金交付。如此這般,組織多達40人以上,并在犯罪團伙內部形成各個窩點,窩點之間各自分工,窩點內部各自分工,環環緊扣的實施整個詐騙流程,詐騙金額據不完全統計已達2300多萬新臺幣,約500多萬人民幣。
公訴機關在指控中,對于能夠查清的詐騙金額,根據每個窩點對應的犯罪金額對其進行指控。對于一些窩點,由于未能查清其實際詐騙金額,而以窩點在網絡群呼系統所統計的撥打次數為定罪依據,認定為詐騙罪未遂。對于各個被告人,根據規定,多人共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被告人應對其參與期間詐騙團伙實施的全部詐騙行為承擔責任。
在網絡群呼系統調出的數據中,每一窩點的撥打次數均達5000次以上。根據《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電信詐騙撥打次數達500次,已構成詐騙罪中“其他嚴重情節”的未遂;若撥打次數達規定次數的10倍,則以“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未遂判處。即符合詐騙罪的第三檔量刑,判處10年以上刑罰,再按照未遂從輕或減輕處罰。
而在本案中一些一線負責接聽電話的話務員,群呼系統甚至非其本人操作,僅僅是負責在群呼系統發出語音包后,若對方有接通,則系統會撥回給一線話務員。其主觀犯意、輸出性質區別于傳統的電信詐騙中,行為人直接手動撥打或者網絡撥打有限電話實施詐騙的主觀犯意。
因此,傳統電信詐騙是否應該與新型電信詐騙的未遂認定相區別?即是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
二.傳統電信詐騙中的犯罪未遂
根據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利用發送短信、撥打電話、互聯網等電信技術手段對不特定人實施詐騙,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1、發送詐騙信息5000條以上的;2、撥打詐騙電話500人次以上的;3、詐騙手段惡劣、危害嚴重的。實施前款規定行為,數量達到前款第1、2項規定標準10倍以上的,或者詐騙手段特別惡劣、危害特別嚴重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即撥打詐騙電話次數達500次或5000次以上,就符合該法律規定情節,而不管其是否接通,均構成詐騙罪犯罪未遂。
三.新型電信詐騙犯罪未遂的分析
1.主觀犯意方面
相比傳統電信詐騙,新型電信詐騙所使用的網絡群呼系統其具有隨機撥號便捷操作的特性,即在群呼系統中設置區號后,只需點擊撥號,后面的電話號碼即可按照數字排列進行隨機撥打。其實施的便捷程度,與出臺該《解釋》時,行為人手動撥打電話、使用互聯網改號或者其他手段撥打電話,實施電信詐騙的便捷程度并非能用統一標準予以衡量。
該規定于2011年出臺,此時新型電信詐騙并非現在如此猖獗。而在當時撥打電話基本都是手動撥打,或者雖利用網絡,但撥打的次數相對有限,撥打電話達500人次,不論是否接通,該主觀惡性之大與群呼系統只需點擊一下即可撥出成千上萬次電話不可一日而語。
且根據該《解釋》規定的“發送詐騙信息5000條以上”與“撥打詐騙電話500人次以上”屬于同一檔量刑情節,不難發現訂立該解釋的目的,即對于操作簡單、便于實施的詐騙手段(發送詐騙短信),規定的犯罪次數遠大于實施較為有難度的詐騙手段(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而現在出現了一種雖以撥打電話為行為模式,但實施卻堪比發送詐騙短信的手段,那么應該如何認定其犯罪次數更為合理?
2.輸出性質方面
傳統電信詐騙的行為人所收集的詐騙對象的電話號碼,一般是從一些可以正規獲取公民電話號碼的平臺上,利用特殊手段非法獲得。而群呼系統的撥號方式是數字排列式隨機組成,其中的空號、已經不再使用的號碼,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號碼的比率明顯上升。因此,傳統電信詐騙所獲得的電話號碼能夠接通的概率往往遠高于使用網絡群呼系統設置區號后隨機撥打的電話號碼。而這種電話類型,占使用群呼系統實施詐騙的行為人撥打電話次數中的較大比重。
綜上,在傳統電信詐騙中以行為人的撥打人次作為犯罪未遂的認定較為合理,但將其運用于網絡群呼系統的新型電信詐騙中,便大幅度擴張了犯罪行為的認定。
3.罪責刑相適應方面
對于量刑方面,我國電信詐騙的未遂根據法律規定,分為“其他嚴重情節”的未遂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未遂。撥打電話達500人次即符合“其他嚴重情節”的未遂;5000次即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未遂。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量刑幅度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對于使用群呼網絡系統一次,即能達到幾千次呼叫的犯罪行為來說,該刑罰遠超于其實施犯罪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這不免使得新型電信詐騙的罪責刑無法相適應。
而從宏觀來看,我國臺灣地區對詐騙罪的法律規定,“第339條:意圖為自已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罰金。”日本刑法對于詐騙罪的法律規定,“第246條:欺騙他人而占有財物者,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德國刑法對于詐騙罪的法律規定“第263條規定:出于使自己或第三人獲取非法財產利益的目的,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通過歪曲、隱瞞真相引起或維持認識錯誤從而損害他人財產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本罪的未遂可罰。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六個月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不難看出,我國對于詐騙罪的量刑幅度遠超其他地區。既然已經對于詐騙罪有如此嚴格的量刑規范,更應當準確其未遂的標準,予以把握及控制該罪的量刑,使之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或許可以提高認定新型電信詐騙未遂的撥打次數,又或許可以對行為人實施新型電信詐騙時所撥打電話的性質予以區分,進而確定可以認定為犯罪未遂的撥打部分。
結語
關于我國的詐騙罪中,對于電信詐騙的規定,雖然有相關規定在不斷完善,但由于法律的滯后性,不能總是與當下社會中的新型問題完美接洽。但這并不影響法律公正的實行,對于出現的這些新問題,在實踐中,可以通過酌定量刑情節等其他方面予以平衡,最終達到罪責刑相適應。
參考文獻
[1]何帆,《刑法的注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2.1.
[2]張凌,于秀峰,《日本刑法及特別刑法總覽》,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4.
[3]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7.1.
[4]《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1.
[5]《臺灣地區新刑法》,200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