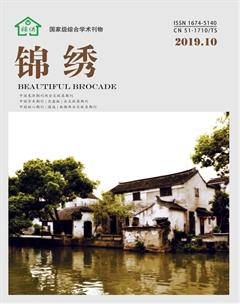淺析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組織的發展
林玉潤
摘 要:善會善堂始于明末,是一種濟貧的教化組織,其創建和管理也是地方公共事務之一。清中后期,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開始走向衰弱,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產生了慈善救濟思想,并付諸實踐。本文結合清中后期的背景,探索古徽州慈善組織的發展,并對他們的慈善救濟思想和活動進行閘述,使人們了解他們的慈善救濟思想在整個慈善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為當今社會慈善組織建設提供借鑒。
關鍵詞:徽州;慈善組織;慈善救濟思想;小社區
徽商賈而好儒。以儒家思想為人生哲學的徽州商人,大多數在經商致富之后,也富有利他精神:在別人處于困難時,慷慨地伸出仗義之手;在社會建設需要時,能慷慨解囊,支持社會事業。明清時代在地產成立的各類慈善組織約為3580個,安徽地區均在數量上占了重要的地方。乾隆以后,慈善組織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清嘉道年間國勢由盛轉衰,經濟發展無法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政府在思想控制上不同于康乾時期一樣苛刻,“新生后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撰述”。[1]面對著政治腐敗、社會問題叢生、糧食短缺、自然災害頻發等諸多問題,國力漸衰的清政府已然沒有十足的能力來應付和解決。這樣便使得善堂所面對的局勢不再如以前一般單純,由此,善堂逐漸發展出與前清不同的施濟模式,尤其是其組織形態體現了小社區的特色,為這一時期徽州的慈善救濟事業的研究提供了借鑒。善會善堂的慈善行為有多種,比如保嬰保育、停棺施棺、施藥養疴等,清中后期保嬰會以及以施棺為主的綜合性善堂其組織形式根據特色,故以下從這兩個方面研究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組織的發展。
一、保嬰保育
中國的育嬰組織,起始于宋代的慈幼局。《宋代·理宗本紀》記載“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2]。明清時代育嬰堂總計約973個,1850年以前約有579個,1850年后約有394個。
民國的《重修婺源縣志》曾有記載“婺貧俗,多溺女”,“族大人繁,貧戶甚多,溺女之風日熾”,由此可知徽州,尤其是婺源縣溺女之風盛行。婺源的百姓們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故以保嬰育嬰為目的慈善組織機構便應時而生。如“中云人癢生王燃承父志,昌集保嬰會,以拯溺女”,[3]“鄉有溺女俗,巽集鄉人立育嬰會,此后無淹斃者”。[4]
清初的育嬰組織拘于官僚形式,主要由政府控制,組織要稱為育嬰堂還需官方的首肯。
從嘉慶開始,育嬰堂的數量愈來愈多,組織形態也比前期更為靈活。19世紀初期,育嬰會的運作主要配合認同感較強的聚落,如安徽寧國的涇縣則在19世紀初期就有濟族中嬰的“好生堂”及“濟嬰堂”。[5]一般一個大族內的育嬰數目就有十余名。清嘉道二十一年(1816年),婺源縣韓家塢設有育嬰堂,在道光乙酉(1825年)至癸巳年(1833年)年間進行了重新修建。[6]當時有識的學子們也曾為保嬰育嬰的慈善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臧坑的太學生臧起震也曾為當地的保嬰育嬰的慈善組織出資辦理和資助其公共事業。由溪人附貢生程鴻緒,“嘗輸千余緡置休城玉堂巷屋卑為育嬰公所”。[7] 嘉道之際,經濟發展無法跟上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溺棄嬰問題又成為議論的焦點之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國傳教士Mline曾訪問過寧波的育嬰堂,據他記載,堂內的嬰兒:“是一群我所見過的最骯臟、最襤褸的小東西;乳母每人要負責兩三個棄嬰。”由此可見,當時能給予棄嬰的生活環境有多不堪。目前還沒有這個時期堂內嬰孩死亡率的資料,不過夫馬進的研究表明,同治時期松江地區育嬰堂的嬰孩死亡率高達48%~50%,[8]海寧育嬰堂在1890年代初期嬰孩死亡率是31%~39%。雖然這些數字是嘉道之后的統計,但在嘉道期間著名的育嬰堂都被譏諷為“殺嬰堂”。連最早建成的的揚州和蘇州育嬰堂在18世紀末已經臭名昭著。相繼而出的便是各種變革濟嬰制度的計劃方案。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商人王喜孫認為應當每月給予有幼嬰之窮困人家金錢上的補助,使其不致拋棄親生嬰兒。而道光末年,社會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央政府對善堂的監管日漸松懈,從而間接地使得育嬰堂里的嬰兒死亡率提高。
19世紀新的“保嬰會”之法是由紳士余治在道光年間設想出來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止親生父母溺嬰,據他所言,“四鄉窎遠,跋涉為艱,故貧乏之家生育稍多,迫于自謀生計,往往生既淹斃……。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貧者淹,甚至不貧者亦淹,輾轉效尤,日甚一日”。[9]新保嬰會的主要原則是收集善款,給予有新生嬰兒的窮苦人家每月600文的補助,相當于當時約3斗米的價錢,或一個二等工10天的工價,為期5個月。若5個月后,還是無能力撫養嬰兒,保嬰局會立即將嬰孩送往縣城內的育嬰堂。這樣既可以降低溺嬰的幾率也可以減少育嬰堂的負荷。另外保嬰會的救濟范圍:“以十里為限,十里外的家庭不受補助”。這便使得這個時期的善堂逐漸體現出較小社區的基本特點。隨著余治等人對保嬰會的奔波宣揚,到了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安徽省已經正式下文推動保嬰會局制度,這種保嬰會的方式正好符合各地所需,故而馬上得到了廣泛的響應。不到十年各州各縣的保嬰會比比皆是。嚴辰曰:“育嬰必須建堂,而保嬰會則無論寺院祠宇及人家間屋。皆可借以舉行;堂必建于城市,而鄉村之憚于遠送或不能周;會則一鄉一村,但得善士為之倡導,皆可舉辦;又其法能大能小,可行可止”。[10] 換言之,同治時期保嬰會在組織上更為靈活,具有較強的小社區、鄰里網絡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咸豐年間,徽州商人在其經營地也熱心于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如太學生胡大沺曾捐幾百金給蘇州建造育嬰堂;[11]棠樾人鮑志遠于揚州復興育嬰堂。[12]同治后期,運嬰網絡困難,嬰數逐漸飽和,育嬰會繼而產生嬰多的壓力。光緒初年(1880年)嬰堂的收嬰量逐漸減少,故使得仍有棄嬰的現象,進而新的保嬰會局才普遍成立。其服務于城外較小的社區,且就地取材以接濟貧苦人家的嬰孩。新的策略具有新的分散組織形式,同時小社區的特色愈發明顯。后期,社會對育嬰愈發重視,為了保證運作,大多育嬰堂都制定了相關的管理條約,例如,婺源育嬰堂董事制定了《婺源育嬰章程二十四條》和《婺邑源育嬰堂征信錄》等。
不經思考,這育嬰效果到底如何呢?
以婺源育嬰堂為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婺源育嬰堂一共收養118位嬰孩,且全為女嬰,有97位存活,其存活率高達82.2%。再后來,除了使溺嬰的數量大大降低,而且在一些撫教局中會為兒童提供基礎教育和相關技能的訓練,較前期更加注重兒童日后的發展出路。另外,晚期的保嬰機構更加接近現代的相關機構,提供較為完備的醫療保健服務,如為嬰孩接種,提供三黃湯、除胎毒等藥劑,強調洗熱水澡的必要,準備必用的火盆熏熨等設備。
二、施棺
施棺給予貧人是最基本的積德善舉之一,且歷史上施棺濟貧的善者很早就出現了。
徽州山多田少,耕獲三不贍一,民人不得不遠徙他鄉,求食四方。生老病死乃是自然法則,異地的游子葉落歸根,不愿客死他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意識。故漂泊在外的徽州人不幸在他鄉離世,也希望能回歸故里。
在外謀生的徽州商人數不勝數,尤其是新安商人,且集中于江浙地帶。于是整個清代的施棺善會約58%以上設在這兩省。新安之人為商,旅于吾浙之杭嘉湖諸郡邑及江南之蘇松常諸郡邑者甚眾。不幸因病,物故欲歸櫬于故里,途必經于杭州。[13]道光年間,司事胡駿譽、金高德等人除自己捐貲以外,還將募集所得的善款用于購買基地以建設善堂,名為“惟善堂”。堂內不僅有辦事的大廳還有二十多間房屋,周圍建有厚厚的墻和院壩。這使得善堂既牢固又可以安置較多的棺柩。而“惟善堂”與其旁邊的“六吉堂”被人合稱為“新安會館”。
創建于道光丙午年(1846年)的祁門同善局,組織勸捐物資,經常救濟當地的百姓。局內置有多口棺木,若是發現死在路上的暴斃者且無法查明其故里便讓局內的雇夫收埋。當時的知縣林用光和知府李興銳以及祁門縣教諭都曾有捐助,共捐銀七百二十兩給同善局,作為長遠之際。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時期,鄰村人逃到祁門縣的人數數以萬計,災病頻發,尸橫遍野。局內每日施棺數以百計,費用甚多。城內的鄉紳、士紳或以銀錢捐贈,或以物資救濟。甚而有些地方官員也為其解囊相助,如誥贈中憲大夫的鄭國恂曾向同善局提供一千余秤。光緒六年(1880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間,為了寄存更多的棺木,惟善堂也一直在置辦新的基地,除了內外堂,還有五十九處。由此可知晚清時期施棺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當然其所耗用的經費也相當多。從光緒七年(1881年)到光緒二十七年(1891年),惟善堂的收入已從當年的一千洋元漲至六千洋元。可見投入其中的經費之高。
明末清初時期,各地大多都是施棺助葬會,主要是一個自助式的組織,一會有40人。善會真正執行工作往往是在一個較小的社區里,且均設立在鎮中,只為當地社區服務。直到嘉道年間,各個鎮市各自均有“民捐民辦,官吏不經手”的善堂,而其中又以施棺助葬著居多。故這些鎮內施棺會的規模被限制于鄰里性較強的小社區內。同鎮內不同社區內的施棺善局也會相互照應著,以求得正常的運作。如休寧萬安鎮和黟縣漁亭鎮等,其鎮內的同仁堂與后來的怡善堂,兩個善堂僅“隔圖相距”,故堂內的經理董事們都相互地照料管理。后來,小社區的特色愈發明顯使得一些善會不如清前期那樣宣傳大同理想,而是純粹的以當地居民的利益為中心。且具有“內”和“外”以及“良”和“賤”之分,即屬于社區內的良民才能得到善會的救助接濟。此時善會的目的分兩大類,一是保障當地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二是救濟社區內部的貧困良民。內外、良賤之分使得社區的自我界定更加地明顯,加深了善會對社區的認同感。換言之,善會是另一種可以界定社會身份的新策略。施棺助葬善會如保嬰會一樣,善會在一個較小的社區內運作,才能發揮它的真正作用,也可能因為小規模的經營使得行政管理更加便捷,主辦人對社區內的人際關系也比較熟悉,使得善會發揮較大的功效。
三、余論
清中后期時期,善會善堂主要分散在各個鄉鎮中發展,且愈發具有小社區的特色。其一可能是中央權力的松懈。嘉道時期政府面臨諸多問題,進而只好鼓勵地方開設善堂,而鄉鎮的善堂善會主要是由地方人自動組織起來的。之后代表中央的縣政權威不如從前,使得鄉鎮對設立小社區的善會不再有所顧忌。換言之,鄉鎮以下的小社區內的善堂善會到清后期才普遍發展起來,且地方的社區按照已有的善會模式發展小善堂以照顧當地的百姓。其二可能是價值取向。賈而好儒,小社區內的慈善組織離不開“儒生化”的思想。受惠人要受社會共同監視,是否違反相關規定,同時善會對受濟者的身份也有較為嚴格的要求。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不斷增強,社會的凝聚力不斷增加,更有利于對“儒生化”價值的宣揚。以道德劃分貴賤,重新界定社會身份。慈善組織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會,而不是分化社會階級。清中后期以來的慈善組織已經逐漸達到這樣的目標,正如梁其自先生曾指出:“此時善會相當有效地凝結著一個日益龐大的中下階層。”
慈善濟貧組織的發展,從明末到清末,其數量上有大幅度的增加,且組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嘉道之后的善會組織更加規模化,規范化,靈活化,但卻一直沒有將救濟問題轉化為“經濟問題”。其重點仍是“行善”,其目標一直停留在教化社會或意識形態的灌輸之上,以施惠人的主觀意愿為主,強調道德,而沒有轉化為經濟層面。而善堂不過是一直扮演者保守性的角色,即維護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秩序和價值。因此,慈善組織也沒有真正解決救濟貧人的真正問題——“脫貧”。這對當今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要打贏脫貧攻堅戰: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林則徐全集》第七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版,第78頁
[2](元)脫脫,阿魯圖,歐陽玄,等.宋史·卷四十三本紀第四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7:840
[3]道光《續修婺源縣志》卷二十六,《人物·質行》,黃應均、朱元理等纂修,清道光五年刊本
[4]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四十五《人物·質行》,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國十四年刻本
[5]《涇縣續志》1825,5:10上
[6]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五《建置二·公署》,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國十四年刻本
[7]道光《休寧縣志》卷十五《人物·鄉善,何應松等修,方崇鼎等纂,清道光三年刻本》
[8]夫馬進1986B,74-75;1990,171-172
[9]余治《得一錄》1969[1869],2/1:上一下《保嬰會規條》
[10]余治《得一錄》1969[1869],2/1:37上-38下嚴辰《桐鄉嚴比部善后局舉行保嬰會序》
[11]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三十八《人物十一·義行三》,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國十四年刻本
[12]民國《歙縣志》卷九《人物志·義行》,石國柱、樓文釗等修,許志堯等纂,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13]胡敏 《新安惟善堂前刊征信錄序》《新安惟善堂征信錄》,光緒二十九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