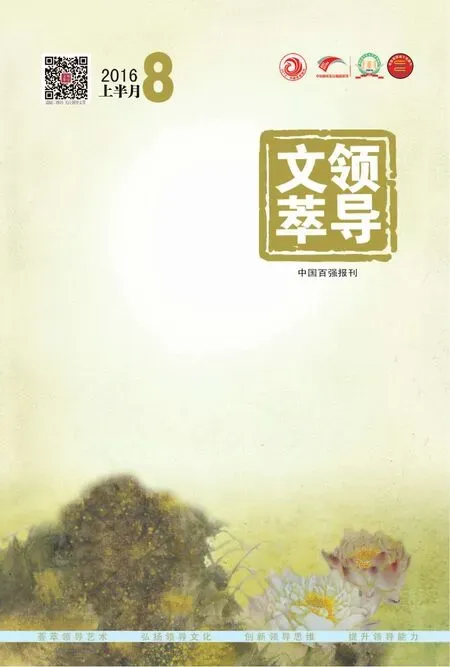在那個平民可以當皇帝的時代
孟憲實
出身豪門,父祖皆是達官貴人,這樣背景的人在官場春風得意、平步青云,實在是太容易理解了。無論怎樣強調自己的努力與才干,觀眾內心的評價依然是:媽的,論才干論努力,老子可比你強,現在之所以甘居下游,就是因為沒有你那樣的老爹。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心理,是中國的老情調。但是,偏偏就有沒有任何門第可炫耀,父祖都是無名百姓的人,忽然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崛起,給你講起另外一種風格的中國故事。
今天要說的是公孫弘,漢武帝時代,差不多屬于第一名的平民宰相。
公孫弘年輕的時候,也在政府干過的,雖然只是跑跑腿、當當差,可出了衙門大院,也算是個人物。咱們漢朝的高祖,當初不是也一樣。可是,公孫弘在官衙沒混多久,就被派遣回家了,是什么錯誤,是誰的錯誤,《漢書》一筆帶過,肯定是弄不清楚了。那以后,公孫弘的人生徹底落入谷底,每天與他為伍的,你知道是誰嗎?是一群豬。因為公孫弘只能靠放豬養活自己。公孫弘的家鄉在齊地淄川國的薛縣,一個臨海的地方。每天,他把一群豬趕到海邊,然后一整天面朝大海,目瞪口呆。豬倌,是鄉村的一種職業,雖然家家戶戶都需要豬倌幫忙,大約因為豬倌屬于大家共同的雇工,所以地位最低。
公孫弘當豬倌,一直到四十歲。已經進入不惑之年,公孫弘忽然困惑起來了。難道,放豬要放一輩子嗎?不,絕不,他決心改變自己的人生。也不知道這么多年都在想什么,已經是爺爺年齡的他忽然要讀書學習了。說干就干,不能再耽擱了。他投奔了齊地著名儒學大師胡毋生,然后就一頭埋下去,絕對認真地讀起書來。當公孫弘從書中抬起頭,眨眨眼看看周邊的世界,那已經是二十年以后的事。六十歲,公孫弘研讀“春秋學”,終于有眉目了。但是,即使到了今天,這也是一個該考慮退休的年齡了。
誰會想到,公孫弘這位老人,恰好遭遇了血氣方剛的國家,于是他的命運開始發生逆轉。漢武帝劉徹即皇帝位,那是公元前140年。漢初運行幾代的功臣政治,終于難以為繼了,漢武帝要建立新的人才選拔機制,面向全國,招攬人才。這年十月,漢武帝下詔要求地方諸侯國和郡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把選拔德才兼備、品學兼優之人才輸送到朝廷。淄川國的領導們,選來選去,最后還是公孫弘勝出。不知道是因為公孫弘的學識贏得了更多的贊揚,還是他的好學精神感動了大家,反正六十歲的公孫弘忽然大放光芒。
到了長安,公孫弘通過了一系列測試,順利成為經學博士。朝廷不僅需要公孫弘的學識,還盼望他能夠在更廣闊的行政領域發揮才干。一項特殊使命派給他,讓他出使匈奴。漢武帝的對匈政策,從后來的情形看,早就成竹在胸,但什么時候開啟戰端,還要等待機會。不知道從匈奴歸來的公孫弘是怎樣匯報匈奴的,顯然與武帝的想法格格不入。閱讀報告之后,漢武帝龍顏大怒,甚至說出公孫弘徒有其名、難當大任的話。長安會有各種謠言快速流傳,而公孫弘也感覺苗頭不對。好在他年紀大,有很好的托詞,立刻向朝廷報告,自己年老多病,希望告老還鄉。這一主動姿態,讓他沒有遭受更大的難堪。滿懷復雜情緒,公孫弘回到家鄉。誰都看得出來,公孫弘的政治生命已經劃上了句號。
六年之后是漢武帝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朝廷正式在全國推行察舉制度,要求各個郡國各舉“孝廉”一人。又過了四年,公元前130年,察舉制要求各地推舉賢良文學一人。淄川國必須完成朝廷的任務,于是又想到了公孫弘。這一年,公孫弘恰好七十歲。家里一貧如洗,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公孫弘告訴長官,上次失敗而歸,朝廷應該有記憶,實在應該推薦別人。可是長官不許,非他不可。一位姓鄒的老鄉送給公孫弘一套衣裝,他這才能夠踏上長安之路。
這一次,公孫弘應該是不該抱有太多希望的。全國一百多名賢良文學代表,公孫弘是最老的一位,而且太常寺的官員們竟然還真的認出了他。在厚厚的一疊報告中,公孫弘的被放在最下面。皇帝沒耐心或許根本就看不到他,這樣就不必再引皇帝煩心了。官員們這么做也是替皇帝著想。誰能想到,如今皇帝思才若渴,所有的報告都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包括最后一篇公孫弘的。令太常寺官員沒有想到的是,皇帝還真的不高興了。因為,皇帝認為公孫弘文章寫得最好,可為什么排名最后?皇帝更改排名,公孫弘名為第一,并且立刻召見。
看著公孫弘的文章,聽著公孫弘的言談,在漢武帝眼中,這為七十歲的老先生一點都不顯老,精神矍鑠,滿腹經綸,真是自己治國的上佳人選。公孫弘于是第二次被任命為經學博士。公孫弘好學篤行,孝養聞名。對于漢武帝而言,他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制度改革、政策推行冠以響亮的名號,加以恰當的理論說明,既能很容易地說服大眾,也不讓那些識文斷字的人找到缺陷。這些,用后人的概括就是內法外儒,王霸道雜之。公孫弘正是漢武帝的急缺人才。十年前公孫弘的長安失敗,是因為沒有摸到皇帝的政治脈搏,急于發言,反而耽誤了前途。這一次,公孫弘接受教訓,謹言慎行,一切按照皇帝的思路。
公孫弘大得皇帝的信用,博士之后不久,任命為左內史,再過幾年,當他七十六歲的時候(公元前124年),他被皇帝任命為丞相,并特別冊封了平津侯。公孫弘是西漢開國以來第一個布衣丞相。以前的丞相,都是功臣及其子弟,在拜相之前就已經獲得了侯爵。公孫弘是平民出身,即使有一定的民爵,也絕不會有侯爵這么高的爵位。拜相封侯,即先拜相再封侯,這個前所未有的特例,就這樣由公孫弘開立起來,成為后來很多平民丞相的登峰之路。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正是推行“獨尊儒術”的時代,這在漢代甚至中國古代歷史中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儒家學說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由此開端,成為中國常態。公孫弘這豬倌出身的丞相,正逢中國的大時代,于是奏出了一段夕陽無限好的人生樂章。司馬遷說:“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公孫弘之后,這類故事的主人公還有卜式、倪寬、主父偃等等,人才輩出與一個大時代,就這樣相互輝映,卓然生趣。
讀書改變命運,公孫弘應該是這方面勵志的典型。但是,這樣的說法,可能會遭遇板磚。這不就是十分腐朽的“讀書做官論”嗎?
做官,參與國家管理,在古代或者中古時期,都不是平民可以想望的事。全世界,最普遍的社會是貴族社會,在那里,貴族幾乎是政治的壟斷者,不是貴族出身而為國家官員者,無從想象。近代以前,在這個叫做地球的小行星上,這才是每日上演的戲碼:政治是貴族們的家事,與平民無關。
只有中國走上了特殊道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歷史變革解除了貴族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存在,平民出身的人可以做官,甚至可以當皇帝。于是,一部二十四史,到處都在發生著公孫弘們的故事。
在那個時代,這就是中國故事。
(摘自“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