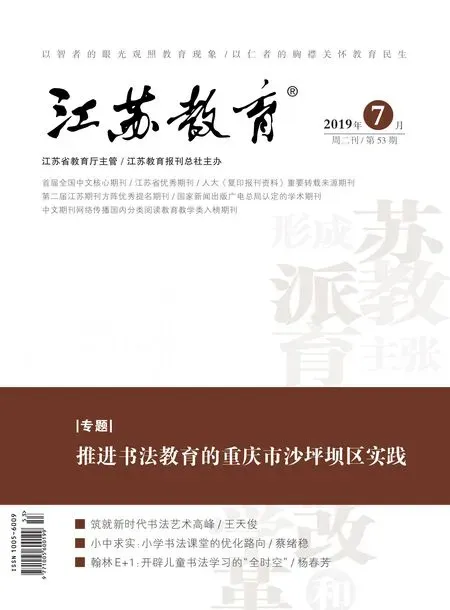真 體(上)
辛 塵閆 帥
關于“真體”,在唐以前多指代不一。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出現“真書”之名,如“真草詔書”,其中“真”意為規范,不可更改,特指官方文書的“定稿”形態;而“草”意為草率,特指官方文書的“草稿”形態。由此可見,在漢代,“真書”并非是指某一特定的字體,其含義是指特定時期通行文字中最規范、工整的形態。正是由于“真書”的這層含義,隨著文字的更迭,造成了“真書”指代不一,與“隸書”混用的現象。大抵自唐以來,“真書”被用來特指某一字體,即今人所講的“楷書”,因此,我們今天從書法藝術原理的角度所談論的“真體”,即指“真體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楷書”。
從現今的考古發現來看,早在東漢時期,民間簡牘、麻紙墨跡中就已經出現了“真體”的雛形,這種以隸體為依托的快捷性書寫方式的出現,反映了民間日常書寫對實用、便捷的需求。在這些文字中,明顯已具備了真體的若干元素,從用筆上來看,這些文字少見波磔,在行筆中依據一定的書寫次序(即“筆順”),且筆勢由“橫”轉“縱”;從結體上來看,這些墨跡上的文字由扁趨方。這種不經意間的草率書寫,反映的是下層官吏的無法之“法”以及無意之“意”,代表了早期真體的雛形。由于并未得到社會上層的普遍關注,因此,嚴格地說,這種漢隸的草率書寫方式,尚不能作為真體書藝的開端。

圖1 鍾繇《薦季直表》(局部)
東漢末年鍾繇的出現,賦予了真體獨特的“法”與“意”,對真體作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書體的形成與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現存署名為鍾繇的真體書作中(見下頁圖1),我們不難發現鍾繇對東漢以來民間流行的“隸體行書”的改造與規范,這種改造后的真體形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就點畫形象而言,提高每一點每一畫的豐富性,所謂“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其二,強化了點畫之間關聯與書寫次序,強調“起收轉折”,這些成為真體區別隸體的重要標志;其三,因為是在“隸體行書”基礎上的規范與改造,鍾繇所改造后的真體難免殘存隸書扁長體勢、翻挑用筆以及行草連帶筆畫等基因。正是一方面繼承了隸書的部分形態,另一方面逐漸突出真體自身的特征,這種“法”所蘊含的“意”被后人概括為“古樸”“巧趣精細,殆同機神”。有別于民間所流行的荒率粗糙的“隸體行書”,經鍾繇改造后的真體形象集中反映出了當時上層士大夫的“法”與“意”,一種對精致、典雅的審美追求。因此,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講,正是由于鍾繇的出現,真體才開始具有書法藝術的價值,并在后世不斷被書法家賦予藝術的生命。
在鍾繇之后,真體書藝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區別于篆、隸的新字體;伴隨著真體楷書的逐漸推廣,真體行書和草書也從隸體行書和章草中脫胎出來、迅速發展,并隨著政治與文化的分化,開始呈現出南北兩種迥然不同的“法”與“意”。正如清代阮元在其《南北書派論》中所言:“而正書、行草之分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則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
南派在繼承鍾繇真體的同時加以革新,形成了“新體”面貌,無疑代表著真體書法向新字體迅速發展的一面。自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士家大族遷徙南方,輔助皇室建立東晉政權;此后歷經宋、齊、梁、陳,史稱“南朝”。政治的遷移無疑是造成文化遷移的重要原因,昔時作為中原地區文化主體的士家大族知識分子,隨著政治勢力的南遷,在南方開始構建起了他們新的文化家園。在構架起的這座新的文化家園中,由儒家與道家相結合而形成的“玄學”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且不斷充實著該時期的文學藝術。在此時的書法藝術領域中,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首的士族子弟將真體書法(包括楷、行、草三種書體)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其實,早在二王之前,士大夫對真體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所謂“‘一’如千里陣云,隱隱然其實有形;‘丶’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ノ’陸斷犀象。‘乚’百鈞弩發。‘丨’萬歲枯藤;‘’崩浪雷奔;‘’勁弩筋節。”可以說,真體的點畫構成已經開始被人們進行總結,真體點畫所具備的審美價值也逐漸被人們發覺,真體的點畫包孕著自然的萬事萬物。如果說“陣云”“枯藤”是篆體隸體筆畫已經具有的意象,那么,“墜石”“崩浪”“勁弩”等,則是真體點畫引發人們聯想的自然物象。
而以二王為代表的東晉南朝書法家的出現,可以說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在他們的真體書作中,將“法”與“意”進行了完美的結合。王羲之作為引領南方群體風尚的書法家,其真體就“法”的一面來講,在用筆上,既強調點畫之間的映帶關聯,追求書寫韻律,又強調起收轉折分明、點畫精巧,以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真體點畫系統,由點畫之間組成的結構上,欹側修長卻緊結勻稱;由字與字組成的篇章上,錯落有致、收放自如。王羲之在真體書法藝術上的貢獻不僅是豐富完善了真體的“法”,更是融“意”于“法”之中,融“情”于“點畫”之內,無怪乎唐代孫過庭對王羲之真體作品的評價:“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啴喛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而王獻之的真體書藝,在繼承其父的基礎上,用筆外拓,結體疏散,整篇大小疏密、錯落有致,因此,較其父更加靈動俊逸(見圖2)。透過二王父子的真體書藝,我們可以看到,“法”與“意”的融合,“形質”與“神采”、“工夫”與“天然”的統一,這充分反映出魏晉士族階層良好的家庭教養以及獨特的人格精神。二王父子的真體書藝在南朝上層社會盛行,直至活動于陳隋年間的王氏后人僧智永,傳承家族法則,其真體依舊強調書寫韻律,用筆一拓直下,點畫顧盼。如果我們從真體書藝的發展來講,以二王父子為代表的新型真體書作的出現,無疑是真體成熟的標志,這不僅是由于自此真體有別于其他字體而形成的一套完整成熟的藝術形式語言,更重要的是二王父子真體書藝成為后世真體書法家不斷取法與學習的范式。

圖2 王獻之《新婦服地黃湯帖》
相較于南方士大夫之間流行的真體書藝,北方真體書藝的發展則呈現出別樣的“法”與“意”。大體來講北方真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早期的北方真體書作呈現出保守的一面,這主要體現在此時的真體過多地保留了隸體的諸多元素,在結字上結體寬博,平劃寬結。而其后北魏時期,北方真體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吸收借鑒南方“新體”的基礎上,形成了以龍門石窟造像記以及邙山墓志為代表的“魏碑體”,它們代表了北方真體書藝的輝煌。從“法”的層面來講,這一時期的真體楷書多橫畫欹側,撇捺開張,折角峻峭,在結體間架上追求“斜畫緊結”。由這種“法”所塑造出的“意”,可用康有為所提出的魏碑十美來進行概括:“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由此,我們感受到了北魏時期真體有別于南方所具有的獨特地域審美特征。而隨著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北方真體在北齊、北周有所倒退,或多或少地又糅合了一些篆隸書體的特征。
綜合來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真體書藝呈現出不同的“法”與“意”。從書寫載體來看,南方真體表現為尺牘信札的小字細楷,北方真體則表現為摩崖碑石上的刀鋒銳斧。從點畫形象來看,南方真體表現出的是點畫的精巧,北方真體則表現出長槍大戟的開闊;南方真體強調點畫的形態以及點畫與點畫之間的韻律節奏,北方真體則追求點畫組合關系,注重間架結構。而從表現的“意”來看,南方真體表現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表現出一種對精致、典雅的追求;北方真體則代表了少數民族政權的審美趣味,一種對古樸、雄強的青睞。總而言之,南方真體代表的是一種“今妍”,北方真體代表的是一種“古質”。
南北方真體的發展隨著南北方政權的統一也開始逐漸融合,這種融合跡象在隋朝就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此際真體既吸收南方真體用筆的精巧與連貫,同時又借鑒北方真體注重結體構造,像《龍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見圖3)等真體書作皆是兼具南北風格的典型代表。而這種南北書風融合的現象,在唐代越發的明顯。

圖3 《董美人墓志》(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