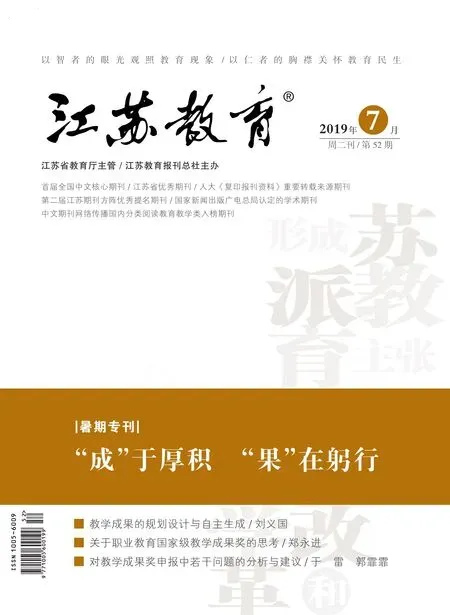關于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思考
——以江浙兩省為例
當前,職業教育已經進入內涵發展時期,職業院校在做好自身建設的同時,更要注重對教育教學實踐的總結和凝練,以期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級教學成果。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般需要具備三項條件:一是國內首創的;二是要經過2年以上教育教學實踐檢驗;三是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1]教育教學工作中的實踐能夠升華為教學成果,特別是成為國家級教學成果,離不開實踐主體的精心培育。本文以江蘇和浙江兩省為例,在分析兩省前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情況的基礎上,探討教學成果獎培育的大致路徑。
一、近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概況
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從2014年開始單獨設立的,到目前為止評審了兩屆,共計產生特等獎3項,一等獎100項,二等獎799項。本文通過對2014年和2018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項目的綜合比較分析,[2]大致呈現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概貌:
(一)東部地區成果獎的獲獎能力“一家獨大”
對近兩屆成果獎的數據分析發現,六成左右的成果獎均為東部地區獲得,無論是獲獎數量還是獲獎質量(獲獎率及獲獎層次),東部地區均呈現出“一家獨大”局面。職教史研究發現,“職業教育的發展是與經濟社會實現良性互動的過程”。教學成果的獲獎能力又一定程度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3]2018年成果獎中各省推薦項目的獲獎比例排名前8的分別為:江蘇、北京、天津、山東、浙江、上海、重慶和廣東,與2017年各省人均GDP的排序基本一致。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各省(直轄市)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獲獎能力是否與該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關系。
(二)高職教育類型的成果獎數量有增多趨勢,中職學校呈現“擠壓現象”
近兩屆的職業教育成果獎數據反映,高職教育類型的成果呈現增多趨勢,高職院校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的數量也呈現增多趨勢;而“中職類型”和“中職學校”均呈現減少趨勢。也就是說,在職業教育成果獎的“獲獎域”方面,呈現出中職學校遭受高職院校和其他單位(本科院校和科研院所)雙重“擠壓”的現象。
(三)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是獲獎的主體單位,但獲獎優勢呈現減弱趨勢
數據分析發現,在近兩屆的成果獎中,不足15%的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獲得了60%左右的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特別是獲得2項及以上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高職院校中,80%的獲獎院校均為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而從兩屆的變化趨勢來看,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的這一優勢有減弱的趨勢,特別是2018年的一等獎的獲獎比例相對2014年呈現減少趨勢。
(四)兩屆獲獎成果所屬的專業基本一致
對比兩屆成果獎獲獎項目面向的專業情況,基本是一致的,裝備制造大類、財經商貿大類、農林牧漁大類、交通運輸大類和電子信息大類仍是高職院校的主流獲獎專業。這一方面反映了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情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前職業院校的專業改革情況。值得反思的是,兩屆成果獎評獎相隔4年,也就是說近4年來職業院校的主流專業設置和專業改革沒有明顯變化。
(五)獲獎成果研究主題反映了當前職業教育的熱點問題
統計發現,兩屆成果獎的研究主題均能緊跟職業教育的熱點問題。本屆教學成果獎中獲獎比例較高的研究主題有“產教融合”“國際化”“協同育人”“創新創業”“‘三農’問題”“現代學徒制”和“質量保障”等。應該說,以上這些成果的主題,與當前職業教育大力推進的產教融合、協同育人、“雙創”教育、現代學徒制試點、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職業教育國際化和社會服務能力提升等政策基本一致。
綜上,前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從區域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個省市);從院校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高職院校,特別是以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為主體;從成果類型分布來看,主要是高職院校的成果;從成果的專業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裝備制造大類、財經商貿大類、農林牧漁大類和交通運輸大類等;從成果的研究主題來看,主要反映職業教育熱點,回應國家戰略。
二、江浙兩省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特征分析
(一)兩省教學成果獎獲獎的基本情況
從兩省近兩屆成果獎的獲獎總數來看,每屆均占全國的20%左右;尤為突出的是,一等獎的獲獎總數每屆均占全國的30%以上。從縱向關系上看,獲獎總數有進一步增多的趨勢,特別是江蘇省,其一等獎和二等獎的獲獎數量均呈現增多趨勢,具體如下頁表1所示。
(二)兩省教學成果獎的主題特征分析
對江浙兩省近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190余個項目進行主題分析,主要發現如下特征:
一是“實戰”與“實境”。主要表現為在實踐教學中突出實戰和情境教學。[4]例如,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等提出的基于“海上教學工廠”的高職航海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杭州市中策職業學校等提出的“行會駐校·名店訂單·企業教室·項目管理——中職烹飪人才培養模式”;等等。主要突出職業教育的實踐性,力求構建真實的教學情境,給學生提供實戰機會,著力提高學生的實操能力。二是“多元”與“融合”。主要表現為在教育教學改革中學校與行業、企業的多元育人,教育與經濟的有效融合,包括“政行企校”的融合、公私融合和產教融合等。例如,常州市科教城(高等職業教育園區)管委會等提出的“政府主導、產教融合、協同育人——區域高職教育常州模式”;杭州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基于校企共同體的服裝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與實踐”;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共建基于利益捆綁的“資源協同體”模式等。主要針對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才培養,從不同視角對具有不同價值體系、功能的學校、政府和企業等的跨界和融合進行了探索和實踐。然而,對于不同價值主體的跨界與合作,如何形成知識領域、行政領域和產業領域的三力合一,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三是“國際化”與“信息化”。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的國際交流、國際合作項目和信息化提升教育教學水平等。例如,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提出“基于‘跨境校企共同體’的高職航海國際化人才培養探索與實踐”;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基于國際化校企合作的高職汽車專業‘雙主體、多元化’人才培養創新與實踐”等。四是“標準”與“質量”。“標準”與“質量”是當前職業教育內涵建設的主要指向所在,近兩屆教學成果獎中表現明顯。如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提出的“省域中等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體系建設的研究與實踐”;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高職院校內部質量保證體系的研究與實踐”;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標準與競賽雙驅引領基于制品生產線流程的模具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索與實踐”等。五是“地方”與“特色”。主要指體現地方性和特色化的教育教學改革項目,如寧波市古林職業高級中學提出的“‘四課堂三機制’培養地方菜肴創新型傳承人的探索與實踐”;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特殊教育師范‘藝術治療’特色課程群建設與實踐”等。六是“農民”與“鄉村”。主要指回應國家戰略,強化職業教育面向現代農業培育新型農民,如蘇州農業職業技術學院提出的“城鄉一體化背景下新型農民培育的蘇南模式創新與實踐”;溫州科技職業學院提出的“‘三創型’農經人才培養創新與實踐”等。

表1 江浙兩省近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情況
三、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培育應注意的問題
需要重點探討的是,為什么近兩屆江浙兩省的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的數量和質量均在全國遙遙領先,且2018年比2014年更有增長的趨勢。筆者結合以上分析,認為原因有三:一是教學成果獎的獲得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直觀表現,同時也是以強勁的經濟社會發展實力作為基礎和支撐的;二是教育教學改革的選題契合了職業教育改革的時代走向,具有獨創性、新穎性、實用性;三是注重教育教學改革成果的總結推廣,江浙兩省作為職教強省,在職業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成果的總結推廣方面也走在全國前列。綜合而言,筆者對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培育提出如下建議:
(一)選題要體現首創性
好的教學成果的選題應當體現首創性,即選擇符合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方向,找準職業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突出中國特色高水平職業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焦點和難點問題,從而便于占領職業教育發展的制高點,研究、制定出具有獨創性、新穎性的教學改革方案。具體而言,2022年的教學成果獎培育要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7〕95號)和《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9〕4號)為指向,在“管好兩端、規范中間、書證融通、辦學多元”等方面做出實踐探索,包括回應國家戰略、探索產教融合協同育人、職教理論創新等,推進職業教育現代化。
(二)實踐要體現痕跡性
教學成果培育方向確定后,依據教育教學改革整體方案實踐就是關鍵。需要注意的是,教學成果要經過2年以上教育教學實踐檢驗。因此,教育教學改革的實施,需要體現痕跡性。也就是說,教育教學改革要注重過程性積累,注重在實踐過程中建章立制,完善規章制度,加強過程性材料的收集,強化階段性小結與成果凝練。
(三)成果要體現影響性
教育教學改革要以成果為導向,且產出的成果要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即標志性成果。一般而言,標志性成果包括:(參與)制定國際或行業標準等,專利授權,服務中小微企業,科研與技術服務到款額,(教師或學生)在全國性專業大賽中獲獎,組織召開全國性專業學術研討會,公開發表高級別的學術論文,出版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等。
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作為職業教育領域的最高獎項,需要利益相關者特別是職業院校理性審視教學成果獎設立的宗旨、意義及功用,堅持問題導向,特色培育,[5]切不可“為了成果獎而成果獎”。筆者以為,成果獎的設立旨在發揮引導、激勵作用,重在推進職業教育基層敢為人先、奮力爭先,推進“自下而上”的自覺的教育教學改革,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因此,教學成果的培育一方面以獲獎為旨向;另一方面也是至關重要的是,通過成果培育樹立全體師生的改革意識,調動師生參與教育教學改革的積極性,切實推進教育教學改革,重在改革、重在行動、重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