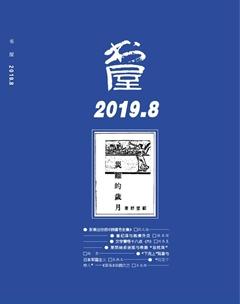萊昂納多迷思與希臘“忘憂珠”
韓秀
一
2007年2月25日晚間,我的希臘女友娜苡阿蒂和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等待第七十九屆奧斯卡金像獎影帝揭曉,她與古希臘的清泉之神同名,卻絕少給我清澈之感,反而總會化平凡為神奇,讓世間情事都披上幾許神秘。此時此刻,她出現在美東,據說只是為了看真正的雪景,果真就讓她趕上了。整個冬天,最美的一場雪,一場因為氣溫不夠低而會很快消失的雪就這么端到了女神面前。順便,我們還能一起看看萊昂納多。誰不想多看他兩眼呢,連主持人艾倫·狄賈尼絲都忍不住說她自己“只不過是那些想多瞧萊昂兩眼的女人之一”。
“他絕對是神的兒子,一如我們的‘忘憂珠。”娜苡阿蒂斬釘截鐵,說的就是萊昂。一年之中居然有兩部精彩大片,我們自然是期待著他得獎。然而,人見人愛、吸引了無數視線的萊昂再次推動整部電影獲獎,自己卻也再次與小金人擦肩而過,一如當年的大片《泰坦尼克號》,他是那夜的新聞焦點。
另外,這一天成為新聞焦點的是偉大的達·芬奇。在佛羅倫薩,專家們又有新發現,達·芬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很可能隱藏在一幅名畫的身后。達·芬奇再次以他的隱喻指引人類陷入困境并考驗人類的智慧以及對他本人畫作的熱愛程度。“他是神在人間的化身,一如我們的惡魔之眼。”娜苡阿蒂含情脈脈,淺淺笑著。
在娜苡阿蒂的思維模式里,世間并不存在任何的偶發事件,任何的巧合都有其必然性。“人們的摯愛還沒有達到沸點,還需要假以時日。”她寧靜一笑,說道,“此時此刻,真想寄一串忘憂珠給萊昂,他需要一點點光明照亮他的前路。一點點朦朧的美感。”她的眼睛望向茶幾上那一本巨大的《達·芬奇全集》,上面盤繞著一串來自克里特島的“忘憂珠”。
“忘憂珠”(Worry Beads),崇信必然而絕不輕言巧合的希臘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神秘與希冀的凝聚之所。初識其美麗是在雅典市中心芤艛納琦的一家精品店里,樸實無華的木質桌面上放置著巨大的珠串,不是可以佩戴的首飾,它們似乎是一種裝飾品。其材質或是人造琥珀、人造瑪瑙、真正的美石或者是玻璃,形狀各不相同。用皮繩串起來,間以金屬的圓球、蒜形珠、環形珠,尾部裝飾則是羅盤、錨、馬蹄鐵、星象符號甚至太陽神阿波羅或者亞歷山大大帝的頭像。它們非常沉重,擺在那里,不但異常美麗,而且給我非常可靠的感覺。從驕陽似火的戶外走進來,只覺涼爽與寧靜。店主是高雅的斯巴達女子阿格麗亞,她仔細地端詳著我,似乎完全不著急做生意。知道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稀罕物,于是打開話匣子,告訴我這“忘憂珠”的哲學意義。現代希臘人崇信東正教,但是,根深蒂固的依然是對古希臘諸神的信賴、依戀與摯愛。人世間充滿著不幸、災難、痛苦與失望,“忘憂珠”凝聚著幸福、吉祥、快樂與希望,在人們身邊、在人們歇息身心的家里,它們的美麗來自天然,比方說美石;它們的美麗來自人工,比方說人造琥珀;它們的美麗來自天然與人力的結合,比方說玻璃。對于阿格麗亞本人來說,“我偏愛玻璃,它讓我留住了阿波羅,讓我不但能夠感覺到而且能夠看到祂的俊美、智慧。有祂在身邊,我的生活里滿是音樂、藝術。而且,我遠離疾病”。她狡黠地深深看我一眼,垂下眼瞼,隱藏住笑意。
很快,我有機會去克里特島,在煙熏火燎的玻璃作坊里看到那些做工并不精細的玻璃珠子,看它們被串起來做成一串串“忘憂珠”。我很想請問的就是,這些顏色美麗如海水的玻璃制品為什么高低不平、看得見氣泡與雜質?滿臉于思的玻璃師傅不等我問完就笑著告訴我:“把完美留給神。”順便很輕松地表示道:“當大家都在突飛猛進的時候,保持數千年不變的傳統工藝,這本身就成為特色、成為傳奇。”我卻覺得,除了哲學意義之外,還有一份深沉的寄托在那里,有一種不忍改變的溫柔。
在克里特,我也找到了“惡魔之眼”的最早藍本。原來那是繪于船頭的眼睛,它們有驅散風暴、帶領船只順風前行的功用。將其搬到了玻璃上,一雙丹鳳眼變成一只圓圓的眼睛,快樂、調皮;它們甚至被鑲嵌到方形玻璃珠的四面,再串成“忘憂珠”的形式,那是把祈福與驅魔兩個任務一肩挑起了。
克里特島不是雅典市中心,玻璃作坊的師傅遇到一個投緣的來客,就會停下手里的活計,煮上一壺毒藥般的咖啡,讓話語趁著海風飛揚,聊個不停。
愛琴海海水究竟是什么顏色?無數程度不同的藍、松石綠、孔雀石綠、金紅、絳紅、酒紅——世界上所有的顏色都在海水里,也在玻璃里。玻璃師傅一往情深地說道:“無色透明,也許是最好的表達。”他捧出一掛“忘憂珠”,粗糙的、疤痕累累的雙手從無色半透明的方形玻璃珠上一粒粒撫過,緩緩停留在尾端的正方形銀飾上。“陽光、晴朗的好天氣,沒有病痛的身體,愉快的好心情,都是住在奧林波斯山上的諸神網開一面的好結果啊。能夠在這些網開一面的時刻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那已經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生了。”
我帶走了那串“忘憂珠”,帶走了那只絕無僅有的黑色“惡魔之眼”,它無法救起“泰坦尼克號”,卻把萊昂帶給我們。“忘憂珠”將阿波羅的贈予斂入甕中讓我時時刻刻享受祂的眷顧,“忘憂珠”與達·芬奇相伴帶我遨游神秘的美麗世界。我記得玻璃師傅的雋語,萬般珍惜著那可貴的“網開一面”。
二
沒有人知道,那一刻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雙親都是國會山莊的律師,自小在華府喬治城的私立學校念書,完全是為了要進紐約的New School念社會學,這才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一幅美國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藍圖本來是清晰而準確地在青年考德威爾面前展開著。但是,這一刻降臨了,他無意中走近了UrBan Glass,一個重要的所在,那個地方散發出來的熱烈氣息如同來自威尼斯的神秘力量一樣,將考德威爾團團圍住。他在瞬間找到了他在天地之間的位置,他當時甚至無法了解。但是,現在,十多年之后,他終于完全明白,他找到的不只是一個獻身的領域,一條充滿挑戰的生活道路,一個不斷創新需要無窮勇氣的藝術家生涯,而且是靈魂的居所。
回首來時路,考德威爾的一頭亂發更加引人注目,他笑逐顏開地告訴來訪者,在課室兼工作間里他曾經怎樣將熔融的玻璃液迅速拉長,直接穿越整個工作間。幸好當時沒有其他學生在場,沒有人因為他的狂想而受傷。玻璃的變化是美麗的,且不必畫蛇添足。任何特別賦予的意義以及理論在光芒四射的玻璃面前都是蒼白的、微不足道的。
但是,他必須為自己的創作尋找靈感吧?
考德威爾靦腆地微笑著。靈感是玻璃自己所賦予的。高溫兩千攝氏度的玻璃,那一小坨橙色的精靈從熔爐中,被笨重的鐵質吹管“沾”了出來的那個瞬間已經在表達它的意愿了。輕輕一吹,用一根手指一碰,那極輕微的一點壓力馬上變成了一種語言,與玻璃之間產生了一種溝通,這溝通使得跟著出現的延展與變形有了意義,手中可能出現的工藝品被賦予了雕塑的性格。手握吹管與鐵鉗的人能否掌握這種性格,也就決定了他是一位工匠還是一位雕塑家。考德威爾坦陳,玻璃工藝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傳統,就算是自己全力向雕塑家的方向邁進,歷史與傳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背離的,它們強大地存在于我們每天的勞作當中。
滿地的玻璃殘片以及那些被煙塵覆蓋的花瓶形狀的半成品沉默不語,卻做了最實在的補充說明。
考德威爾身穿臟兮兮的卡其布襯衫,神態自若。他是那種一見面馬上就會被青少年視為偶像的三十出頭的中年人。藝術評論家們分析華府畫廊界龍頭Gfine Art為他舉辦個展的原因,以及他的作品迅速被廣泛收藏的原因。其中一個論點就是,他不止是一位藝術家,他更是科學家。他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己身體的關系,人與空間的關系。具體的,比方說樹枝、珊瑚礁、骨骼、腸胃、肋腹、反射鏡;抽象的,比方說和煦、端凝、毅力、氣魄、堅韌、空靈,這也就是為什么考德威爾的作品常常“無題”,卻給了觀賞者更廣闊的想象空間,或具體或抽象,無窮的可能性。
“我喜歡復雜的東西。”考德威爾如是說。他不但喜歡延展與變形帶來的歡愉,他甚至喜愛玻璃的易碎,玻璃碎片折射出的支離破碎與幾十面反光鏡所折射出的氣象萬千之間并非橫亙著萬水千山,“它們之間的聯系遠遠勝過它們的區隔”。藝術評論家與收藏家都鐘愛那四十面反射鏡聚集于墻形成一件作品所帶來的奇詭的視覺效果。
玻璃與鐵的契合是考德威爾作品的獨特風格之一。玻璃,無論是管、是球、是面,都依靠鐵質的環、鉤、支架來支撐與組合。一個被拆掉的建筑物里面的陳舊的“廢鐵”被考德威爾拿來回爐,用來做成他的獨特的雕塑品的部分背景。很多時候,甚至成為重要的角色,因為玻璃這種“緩慢靜止的水”是透明的,原本是背景的鐵架透過玻璃的透視效果而走到了前臺,與觀賞者的距離大大地縮短,它們無意中揭示的某些意念會在極短的時間里打開觀賞者的視野與心胸,產生的震動常常出人意表。
在Gfine Art四壁雪白的展室一角,在四平方英尺的面積上,二十多個黑色鐵鉤上面懸掛著無色透明、圓滾滾的玻璃球。墻角,正好也有兩根黑色鐵條,似乎是用來加固墻壁的普通建材。走近一看,這樸實無華的建材透過玻璃正在上演最具童趣的活劇。人們不禁微笑,轉頭看到那一尺之外的兩根鐵條卻又是“一臉無辜”的模樣。這樣的“魔術”表演怎么不讓收藏家動心?想象一下吧,如果近在咫尺的是一只花瓶、一尊唐三彩陶俑、被風吹動的窗簾、畢加索的堂吉訶德、達利的鐘、馬蒂斯的和平鴿,又當如何?人與世界可以是這樣和諧、童真而趣味無窮的,只要我們張開眼睛。
美麗是無法拒絕的,然而美麗的實現需要的不但是勇氣、天分,還需要精益求精。如此小小的玻璃制品,單件已經需要工藝的精湛,那許多的套接,那些無與倫比的完美弧線又是怎樣完成的?“最難的事情,是把一坨玻璃液拉成一個完美的長方形。做到了,那感覺極棒,雖然玻璃本身已經很棒了。”考德威爾這樣說,“回爐,是唯一的不二法門。不能完美表現主題,而玻璃已經冷了,除了回爐或者部分回爐之外并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這也就是為什么別人都在海濱避暑,而他卻在與兩千攝氏度高溫的橙色液體糾纏不清,樂此不疲且越戰越勇。
藝術評論家們感覺考德威爾多少有些達·芬奇的影子。達·芬奇每天新鮮點子層出不窮,有些還曾經嘗試付諸實施,許多都只是一閃而過,來不及實踐。考德威爾也有不少好點子,但是他不肯放過其中任何一個,一定要一試再試,他的勇氣正是來自玻璃本身。這靈魂的居所幾乎無所不能,其變化的美妙根本非人力能夠限定。
追隨玻璃,將玻璃本身的意愿表達出來,樸實而堅定,那就是考德威爾的方向。
三
初秋的傍晚,站在紐約長島牡蠣灣的街心公園里,放眼望去,水天相接之處云蒸霞蔚。那顏色卻似乎不大對,怎么會紅得如此嬌艷欲滴?應當是莊重的、柔和的、淺淺的水紅色,甚至有著一抹淺灰色透明的煙靄才對啊。更不消說眼前并沒有那累累的紫藤蘿,沒有那懸垂在天際、懸垂于水上的千嬌百媚。當然也沒有那曲曲折折、攀援而上的老藤與新枝。
這里,本來有著一所巨大的莊園,叫作Larelton Hall,從那莊園的長窗眺望牡蠣灣,才會出現那樣一種風景。而這風景卻是被劉易斯·蒂芙尼永遠地留給了我們,留在一扇巨大的含鉛彩色玻璃窗上。跨越了百年的風霜,那柔美的景致永遠地存留下來了,存留在我們心里,面對著某一道自然的尋常風景,反而感覺不真實。
以珠寶設計與繪畫為起點,1879年到1915年,劉易斯走進了他創作的巔峰時期。這扇牡蠣灣風景窗正是他1908年的作品。它曾經是一扇真正的窗戶,鑲嵌在紐約曼哈頓的一所豪宅,直到1957年拉瑞爾頓莊園遭到火災之后,它才隨著蒂芙尼的其他作品一道,陸續地進入博物館收藏,逐漸地廣為人知。
在大都會博物館,我常常有著一種無法克制的陶醉其中的感覺。我們欣賞古代希臘與羅馬的六千多件展品,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時代的輝煌。我們欣賞印象派上百件珍品,我們會無比贊嘆那一批大師的登峰造極。但是,蒂芙尼卻是一個人造就出一連串的風景。短短三十六年之中,上千件精品深入人們的生活,引導了時尚與潮流,甚至改變了建筑形式,成為一種文化。自然景觀被這樣細致入微地引進了室內,人們可仰望、可觸摸、可面對沉思。孔雀羽毛化身花瓶,蜻蜓飛上了燈罩,玉蘭、鳶尾花、木蘭、紫藤蘿躍上長窗。天地之間的美麗被一一地復制出來,其媒介卻是玻璃。
這玻璃的五彩繽紛不是繪制的,而是將顏色融入了這透明、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的物質,用鉛、用銅這些低熔點的金屬將設計好的玻璃連接成一幅畫、一扇或者多扇彩窗。甚至用酸等化學物質在玻璃的背面下功夫,而使玻璃的正面出現驚人的變化。
在一扇高一米五寬一米的彩窗《飼火鶴》的制作過程里,這些技藝得到充分發揮。畫面中心是那喂食火鶴的女子的手,兩只火鶴正滿心信賴地從這只手里啄食。畫面充滿溫暖、信賴與誠意。這幅作品曾經是拉瑞爾頓莊園客廳的一扇窗。當初的樣子,我們今天只能從Ernest Edward Oelhrick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拍攝的一幀照片看到端倪。原作在數年后的大火里被毀,但是沒有全毀,最終得到了恢復,恢復的過程使得整個畫面格外逼真,劉易斯當年非常自豪的乳光玻璃在表現女子肌膚時達到極佳效果。女子衣裙的折皺則依賴玻璃厚度的改變來體現,女子腳邊的小地毯被賦予更多色彩而增加了質感;懸吊于空中的魚缸,色彩更加明麗,似乎魚兒正在水中游動;畫面正中小小噴水池那激噴而出的水柱是在玻璃背面用酸處理而成的。隨著技術的進步,在經過蒂芙尼工作坊藝術家們的精心處理之后,被修復的作品較原件更為精彩。
并非每件重要的作品都有如此好運。曾經在拉瑞爾頓莊園客廳占據整整一面墻位置的巨大橫窗作品《浴者》在制作過程中不斷豐富,其結果甚至超過了他早先的設計,而成為他最為得意的作品。莊園近牡蠣灣,陽光透進彩窗,美麗的女子與池水相輝映,浪漫的人體凸顯在色彩斑斕、生機無限的自然背景之中,不但是美麗的畫面,更是玻璃技藝的更上層樓。那是劉易斯首次使用乳色玻璃并獲得空前的成功,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玻璃藝術家在彩窗制作中,人體部分還是要依靠彩繪而不能完全以玻璃本身來體現。劉易斯去世之后,他的密友邯莉女士就向蒂芙尼基金會建議,將拉瑞爾頓莊園的彩窗送給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作為永久的珍藏。她的建議開始并沒有被采納,1957年的大火完全地毀掉了這幅重要的作品,消防隊趕到火場之后破窗而入,那扇窗正是精美絕倫的《浴者》。現如今,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美國藝術新翼,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一幀照片。池水里的睡蓮、池旁紫色的鳶尾花、高視闊步的孔雀、陽光在樹梢與枝葉間的閃爍、美麗女子的歡愉,都還有著很好的呈現。然而,已不再是玻璃,只留下了無限的悵惘與念想。
彩窗作品《木蘭》,本來是五扇聯結在一起的長窗,火災之后,只余得三扇。北美洲的星狀白色木蘭(Star Magnolia)是早春天氣最早綻放的花朵。在純凈、湛藍的碧空映襯下格外高潔。這讓我們想到在蒂芙尼家族的巨量藝術收藏中間那許多來自東方的瑰麗。劉易斯是一位絕對不肯墨守成規的藝術家,他熱切地吸收著人類創造出的一切美感,將之融入自己的創作。這無葉的木蘭,讓我們聯想到東方美術的簡潔與留白。玻璃的厚度使得花朵如同浮雕,宛如舞蹈著的精靈般栩栩如生。花蕊的部分不但使用了琥珀色甚至使用了寶藍色,這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不但使我們看到了東西方交融的那一瞬,也讓我們看到了劉易斯作為新藝術(Art Nouveau)代表人物的一個典型例子。精巧、自然、率真,而且絕不拒絕采用新材料、新技法與新觀念。
最終,我長久地將目光停留于《四季》。1900年,劉易斯帶它參加在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四季》本身以大膽設色的四扇窗組成畫面中心,周圍的設計卻如同古老書冊中的插圖與邊角設計,以極其細致的琥珀色圖案,如同工筆,勾勒出頂端的雄鷹、下方的陶甕、兩邊的花卉。外圍的精巧、細膩與主題的自由、奔放所形成的強烈對比已經很難用適切的言辭來形容。我只是牢牢記得了佛羅里達州那個叫作冬之苑的郡,在那里有一家美國藝術博物館,他們那里才是當今世界上蒂芙尼珍品最豐富的藏家。或遲或早,我必得到那里去走上一趟,為了那些永遠不褪色的、流行的風景。
四
金秋十月,大家都往新英格蘭方向去賞楓,我卻決定要往南走,不是十里八里的路程而是整整一千英里的距離。那地方在哪里?朋友問我。在佛羅里達。東邊還是西邊?東邊,靠近奧蘭多。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除了迪士尼樂園之外還有什么?朋友嗤之以鼻。那地方最近可是蕭條得緊,商家紛紛關門,房市跌得一塌糊涂!咦,你不是要乘機在那里買房子吧?朋友露出高深莫測的表情,盯著我不放。
噢,當然不是。我只不過要向一對夫婦表達我的敬意而已。他們姓馬崁,在奧蘭多北邊的“冬之苑”建造了一家博物館,真正承擔起美學教育的重責大任。朋友支吾說,從來沒有聽說過。
雖然是信息泛濫的二十一世紀,少為人知的人間至美依然多著呢。
十九世紀中葉,十七歲的少年穆爾斯進入一家機械制造公司,年薪五十美元;七年之后,二十四歲的穆爾斯進入公司高層。之后,他有膽有識地買下公司,并且使其逐步成為十九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機械制造業巨子,富甲一方。巨大的財力使得熱愛藝術的穆爾斯成為美國藝術的大收藏家。他不喜終日喧騰的芝加哥,雖然他在那里揚名立萬,他卻珍愛佛羅里達的氣候宜人,尤其喜歡冬之苑的靜好。于是,他在那里廣為置產,并且在那里退休。
穆爾斯夫婦育有一個女兒,女兒熱愛藝術,婚后也生了一個女兒,名字叫作婕涅特,乖巧的小婕涅特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與母親的大量藝術藏品使她在幼年時期已經等于是生活在博物館里,而她對蒂芙尼玻璃的認識更是與生俱來,因為家里的長窗、桌上的花瓶與臺燈正是蒂芙尼的作品。幼年時代與外祖父在冬之苑的生活也奠定了她日后為此地奉獻一生的感情依據。外祖父在她十二歲的時候故去了,母親在她十九歲的時候也故去了,那時候,正在求學的婕涅特已經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藝術家,她離開了人去樓空的芝加哥大宅,轉向冬之苑,她在那里的羅霖學院求學,并且從1942年到1975年在校董會里為這所大學服務了三十三年,為大學提供了豐沛的資金,從美國名校延聘知名學者、作家來到羅霖學院執教,成為大學最可靠的支持者。
婕涅特與羅霖學院藝術系教授修的結識也是緣于其外祖父藝術藏品的收藏與展示方面的技術性問題。沒想到兩人一見鐘情,結為連理,攜手為美學教育的推廣努力,兩袖清風的教授修在婚后更擔任羅霖學院的校長長達十八年之久。權勢與財富卻沒有改變這位學者的人生態度,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將人文的藝術的創意付諸實施而已,最偉大的建樹自然是穆爾斯博物館在“冬之苑”的建立以及蒂芙尼藝術品的搶救工程。
1957年,位于紐約長島的蒂芙尼故居拉瑞爾頓莊園遭到大火。那時候,整個莊園已經賣出且被閑置,完全無人居住,空屋遭到祝融之災成為廢墟。蒂芙尼基金會沒有財力買回更沒有財力修復,蒂芙尼的女兒給修寫信,希望馬崁夫婦“也許有興趣買一扇窗戶”。因為兩年之前,正是由于馬崁夫婦的大力促成,蒂芙尼藝術品在羅霖藝廊得以盛大展出。我們可以想象,當修與婕涅特抵達長島,站立在殘窗與斷壁之間面對那一片焦黑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地震驚與心痛。
馬崁夫婦當下做出了決定,他們將買下這全部的廢墟,搶救所有的殘片,盡一切可能修復之。這個決定使得這對夫婦在美國藝術史上留下了永遠的輝煌,這對默默付出的夫婦所付出的不只是無法計量的金錢,更是他們的生命與心血。全部的修復工作在近半個世紀之后的1999年才完成,那時候,婕涅特已經辭世十年,而修也故去五年了!每念及此,我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
現在,我走進了穆爾斯博物館,面對著一扇樸實無華的木頭大門,上面有一個浮雕十字,在這扇門的后面就是曾經曇花一現然后消失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蒂芙尼重要作品——蒂芙尼禮拜堂,今天的人們不知世界上有這件珍品的不知凡幾。從拉瑞爾頓莊園移來的這扇木門是鑲嵌在影壁上的,繞過影壁,我們面對的是歷史的、藝術的、文化的整體結晶。禮拜堂以莊嚴、浪漫、輝煌烘托出的質樸攝人心魄。四層半圓形穹頂十二根廊柱呵護著祭壇。祭壇后方的壁上,冠冕之下,兩只正在開屏的孔雀成為華麗的極致。所有都是用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彩色玻璃鑲嵌而成的巨大馬賽克建筑。如此的登峰造極卻不給人難以趨近的感覺,層層臺階以平實的大理石鋪就,立面近大遠小,彩色馬賽克裝飾成活潑的圖案,似乎在召喚著人們的親近。有著拜占庭風格的禮拜堂卻沒有拜占庭的森冷與清癯。大堂正中的天花板上懸吊著三度空間的巨大十字燈飾,巨大的鮮嫩綠色的玻璃與無色透明鉆石般的水晶玻璃交相生輝,那種一覽無遺的瑰麗是典型的蒂芙尼風格了。雖然宗教故事不可或缺,但是蒂芙尼不會拒人于千里之外,圓窗上的人物豐滿、圓潤,甚至有些喜氣洋洋。走進這禮拜堂的人們不會心生戒懼,反而會滿心歡喜。禮拜堂側殿的受洗之處是一個美麗的球體,那是一個受洗盆,不舉行儀式的時候,半圓形的蓋子是合攏的,它讓我想到古希臘阿波羅神殿中那世界的“肚臍”,是那樣的自然而風趣,人與神之間大約可以是那樣親如兄弟的罷?而這受洗之處的后壁則是巨大的蒂芙尼長窗,水之濱,白色百合花盛開著,這是對生命的禮贊了。
博物館的設計善解人意,知道我們是多么希望親近這美麗之所,所以允許觀者直接走近受洗側殿,沐浴在花影之下,享受美麗的球狀“受洗盆”帶給每一個人的無限慰藉。
但是,親愛的人們啊!你們能相信嗎,這樣純凈的美好竟然曾經深陷地底不見天光,而且曾經遠離塵世達百年之久!
1893年,盛大的哥倫布世界博覽會在芝加哥舉行,“蒂芙尼禮拜堂”堂皇展出,吸引數十萬人參觀、贊嘆,報紙上的評論更是花團錦簇。博覽會結束,一位教友將禮拜堂買下,捐贈給正在創建中的紐約圣若望大教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哪里想得到,這個教堂的建筑師與主教根本不欣賞蒂芙尼,更不喜歡這個禮拜堂,認為這“新拜占庭”風格的作品不適合圣若望,并且堅決地表示,這個禮拜堂應當永遠不見天光。蒂芙尼公司忍辱負重,將禮拜堂的穹頂拆掉一半以適應圣若望大教堂地下室的高度。整個禮拜堂縮在黑暗的角落里,完全失去了在博覽會中的光彩。
1916年,圣若望教堂的地下室水深盈尺,禮拜堂完全成為“棄物”浸泡在水中。蒂芙尼寫信給主教,他在信中說,禮拜堂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積水對這件作品絕對不利,既然現在教堂棄之若廢物,不如讓蒂芙尼公司給禮拜堂換個地方。那一年,那位捐贈者也故去了,主教完全無所謂,就讓蒂芙尼將禮拜堂拆遷了。拆遷過程痛苦不已,禮拜堂不但被砍頭削腳,那巨大的懸吊燈飾也不翼而飛了。蒂芙尼公司將這幾十萬片玻璃運到長島,在拉瑞爾頓莊園里,與主體建筑有一小段距離,蓋了一所房子,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禮拜堂。如此這般,又經過幾年的努力,這美麗、祥和的禮拜堂才恢復了在博覽會上曾有的輝煌。修復工作也苦澀不堪,因為產權還屬于圣若望教堂。直到1935年,劉易斯·蒂芙尼去世兩年之后,主教大人才高抬貴手將產權還給蒂芙尼公司。
1957年的大火將拉瑞爾頓莊園的主體建筑破壞殆盡,禮拜堂的損失不是太大。經過蒂芙尼親手修復的禮拜堂與拉瑞爾頓的其他殘片一道被再次搬運,抵達“冬之苑”。馬崁夫婦的大力援助對于困窘不堪的蒂芙尼公司而言是巨大的鼓舞,藝術家們紛紛熱情地投身這一漫長的修復工程。那最后一次的搬遷也是笑中有淚。一家名譽極佳的搬運公司接受了馬崁夫婦的要求,將這些“廢物”從紐約運到佛羅里達,那時候州際高速公路尚未通車,那搬運工作是比較漫長而辛苦的。抵達之時才發現,所有的殘片只是胡亂與廢舊輪胎等一道堆放著。“因為,這實在都是廢物呀。”搬運公司坦言。藝術家們不再多說,小心地將全部殘片放進預先準備好的巨大工作間,自此開始,每一片玻璃才真正回到專家們手里,清理與修復的巨大工程于焉展開。
現時現刻,我坐在博物館對面軒敞的咖啡館里,從人聲鼎沸、色彩斑斕的遮陽棚下看著對面這座鋼筋水泥的堡壘。她與周遭浪漫的西班牙建筑完全不同,窄小的窗戶完全沒有采光的作用,但是水火不侵,固若金湯。馬崁夫婦給基金會最后的指示是:“這所博物館不能成為‘冬之苑的負擔,而應當為此地帶來繁榮。”我們周遭的一片欣欣向榮正好是最貼切的佐證。
在2007年,這個為蒂芙尼作品以及玻璃藝術量身打造的博物館,門票三美金,可以多次出入。外子與我從咖啡館站起身來再次走進這家完全靠燈光照明的博物館,設計高明的燈光使得玻璃如同寶石、如同飛瀑、如同花瓣與飛旋的樹葉、如同佳人細致的肌膚,給人不同的“觸覺”與感受。我長久站在整個展覽空間第一幅作品前面,那是一百一十年以前,劉易斯·蒂芙尼為英國商人Joseph Briggs所創作的一扇彩窗,黝暗的背景中心是異常明亮、歡快、鮮艷、怒放著的一束玫瑰。外子站在一間展室的中心,長久凝視那些雖然不能再修復但是依然是玻璃工藝極品的片段,它們被仔細地鑲嵌在透明的裝置里,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欣賞它們,想象它們在原來的創作中所擁有過的燦爛。當我們終于在博物館即將關門的時分緩緩步向出口的時候,一件作品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歸來。工作人員大大方方在我們面前將作品取出,仔細懸掛回它原來的位置。眼前一亮,正是那幅《飼火鶴》。
當美學教育成為唯一目的的時候,美好與祥和的實現便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