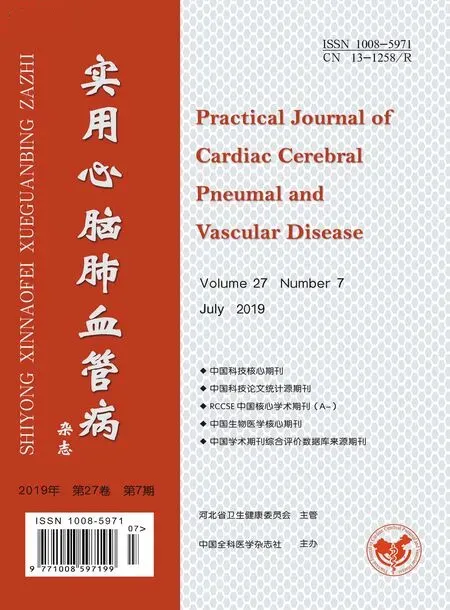不同模式間歇性充氣擠壓泵對腦卒中患者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預防效果的對比研究
周立紅,蘇丹,張倩
靜脈血栓栓塞癥(VTE)主要由深靜脈血栓形成(DVT)及肺栓塞(PE)引起的一組臨床綜合征[1]。由于DVT主要發生部位為下肢,故又稱為下肢DVT。DVT的年發生率約為1.0‰,復發率約為30%,是常見的心血管疾病之一,且位居在冠心病、高血壓之后,可嚴重影響患者生命質量及生存預期[2-4]。腦卒中常因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導致長期昏迷、肢體運動障礙而使患者長期臥床,極大地增加了DVT發生風險,且約10%腦卒中患者可因PE而死亡[5]。因此,預防腦卒中DVT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間歇性充氣擠壓泵(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IPC)的模式主要包括足底靜脈模式、小腿-足底靜脈模式、小腿靜脈模式及小腿-大腿靜脈模式。既往研究表明,使用小腿-大腿靜脈模式〔壓力為45 mm Hg(1 mm Hg=0.133 kPa)〕可預防髖關節置換術后DVT[6],但臨床實踐中發現該模式需要長時間使用IPC氣套,但其不透氣現象較為嚴重,尤其是氣溫較高、使用時間較長,導致下肢發熱、出汗,嚴重者可出現皮膚發癢、感染等并發癥[7]。小腿-足底靜脈模式可較好地解決小腿-大腿靜脈模式不透氣問題,但其能否預防腦卒中患者DVT目前尚未有研究報道。本研究旨在比較不同模式IPC對腦卒中患者下肢DVT的預防效果,為進一步降低腦卒中患者DVT發生風險提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2月—2018年6月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接受治療的腦卒中患者180例,均符合《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及臨床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1995)》[8]中的腦卒中診斷標準,并經影像學檢查確診[9]。納入標準:(1)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14分并伴有重度意識障礙(昏睡、最小意識狀態及昏迷)者;(2)發病3 d內入院治療者;(3)多普勒彩色超聲檢查結果顯示髂股靜脈、股總靜脈、腘靜脈、脛后靜脈、大隱靜脈、小隱靜脈及小腿肌肉靜脈叢等無血栓形成者。排除標準:(1)有PE者;(2)合并嚴重下肢動脈硬化、血栓性靜脈炎、缺血萎縮性血管疾病等下肢血管疾病者;(3)合并嚴重心、肝、腎功能障礙者;(4)合并惡性腫瘤者;(5)腿部大范圍水腫、嚴重畸形等下肢異常者;(6)對本研究所用設備不耐受及所用藥物過敏者;(7)治療期間死亡、轉院、出院、轉科導致臨床資料不全者;(8)家屬中途放棄參與本研究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所有患者分為對照組、A組、B組,每組60例。對照組患者中男31例,女29例;年齡38~76歲,平均年齡(57.1±11.9)歲;A組患者中男32例,女28例;年齡38~75歲,平均年齡(56.9±12.3)歲;B組患者中男30例,女30例;年齡39~79歲,平均年齡(56.6±12.0)歲。三組患者性別(χ2=0.133)、年齡(F=1.523)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所有患者及其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尿激酶、華法林、阿司匹林等常規藥物治療及并發癥護理、下肢護理、心理護理等常規護理措施。A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采用便攜式間歇充氣壓力治療儀SCD Express(美國OVIDIEN公司生產)治療,壓力模式為小腿-足底靜脈模式,足底壓力為130 mm Hg,小腿壓力為45 mm Hg,小腿充氣11 s,足底充氣5 s。B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采用便攜式間歇充氣壓力治療儀SCD Express治療,壓力模式為小腿-大腿靜脈模式,壓力為45 mm Hg,充氣11 s。三組患者均連續干預14 d。
1.3 觀察指標
1.3.1 下肢DVT發生率及其發生時間 所有患者采用便攜式二維超聲儀,Micro Turbo HFL38x,美國Sonosite公司生產,監測髂股靜脈、股總靜脈、腘靜脈、脛后靜脈、大隱靜脈、小隱靜脈和小腿肌肉靜脈叢等血流通暢情況,并于干預后7、14 d進行雙下肢B超檢查,檢查方法:將多普勒系統預設參數中多普勒頻譜儀與血管壁夾角設定為45°,探頭頻率5 MHz,檢測時探頭與股總靜脈的夾角保持45°~60°,所有患者由同一人醫師操作。根據多普勒彩色超聲檢查記錄下肢DVT發生情況(包括左下肢、右下肢、雙下肢)及其發生時間。
1.3.2 血清D-二聚體水平 分別于干預前及干預后7、14 d抽取三組患者靜脈血5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管,3 000 r/min離心10 min(離心半徑15 cm),取上清液,采用酶聯免疫熒光法檢測血清D-二聚體水平。
1.3.3 皮膚并發癥 觀察三組患者治療期間下肢皮膚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發紅、皮癢、皮癬、壓瘡等。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分析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下肢DVT發生率 對照組患者下肢DVT發生率為28.3%(17/60),A組患者為10.0%(6/60),B組患者為15.0%(9/60)。三組患者下肢DVT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373,P=0.025);A組、B組患者下肢DVT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6.508、3.612,P<0.05)。三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情況見表1。

表1 三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情況〔n(%)〕Table 1 Incid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in the three groups
2.2 下肢DVT發生時間 對照組患者中17例下肢DVT發生時間為(3.9±1.0)d,A組患者中6例下肢DVT發生時間為(8.4±2.5)d,B組患者中9例下肢DVT發生時間為(5.7±1.9)d。三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64.25,P<0.01);A組、B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時間長于對照組,A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時間長于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血清D-二聚體水平 時間與方法在血清D-二聚體水平上存在交互作用(P<0.05);時間、方法在血清D-二聚體水平上主效應顯著(P<0.05)。干預后7 、14 d A組、B組患者血清D-二聚體水平低于對照組,A組患者血清D-二聚體水平低于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患者干預前及干預后7、14 d血清D-二聚體水平比較(x±s,mg/L)Table 2 Comparison of serum D-Dimer level in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7 and 14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2.4 皮膚并發癥發生情況 治療期間對照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為26.7%(16/60),A組患者為13.3%(8/60),B組患者為35.0%(21/60)。治療期間三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644,P=0.022);對照組、A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低于B組,A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三組患者治療期間皮膚并發癥發生情況〔n(%)〕Table 3 Incidence of cutaneous complications in the three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3 討論
DVT是一種靜脈內血凝塊堵塞性疾病,可發生于人體任何部位,以下肢最為多見,其發病機制可能與血管內膜損傷、血流速度緩滯、血液高凝狀態等有關[10-12],而具備上述3項中任意一項及以上特征人群被臨床定義為DVT高危人群。急性期DVT常合并PE、“股青腫”和“股白腫”等,診療不及時可導致截肢或死亡等一系列嚴重不良后果,嚴重影響患者工作及生活質量。既往研究表明,重癥腦血管疾病患者DVT的發生風險高于其他人群,且復發率較高[13]。
目前,DVT的預防方法主要是圍繞發病機制的三大原因開展,包括藥物和物理方法,其中藥物是通過直接使用藥物來快速改變血液高凝狀態,從而達到預防效果,但抗凝藥物常具有較多絕對或相對禁忌證(如有活動性出血及凝血障礙、骨筋膜間室綜合征、嚴重顱腦創傷或急性脊髓損傷、既往顱內出血、既往胃腸道出血、急性顱內損傷或腫物、血小板計數降低等)和藥物不良反應;目前臨床上采用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預防DVT,但需要反復注射,易引發出血,需定期監測凝血時間,且藥物價格昂貴,故限制其臨床應用。物理方法主要通過利用機械外力對肢體形成擠壓、按摩效果,增強靜脈泵,加快靜脈血液流動速度,減輕靜脈血液淤積,從而達到預防DVT的目的。氣壓泵就是利用擠壓原理來預防DVT發生,臨床實踐效果較好[14]。
本研究結果顯示,A組、B組患者下肢DVT發生率低于對照組,下肢DVT發生時間長于對照組,且A組患者下肢DVT發生時間長于B組;治療7、14 d A組、B組患者血清D-二聚體水平低于對照組,A組患者血清D-二聚體水平低于B組;治療期間,對照組、A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低于B組,A組患者皮膚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分析其機制可能如下:(1)為防止腦卒中患者再次發生出血,臨床上通常要求患者臥床休息,嚴重者甚至喪失走動能力,導致足底壓力缺失,容易產生下肢血液淤滯。小腿-足底靜脈模式為長期臥床腦卒中患者提供了與自然行走時的同等足底壓力,促使機體足底靜脈叢血液回流,緩解血液淤滯現象。(2)小腿-足底靜脈模式的足底壓力為130 mm Hg,高于小腿壓力的45 mm Hg,呈階梯式壓力,可最大限度地促進雙下肢血液回流,改善血液循環,有效預防凝血因子聚集及黏附血管內膜。(3)D-二聚體是不可溶纖維蛋白裂解后交聯形成的產物,當機體處于高凝狀態時,凝血酶會催化水解纖維蛋白原釋放大量纖維蛋白肽鏈,同時形成大量可溶性纖維蛋白單體,這些單體經纖溶酶水解及活化因子ⅩⅢ交聯后形成D-二聚體,因此在腦卒中患者中D-二聚體呈高表達[15]。此外臨床上也常用D-二聚體水平反映機體血液凝集狀態[16]。而小腿-足底靜脈模式可有效改善腦卒中患者雙下肢血液循環,降低高凝狀態及血清D-二聚體水平,進而降低DVT發生風險。(4)小腿-足底靜脈模式給予的外在壓力可有效抑制腦卒中患者深靜脈擴張,從而對靜脈內膜起到一定保護作用。(5)小腿-大腿靜脈模式因加壓小腿和大腿部位的壓力相似,且部分患者自身靜脈回流壓力小于小腿-大腿靜脈模式壓力,導致血液流向足底靜脈叢,不能發揮出雙下肢血液循環作用,故其在預防DVT效果不及小腿-足底靜脈模式。(6)小腿-足底靜脈模式使用過程中主要接觸腦卒中患者小腿和足底皮膚,這些部位因平時外露或曝光時間長于大腿部位,其耐磨性及抗壓性高于大腿部位,因此可較長時間耐受IPC帶來的不透氣,減少并發癥發生風險。(7)有效的血液循環可降低皮膚并發癥發生風險,因長期血液淤積、血流不暢易導致皮膚缺血缺氧、壞死及壓瘡[17]。
綜上所述,與IPC中的小腿-大腿靜脈模式相比,小腿-足底靜脈模式可更有效地改善腦卒中患者下肢血液循環及高凝狀態,有效預防下肢DVT的發生及延長下肢DVT發生時間,減少皮膚并發癥的發生,值得臨床推廣應用;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小,今后仍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聯合多中心以證實研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