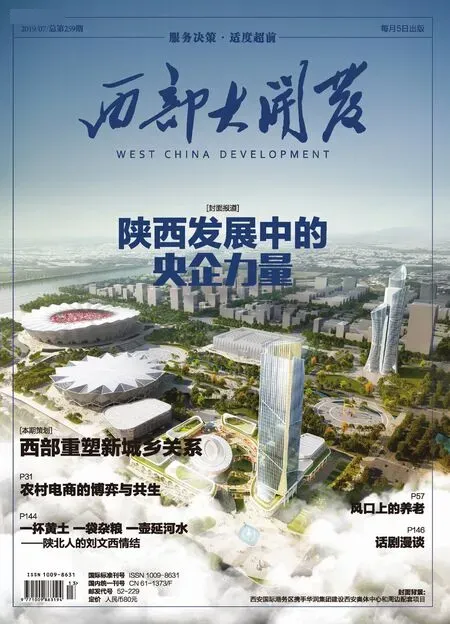雷珍民:水滴石穿寫清逸
文 / 本刊記者 張義學 李斌
窗外細雨斜織,淅淅瀝瀝;室內一壺普洱,暗香浮動。端午前夕,正是煮茶論道的好時節,我們享受著這份溫馨和愜意,聽雷珍民娓娓地講述童年軼事。雷珍民是著名書法家,2006年起擔任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在全國書法界威望很高,德藝雙馨。
“解放前,我出生在陜西省合陽縣的一個平凡而普通的村莊,祖父是當地很有名氣的進步鄉紳。家境在當時來說,是很富足,也可謂‘書香門第’了。祖父供養父親讀了黃埔軍校,父子倆人都寫的一手好字。我父親黃埔軍校畢業后,就回到家鄉。明面上是國民黨合陽縣黨部的主要領導,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為八路軍、解放軍做過很多事……”雷珍民老先生一邊給記者們斟茶,一邊講述自身經歷。“我的青少年時代卻是一路坎坷,命運多舛。1951年‘鎮反’時,我的父親被冤殺了。當時,合陽縣上下沒人能證明他是中共黨員,此后很多年,也沒法證明。失去父親的時候,我只有6歲。從此就和母親相依為命、艱難度日了。”
雷珍民剛一開始講述,就讓我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半空中。
雖然世事變化,人生多舛,祖父對于雷珍民的啟蒙教育卻絲毫沒有耽誤。“4歲時,祖父就開始指導我習字、臨帖。那個年代,小學、初中娃娃都是用毛筆寫字、做功課,就看誰寫得工整,寫得認真,寫得好……”雷珍民娓娓講述著,“可惜,初中上完我就不得不輟學回家。”
少年坎坷志不移,贏得“雷工”美譽
此后多年,雷珍民就游走在務農勞動與文化工作之間,一段時間進城工作,一段時間被迫回鄉務農,多次反復,極不穩定。但是,不管生活如何艱辛,他依然堅持臨帖習字。隨后,命運的多次轉機,還是得益于他有一手好字。
“‘文革’前,我在合陽縣文化館有過短暫的工作經歷,沒干多久就辭職回鄉了。‘文革’初期,合陽縣修水庫,村上派我去勞動。勞動間隙,我經常主動為水庫建設指揮部寫宣傳標語,刻印毛主席像章,開展文化宣傳工作。”雷珍民回憶年輕時的勞動情況,不禁感慨地說,“那時候,雖然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但年輕人樂觀向上,積極追求進步,不論在啥單位都爭著搶著干工作,體力勞動也不偷奸耍滑。”
就在建設水庫期間,47軍的一位副軍長前來合陽調研。這位副軍長姓白,看到宣傳標語上的字跡,很是喜歡。當他了解到這些字跡出自年輕的雷珍民的時候,一股強烈的愛惜人才之情油然而生。他一方面動員雷珍民參軍,一方面向合陽縣革委會領導“要人”。經過一番動員和交涉,雷珍民參加了解放軍,并在47軍軍部鍛煉了5年時間。1974年,他退伍回到家鄉,1979年落實政策,他成為合陽縣黑池鄉文化站的文化干事。1980年,他又因某種機緣被調到西安人民大廈做“美工”。這期間,雖然工作多次變動,但他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天天堅持臨帖,堅持練字,甚至堅持畫畫。好運的橄欖枝,又一次不知不覺地向雷珍民伸了過來,他的人生又將迎來一次轉機。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文化底蘊深厚,這讓酷愛傳統文化的雷珍民飽受熏陶。西安人民大廈是陜西省委、省政府最重要的貴賓接待場所,國內外許多重要的高官政要、文化名家,也不時下榻于此。
1982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來西安參加鳩摩羅什雕像落成安奉儀式,下榻在西安人民大廈。時任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連璧陪同趙樸初前往“鳳凰廳”用餐,剛步入大廳,趙樸初抬頭看見“鳳凰廳”三字,不禁駐足感嘆:“這是哪位老先生題的!”他指著“鳳凰廳”三個字對李連璧說,“雖然字寫得規矩了一些,沒放開,但能寫這樣的字,很少見。此字有功力,能守住傳統,不易呀!”當時,西安人民大廈滿紅光經理對趙樸初解釋說,“寫這字的人不是老先生,而是30多歲的年輕人!”趙樸初高興地說:“哦,是年輕人?能否請來見一面?”
“那天,我正患重感冒呢。聽到趙老要見我,心里既激動,又有許多忐忑。被同事拽下床,臨時借了一件軍大衣批上,就趕了過去。”雷珍民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趙老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交談中,滿是欣賞和鼓勵。趙老當時說,‘你年紀不大,但是書法功力不錯。學書法,你從楷書入手就走對啦,只要發揚水滴石穿的精神,好好練,好好寫,再過二十年,中國書壇也會有你的一席之地的’。”
當時,作為“美工”的雷珍民除了書法之外,也學繪畫。聽到德高望重的書法大家趙樸初老先生這樣的鼓勵,心里美滋滋的。交談中,趙樸初還建議他放棄繪畫,專心一意攻書法。得到趙老的點撥,雷珍民茅塞頓開,從此更加專心用功于書法。并且很多次專程去北京,向趙樸初請教,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上世紀整個八九十年代,雷珍民的工作生活也日益穩定,裝潢事業步入發展快車道,單位同事和熟悉他的人,都親切地稱呼他為“雷工”。這期間,他的書法藝術更是不斷精進。

領導“書協”入正軌,尊師重道揚正氣
在文化藝術界聲望日益高漲的雷珍民調入陜西省國畫院,成為主管“三產”的院務委員。不久后升任副院長,再后來全面主持陜西省國畫院工作。2004年,雷珍民當選為陜西省文聯副主席,2006年6月,又當選為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
雷珍民當選陜西省書協主席之時,陜西省書協主席職位已經空缺很多年。書協缺乏得力的領軍人物,內部機構不健全,書法家隊伍也很渙散,派別林立,混亂一團。雷珍民的當選,社會各界普遍寄予厚望,盼望他能帶領陜西書法家在全國書壇贏得一個文化大省應有的席位。
“在省書協主席任上,我主要走了三大步:整合、傳承、學習。”雷珍民回味了一會兒,才向本刊記者介紹道,“第一步,整合——團結協調各派別,平掉了一些‘小山頭’,共成立了11個專門委員會,健全了書協內部的機構(特別是成立了書法家維權委員會,第一件案例就是為著名書法家茹桂打‘華山’題匾的官司。這也為全國各省書協、美協開創了先河;并且跑遍了陜南、陜北和關中,為全省十個市搭建或完善了市級書法家協會組織,使書協的觸角真正地延伸到基層。第二步,傳承——首先為葉農、曹伯庸、霍松林和邱星四位德藝雙馨的老書法藝術家辦書法展覽,引導全省學書之人學習老一輩藝術家的書法藝術,學習老先生們的高尚品德,學習他們的敬業精神;努力普及書法教育,推進‘書法進校園’。第三步,學習——加強主席團領導班子成員的業務學習,統一思想,提高服務意識;堅持開展書法骨干會員的培訓提高工作,整體提高會員們的書法水平;積極推薦優秀書法家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使陜西省的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從不足百人提升到300多人。”
雷珍民輕描淡寫地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他主持陜西省書協的一些基本工作情況。這些基礎性工作,把停滯已久的書協拉回到為書法家服務的正軌,給堅守墨池者帶來了希望。
本刊記者進一步了解到,在雷珍民的主持下,2007年陜西成功舉辦了第一屆全省書法臨帖展,這在全國尚屬首次。2008年又成功舉辦了書法家自作詩文書法展。隨后,此兩展成為陜西書法展的“常規動作”,每年一展,循環舉辦,為陜西書法弘揚了傳統風氣,遏制了“江湖書法”風氣的蔓延勢頭。2006-2012年中,陜西書法活動蓬勃開展,隊伍由門派林立、散兵游勇向團隊整合,先后搞了三屆全省書法臨帖展及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建黨90周年、迎接黨的十八大等書法展覽。這6年中,共搞大型書法展40個,舉辦書法報告會10多次,使陜西省的書法水平大大提高,優秀傳統文化得到極大弘揚。
中國書壇有一席,人人敬稱“雷公”
2013年,年近古稀的雷珍民卸下了眾多社會職務,推掉了許多社會活動,深居簡出,遠離喧囂,開始潛心創作《雷珍民書古文經典》,這是一項浩瀚的文化工程。
“我靜心抄寫古文經典、名家評傳,目標是完成100本手稿的創作和出版。這100本手稿,古書占一半,自書占一半;楷書手稿占一半,行書手稿占一半。目前,已經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手稿有86本,離目標的完成不遠了。”雷珍民告訴本刊記者,“因為是自己選擇的、想要做的,所以即使累也覺得很快樂。”
在短短的兩小時采訪過程中,雷珍民的書齋來了兩撥求字題匾者。第一撥是臨潼的一個書畫家,請“雷公”為他們的書畫院題塊牌匾。雷珍民起身向本刊記者致歉說,“咱不能讓遠道而來的客人等太久了……”題寫完畢,又和藹地送走客人,接著和本刊記者攀談起來。第二撥,看起來是求字的遠方親戚吧,也正是我們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雷珍民又親切地帶領著“親戚”和本刊記者一起參觀了他的展室,展室內有剛剛捐給合陽博物館作品的復印件,也有他創作的古文經典。
70年來,雷珍民對于墨池的堅守,對于硯臺的鐘愛,勤奮地不輟練筆,正如當年趙樸初老先生預言的那樣,在中國書壇贏得一席之地。對于書法藝術的癡迷之外,他對于書法家呵護之意,對于書法愛好者的提攜之舉,溫文爾雅,和善可親,也為他贏來了“雷公”的敬稱。
近幾年秋冬季節,70多歲高齡的雷珍民在海南三亞的書齋中,每天都會創作10多個小時,爭分奪秒,堅持不懈。數十萬字的《雷珍民書古文經典》既有對先賢的敬畏和尊重,又表現出書法家的淹雅和獨立。雷珍民告訴本刊記者:“我潛心抄寫經典的過程,也就是自己在不斷學習、不斷反省的過程,我自己在學習中,使得自己的靈魂能得到進一步的凈化。”
墨跡淡遠,秀韻入骨;優雅含蓄,暗香浮動。在向往古典、學習古典的漫漫歲月中,呈現出雷珍民關于藝術、人生的深沉思考和書法張力,流露出書法家特有的清逸風懷和細致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