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gè)數(shù)學(xué)家的成長史
編譯 許林玉
1940年,當(dāng)不列顛之戰(zhàn)在上空肆虐時(shí),英國數(shù)學(xué)家哈代(G.H.Hardy)發(fā)表了一篇名為“一個(gè)數(shù)學(xué)家的辯白”的文章。如今,這篇文章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它簡(jiǎn)短而有力地對(duì)數(shù)學(xué)家的戰(zhàn)壕式生活進(jìn)行了辯白。這位63歲的著名數(shù)論學(xué)家和分析學(xué)家表示:“對(duì)于一位職業(yè)數(shù)學(xué)家來說,發(fā)現(xiàn)自己在寫關(guān)于數(shù)學(xué)的事情是令人沮喪的。數(shù)學(xué)家的本職工作是要做出實(shí)績(jī),證明新的定理,推動(dòng)數(shù)學(xué)的發(fā)展,而不是談?wù)撍蚴瞧渌麛?shù)學(xué)家已有的成就。”近一個(gè)世紀(jì)后,關(guān)于現(xiàn)代數(shù)學(xué)家生活的書籍寥寥無幾,這表明大多數(shù)數(shù)學(xué)家們?nèi)匀毁澩系挠^點(diǎn),他們更愿意通過方程式,而非文字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歷史學(xué)家和其他學(xué)者會(huì)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回憶錄、自傳、日記、有意義的通信或口述歷史,我們將很難再現(xiàn)數(shù)學(xué)家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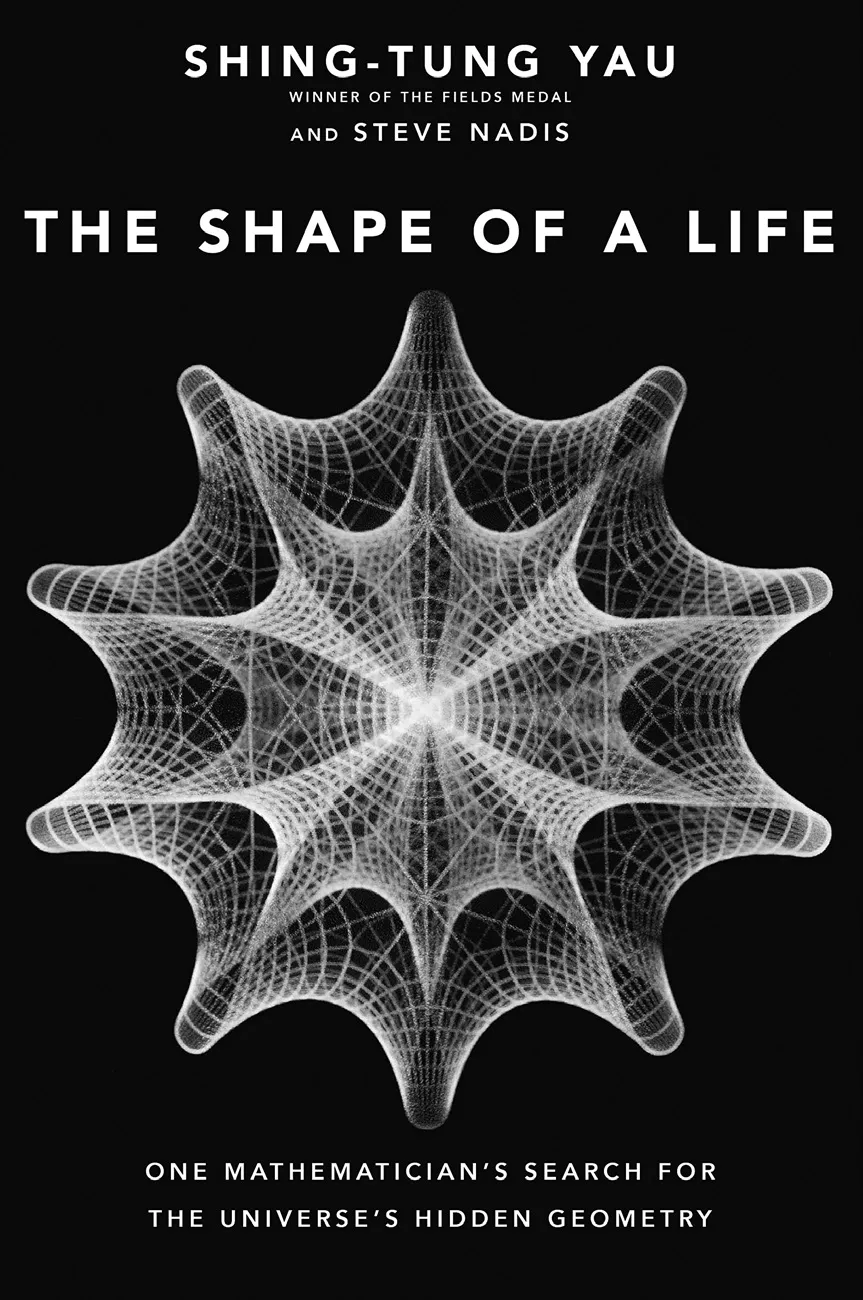
《生命的形狀:一位數(shù)學(xué)家對(duì)宇宙隱藏幾何學(xué)的探索》(耶魯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作者丘成桐、史蒂夫·納迪斯
哈佛大學(xué)幾何學(xué)家、美國國家科學(xué)獎(jiǎng)?wù)潞头茽柶潽?jiǎng)得主丘成桐的自傳《生命的形狀:一位數(shù)學(xué)家對(duì)宇宙隱藏幾何學(xué)的探索》(The Shape of a Life: One Mathematician's Search for the Universe's Hidden Geometry)則是一個(gè)廣為人知的反例。1977年,丘成桐發(fā)表了關(guān)于卡拉比猜想的證明,成為國際數(shù)學(xué)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卡拉比猜想在20年前由美籍意大利數(shù)學(xué)家歐金尼奧·卡拉比(Eugenio Calabi)提出。他相信,這樣的故事會(huì)讓某些讀者產(chǎn)生興趣。丘成桐在書中寫道:“于我而言,數(shù)學(xué)就是一本通用護(hù)照,讓我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與此同時(shí),我也利用數(shù)學(xué)強(qiáng)大的工具來了解世界。”
鑒于該書使用第一人稱單數(shù)進(jìn)行敘述,了解該書的合著者史蒂夫·納迪斯(Steve Nadis)在幫助描述丘成桐的個(gè)人經(jīng)歷和職業(yè)生涯方面發(fā)揮了什么作用,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作為功成名就的科學(xué)作家,納迪斯曾帶著錄音機(jī)坐下來采訪過丘成桐嗎?這兩個(gè)人是否積極地共同構(gòu)思了這本書?對(duì)此,書中幾乎未費(fèi)筆墨。當(dāng)丘成桐講到他與后來成為他愛人的物理學(xué)研究生的五年異地戀情時(shí),他承認(rèn),在他的工作領(lǐng)域里,人們?cè)跀?shù)字方面通常比語言方面更熟練。這一說法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更多關(guān)于這個(gè)引人入勝、可讀性強(qiáng)的故事是如何組合起來的細(xì)節(jié)。
《生命的形狀》詳細(xì)介紹了丘成桐及其數(shù)學(xué)成就、知識(shí)、所處的文化氛圍和政治環(huán)境。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廣東汕頭,在他出生后的6個(gè)月,他和父母移居香港。書的開頭幾章講述了丘成桐在中國大陸以及后來在香港的貧困童年,他生動(dòng)地再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和當(dāng)時(shí)的環(huán)境:擁擠的公寓樓里沒有電和自來水,沒有錢買食物,違反學(xué)校著裝規(guī)范的行為會(huì)受到懲罰。
1969年,丘成桐以數(shù)學(xué)研究生的身份進(jìn)入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此時(shí)正值該大學(xué)掀起抗議越南戰(zhàn)爭(zhēng)的高潮。在那里,他發(fā)現(xiàn)自己對(duì)數(shù)學(xué)的興趣主要轉(zhuǎn)向了幾何學(xué)和非線性偏微分方程。他這樣寫道:“在我的腦海中產(chǎn)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覺得可以用偏微分方程作為連接線,將幾何學(xué)和拓?fù)鋵W(xué)聯(lián)系起來。”1970年,丘成桐參加了一些有關(guān)廣義相對(duì)論的講座,第一次對(duì)愛因斯坦方程式中的核心術(shù)語里奇曲率張量有了了解,這是以意大利數(shù)學(xué)家格雷戈里奧·里奇-柯巴斯特羅(Gregorio Ricci-Curbastro)的名字命名的張量(里奇-柯巴斯特羅于1904年將其張量應(yīng)用于研究高維空間中曲率的局部分布,并從幾何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了闡釋)。丘成桐回憶說:“正是對(duì)里奇曲率的興趣,直接讓我產(chǎn)生了對(duì)卡拉比猜想的興趣,這既是因?yàn)樗旧恚彩且驗(yàn)樗c廣義相對(duì)論相關(guān)。”他確信,無論卡拉比猜想正確與否,都是理解里奇曲率的關(guān)鍵。他很快就沉迷于卡拉比猜想——他在這件事上表現(xiàn)出來的情緒化本能反應(yīng),連他自己也無法完全理解。
丘成桐解釋說:“這個(gè)猜想適用于具有特殊幾何形狀的空間。卡拉比曾提出一種系統(tǒng)的策略,來構(gòu)造大量具有特殊幾何性質(zhì)的流形。”但是,包括丘成桐在內(nèi),沒有一個(gè)人見過這樣的流形。

圖片選自《生命的形狀:一位數(shù)學(xué)家對(duì)宇宙隱藏幾何學(xué)的探索》一書,左為卡拉比,右為丘成桐
從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到普林斯頓大學(xué)高級(jí)研究所,再到紐約州立大學(xué)石溪分校、斯坦福大學(xué)和紐約大學(xué)古蘭特研究所,最后到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丘成桐一直全神貫注地投入到這個(gè)猜想中。在六年多的時(shí)間里,他一直斷斷續(xù)續(xù)地研究該問題,有時(shí)甚至到了體力透支的地步。1976年,他最終在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證明了卡拉比猜想。而在幾年前,他還曾錯(cuò)誤地認(rèn)為自己推翻了這個(gè)猜想,這段經(jīng)歷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當(dāng)回憶起自己在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反復(fù)研究自己的新證明時(shí),他寫道:“我告訴自己,如果這次算錯(cuò)了,我就將徹底放棄數(shù)學(xué),去嘗試一些不同的東西,甚至可能去養(yǎng)鴨子。”(他的一位叔叔曾主動(dòng)提出幫助他做這件事。)
此外,丘成桐還將證明過程的復(fù)印件寄給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的卡拉比,并在第二年的《美國國家科學(xué)院院刊》上發(fā)表了一個(gè)簡(jiǎn)短的總結(jié)。1982年,丘成桐憑借此項(xiàng)工作獲得了數(shù)學(xué)界的諾貝爾獎(jiǎng)——菲爾茲獎(jiǎng)。
書中還詳細(xì)介紹了一些其他主題,包括丘成桐在幾何分析方面的工作以及他與研究相對(duì)論的物理學(xué)家之間的協(xié)作。幾何分析是他幫助建立起來的一個(gè)新的數(shù)學(xué)分支,與卡拉比猜想證明息息相關(guān)。這本書的12章內(nèi)容還包括:丘成桐關(guān)于正質(zhì)量猜想的工作、發(fā)現(xiàn)“里奇流”并證明龐加萊猜想是一個(gè)特例的數(shù)學(xué)家理查德·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的故事,以及里奇-丘流形在弦論中的核心作用(旨在將引力和量子理論統(tǒng)一起來)。
對(duì)于那些喜歡淺顯易懂且基本上不涉及專業(yè)術(shù)語的數(shù)學(xué)解釋的人來說,《生命的形狀》一書可以讓他們聚精會(huì)神地讀上數(shù)小時(shí)。讀者可能還會(huì)喜歡丘成桐對(duì)學(xué)術(shù)政治的生動(dòng)描述,包括他與美國和中國同事之間的激烈爭(zhēng)吵。丘成桐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在中國還有多個(gè)項(xiàng)目正在進(jìn)行之中。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在這兩個(gè)國家都從未感到很自在。他對(duì)自己深處于數(shù)學(xué)這個(gè)自然家庭中的描述以及他對(duì)自然深層真相的探索,都證明《生命的形狀》是一部?jī)?yōu)秀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