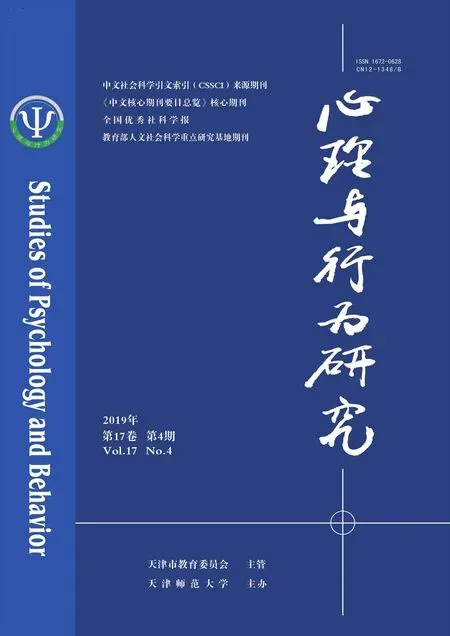大學生生命意義感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
張秀閣 秦 婕 黃文玉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國民心理健康評估與促進協同創新中心,天津 300387)
1 引言
生命的意義感(meaning in life),指的是個體積極尋找意義并發現自己的生活有多大意義的程度(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 Kiang &Witkow, 2015)。Steger 等人(2006)認為,生命意義感包括兩個方面:意義存在(presence of meaning)和意義追尋(search for meaning)。其中,意義存在指的是個體是否認為自己的生命是重要的、有目的的和有價值的;意義追尋指的是個體努力理解自己生活的意義和目的的力量、強度以及活動性。很多關于生命意義感的研究采納了S t e g e r 等(2 0 0 6)所確定的定義和構念(Heintzelman & King, 2016; Kiang & Witkow, 2015;Waytz, Hershfield, & Tamir., 2015)。
手機成癮傾向指的是由于某種原因過度地濫用手機而導致手機使用者出現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適應的一種病癥(韓登亮, 齊志斐, 2005)。手機成癮傾向會給大學生帶來了諸多負面后果,比如述情障礙(侯日瑩, 楊蕊, 胡潔蔓, 姜博, 2016)、睡眠質量不良以及孤獨感(李麗, 梅松麗, 牛志民, 宋玉婷, 2016)等負性情緒。近年來,隨著對手機成癮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發現生命意義感與成癮傾向或成癮行為關系密切。比如,生命意義感與藥物濫用(Ery?lmaz, 2014)、酗酒(Thurang &Bengtsson Tops, 2013)、網絡成癮(Zhang et al.,2015)、鎮靜劑使用(Koushede & Holstein, 2009)以及吸煙(Konkol? Thege, Urbán, & Kopp, 2013)負相關。從生命意義感的功能來看,它是個體幸福生活必備的元素。生命意義感低的個體缺乏內在的生活目標與追求生命意義的動力,生活空虛且沒有價值感,容易用成癮活動來填補空白,從而形成成癮傾向和行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討生命意義感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從而為手機成癮傾向的防治提供理論依據。
自我控制指的是超越或改變一個人的內在反應的能力,包括有意識地打斷思維流、改變情緒、抑制不受歡迎的沖動和沖動行為的能力(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提高自我控制是生命意義感的功能之一(K e s e b i r &Pyszczynski, 2014),生命意義感促使個體調節自己的行為和情感模式。一個缺乏生命意義感的人,自我控制水平低下,其行為只能建立在沖動和本能的基礎之上。Hedlund(1977)指出,生命的意義是個人存在的基礎,生命意義感強烈的個體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的,這樣的人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他們會調控自己的行為,有動機去認真做事,使之與自己生命目標一致。所以,這樣的人具有較強的自我控制能力。實證研究也發現,生命意義感對自我控制具有積極地預測作用(Kim & Kang, 2012)。
自我控制對一些積極行為具有正向預測作用,比如學術成就(Duckworth & Kern, 2011)、利他行為(Wills, Duhamel, & Vaccaro, 1995)以及社會責任感(羅蕾, 明樺, 田園, 夏小慶, 黃四林,2018)等。自我控制對一些消極行為具有負向預測作用,比如手機成癮(周紅燕, 2017)、游戲成癮(Kim & Kang, 2012)等。Hofmann,Friese 和Strack (2009)提出的自我控制雙系統模型(dualsystems model of self-control)包括兩個系統:沖動系統和自我控制系統。沖動系統鼓勵滿足個體自身欲望的沖動行為,激發對誘惑刺激的正向評價;面對誘惑時,自我控制系統則引導個體進行深思熟慮的評價和抑制標準(Strack & Deutsch,2004),進而采取理性行動,自我控制系統具有抑制心理和行為上沖動性反應的能力。這兩個系統受到一些狀態或者特質變量的調節。兩個系統的力量的對比決定著個體最終采取什么樣的行為。
通過整理實證研究的文獻可以發現,生命意義感對成癮行為或傾向具有預測作用,對自我控制具有預測作用;自我控制對于成癮行為或傾向也具有預測作用,這樣的研究結果,符合自我控制可能對生命意義感與成癮行為或傾向的關系具有中介作用的范式(溫忠麟, 劉紅云, 侯杰泰, 2012)。在理論方面,Mackenzie 和Baumeister(2014)指出,個體的自我控制受其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生命意義感能夠使個體參照其所在的文化標準來確立自己的長期目標,在此基礎上,個體通過加強自我控制,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進而實現其長期目標。Kim 和Kang(2012)在韓國被試中研究發現,自我控制對生命意義感與游戲成癮的關系具有中介作用。但手機成癮傾向與游戲成癮雖然具有成癮傾向的共性,但二者的區別顯著,一方面,手機成癮傾向并未達到“成癮行為所致障礙”的診斷標準(ICD-11),它只是一種傾向而已;另一方面,引發手機成癮傾向的偏好內容不只是單純的游戲,還包括信息查詢、聊天、刷微博、購物、各種APP 的使用等方面的內容。基于此,本研究將以我國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自我控制是否對生命意義感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為大二和大三的大學生,發放問卷204 份,收回有效問卷202 份。在有效被試中,男生33 名,女生169 名;大二學生140 名,大三學生61 名,其中1 人的年級信息不詳;出生地為城鎮的學生96 名,農村學生106 名;被試年齡的平均值為20.43 歲,標準差為0.94。
2.2 研究工具
2.2.1 人生意義感問卷
《人生意義感問卷》(MLQ)由Steger 等人2006 年編制,包括10 個項目,采用7 級計分。量表包括“意義存在”(MLQ-Presence)和“意義追尋”(MLQ-Search)兩個維度,分別用于測量個體人生意義感的存在水平和尋求程度。王孟成和戴曉陽(2008)探討了中文人生意義感問卷(CMLQ)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中的適用性。研究表明,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兩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5 和0.82,兩個維度間隔2 周的重測相關系數分別為0.74 和0.76。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均表明該問卷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該問卷還具有較好的聚合效度與區分效度。受測者得分越高,其生命意義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意義存在與意義追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為0.858。
2.2.2 大學生自我控制量表
《大學生自我控制量表》由Tangney 等2004年發表,在美國具有較好的信、效度。量表包括5 個維度:沖動控制、健康習慣、抵御誘惑、專注工作和節制娛樂。譚樹華和郭永玉(2008)以799 名大學生為被試對量表進行了信、效度檢驗。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62,重測信度為0.850。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該量表的五因素結構擬合較好。以被試的人際關系滿意感、心理健康水平、生活滿意感以及平均學分為效標,與該量表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80、0.317、0.163、0.146,驗證了該量表的效標效度。量表包括19 個項目,5 級評分。為了被試更精細地表達自己的判斷,本研究采用7 級計分,受測者得分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差。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41,分量表沖動控制、健康習慣、抵御誘惑、專注工作和節制娛樂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78、0.748、0.792、0.722 和0.767。
2.2.3 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量表
《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量表》由熊婕、周宗奎、陳武、游志麒和翟紫艷(2012)編制,包括16 個項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獲得4 個因素: 戒斷癥狀、突顯行為、心境改變和社交撫慰,累積方差貢獻率為54.3%。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3,4 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在0.5 5-0.80 之間;總量表和分量表的重測信度在0.75-0.91 之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四因素模型擬合良好。為了被試更精細地表達自己的判斷,本研究采用7 級計分,受測者得分越高,手機成癮傾向越嚴重。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64,分量表戒斷癥狀、突顯行為、社交撫慰和心境改變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88、0.779、0.806 和0.766。
數據處理采用社會科學統計軟件包SPSS17.0和Amos17.0 進行。
3 研究結果
3.1 大學生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的描述統計
對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量表的各個維度均分以及三個量表的總均分,分別計算了它們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見表1)。

表 1 大學生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均分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維度均分以及量表總均分在5.12-5.21 之間;手機成癮傾向各維度均分以及量表總均分在3.18-3.87 之間;自我控制各維度均分以及量表總均分在3.42-4.28 之間。
獨立樣本t 檢驗的結果表明,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總均分不存在年級差異,p 值在0.22-0.50 之間;不存在性別差異,p 值在0.06-0.95 之間;不存在生源地差異,p 值在0.51-0.88 之間。
3.2 大學生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的相關關系
有研究發現,意義存在具有積極的心理健康意義,比如,意義存在與主觀幸福感、積極情感、職業或學習適應等呈正相關(Damon, 2009;Kiang & Fuligni, 2010; Zika & Chamberlain, 1992;Kiang & Witkow, 2015),并且,意義存在與幸福感的關系具有跨時間的穩定性(Steger, Oishi, &Kashdan, 2009)。而意義追尋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卻比較復雜,一方面,Steger 等人(200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意義追尋是有益的。Frankl(1963)也指出,人類的特點就是尋求意義,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動力,這種動力對人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會使人陷入心理痛苦;但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意義追尋與低自尊、低情緒穩定性、負面情緒呈正相關(Kiang & Fuligni, 2010;Steger, Kawabata, Shimai, & Otake, 2008)。在理論方面也有這樣的觀點,例如,Erikson(1968) 指出,個體在追求自我同一性和生命意義的過程中,內心可能充滿混亂和不安;Marcia(1966)用“暫停”(Moratorium)描述那些正在進行意義追尋的個體的特征,認為這樣的人處于危機之中,并受困于內部斗爭。通過文獻回顧發現,生命意義感的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兩個維度與身心健康指標具有不同的關系模式,所以,在分析生命意義感與自我控制以及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時,不以生命意義感總分的方式進行,而是分別分析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兩個維度與自我控制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意義存在與意義追尋相關不顯著;意義存在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負相關;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正相關;自我控制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正相關(見表2)。注:*p<0.05,**p<0.01。

表 2 大學生的意義存在、意義追尋、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的相關(r)
3.3 自我控制對生命意義感與手機成癮傾向關系的中介效應
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中介效應需要建立兩個模型(溫忠麟等, 2012)。為了檢驗自我控制對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的預測作用的中介效應,本研究建立了圖1 和圖2 中的模型。
圖1 的模型檢驗的是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是否具有直接效應。檢驗結果表明該模型的擬合指數符合要求(見表3)。并且,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效應均顯著,直接效應路徑系數分別為-0.30(p<0.001)和0.25(p=0.002)。
圖2 的模型檢驗的是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是否具有間接效應,也就是自我控制對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傾向關系的中介效應。經過檢驗,該模型擬合結果符合要求(見表4)。
在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模型(圖2)中,意義存在對手機成癮傾向影響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04(p=0.717),路徑系數不顯著,說明自我控制對意義存在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影響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16(p=0.044),路徑系數顯著,但與圖1中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路徑系數(0.25)相比顯著降低,所以,自我控制對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控制對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關系的中介效應為9%(0.20×0.47),占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總預測效應的36.00%(0.09/0.25)。

表 3 意義存在與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直接效應模型的擬合指數

表 4 自我控制中介效應模型的擬合指數
同時,根據甘怡群(2014)的建議,本研究利用統計軟件SPSS 的插件PROCESS 2.16.3,采用Preacher 和Hayes(2004)的Bootstrap 方法,檢驗了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是否顯著,Bootstrap 方法不要求中介效應量的數據服從正態分布。設定隨機抽樣5000 次,選擇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法進行取樣,并設置置信區間的置信度為95%。在意義存在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中,自我控制中介效應的區間(LLCI=0.2664, ULCI=0.5473)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在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中,自我控制中介效應的區間(LLCI=0.2845,ULCI=0.5377)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
4 分析與討論
4.1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水平的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量表,均采用7 級計分。表1 的結果表明,在大學生的自我認知中,其生命意義感在中上等水平(平均分在5.12-5.21 之間),手機成癮傾向在中下等水平(平均分在3.1 8-3.8 7 之間),自我控制在中等水平(平均分在3.4 2-4.28 之間)。
4.2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傾向以及自我控制相關結果的分析
在本研究中,意義存在與意義追尋相關不顯著(r=0.018)(見表2),這與該量表編制時的結果(Steger et al., 2006)以及該量表中文修訂時的結果(劉思斯, 甘怡群, 2010)一致。已有研究表明,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不存在必然的聯系,例如,橫斷研究(Steger et al., 2008)和縱向研究(Kiang& Witkow, 2015)均發現意義追尋對意義存在沒有預測作用,反之亦然;意義追尋維度相對穩定,而意義存在維度逐年增加(Steger et al., 2009);Steger 等(2008)跨文化研究的結果顯示,美國人的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呈負相關,日本人則呈正相關。這表明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的關系受文化、年齡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導致了它們的關系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模式。
本研究發現,意義存在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負相關(見表2),意義存在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的水平越低。很多研究發現了意義存在對于成癮等偏差行為的積極意義。Ery?lmaz(2014)通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發現,與物質濫用者相比,非物質濫用者對自己的生活賦予更多意義,并且,非物質濫用者設置的長遠生活目標很多。Kleftaras 和Katsogianni(2012)研究發現,酒精依賴者在治療初期對生活各方面持消極態度,并感到生活空虛;隨著治療的進行,他們的意義存在水平增加。如果意義存在感較弱會導致無聊傾向增加(Melton & Schulenberg, 2007),進而用酒精或其他成癮行為填補空虛,提高了成癮等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比如吸煙(Konkol? Thege et al.,2013)。另外,意義存在感水平低的個體,關注的生活內容是具體的、是當下、眼前的(Vallacher &Wegner, 1985),在這種狀態下,當前的誘惑性刺激或沖動變得異常強烈(Vohs & Schmeichel,2003),容易沉迷于成癮等偏差行為而不能自拔。
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正相關(見表2),意義追尋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越嚴重。本研究中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有以下幾種可能的解釋:①與身份認同有關。Brassai, Piko 和Steger(2012)指出,意義追尋過程是青少年身份認同的啟動器。意義追尋伴隨著持續的評價過程,伴隨著身份認同,特別是在青春期階段。迷戀手機有可能被大學生評價為是有意義的、是自己身份的象征之一。所以,造成了青少年負面問題的根源是與身份認同相關的認知困擾或混淆,而不是意義追尋本身(Berman, Weems & Stickle,2006)。②與意義追尋的層次有關。Reker 和Wong(1988)認為,生命意義可以劃分為四個層次,從淺到深依次為:享樂和個人舒適、個人成長、服務他人和社會、自我超越的終極意義。有手機成癮傾向的大學生,其意義追尋的層次最低,即追求享樂和個人舒適,這個層次意義追尋的程度越高,手機成癮傾向越嚴重。
自我控制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正相關(見表2)。在本研究中,受測者的自我控制量表得分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差,所以,自我控制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正相關,意味著自我控制水平越高則手機成癮傾向水平越低。高水平自我控制的個體,能夠通過調整自己的思維、情緒和行為,從而更加適應生存環境,更好地學習、工作和生活。前人的研究也發現,自我控制水平越高,網絡成癮程度越低(聶衍剛, 竇凱, 王玉潔, 2013)、吸煙過失越少(Muraven, 2010)。任何行為的發生都受到動機的驅使,滿足著個體的某種心理需求。自我決定理論指出,個體能否健康發展有賴于環境能否滿足其三大基本心理需求:勝任、自主和歸屬。其中,勝任指的是個體在從事各種活動的時候體會到的勝任感;自主指的是個體能否根據自己的意愿進行選擇;歸屬指的是個體能否得到他人的認同和接納。自我控制水平高的個體,能夠修正自己的行為和表現,使之符合社會需要。自我控制過程本身即是一個自我選擇的不斷努力提升自己的過程,個體能感受到較高水平的自主感;在努力奮斗的過程中,這樣的人擁有更高水平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增加了勝任感;另外,他們的表現符合社會期望,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認同和欣賞,提高了歸屬感。自我控制水平高的人,其基本心理需求得到了滿足,不容易形成不健康的成癮行為。對于自我控制水平較低的個體來說,手機具有信息獲得的即時性、便攜性、娛樂性的特點,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它便成為個體獲得心理需求滿足的非常容易采納的手段,但手機成癮只是其基本心理需求的一種替代滿足或虛假滿足。
4.3 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分析
在本研究中,自我控制對意義存在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說,意義存在(量表得分越高)水平越高,自我控制(量表得分越低)水平越高,進而手機成癮傾向(量表得分越低)水平越低。這與本研究中意義存在與手機成癮傾向顯著負相關的研究結果一致。情緒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 of emotion)(Schachter & Singer, 1962)認為,一種生理喚醒要轉變為情緒,這個過程既來自生理反應的反饋,也來自對導致這些反應的情境的標記。當個體將自己標記為具有較強的生命意義感時,便可以獲得極大的、極豐富的內在動力,進而,個體可以使用這個內在的意義系統調控自己的外在行為和表現,摒棄更本能的、沖動的生活模式,超越手機成癮帶來的簡單的、缺乏生命意義低等級快樂,去獲取更多有價值的知識,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豐富和完善自己,去過更加有意義的生活。
本研究發現,自我控制對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占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總預測效應的36.00%)。在中介效應中,意義追尋(量表得分越高)水平越高,自我控制(量表得分越高)水平越低,進而手機成癮傾向(量表得分越高)水平越高。這與本研究中意義追尋與手機成癮具有正相關關系的研究結果一致。追尋生命意義的個體,如果注重長期目標的實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會更加關注自己內在的、社會方面的和情境方面的表現,自我集中的注意(self-focused attention)更強烈,對自我的關注和自我評價過程使得個體更有動機去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達到目標(Wicklund & Duval, 1971)。在本研究中,高水平的意義追尋之所以會導致自我控制水平的下降,可能也與意義追尋追求的層次有關,追求享樂和個人舒適,容易導致自我控制的失敗(Vohs& Schmeichel, 2003),進而造成手機成癮傾向的提高。
自我控制對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關系的部分中介作用,意味著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影響只有一部分通過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實現,另一部分影響或者通過意義追尋對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作用實現,或者在該中介模型中有遺漏的中介變量(Zhao, Lyhch, & Chen, 2010),有待于通過后續研究進行探討。
Hirschi(1997)非常重視自我控制的作用,他指出,所有人都具有“動物性沖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犯錯或犯罪,其原因就在于人們的自我控制水平的差異,犯罪或偏差行為傾向是沒有馴服和控制人的動物本能的結果。Gottfredson 和Hirschi(1990)提出的自我控制理論強調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他們認為,自我控制水平低的個體更容易出現犯罪或偏差行為,自我控制是解釋犯罪或偏差行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其它因素對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影響都是通過自我控制這一變量間接實現的。
本研究的結果提示,矯正大學生的手機成癮傾向,包括修正大學生自我控制水平和生命意義感水平兩個途徑。生命意義感的修正涉及到意義存在和意義追尋兩個方面。在本研究中,意義追尋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越嚴重,這可能涉及到意義追尋的類型與層次(Reker & Wong, 1988),所以需要引導大學生進行健康的和高層次的意義追尋,而不只是追求享樂和個人舒適;意義存在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的水平越低,所以,提高大學生的意義存在水平有利于改善其手機成癮傾向。已有研究表明,對生命意義感的干預對修正偏差行為是有效的,比如可以降低自殺風險(Lapierre, Dubé, Bouffard, & Alain, 2007)和酒精依賴程度(Thurang & Bengtsson Tops, 2013)。目前有幾種干預措施可以修正生命意義感,如, 意義制定應對策略(meaning-making coping strategies)(Lee,Robin Cohen, Edgar, Laizner, & Gagnon, 2006)、人生回顧干預(life review intervention)(Westerhof,Bohlmeijer, van Beljouw, & Pot, 2010; 肖惠敏, 鄺惠容,彭美慈, 莫孫淑冰, 2012)、詮釋學的方法(明星,2013)、調整感激和勇氣(Kleiman, Adams,Kashdan, & Riskind, 2013)、存在主義治療手段(Kotoucek, Ezekwesili, Hrianka, Hriankova &Nanistova, 2015)等。
本研究發現,自我控制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水平越低。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既可以直接降低手機成癮傾向,又可以中介生命意義感對手機成癮傾向的作用。目前研究者已經發現了幾種提高自我控制水平的方法,比如,Meichenbaum和Goodman (1971)的自我指導訓練法、但菲、楊麗珠和馮璐(2005)的自我控制能力的游戲訓練(2 0 05)、Du ck w or t h,W hi t e,M a t te u c c i,Shearer 和Gross(2016)的執行情境修正策略(implement situation modification strategies)等。
5 結論
本研究發現,意義存在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的水平越低;意義追尋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越嚴重;自我控制水平越高,手機成癮傾向水平越低;自我控制對意義存在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對意義追尋和手機成癮傾向的關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