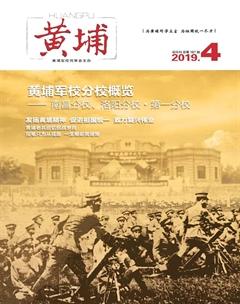1926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賈曉明
1926年3月1日,黃埔軍校由原來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與國民革命軍各軍開辦的軍事學校合并,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歸屬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址仍然設在黃埔島。當天上午,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舉行了成立典禮,宣布由蔣介石任校長,汪精衛任黨代表。在成立典禮上,汪精衛做了一篇頗具“深意”的訓話,其內容涉及軍校改組的原因、今后發展的設想以及存在的問題等內容。
強調“統一”
在汪精衛的訓話中,特別強調了各軍校統一到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必要性。據汪精衛說,“為打破地方主義,為集中人才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后來因為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后無論什么軍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
自黃埔軍校創立之后,在廣州的各軍也相繼辦了各自的軍校。其中滇軍設干部學校,湘軍設講武堂,粵軍設講習所,桂軍設軍官學校。這些學校“雖然名義上隸屬革命政府,卻完全因襲軍閥部隊的管理方法”。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后,將各軍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各軍中的軍官學校依然存在。到了1926年,國民黨執政地位更加鞏固,軍政日臻統一,獨立存在的各軍軍校被“統一”到中央也就成為必然趨勢。而對于各軍軍校中那些立志革命、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來說,黃埔軍校的新型政治軍事教育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早在1924年11月底,程潛所辦的湘軍講武堂的學員就紛紛要求立即將講武堂并入黃埔軍校,遭到湘軍教官的拒絕后,陳賡首先退出講武堂,考入黃埔1期。在他的影響下,緊接著又有許多同學帶上槍支彈藥相繼離校前往黃埔。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軍軍校中要求合并到黃埔軍校的呼聲也日見高漲。為了“組織和指導一種統一的政治工作,使各軍軍官消除省區觀念的舊傾向”,“軍官們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軍事政治知識”,由汪精衛提議“合并軍校暨各軍所立學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軍官班、軍官預備班、入伍生班,仍于埔校為校舍”,獲得軍事委員會通過。
國民黨“二大”后的1926年2月1日,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等7人為改組籌備委員,11日,發出《令知派員考察各軍軍實教育情形文》,文中稱“茲特派員調查各軍,及各軍校之軍實教育,庶使一切設施、得以推行盡利,以收軍政統一之效”。第二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出了《為歸并各軍軍官學校及講武堂所有各校舍財務應點交軍需局接管仰各遵辦具報文》,要求各軍校的財務、教育用具,全部交由軍需局接收保管,統一轉發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對于如何廢止各軍軍校,《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組織大綱》中做出規定:一、各軍軍官學校不準再招生;二、各校所到的新生,概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處理;三、入校不及兩個月的新生,同樣送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四、對于在校兩個月以上的學生,允許在各該校畢業,畢業后送各該校所屬的軍,充做排長;五、各軍長須確實將現在該軍將畢業的人數,和將來支配各畢業生于軍隊中的詳細辦法,報告參謀團,因這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數和分配畢業生于各軍的計劃,均須跟著各軍所報告的數目;六、對于各軍的舊校畢業生,另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處理,其校內原有的官長和軍事政治教授的處理和支配,全部由這個特別委員會處理。經過一系列繁忙而具體的準備工作,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最終于1926年3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
突出“政治”
汪精衛在訓話中,強調今后在新組建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政治和軍事“同時要注重”,“精神上技術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有研究指出,所謂“政治”指的是軍校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黃埔軍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對黃埔軍校實施的軍校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價值的充分肯定,并展示了國民政府準備進一步推廣這兩種制度的決心。
“中國軍隊中之有政治工作,自本校開始。”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在中國共產黨及蘇俄的幫助下,就建立起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軍校設置了黨代表和政治部,廖仲愷被任命為軍校的國民黨黨代表,一切重要的校務和命令,均需有黨代表簽署。黃埔軍校增設教導團時,又按照蘇聯紅軍編制,先后在教導第1、第2團的團、營、連三級設立了國民黨黨代表,并規定由校政治部主任秉承校黨代表之命進行指導。此后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漸推廣到整個國民革命軍。身為黃埔軍校校長和黨軍指揮的蔣介石也曾參與推行黨代表制度,還公開說“本校長對此制度志在必得”,并和黨代表廖仲愷相處得很融洽(廖仲愷將黨代表圖章放在蔣介石處,不在時蔣介石就會幫著蓋章)。
“權在黨代表,事在政治部。”在黃埔軍校,黨代表負有政治訓練和指導黨務工作的任務,一般要通過政治部進行。周恩來主持政治部工作后,不斷充實機構,制定《政治指導員條例》等各項條例,使軍校政治部真正成為校黨代表進行政治工作的職能機構,全面負責黨務、組織和宣傳等政治工作任務。
在周恩來、魯易、熊雄、包惠僧等共產黨人的主持下,政治部負責制定政治教育計劃。軍校的政治課授課者多數是共產黨人。據4期生文強回憶,周恩來的“每次講演博而能約,條理成章,易于筆記,也容易背誦,且聲情并茂”,“最能感動人”。為了聽周恩來上課,連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都“化敵為友”,共同“一聽到底”,課后還互借筆記傳抄。其他政治教官如惲代英“學養有素,器識凝重”,蕭楚女講課時聽者“凡二三千人,大禮堂亦不能容,則在操場中授課”。除政治課外,軍校還定期舉行演講會、報告會、政治討論會和政治問答,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如毛澤東、鄧中夏、彭湃等都到軍校作過演講。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問答箱”每星期一開箱,對放置其中的學生提問,由教官惲代英、蕭楚女、張秋人分別或書面或口頭進行答復。后來政治部還匯集問答內容出版了《政治問答集》。
軍校實行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對不同的革命思想理論兼收并蓄,“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書籍以及表同情本黨或贊成本黨政策而極力援助本黨之一切出版物,除責成政治部隨時購置外,本校學生皆可購閱”。軍校出版的大量期刊,如《黃埔潮》《黃埔日刊》等,緊密結合形勢,宣傳革命思想,有的刊物發行量高達5萬份之多。此外,軍校還出版了不少講義和書籍,進行革命宣傳,既開拓了學員的知識面,又提高了政治素質。
為了將學生培養成“既是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又是政治理念的傳播者”,政治部還組織學生支援工農運動,參與社會革命實踐。在廣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游行、群眾集會,都有軍校學員參加。政治部還組織學生成立宣傳隊,在群眾大會和軍民聯歡會上演出,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政治宣傳。后來,軍校的政治宣傳擴大到對敵策反工作。1925年6月初,在平定楊劉叛亂中,軍校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成員就奉命在滇桂軍中頒發《兵友必讀》,并動員前滇桂軍畢業生到叛軍處做思想工作,取得相當成果,叛軍“相率響義”,僅6月6日上午,就有100余人前來歸順。
在改組后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政治”得到進一步加強。政治部的機構進一步擴大,人員增至70多人,下屬機構增設了編譯委員會,設立了總務、宣傳、黨務三個科,并相應增加了政治指導員和政治教官。同時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綱草案》,健全了《組織條例》《服務細則》以及各項規章制度,從組織機構、規章制度上進一步保證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根據“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的原則,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時間學軍事,十分之三時間學政治,政治科則相反。自第4期開始,制定政治教育大綱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內容也進一步充實和豐富,政治課程增加到26門。
暗示矛盾
在訓話中,汪精衛雖然提出“仍請蔣介石當校長”,理由是“對于蔣校長的人格和他努力奮斗的精神,本黨各同志都是極端的敬佩”。但又說,關于軍校改組,是在“蔣校長在汕頭擔任東征總指揮”“不能回來”的時候決定的,蔣回來后“實行”就可以了。
黃埔軍校創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汪精衛僅僅因到校講課和蔣介石有所接觸。到了軍事委員會成立,汪任主席,蔣任委員,二人才正式在一起共事。廖仲愷遇刺案發生后,兩人密切配合,形成汪主黨政、蔣主軍事的格局。國民黨“二大”后,汪精衛集中常會、中政會、國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于一身,儼然成為黨政領袖;蔣介石也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軍委會常委,進入國民黨的權力中心,并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其作為軍事領袖的形象也更加突出。
不過,此時的汪蔣關系卻急速惡化,“在對俄顧問的立場方面、對國共關系和處理軍事財政事務方面,他們間的歧見漸深”。汪精衛上臺后,便打著“以黨治軍”“聯俄聯共”的幌子,鼓吹自己的“左派”領袖地位,借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的力量削弱蔣介石的影響,為插手被蔣介石視為禁臠的軍隊和軍校不斷造勢。汪精衛主持把各軍政治部主任一職改為“副黨代表”,并大批選用共產黨人擔任,“代行”總黨代表的職權;還讓親信陳公博主持編寫《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有“審查軍隊行政之權”,“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在“發現指揮官分明變命或叛黨時”有權予以制止,讓蔣感到其軍中權力和威信被制約,甚至到了“喧賓奪主的地步”。蔣介石起初也采取對抗措施,提拔一批親信任黨代表,但這些人和“同級軍官一團和氣,吃喝嫖賭,不發生任何作用”,連戴季陶都說“隨便放了許多人去充數,其結果不但是不好,而且只有搗亂的”。
第二次東征期間,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中的影響也日益發展壯大:特別黨部5名執行委員中,除蔣介石外,其余4人都是共產黨員;7名候補委員中,6人是共產黨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秘書以及政治教官的大多數為共產黨員;黃埔軍校所辦的刊物,基本上由共產黨員負責,“發的書籍,比蔣介石的《曾胡治兵語錄》不知多幾倍”。而一些共產黨員的言論,如廣東國民政府由“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的條件已經成熟、蔣介石早已“存了繼任領袖的野心”、“打倒這里的段祺瑞”等,讓蔣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共產勢張,四圍都非同志”。而此時的汪精衛,不但在軍校畢業證書上加署自己的名字,還常去黃埔軍校演說,召開會議,到處宣揚“黨”高于政府,高于軍隊,高于軍校,甚至插手軍校的經費分配,更公開宣稱在軍校“要選拔幾個青年同志”,拉攏王懋功等“背叛官長”。
當時,蘇聯顧問的意見對廣州國民政府有著很大影響。廣東統一后,自詡為“軍隊中之重心”的蔣介石提出,為推進北伐,“革命應統一指揮”,積極謀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但蘇聯顧問中的一些人認為,“蔣的軍權日大,威脅堪虞”,“不能讓他擁有超過3個師的兵力”,還有的表示要“為黨代表撐腰”。國民黨“二大”后,軍事委員會只授予蔣“國民革命軍總監”職務,讓蔣“總攬”軍事“事務”,“督查各軍的整改工作”,但不包括軍需后勤問題和“一切政治問題”。這和他要求的“總司令”相距甚遠。蔣以退為進,表示辭去總監、廣州衛戍司令職務,“愿專任軍官學校校務”,并多次找汪精衛談話,建議“撤換蘇俄人員”,但汪不給“明確的答復”。蔣本來就“脾氣很大、氣量很小”“是最多疑的”“懷疑到極點,以為共產黨要趕他,或者精衛要趕他”。
當時軍事委員會采取合議制,但組織法規定“凡軍委會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通過方為有效;如多數委員不在軍委會所在地時,主席與委員一人有決定處置之權”。按照包惠僧的說法,“書生氣重”的汪隨著其黨政“領袖”地位日益鞏固,越發顯示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勢態”,認為“不必要遇事都要由蔣介石來決定”。就像汪精衛在3月1日的訓話中所說:“無所謂特別的黨校,也就無所謂特別的黨軍。”這更讓蔣介石判斷在“本軍里或本校里”“共產黨員和蘇聯顧問的反蔣趨勢已經成熟”,甚至“連汪兆銘已經和他們一鼻孔出氣”,從而加快了采取對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