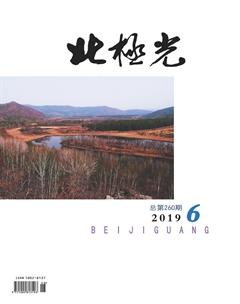龍灣
魏龍
鴿子花一收翅冬眠,竹蘇蛋就欲冒出來過年。節登遠望的枝枝竹葉,宛若排排飛槳,當陽光開始普照,猴面鷹開始鳴叫,夢中的小舟便嘩啦啦地劃向了碧波蕩漾的萬里長江邊的龍灣沱。龍灣沱,母親的故鄉,位于四川盆地南緣的江安縣。
歲末年初的這個夜晚,夢見了母親,母親說想回故鄉看看。夢醒時,除了揉眼傷心,便是悲愴的一聲嘆息,母親病逝已經四年多了。
今年春節前,擇一風和日麗的天氣,我和妻子一道,第一次回到母親別了五十多年的故鄉,見到了姨媽、舅娘,還有幾位表姐妹、表弟以及一大家親戚。
姨媽的瓦楞屋,坐落在城鄉結合地的農村里。屋前方的淺丘上建著一棟棟美廬,屋的一側是毛竹林,另一側的斜下方是養著魚兒的半畝方塘。
清瘦的姨媽沒有母親高,但白里透紅而又細膩的皮膚與母親的極其相似,八十六歲的她,吧唧著嘴,瞇了瞇深邃但有光亮的眼睛。
望著姨媽飽經滄桑的老年斑,我意識到她的每一塊老年斑,都寓意著一個黯淡的故事。她的每一道額頭紋,都隱藏著人生的坎坷。旁邊,胖乎乎的圓臉的舅娘十分健談,她用地道的江安話告訴我不少過去的往事。
解放前,外公、外婆和我母親在龍灣沱過得很苦,只有一間茅草房。一個圓月高掛的夜晚,外公正在清江邊刨地種菜,祓突然捆綁,被押到江堤上,瞅著寒光閃閃的刺刀和全副武裝的士兵,外公明白自己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半年后逃回龍灣沱的外公被迫給地主當了長工。
解放后,外公當上了燈桿村的村長。外公去逝后,我舅舅龍寶安當選村長直到他病逝。現在燈桿村的村長是一位皮膚微黑、辦事果斷、具有男人性格的女村長。她叫陽永紅,是二表弟龍挺武的媳婦。
“燈桿村是貧困村嗎?精準扶貧多少戶?”我關心地問她。女村長把染燙的短發搖晃得像兩江口的浪花。她說:“燈桿村一千六百多人,都過上好日子咯!大多數村民已住進了城里的安置房或帶電梯的高樓,政府還為他們買了‘保險………我們不是貧困村,也沒有貧困戶。”
我到姨媽的廚房里,菜墩右邊,安置著天然氣爐盤,燃氣灶冒著藍色的火焰,鐵鍋里正咕嘟嘟煮著香噴噴的魚肉。
曾經聽父親說過,早在1956年5月,父親所在的單位四川石油普查大隊,在江安縣廣福坪構造K-5井,打出過第一口噴氣井。如今的江安已擁有數十口工業氣井,主要分布在廣福、桐梓等地。
院壩外,雙莢決明樹上成對的莢果在微風中搖曳波動,兩株蠟梅綻放著寒冬的凝香,梔子樹葉下一盆天竺葵盛開著鮮紅的花朵,紅得那樣溫馨和喜慶,像灶膛的火焰,點亮了紅紅火火的日子。
“大表叔,石缸里有好多魚。”七歲的表侄女悅悅跑過來開心地說。靈秀聰慧的小姑娘惹人喜愛,一雙靈動秀美的大眼睛充滿著純凈、天真、好奇的目光。她仰著粉嫩桃紅的小臉笑盈盈地告訴我,明天星期天她和村上的小朋友還要去武館練習武術和跆拳道呢。
龍灣沱龍家幾代人的變化過程不正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真實寫照與縮影嗎?
向晚,樹杪、竹梢上的夕陽暖暖地照著房頭前的魚塘,游嬉的魚群正泛起金橙色的漣漪。
“開飯咯,喝酒咯。”至親們把三桌壩壩宴的酒杯舉到了空中,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圓。江邊的紅日也像喝了幾杯故鄉的敬酒,酡紅著圓潤的臉。望著那輪紅日,我想起了慈祥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