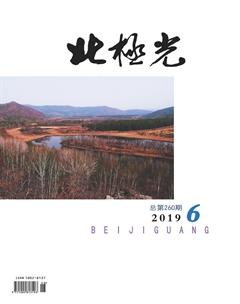在人生的天空布一道詩的彩虹
邢海珍
1
人活在世上,自然要做許多事,比如說寫詩,它也是構成整個人生的一項活動。朝大處說,詩屬人的精神世界,意識形態、文化傳播,事關人類文明、社會進步、時代發展、生命價值等諸多問題,是神圣的大事業。若往小里說,寫詩是個人的追求,喜歡寫就寫,心性、情懷是生命存在的要端,有話要說,形諸文字,與自我與他人,都有一定的意義。我知道,寫詩難,不容易大紅大紫、大富大貴,所以大多數人只能停留在愛好的層面,不敢高攀和妄想成為寫出經典之作、產生深遠影響的大詩人,而只是與詩結緣,成為有一己愛好的寫詩的人。我想當下中國大多數詩人都處在這樣一種狀態,點滴成河,眾水匯聚,于是便有了詩的汪洋大海。女詩人王恕就是詩歌洪流中的一個癡迷者。
前幾年,因為都是心向詩歌的蕓蕓眾生,一個偶然的機會與王恕相識了。所謂相識者,其實也只是至今未曾謀面的交流,于是有了一些關于詩歌的對話,陸續讀了她的一些詩作。在這條路上,由于我們的起落高度差不多,我很認可她的人,也喜歡她的詩。
王恕出生在黑龍江五大連池,祖籍遼寧遼陽,從小在遼陽上小學。遼陽是清代著名文人王爾烈的故鄉,王恕是王爾烈的后人,先祖的文脈從先陰之河流進了她心靈深處。從小就聽爺爺、父親講述王爾烈的故事,眾多鄉親傳誦這位大才子的文名,無意中便受到詩歌的熏陶,詩的種子在她人生的土地上發芽、生根。后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她在北大荒農場扎根,當了一名中學教師。多年來一直堅持寫作,無論走到哪里,心中詩的火焰總是燃燒不滅,并陸續在《光明日報》、《星星詩刊》、《詩選刊》等報刊雜志以及網絡平臺上發表了大量詩歌作品。
2017年,王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秋林樺影》,這是詩人的心血之作,也是她多年來堅持詩歌創作的總結。作為詩友,我為她取得的成就高興,祝愿她的詩歌花朵在遼遠的大地上開得燦爛,為讀者朋友奉獻一縷馨香。正如詩人趙寶海在詩集序言里所概括的那樣:“王恕的詩,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堪稱心靈的密碼。它靈泉暗涌,意象朦朧,清純瑩澈,意蘊豐厚,情趣理趣具足,如一顆顆通體晶瑩的寶石珠子,被情感的絲線,精致地穿起來,配以心形的吊墜,閃耀著屬于自己的獨特光彩。”
歲月流逝,詩人王恕轉眼走進了夕陽的光影,但她仍是童心未泯,仍然邁著青春的腳步走在詩意的春天里。在《秋林樺影》的后記中,詩人寫下了這樣一段富有浪漫情懷的文字:
一棵草有心,一棵村有眼,一朵花有靈,一個人有根……
山野的孩子佇立或行走,心中自然就有一份深深眷戀。秋楓如血,脈絡里依然會有青蔥流嵐,化作云雨回報大地母親。一些心靈囈語點點滴滴,深深淺淺的足跡顫若雁行或飛或落。寧靜之心穿越紅塵煙雨,布一道彩虹……
擁抱大自然,眷戀大地母親,無限美好的童心和熱愛,是一個詩人所必然擁有的精神財富。王恕懷有一顆詩心在人生的山野上行走,與花草樹木為鄰為伴,吸納萬物靈性,在生活的沃土之上,養成了一個詩人生命的根性,朝著人生的天空布一道詩的彩虹。
2
從詩集的名字“秋林樺影”看,王恕偏愛山林樹木,這大約與她長期生活的環境有關,或是與詩人某種隱逸的心性有關,遠離喧囂,在安靜的環境中進入一種幽秘的詩意境界。
著名散文家、哲學家周國平在《人與永恒》一書中說:“詩應當單純。不是簡單,不是淺顯,是單純。單純得像一滴露水,像處女的一片嘴唇。”他所強調的“單純”是精粹、純正,是明媚、高遠。是沒有任何刻意遮蔽的通透,是祛除了矯情的裝飾而卓然獨立的風姿。單純是詩的極高的境界,“像一滴露水”那樣清新透明,“像處女的一片嘴唇”那樣潔凈鮮美。
王恕在詩歌創作中,努力追求自然、單純之美,每每運用意象,總是與自我內在的心性融合在一起,進而走向抒情的深度。在《從未給夜晚下定義》這首詩中,結尾一節是近于寫景的文字:
野蒿覆蓋小路,漢字里穿行
一滴水異鄉瘦弱
迎向火焰,吹起口琴,心就濕透了
飲盡杯中山水
夕陽無人認領,坐在山下
從未給夜晚下定義
詩人筆下的黃昏風景,透出一種憂傷的心緒。野蒿、夕陽以及“杯中山水”,皆未脫自然之氣,并無作者故作高深所施放的“迷霧”。這樣的詩還可以說是借景抒情,是一些帶有情緒化的詞語如“異鄉”“濕透”“無人認領”等透出了某些情感的趨向。我們可以讀出詩人借黃昏寫懷鄉之思,詠嘆光陰流逝的惆悵。王恕寫風景不失意象化的追求,“一滴水”、“夕陽”除了自然的物性之外,還有象征意義,但詩人并未給閱讀造成障礙,只是留有余地,促成了詩的含蓄效果。
單純的追求,并不影響詩的深刻。《一條魚的夢想》是王恕詠嘆人生的一首詩,詩人以“魚”喻人,寫人的命運被扭曲,只是“一串串氣泡/心在路上走著”,“一生睜大眼睛看世界“,但也難逃剝落鱗片、油鍋煎熬的命運。在結尾兩節詩人這樣寫道:
藍天若一片大海
一張網
云有黑有白有聚有散有悲有喜
是另類的魚
兩岸翠巒探身水中
試圖拎起一條江翻看
魚的夢想其實很簡單
有尊嚴地活著
直立行走
開口說話
詩人王恕把“魚的夢想”大而化之,涉及天地萬物,以意象的方式構建了一個“夢”的大境界,在虛化中讓世界顛倒,然后又回到“夢”的現實中來——“有尊嚴地活著/直立行走/開口說話”,凸顯主題,真如撥開云霧,鏗然有聲。這是一首立意非常單純的詩,直指人生世界的悲劇性,大義凜然地宣示了“尊嚴”的理性精神,具有思辨的深刻性。
從《秋林樺影》所收詩作看,是短詩居多,這樣的詩也可稱為“小詩”。王恕善于在這種小的體制中凝聚詩意,抒寫情懷,有感而發,心中靈光一閃,表達即在快速中完成。比如說《暴雨喧嘩》本是很平常的題材,詩人只是簡而化之,幾筆便在描述中把暴雨施虐歸結為“情感泛濫”,于天地人情的統一中推出“夏天痛哭失聲”的特殊意境,自然之雨有了“人事”的因素。《童年那只鳥》也是一首單純的詩:
人們不斷地
被時光之書轉載擺渡
六十歲不短不長
童年沒抓住的
那只鳥
叼一枚紅櫻桃飛走
黃嘴丫還沒全退掉呢
眼見麥子一茬茬
由綠變黃
發絲一年年
由黑變白
比詩很見構思的獨到之處,“童年”是一只鳥,飛了,沒抓住,而且這鳥“叼一枚紅櫻桃飛走”了,情境效果非常好,生動鮮活。人到“六十”,宛如夢境,轉眼之間,麥子和發絲,一切都改變了模樣。而這些改變了的事物,都是“那只鳥”眼中所見。這樣的抒情不空泛,是托物言志,文字不多,但寫得不平淡,有聲有色有波瀾。寫得單純,但感懷人生短暫,很深刻,一唱三嘆的余音不絕,人生五味全在其中。
在王恕的詩中,幾乎沒有那些拖泥帶水的鋪陳和敘述,可以讀出快人快語的個性,無論是言情還是喻理,都帶著一縷迅疾之風,像行俠者的飛鏢,出手極快。這樣的詩就像古詩中的絕句,注重含蓄,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往往是以少勝多,點到為止,不是把話說盡。《月牙泉傳奇》一詩言簡意賅,詩的境界可謂深邃而又遼遠,詩人以意象之美抒發了人的抗爭精神:
即使彎月在沙漠上輕劃
無邊疼痛也會
不斷滲出纏綿的綠波
鳴沙山月牙泉
沙吼如雷空叫陣
美人尋愛累臥邊塞
淚眼千年
多少辰光植被城池村莊牛羊
覆沒黃金甲下
陽關
咀嚼夕陽
翻閱一部沙不掩泉的
神奇故事
詩中的大漠風景真是美不勝收,沙原寥廓,彎月輕劃,誰的“無邊疼痛”里生命漸漸舒展,我們看見的是“纏綿的綠波”。沙海之中掩埋了多少人間悲劇,但陽關矗立,月牙泉水仍在“神奇故事”中潺潺流淌。詩的語言干凈洗練,意境之中飽含著美感和力量。
王恕詩歌的單純之美,是詩人對詩歌文體獨立性的追求,是打造詩體精致的自覺努力。比之小說和散文,詩歌文字量小是一個鮮明的文體個性。在詩歌創作上,王恕選擇“小詩”這種體制,盡量做減法,注重提煉和壓縮。在明快的表達中驅遣意象,意蘊豐贍,但不是故作曲折而言不及義。她的詩單純,但不失凝重和深刻;她的詩短小,但又內含豐富,思想和情感的底蘊厚重。
3
說到底,詩是生命情懷的抒寫,是生活體驗和感受的懷想和憶念。人生的足跡留在世界上,或與心靈相應和,形諸詠嘆,形諸文字,便有了詩歌故事的發生。對于詩和詩人來說,人生的過程、生活的經歷永遠都是根性的存在。宋代大詩人陸游在一首題為《讀唐人愁詩戲作》的詩中有這樣幾句:“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這里詩人的“戲”說,是把詩與生活的關系逆向來看的。其實,是有了“零落在蒿萊”、行吟“澤畔”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經歷,才有文人因切膚之痛而進入深刻的反思,才有經典光照后世。
在黑龍江的遼闊大地上,王恕從當年的懵懂少年一直到如今的鬢染霜痕,漫長的人生之路為她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堅實的生活基礎。北大荒的耕種歲月,尾山農場的教師生涯,都是詩人不能缺少的生命財富,她詩歌的一字一行都源自這些生活的泥土。王恕的詩雖然很少有直接再現她生活經歷的內容,但詩人的意象儲備和選擇,卻與她的經歷、經驗有著血肉般的關系。至此詩人的創造對于意象的選擇,其實就是人生經歷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等諸多事物蓄積于心,而后通過情感或思想的再造所形成的一種具有鮮明個人化色彩的具象形態。在《鄉情剪影》一詩中,詩人形象地把記憶中的農場生活場景呈現在讀者面前:
連一塊青苔也沒找到
老屋嗆人的灶火
已熄滅在
一片麥田下面
鄉村早已搬進城鎮
青楊也嫁給遠方
柴草垛里孵出的雞崽兒
毛茸茸的在心頭
溜達
午后廢棄的場院
凸凹的斷墻內外
幾個小孩在抓螞蚱
狗尾巴草們
守在銹跡斑斑幾近裸奔的
脫谷機旁
很率真
轟鳴聲乍起
把自己嚇了一跳
小咬和塵土
一起炫舞
男男女女一起
會戰的情景閃現眼前
詩的整體情境是財往事的回憶,詩人憑著當年生活的留痕回到了昔日的生命過程中來,以富有現場感的活力營造了人間煙火氣息濃郁的風俗畫。時光流逝、時代和社會前行,“鄉情”成為詩篇,留在心中,或是不無感傷的珍貴的紀念。曾經居住的老屋不見了,過去灶火燃燒的地方如今已成麥田。廢棄的場院、銹跡斑斑的脫谷機收藏多少如煙往事,廢墟和遺跡之后是詩人無邊無際的感慨。那毛茸茸的雞崽兒,那男男女女們“會戰的情景”,當是遙遠日子留駐心中的一縷暖意。
詩是文化的載體,人生經歷和生活經驗的本身不是詩,經歷了同樣生活的人不可能都成為詩人。詩是精神的創造和文化的選擇,由人生、生活到達詩是生命形態的改變。因為想象和思考的參與,詩人筆下的生活現象、自然現象已不再安分守己,心靈的馴化和浸染,本來那些比較客觀的事物,忽然主觀化了,已為詩人的心性、情懷所擁有。在王恕的筆下,生活的形態不是拘泥于一種客觀的實在性,而是經過變形、延展,指向了形而上的維度。比如《蒿草爬上房頂》中的事物雖然不無實在性,但暗中已被虛化,已經有了超脫的可能:
一條河繞著村莊流過
千年戀著遠方
公雞報曉啼叫了三遍
主人的柵欄門沒開
燕子起得早
在天空中翻飛
幾蓬蒿草爬上房頂
嘹望
千萬別觸碰清晨的被角
露珠里睡熟了星星
這首十行短詩中涉及許多的生活事物,本來很平淡,或是詩人有意淡而化之,意欲擺脫生活的實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寫河流,關注的卻是“千年戀著遠方”,蒿草爬上房頂“嘹望”,“清晨的被角”以及“露珠里睡熟了星星”,是高遠的虛空之境,或有一種童話情結藏匿其中。詩有了一些玄思的意味,指向生命的遠方,走進了形而上的境界。《粉筆走失》是用比喻的方式把生活中的某種事物轉換為詩的意象:“一支支粉筆列裝/山鄉中悄悄地/走失/漂白了鬢角/瀟灑成北國之雪//黑板幻化成沃土/中國符號結成果實/從一紙掛圖上躍下/趟過世界之河”,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是以“粉筆”喻人,由“漂白了鬢角”到“北國之雪”,象征著人生像粉筆一樣在歲月中磨損而青春不在。從“黑板”到“沃土”、從“符號”到“果實”以及“趟過世界之河”,都是通過比喻把生活的事物轉化為詩的意象。詩人王恕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扎實的知識儲備,是她詩歌創造走向成熟的不可缺少的底蘊。
4
《秋林樺影》是一部抒情短詩集,可以看出詩人王恕多姿多彩的抒情風格。作為女性詩人,王恕幾乎沒有小女子式的溫情和柔弱,沒有那些卿卿我我和無端“五十弦”的人生愁緒。王恕的詩很富男性的特點,有些風風火火,足具生命的陽剛之氣。在《春的蒙太奇》一詩中,“春”的季節景觀是生命力的象征,充滿了抗爭和奮進的向上精神:
叢林
像刺猬插滿吸管,心是誰的乳汁
大小興安嶺也半睡半醒
一夜間,達子香泣血怒放
凄美的故事,悄然洞穿冰雪
無聲的情懷盛開,彌漫
燃燒,注定是一種犧牲
目極處,時光在唇邊次第隱退
忽明忽暗
套馬桿,劃破淡紫色的云朵
揪心斷腸,扯出的距離,苦了誰
河水卷起褲腿,假寐的冰排
簇擁著葦花兒的劉海兒
向東向東
別說你的心空,已裝訂成冊
記憶的枝頭棲滿霞影
南來的候鳥們,無暇留意
野玫瑰拋出的媚眼
仍舊,艱辛執拗地丈量著,春的厚度
春,是一個季節
種子埋下頭還會揚脖
春不是一個季節
心靈的喀斯特高原
傾聽,太陽的親切召喚
夢的角度在不斷調姿,鮮活
詩人是昂起頭遠望的姿態,大小興安嶺起伏,達子香盛開,凄美的故事洞穿冰雪。荒火、馬群在時光中“次笫隱退”,以河水、葦花兒寄托人性情懷,候鳥們、野玫瑰風情無限,春天的夢幻在種子生命向上的追求中,是那樣神奇和多姿多彩。
王恕的抒情不是直接抒情,是傳統詩歌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用意象來創造情境,是感性和具象的方式,傳統文化精神是王恕抒情的底蘊。像《春的蒙太奇》全用意象來鋪展,順意而進,不是胡亂堆砌,沒有晦澀的云霧,可謂明心見性。
在堅實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王恕詩歌的藝術表現追求充分的現代性,注重事物之間的合理對接,大幅度變形、跳躍,運用意象象征等手法,意識流以及化出化人,閃回、蒙太奇常在詩中出現,使詩的創造更靈動,更具活力。她的詩少有平鋪直敘的散文化筆法,多是大跳躍,刪減繁雜,突破一點,集中實現詩意全方位整合的目標。在《陀螺。念及蕭紅》一詩中,詩人把現代女作家蕭紅短暫的人生比作陀螺快速旋轉,全詩如下:
一記記鞭策
抽在身上,痛,快樂得天旋地轉
呼蘭河間或擰成繩索
晾曬身邊小城一百多年前那幅市井圖
淡積云——濃積云——積雨云消散風雨雷電
蕭紅騎著火燒云不時回來
一次次撥出心中“砂粒”,砸碎“苦杯”
把自己交給風,31歲一串念珠
文壇如釜,翻炒,形形色色
淺水灣喘息猶在,松花江歌謠凄婉
你從悲苦浸泡中撈出自己,掙扎著,投向光明
腳印交織高高摞起,愛憎清澈
文字不朽,記錄著繁華背面另一幅《生死場》
即便塞住耳朵
依然會清晰聽見筆尖劃紙咚咚心跳
這首詩的構思很機智,詩人把蕭紅31年的人生命運寄托在被抽打、快速旋轉的“陀螺”之上,是大跳躍,是意識流動,把蕭紅的悲劇命運凝聚在十幾行詩中。詩的冷靜、壓抑的情調,對于情感起伏的把控,強化了詩意表達的深度。游刃有余的語言風格、自然而舒緩的節奏,表現出詩人王恕多年積累打磨在創造精進上的收獲,或說她已臨近成熟之期。
王恕詩歌的抒情比較自覺地追求意趣盎然的效果,時而率性而為,時而出之幽默,情理畢現,筆致深入淺出。收入《秋林樺影》中的一些小詩,就很有情趣,表現出另一種灑脫的抒情風格。《果園小趣兒》一詩只有這樣幾句:
想起
“瓜田李下”這個成語
手插兜里走路
別低頭
枝上那些果子
可不認得你
走路的人,怕人懷疑自己搞了果子,是環境驅使自我產生心理壓力,“手插兜里”、低頭走路的人,其實是多此一舉。心底無私天地寬,人沒必要為人為己徒增煩惱。這樣的詩很有趣,在一種輕松的狀態下就可領略詩的妙處。《真真假假》是一種幽默調侃的寫法:“隊里發了耗子藥/兩根挺香的大果子/一個老奶奶不知/吃下它被搶救/老鼠們倒很開心/有人替它們來品嘗//又發一包瓜子/它們磕開皮把仁兒吃了/沒咋的”,人和耗子的事,鼠藥的真真假假,令人忍俊不禁。這樣的詩都有關情趣。還有理趣,重思辨性,思想燃燒,把一些感悟賦以詩的形式。如《三棱鏡》:
枕著時光打盹的人,思想會慢慢
長出胡須來。
只喜歡聽別人演奏,心中的短笛
能吹響么。
撐不起正義之傘,鳥鴉會在你的
頭頂筑巢。
泥沙是走失的土地,哦,大海臂彎里的
那個小島可是你懺悔的足跡?
許多詩意的思考,可以給人帶來認識和理解世界人生的角度,詩人給人的不是理論的思考,不是結論性的東西,而是詩意的情境所含納的思辨鋒芒,從特殊的角度刺破被包裹、被封閉的思維外殼。王恕把如此深切的理趣與詩的形式熔于一爐,不是理性說教,不是赤裸裸的大道理,而是讓人人情人境而引發思考,為詩意所感染,在詩意中回味。
轉眼幾十年過去,詩人王恕的詩路還長朝前延伸,《秋林樺影》是一個秋天的佳境,這里是詩歌的收獲季節。
王恕有一首題為《虹》的短詩,我錄下其中這樣幾句“有一天/我們會從中間向兩端落下/七彩盡頭/仍舊依戀江河山川/遠離疼痛/一些腳印隱藏起來/像從不認識的陌路人”,人生之路,與詩相遇,是一種特殊的緣分,就像彩虹,以生命招展輝煌,像橋一樣高矗于江河之上,而其實是虛空之象,是人生的理想化追求。朝著未來,靈與肉的疼痛也漸去漸遠,即使不見了腳印,我們還要走下去,因為那是詩的遠方。
我祝王恕詩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