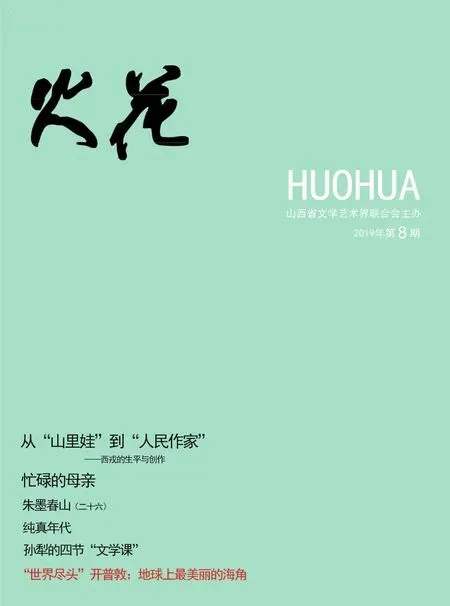純真年代
羊白

一
童年是一個人的首都,有許多純真的東西,在那里已經發芽,而且不懼時光,頑強生長,影響我們一生。
二
我們小時候,農村幾乎不種菜。種也是蘿卜白菜,蘿卜可以做咸菜,白菜可以泡酸菜,一年四季,似乎就是咸菜和酸菜,幸虧家家戶戶都這樣,也就不覺得日子苦。
在湑水河畔,有一塊平整的沙地,是部隊的蔬菜基地。菜地四周繃著鐵絲網,網上還有防攀爬的鐵蒺藜,平時有軍人專職看管。在那個年代,可以不夸張地說,蔬菜基地就是我們的啟蒙老師,讓我大開眼界,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多好吃的東西,西紅柿、黃瓜、梨瓜、洋蔥、豌豆、甘蔗……實在是太誘人了,隔著鐵絲網看得清清楚楚。我們附近幾個村的孩子,蠢蠢欲動,尋豬草總愛往那兒跑。也真難為了看守的軍人,要和一幫孩子斗智斗勇。不管吧,我們太猖獗;管吧,軍民一家人,孩子們渴望的眼神,他們未必下得了狠手。
時間一長,我們摸出了規律。知道了看守的軍人并非時時防范,過一個小時會巡視一次,其余時間基本不出來。于是就跟玩闖關游戲似的,密切注視里面的動靜,一旦找準機會,從玉米地里突圍出來,快速在鐵絲網的下部掏出一個地坑,爬過去,瞅準目標出擊;一有風吹草動,立馬撤退,從地坑處爬出去,退到安全區域。
那實在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仿佛是電影里的場景。
因為,不但要和軍人斗,還要和里面養的一條狼狗斗。軍人不出來,不意味狼狗就不管了。那家伙耳朵鼻子靈著哩,我們最怕的就是狼狗。
為了打贏戰爭,單獨行動是不行的。往往至少要有三個伙伴,一個放風,觀察敵情;一個進攻;一個接應,并守好后方。
放風的,要觀察好軍人和狼狗的動向,并及時準確把信息傳遞過來。進攻的,要選好地點,要膽子大,還要果斷,沉著冷靜。比如,爬地坑時,再著急,都要把衣服收緊,千萬不能被鐵絲網掛住,一旦掛住,就麻煩了。有一次,王安斌就被鐵絲網掛住了,我和鐵牛去接應,卻怎么也幫不上忙。眼看著狼狗嚎叫著沖過來,軍人在后面也急了,吼不住,讓趕快脫掉衣服。王安斌撕掉衣服,總算逃了出來,后背上卻劃了好幾道血口子。王安斌一爬出來,鐵牛和我迅速把準備好的石頭堵上去,狼狗呲牙咧嘴地咬著鐵絲網。我們拔腿就跑,鉆進了玉米地。在玉米地里,還聽見軍人在罵,罵些什么聽不清楚,因為那些軍人是外地口音。軍人一邊罵,一邊把王安斌的衣服扔了出來。
我膽子小,通常負責接應,在玉米地里守后方。守后方其實也挺重要,要隱蔽,而且要會轉移。有一次,胡小山他們偷蔬菜基地的香瓜,已經偷的差不多了,卻被軍人逮住了,守后方的沒有及時轉移,結果所有的勝利果實都被沒收了。
可不管怎么說,平心而論,進攻的人功勞最大,因為進攻的人最危險,沖鋒陷陣在第一線。因此最后分配,我和鐵牛都是主動讓步,王安斌拿四份,我和鐵牛各拿三份。有一次,王安斌腳腕受傷了,沒法進攻,我和鐵牛沉默著,知道應該挺身而出,心里卻膽怯,都不吭聲,惹得王安斌很不高興,罵一句膽小鬼,提起尋豬草的籃子,扭身要走。
我臉臊得通紅。鐵牛說,要不,咱們抓鬮吧。
我倒是想抓鬮,這樣誰也沒說的。可我認為這樣太難看,太對不住王安斌了。不知哪來的勇氣,我應承了下來。
這樣一來,鐵牛面上掛不住了。他說,要不,還是我上吧。
王安斌推他一把,說去球,早干啥去了,少裝樣,有種,下次你上,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鐵牛可憐巴巴地說。似乎王安斌是我們的首領,他在表決心,又像是在對他自己說,在為自己壯膽。
那次行動,我記憶猶新。我們的目標是翠脆的黃瓜,我進攻了兩次,總共收獲了二十九根。我把衣服脫下來,把兩只袖口綁住,反吊在自己的脖子上,便是一個現成的口袋。
我第一次上前線,戰斗基本順利。期間雖有狼狗,但被王安斌從側面引開了,并沒有想象的那樣困難。這讓我很是欣慰,原來自己也可以出戰,為團隊出力。最后分黃瓜,三九二十七,剩下兩根,鐵牛主動給我。我認為雖然這次我是主攻,但平時一直是王安斌,我不配擁有這樣的榮耀,因此我把一根給了王安斌,我十根,他也十根,鐵牛九根。
分完,王安斌威嚴地看著鐵牛,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惹得他不高興。
我問,怎么了?我以為王安斌對分配的事有分歧,可,這有什么不妥嗎?我正疑惑,王安斌吼一聲:讓他自己說。
鐵牛囁嚅道:說什么?
你自己清楚!王安斌嘩啦一下把鐵牛的豬草籃子倒了個底朝空。豬草里,跳出了兩根黃瓜。
鐵牛不說話了,罪人似的看著腳尖。我拉拉王安斌的袖口,意思走吧,回家吧。
王安斌繼續威嚴地盯著鐵牛,故意不吱聲,讓他自己解釋。
鐵牛眼淚都出來了,就仿佛他是個叛徒。干了骯臟的事情,任何解釋都是白搭,我們不會原諒他的。他咬緊嘴唇,為自己的恥辱難過。
王安斌掂掂頭:不說是吧,我們走。
鐵牛看我們丟下他,不要他了,撲通一聲跪了下來。
自始至終,鐵牛沒有說一句話,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悔恨和難受。正如王安斌所說:叛徒,是不可饒恕的。
我的心突突跳,甚至都不敢去拉鐵牛一把。因為我也私藏了一根,只不過我這個叛徒沒有被發現罷了。在良心的審判里,其實我已經跪下了。
三
我們班里有個女孩,叫李春芽。李春芽長得眉清目秀,我們男孩都喜歡她。
有天,李春芽削鉛筆時,把食指削了,血流不止,老師趕快用布條給她包扎了一下,然后讓她回家休息。
第二天,李春芽來上學,同學都爭著搶著看她的食指,關心她,問她疼嗎?這讓她難為情,搖頭,又點頭。胡振山頭頭是道地說:“能不疼嗎,十指連心呢……”胡振山還說,他大伯家有云南白藥,治傷口可管用了,他給李春芽要一些。
胡振山的一席話,讓我羨慕,又自卑,覺得只有他配關心李春芽,我呢,縱然也想愛護,可我能干什么呢,一點力也出不上。
幾天后,李春芽的食指還是裹著布,寫作業都困難。我問她,胡振山給你弄來云南白藥了嗎?李春芽紅著臉,搖搖頭。我一籌莫展地寫作業。突然想起前幾天,我囫圇吞棗看過的一本武俠小說里,一位大俠在山野受傷,他找來蘆薈,切片取汁敷在傷口上,很快愈合了。蘆薈有如此神奇的療效,讓我驚奇。如果我也弄到蘆薈,李春芽的手不是很快就可以好了嗎?我眼睛一亮,興奮起來。接下來的課堂,我一直在琢磨蘆薈的事情。
當時農村艱苦,吃都緊張,沒人養花養草。至于蘆薈,我壓根就沒見過。查新華字典,字典里有“蘆”這個字,解釋的詞條卻是蘆葦。我再查“薈”,解釋的卻是薈萃。我問了好多同學,他們也不知道蘆薈。不過王宏斌告訴我,語文老師有一本大字典,興許里面有,可以查一查。
我編造了一個學習上的理由,問李老師借來了那本大字典,一查,居然真有,還配有蘆薈的簡圖。文字里也明確說了,蘆薈有消炎的作用。我心里大喜,像是看見了一道曙光。可是,到哪里去找蘆薈呢?
農村顯然沒有,學校也沒有。唯一的希望,就是去鎮上看看。為了保險起見,我特意找來一張白紙,把蘆薈的簡圖畫了下來。
放學后,我向鎮上飛跑而去,跑到鎮上,已是大汗淋漓。我脫掉衣服,先在湑水河里洗了個澡,然后去衛生所、供銷社、鄉政府看了看,都沒有我要找的蘆薈。我想不明白,這么好的東西,為什么就沒人種呢?
反過來想,沒人種,不正說明其稀奇珍貴嗎?稀奇的東西必定神奇,有特殊的療效。這就等于說,書上的說法是可信的。
我精神高漲,繼續在鎮上游蕩,眼睛像獵犬一樣機警地搜尋著,心里念著:蘆薈,蘆薈。希望有奇跡出現。
整個桔園鎮都被我轉遍了,依然不見蘆薈。
我意識到,必須得冒險,去791部隊看看了。
791部隊在鎮西的伏牛山山腳下,大鐵門常年有警衛把守。聽人說,那里面很大,有秘密的山洞,里面裝著槍支彈藥。
來到791部隊的大門口,看著筆直的警衛,我心里“啪”地一聲,似乎是一只蒼蠅被人打住了,驚慌又絕望。
如何才能進去?繞到后面爬圍墻,這是個辦法,卻太冒險。我個子矮,況且不清楚里面的布局,說不定剛跳下去就被人家活捉了。
做賊心虛,怕警衛員留意到我,我躲到側面的角落里想辦法,做思想斗爭。
很快,過來幾輛牛車,上面裝著石頭。部隊里面常年有土木工程,我快步跑上去,給一位農民老伯推車,假裝是他的孩子,混了進去。
我心懷忐忑地四下張望,里面有許多紅磚砌就的樓房,高大、氣派,多是三層四層。我舉棋不定,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去。
我琢磨,軍營里肯定沒有蘆薈,必須找家屬區。我開始留意哪有女人,哪有小孩,走走停停,心虛得不行。后來,我終于找到了家屬區,有三四棟,皆是三層高的青磚樓房。我尋來找去,阿彌陀佛,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一家二樓住戶的陽臺上,豁然出現了一盆蘆薈,肥厚碧綠的葉,小劍一樣舒展著,讓我眼里放光。我拿出簡圖,就像是拿著一張尋寶圖,正兒八經地比對著,沒錯,就是我要找的寶貝。
登門討要顯然不可能;爬樓,高雖不高,卻不實際,大白天,被人看見怎么辦?
于是,一個念頭在我心里冒出來,那就是等天黑再行動。
里面有竹林,我貓到背人處,折來一根長竹竿,又在竹竿的頂端破了口,弄成一個夾子的結構。我打算用竹竿把蘆薈葉夾下來幾片,神不知鬼不覺的,住戶應該不會發現。
等到天黑,各家住戶的燈陸續亮了起來,小區里并沒有閑人走動。我躲在樓下的樹影里,心突突直跳,生怕有住戶會突然出來。因此我輕手輕腳,盡量不發出聲響。
我的計劃基本可行。只是夾子有點軟,要把柔軟的蘆薈葉子取下來并不容易。為了增加力量,我不得不旋轉竹竿,左右扭動。
終于,我取下來了兩片蘆薈,心里好激動。
取第三片時,由于扭動的力量過猛,把旁邊的一個小花盆碰了一下,只見一個黑影墜落下來,我本能一躲,頭躲過了,卻“砰”地一聲砸在了我的腳背上。我顧不上疼痛,扔掉竹竿,落荒而逃。
我一口氣跑出很遠,心都快跳出了,感覺隨時會被人甕中捉鱉。
出大鐵門時,我以為警衛會盤問我,可是沒有,就好像我不值一提,一只流浪貓而已。
出了791部隊,我長舒一口氣,這才意識到腳上的疼痛,肚里的饑餓。我,狼狽不堪的我,總算勝利而歸了。
第二天,我的腳腫得像一塊饃。我一瘸一拐地,把三片蘆薈葉送到李春芽家。我自信滿滿地對李春芽說,這蘆薈葉很神奇的,把汁液涂在傷口上,很快就會好的。李春芽將信將疑,問我,這玩意是從哪里弄來的?我沒有說,也沒告訴她我腳瘸的原因,只是說不小心把腳扭了。
幾天后,我問李春芽,手好些了沒有?李春芽說,好些了,你看,新肉都長出來了。我好高興,感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可春芽接著又告訴我,那三片蘆薈葉,她壓根就沒用。因為她媽媽問了醫生,醫生說了,蘆薈不是藥,只能起輔助作用,還是用云南白藥可靠一些。
那一刻,十三歲的我,恨恨地把我的瘸腳又跺了一下。一股錐心的疼痛,蔓延了我的全身。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我為什么要流淚。
四
有年夏天,我大概八歲的樣子,自家場院里曬著麥子,媽媽扛上鋤頭干活去了,讓我在家看著,怕雞鴨及鳥雀偷吃。
那些年,吃上饅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麥子和稻谷都很珍貴,真是“粒粒皆辛苦”,被雞鴨鳥雀偷吃了會很可惜。因此我也聽話,寫完作業,就坐在門墩上,老老實實看場,也不出去瘋跑。
這期間,鐵牛劉棗王安斌來找過我,邀我和他們一起出去玩。我當然也想出去,但考慮到麥子、饅頭,媽媽交給的任務,我還是拒絕了。他們走后,我有些失落,看著天空發呆,在一篇叫《饃饃》的散文里,我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我無聊地看著天空,看著看著,在云朵里看見了饃饃:
那么大的饃饃!那么白的饃饃!那么多的饃饃!
我這樣寫,雖有夸張的成分,但情緒是少年的情緒,有一種很美很悵惘的向往。
終于有一天,媽媽說該曬的都曬干了,不會生蟲了。我舒一口氣,自由了,可以和小伙伴們出去瘋跑瘋玩了。
夏天,我們最愛的便是游泳。怎么學會的,我忘記了,反正在水里撲騰撲騰著就學會了。
我們年齡小,只敢在河邊游,深水區是不敢去的,大人也明令禁止,說你不想活了你就往里面游吧,那里面有水鬼。我們雖調皮,安全意識其實還是有的,什么地方該去什么地方不該去,我們有自己的尺度。
在淺水區,其實更有意思,可以站在水里撲騰,打水仗,或是笑嘻嘻地做游戲,我們都光著屁股,享受著美好的天賜時光。
除了在河里游,我們有時也去池塘游,池塘是死水,游起來會困難一些,因此是我們的第二選擇。但池塘里有小魚小蝦,還有菱角,我們可以比賽抓魚抓蝦,找菱角。
有一天,我和鐵牛鬧了矛盾,他偷偷串聯劉棗和王安斌,吃完早飯就出去尋豬草了。前一天說好的,我吃完飯去找他們,可他們都跑了,分明是在整我。我想提著籃子去湑水河灘找他們,但心里又咽不下這口氣,折轉身,我一個人去了坡上。
坡腳有個池塘,有三四畝大小,會把下雨時從坡上流下來的雨水收集起來。池塘邊歪歪斜斜長著幾棵柳樹和苦楝樹,這個地方我們經常來,除了游泳,我們在柳樹下打牌,爭論前些天看的電影里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比誰厲害等等在我們看來很重要的事情。
那天我一個人,心情郁悶,我挎著籃子,在玉米地里尋豬草。突然,胡小山跑了過來,要我和他去池塘里游泳。胡小山比我大一歲,他家住村頭,我們平時并不來往,我說,我還尋豬草呢。胡小山說,他待會幫我,這么熱的天,游一會吧,你教我。
我這才知道,胡小山不會游泳,或者說他游得不夠好,不敢單獨游。他讓我教他,我無形中成了老師,這升起的成就感,使我改變主意,答應了他。
衣服脫光,我們噗通跳了下去。
池塘邊是慢坡下去的,池塘里的水也不算深,到了中間,水也就到我們脖子,因此我們并不擔心,開開心心玩了起來。
或許正是因為胡小山不會游泳,我的虛榮心在作祟,我告訴胡小山,你水平不行,就老老實實在岸邊游,我去中間游會兒,馬上過來。
胡小山看我能去、他不能去,有些不高興,但還是答應了。
我潛到水里,像一個重任在肩的密使一樣往深水區挺進。我像一條鯨魚,在水里鉆出鉆進。
我正游得美,聽到胡小山在叫我,我扭頭一看,他在離我十幾米開外的地方掙扎。我趕快往他跟前游去,剛到他身邊,他一把抓住我,把我壓在了他身下。
我被他壓著,沒有反抗的余地,我只有往岸邊游,使勁地游。所幸的是,離淺水區并不遠,我們獲救了。
上到岸上,我們都不說話。我生氣他壓我,他后怕剛才的一幕。太陽就在頭頂,熱辣辣的,我們都不說話,似乎在回味,回味剛才那可怕的一幕所散發出的死亡氣息。
我們一直沒有說話,我甚至也沒有抱怨他。我們離得很近,可都覺得孤單。
我想盡快離開這里。我走出十幾步,他跑過來,把手掌壓在我的耳朵上,神秘又恐懼地說:回家不要告訴你媽。
我當然不必聽他的。但我還是按他說的那樣去做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至今我母親也不知道這件事情。我想他回家后也沒敢把這件事告訴他媽,他母親同樣不知道那件事情。我們把一個秘密,吞進了肚里,永遠藏在了池塘里。
有一年,我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了胡小山。我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當年我救他的那件事情。他沒有說,我也就不必提,就好像壓根沒發生過似的,我們隨便聊著,聊世俗的生活。
五
今年,我四十六歲,依然熱衷寫成長故事,熱衷去露天水域游泳,這多少被人嘲笑,天真也罷,土氣也罷,我的確有些不合時宜。我向來覺得,成長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迷戀的,并非回憶,而是我踩出和未踩出的那些可能。就說那個夏天在池塘發生的事情,我后怕嗎?當然。但依然讓人留戀。那個八歲的少年,他聽到同伴的呼聲沒有任何猶豫和權衡,他向他游去,不懂得如何救人,卻還是稀里糊涂地救了同伴。這要放在今天,以新聞的方式曝光出來,我,也算個小英雄哩。
———我這樣安慰自己,其實,不過是在說服自己,我確實被死神吻過額頭,他的樣子太嚇人,讓人喘不過氣來——但他最終還是饒了我。我才有機會,把這些純真故事講給現在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