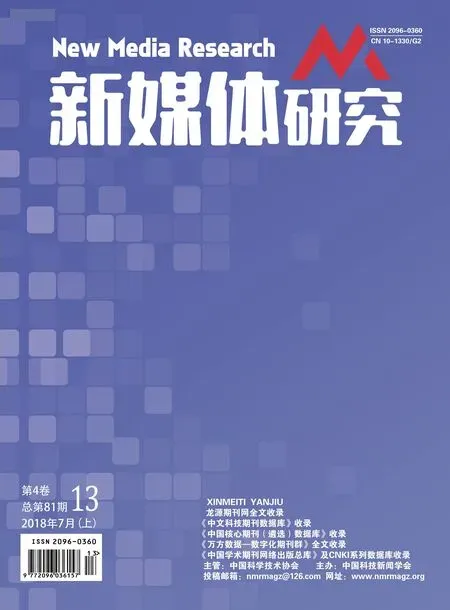“全民表演”:社交軟件中“打卡學習”行為動機研究
閆明


摘? 要? 用新聞傳播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對于調查問卷結果進行量化分析,結合一系列新聞傳播學相關理論,分析出“打卡學習”用戶的動機,并對于問卷中呈現的各方面特征進行總結,旨在為用戶由于外部自我形象呈現而形成的“全民表演”性質的“打卡學習”行為提出發展的合理建議。
關鍵詞? “打卡學習”;新聞傳播學理論;“全民表演”;動機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9)13-0054-02
1? 研究意義及方法
“打卡學習”這一行為能夠短時間內迅速火爆,將絕大多數人的朋友圈霸屏,可謂網絡傳播中成功的營銷手段。但這一現象也引起了很多爭議,隨著微信官方對這類現象的治理和打擊,“打卡學習”這一行為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在“打卡學習”這一網絡傳播行為背后蘊含著著豐富的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以及符號學內涵,并折射出網路傳播者“受眾者為中心”傳播理念的演變與網絡文化的傳播心理階段性轉變[1]。本文將以社交軟件中的“打卡學習”行為作為切入點及研究出發點,進行問卷調查,獲取“打卡學習”行為的用戶心理、動機、自我滿足等方面的數據,配合運用文獻研究法,將所得數據與傳播學、心理學、行為學等相關理論進行聯系。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獻研究法、問卷調查法,并做出以下假設:
H1:每次進行打卡學習所花費的時間越長與堅持打卡的天數呈顯著正相關;H2:男性和女性在“打卡學習”實現自我管理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
本研究通過在“問卷星”網站平臺發布調查問卷,并利用數據分析服務進行相關數據整理和分析。依托問卷星網站考察了182個抽樣對象,獲得有效問卷182份,其中有過“打卡學習”行為的為117人。
2? 相關性分析
我們根據提出的假設1:每次進行打卡學習所花費的時間越長與堅持打卡的天數呈顯著正相關,對于兩者進行相關性的檢驗。通過皮爾遜系數檢驗,我們得到表1。根據表中數據可得,P<0.01,因此兩者成顯著相關關系。在通過觀察影響系數(0.262)為正數,可以得出“您打卡學習行為堅持了多久”與“您每次打卡學習所花費的時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3? 獨立樣本T檢驗
根據我們提出的假設2:男性和女性在“打卡學習”實現自我管理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結合問卷,我們認為問卷中的5個題項構成了自我管理這一特征。因此以李克特量表的特點,我們把5個題項與性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根據表2的結果,這5個題項的P值均小于0.05,因此說明男女在這5個題項中的表現具有顯著性差異。再比較男性和女性在這5個題項中的均值,可以發現女性的均值全部高于男性,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男性和女性在自我管理上的存在差異,女性通過打卡提高自我管理水平的意愿更加強烈。
H2成立。
4? 研究結論及“打卡學習”的影響
1)積極影響:自我成就的滿足與堅持效應的產生。在我們的數據分析中,我們驗證了假設1,即人們每次打卡學習所花費的時間與用戶的堅持打卡時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這也說明了用戶在進行打卡活動中,一直在努力堅持,不斷進行自我激勵,通過自我成就的滿足,使得“打卡學習”這一網絡傳播行為激發了堅持效應。
2)積極影響:用戶通過“打卡學習”實現自我管理。我們通過調查可以發現,用戶十分注重打卡的實用性功能和學習效果的提升,注重考試和碎片化時間的利用,這些都有助于自我管理的實現。并且通過H2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驗證男性和女性在自我管理上的存在差異,女性通過打卡提高自我管理水平的意愿更加強烈。
3)消極影響:自我形象的外部呈現使用戶無法安心聚焦。通過我們的研究發現,打卡的用戶很大程度上有外部自我形象構建的需求,并且在這一方面女性大于男性。這也與我們本章的標題相契合——“全民表演”。“打卡學習”更像是在演戲,一方面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學習,為自己打造“學霸”的人設;另一方面也是在對自己演戲,讓自己心安理得地投入到打卡學習的社交性中,是自己滿足于自己的時間管理。這種表演是在不斷強化并重復的,像是一種勸說與說服,告訴別人我在學習,告訴自己我在學習。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說,“整個世界是一座舞臺,所有男女不過是舞臺上的演員”,社會情境中的人類行為總是有表演的成分,即使我們相信自己是最本能和最真誠地對他人進行反應[2]。
4)消極影響:“返現”等獎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對用戶形成了過度刺激。商業化氣息過于濃厚也是“打卡學習”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在我們的調查中也可以發現很多用戶是基于有朋友圈打卡的獎勵,才進行打卡學習的。這種行為其實是部分商家以利益為誘導使用戶分享,會給朋友圈帶來不良的使用體驗,也會使用戶的學習行為過于功利化而忘了初心,甚至于迷失方向。
5? 對于“打卡學習”的建議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朋友圈“打卡”這種方式來堅持。想讓用戶長期堅持一件事,比如閱讀或運動,養成好的習慣,應該讓用戶真正喜歡它們,從中體會到樂趣,而不是拘泥于形式。只有內部動力才是最持久、最有利的,外部的激勵只能作為輔助手段,不能完全依賴。從“打卡學習”在朋友圈盛行看來,這已經是一種借助網絡傳播的特殊營銷手段,但我們也要意識到網絡傳播既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在網絡傳播中“以受從為中心”的傳播理念將成為現實。網絡傳播增強了受眾的主體意識,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獲取信息,并判斷信息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不再盲目地受傳播者的灌輸和支配[3]。但打卡行為是否真的是由受眾占主體呢?答案是否定的。可見受眾與傳播者并沒有實現主體地位,完全沒有傳播自由可言。因此我們建議要認準傳播者的主體地位,讓“打卡學習”不再是強迫性的,而是完全的自愿性質的。
參考文獻
[1]鄧銀華.微信朋友圈大學生用戶信息分享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D].湘潭:湘潭大學,2015.
[2]岳山,李夢婷.表演與互動:網絡運動場上的人際傳播——以微信朋友圈“運動打卡”實踐為例[J].新媒體研究,2018(12):8-9.
[3]趙志立.網絡傳播條件下的“使用與滿足”——一種新的受眾觀[J].當代傳播,2003(1):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