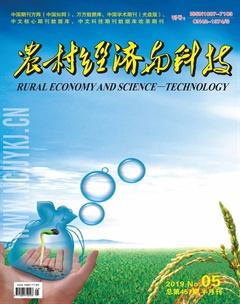我國突發性環境監管問題與對策
麻濤
[摘要]2018年11月4日,福建泉港發生大范圍碳九泄漏,造成港口周圍海域污染,同時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部分人群身體損害。責任主體卻在事故中隱瞞實際污染泄漏量,嚴重影響后續的清除安排,暴露出我國在突發性環境監管中存在配套環境污染監管制度不完善,信息公開不全面等諸多問題。
[關鍵詞]碳九泄露;環境監管;海洋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X83[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2018年11月4日凌晨,福建泉州碼頭一艘石化運輸船發生碳九物質泄漏,69.1t碳九產品流入海洋中,造成水體嚴重污染。次日,泉州區農林水局發布《關于暫緩起捕、銷售、使用轄區肖厝村海域水產品的緊急通知》,但未對碳九泄漏之事進行詳細的信息公開,而是由區環保局于4日緊急發布關于碳九泄漏事件處理情況通報,通報中稱天桐#1與碼頭連接軟管處發生泄漏,共造成6.97t碳九泄漏,并稱下午4時左右已基本完成清理工作。但11月25號福州市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卻指出實際泄漏量達69.1t。事后查明是東港石化公司故意隱瞞實際泄漏量,并要求企業中層以上員工統一口徑。同樣的事情在2011年的渤海灣漏油事件中也曾發生,康菲公司在處理漏油事件中一開始也隱瞞實際泄漏量,直到最后無法隱瞞了才公開了實際泄漏量。為什么類似的事件都過去了將近8年,在突發性環境污染問題管理上還是存在各種問題,行政機關難以第一時間取得污染的確切材料,對后續的賠償以及修復產生不小阻力,暴露出我國在突發性環境監管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2 福建碳九泄漏事件暴露出我國突發性環境監管方面的問題
2.1 監管體系混亂,信息公開前后矛盾
福建碳九泄漏事件牽扯到很多監管組織,如區環保局、區農林水局、區政府,但是它們處理泄漏事件缺乏聯防聯控,并沒有體系化的應對災情。如環保局在4日發布緊急通報稱泉州天桐#1與碼頭處發生碳九泄漏,大概6.97t,于下午4時基本清理完成,但并未對碳九物質危害性進行說明,而區農林水局與次日只是發布了關于水產品暫緩銷售的通知并未對相應的原因進行細述,區政府于11月25日記者招待會上公布的實際泄漏量高達69.1t則明顯于之前區環保局公布的6.97t有巨大的差距,讓人很難信服之前區環保局說的于11月4日下午4時基本完成碳九清除工作。
2.2 環境主管部門環境監測滯后
福建碳九泄漏后第一時間并不是由專門的監管機構對泄漏情況進行檢測,而是由污染責任人東港石化公司提供的相關材料推導出泄漏量6.97t。責任人東港石化公司為了減少自身責任,強制要求企業中高層員工統一口徑,這種行為阻礙了專門清除人員對于災情的預判,對后續的油污清除產生很大的影響。而區環保局就采用東港石化公司提供的泄漏量并通告,可見災后政府監管組織并未在第一時間自行對災區進行油污泄漏檢測,其實際泄漏量69.1t應當是在后續清理時才發現的。兩者巨大的誤差,讓人們對政府后續的清理修復工作是否屬實產生猜想,嚴重影響政府信息的公信力。
2.3 災情缺乏后續監管
11月25日福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災情做了官方通告,27日福建檢察院以涉嫌重大污染事故罪將東港石化公司涉案人員依法批捕。而對于受損的海域只是對其中的水質進行了檢測,以水質標準來確定污染的清除情況。碳九是一種復合型化合物,經裂解很容易致癌,大面積的碳九泄漏肯定會對港口的海洋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其中的海產品、微生物群落等都會產生影響。水質的恢復并不代表著生態環境的恢復,可是政府監管部門并沒對該海域后續監管及后續修復監管等工作做出聲明。
3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相關經驗及啟示
3.1 政府主導修復體系
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雖然和我國此次福建碳九泄漏事件有一定的區別,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是跨國油污泄漏事件,處理起來比我們的更加復雜。美國在油污泄漏的第一時間由16個聯邦政府組成應急指揮中心,協調各個州縣對于油污的處理方式及協調工作。事故當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即要求調查機構限期提交事故調查報告,將災情的具體情況向民眾公告。美國政府同時要求責任主體英國石油公司加入后續清理中,由英國石油公司建立200億美元的賠償基金,整合責任人、政府組織以及群眾力量系統的對災情產生的污染進行清理。
3.2 監管機制嚴謹、信息公布到位
美國在墨西哥灣漏油的第一時間組織專門的災情調查組織,限期一個月對災情的具體情況、數值、污染范圍等等信息做出具體的匯報,這也是后續責任人賠償的主要依據(美國的《石油污染法》是以責任人泄漏的石油桶數來計算賠償數額)。在后續的清理環節中,美國政府開設了專門的信息公開平臺,每日向公眾會報油污清理情況以及海域的生態環境損害情況,甚至連對候鳥等遷徙情況的影響都有相應的信息匯報,使清理情況處于完全公開的狀態。
3.3 建立賠償基金會用于后續賠償
英國石油公司在一開始提供了價值200億美元的基金會用于災后重建的基礎上,再次向基金會投入一筆巨資用于后續對海域生態環境重建。在基本處理完墨西哥灣泄漏的石油后基金會致力于對墨西哥灣周邊受損的海洋生態環境的修復,由專門的監管組織對周圍的海域進行檢測,通過一定手段對破壞的海洋生態環境進行恢復,持續一段年限,其所有的后續監管費用都由基金會支出。
4 我國環境監管制度完善的對策
4.1 落實環保組織主導的聯防聯控監管體系
泉州市環保局在2012年出來《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以下簡稱預案),《預案》通過災情來劃分等級,不同的等級其主管部門也有所區別,《預案》原則為:統一領導,分級響應,屬地為主,積極配合,部門聯動,地域合作。但《預案》的法律層級較低,而各部門之間又屬平級,各部門主管在事件中缺乏聯動,與《預案》原則有一定差距。在2015年出臺的《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關機辦法》第四條中則規定縣以上環境保護部門應當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對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日常工作實施監督管理,其將政府部門設定為主導單位,這就造成在一些環境突發問題中,因主導部門沒有明確的規定,缺乏聯動。政府部門在應對突發性環境問題上并沒有環保部門的專業基礎,政府部門主導下是以各職能部門提交的信息材料作為指導依據,缺乏對材料的核實,會出現實際情況與政府得知的情況不符的現象。美國治理墨西哥灣的相關經驗,與我國在碳九泄漏后政府各部門的實際監管相比較,不難發現在監管體系上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國實際監管中各個部門單獨實施各自部分責任,監管信息通知上存在矛盾、差異,難以滿足監管的實際需求,因此需要建立明確的監管體系,由專業的組織作為主體統籌監管的進行。美國由各個州縣推選代表組成專門的指揮中心來對漏油事件進行處理,而我國由于國體的限制,不存在州縣制度,但是在實際執行中美國的州縣可以對應我國的各個行政單位如衛生局、環保局等。在災害發生時各個行政單位承擔著各自的監管責任,并對外單獨作相關通告,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矛盾、分歧,無法滿足聯動監管原則,反而使民眾對政府的監管能力產生質疑。因此,在災害監管時應當形成體系化管理方式,先明確環保部門在事件中的主導地位,各個分管部門同時配合環保部門展開修復工作,由環保部門結合各個行政單位監管的信息統合后綜合得出全面的信息,并結合災害的實際情況向民眾提供最真實、具體和有用的信息,避免各部門之間信息混亂、延誤,使民眾可以在第一時間了解到災害的情況,以及各組織在災害中承擔的責任,避免責任重疊以及監管任務的遺漏,而政府則作為環保部門后的監管組織在整個應急環境事件中做一個監督者監督環保部門在事件中的行為。
4.2 形成新型監測模式
《預案》第四章第二十六條規定:獲知突發環境信息后,縣級以上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當立即組織排查污染,初步查明事件的發生時間、地點、原因、污染物質數量、周邊環境敏感區等情況。而在福建碳九泄漏事件中,區環保局以責任主體向相關機構匯報災害情況為依據發表了通告,其中存在的問題實在耐人尋味,究竟是區環保局在實際檢測時存在漏洞,直接采用了責任主體提供的相應數據,還是因為區環保局害怕自己管理的區域內發生重大突發環境事件,害怕承擔過重的責任而有意少報污染泄漏量。不論是以上哪種原因都對后續的修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傳統的監管模式需要革新。美國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會組織相應的專家調查組對災害情況進行監測,全方位了解災害情況,我國未來的監管模式應當也要向其靠攏。應當由專家組、責任主體以及災害當地的一線居民共同組織監測小組,對災害實際情況進行監測,得出全面的災害統計報告,避免因為監察災害信息上存在問題而影響了后續的行動。
4.3 制定后續長期監管制度
《預案》第五章事后恢復只是粗略的對規定由縣級環境主管部門參與恢復工作,并沒有對恢復后是否需要在一定期限后進行生態修復評估做規定,也未對后續生態恢復監管做出規定。由于受到民法恢復原狀思想的影響,我國在環境修復中形成一個慣性思維,認為對受害環境進行污染清除、損害賠償以及修復后,各項指標達到相應標準,就不需要再對受害環境進行后續監管和環境評估,但是環境問題與傳統的民法問題不同,生態系統不是具體的物,它不存在正真的“恢復原狀”,而是盡可能的恢復到受損之前的情況,這就存在一個后續監管的問題,修復后生態系統是否可以繼續正常運轉,修復后的生態修復的生態價值是否產生影響?這些都是需要長期的監管的,需要對后續的水質及生態環境情況做詳細的監測,以及后續修復金使用的監管問題。
單純依靠責任主體的力量應對生態環境損害責任是不現實的,其往往無能力應對如此重大的責任,應當引入社會救濟機制對損害進行救助,成立相應的生態損害修復救濟基金,由責任主體每年按照相應的比例向基金會注資以及政府組織和社會組織向基金會注資維持基金會的長期運行,持續對災害區域進行后續的修復。因此,需要建立專門的后續監管制度對基金的使用及后續環境修復的監管進行監督,引入專門的管理人員及當地民眾加入到后續監管體系中來,實現對受災環境的長期監管和修復。
5 結語
突發性環境監管貫穿于突發環境問題的始終,從預防到清除、賠償、修復以及事后服務都離不開環境監管,體系化的監管模式,明晰的監管責任有利于監管的實施,制定新型監管方式,有利于環境損害后續的工作開展,而事后的長期環境監管可以避免因為環境破壞問題滯后性的原因而引起的后續問題。
[參考文獻]
[1] 何育妍.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中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探討[J].新余學院學報,2017,22(02):97-99.
[2] 殷建平,任雋妮.從康菲漏油事件透視我國的海洋環境保護問題[J].理論導刊,2012(04):91-92+95.
[3] 張麗軍.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應急監測研究[J].資源節約與環保,2017(09):41-42.
[4] 陳偉錦.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應急處理措施研究[J].環境與發展,2017,29(10):62-63.
[5] 蔡靜,李敏.突發性環境事件應急監測現狀分析及建議[J].綠色科技,2017(14):146-147.
[6] 阮志華.淺談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監測要求[J].環境工程,2014,32(S1):808-809+814.
[7] 呂忠梅.“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法律辨析[J].法學論壇,2017,32(03):5-13.
[8] 萬本太.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技術[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
[9] 羅光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由誰管?怎么管?——基于地方探索實踐的一些思考[J].中國生態文明,2018(04):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