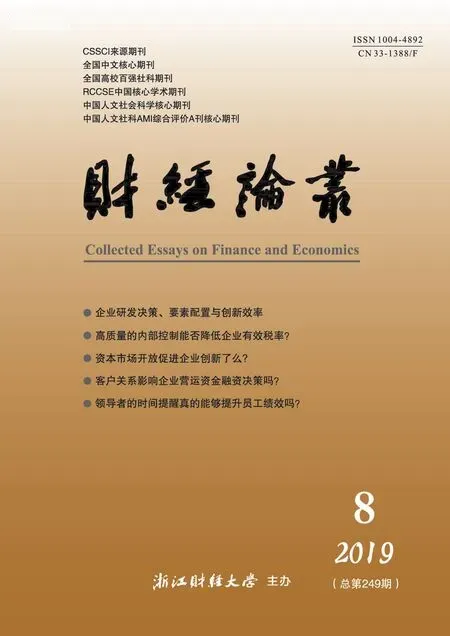農業技術支持、生產行為規范性與農產品質量提升
明 輝,漆雁斌,鄧 鑫
(1.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2.四川農業大學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 言
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行為的規范性直接決定初級農產品質量的高低。農業標準為農產品生產提供科學、規范的技術支持,降低機會成本,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技術標準的積極推廣有助于實現農業標準化生產和智能化監管,促進農產品品質的提升。現階段,我國農業技術支持的供給和需求呈現多元化特征。首先,為破解投入成本低、見效快且使用簡單技術來提高產量的“生產方式鎖定”問題,部分風險偏好型農業經營主體產生主動獲取先進農業技術的需求,其技術選擇偏好、強度和效果與通過參加政府組織的培訓等被動方式獲取農業技術的經營主體存在顯著差異。其次,作為農業技術支持的重要載體,公益性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正積極利用各類農業科技資金投入整合多種科技創新資源,以促進農業生產規范化,產生直接和間接的提質效應。而通過培育科研機構和農業企業成為技術市場主體,建立有效的經營性農業技術成果轉化機制,則有助于改善有效供給、刺激有效需求。最后,異質性農業經營主體在技術獲取渠道、內容和成本接受度等方面呈現不同特征,產生不同的提質增效效應。那么,這些多元化的、不同類型的技術支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農產品質量?技術支持是否規范了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行為?生產行為規范性在不同類型的技術支持與農產品質量提升之間是否發揮顯著的中介效應?對上述問題的深入分析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進一步厘清技術供給、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行為規范性與農產品質量之間的聯系,揭示不同技術支持渠道的管理效率,驗證生產行為規范在技術支持和農產品質量提升間的中介效應(尤其是不同生產環節上的中介效應)。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技術、生產行為規范和農產品質量提升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結論:第一,農業技術和標準的制定與實施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農業技術在高產優質農產品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投入品類、標準法規類、生產過程控制類和生產地環境保護類技術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主要決定因素[2]。種養殖技術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可保證地理標志農產品質量,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3];第二,合理的治理模式和組織方式能規范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行為,從而提升農產品質量。供應鏈內部協同是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根本[4]。不同組織和模式的培訓均可降低種植戶農藥過量施用水平,而村委會組織的培訓和田間指導的培訓效果較好[5]。通過合作社實施的農業標準在農業技術推廣中發揮重要作用[6]。但奧地利葡萄酒市場的經驗證據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合作社提供較低質量的葡萄酒[7];第三,農業經營主體采納與否是技術標準實施和作用發揮的關鍵因素。農業標準提高幅度較小時激勵農戶生產安全農產品[8]。特色種植農戶對不同技術供給模式的采用效率具有差異性[9]。芬蘭有機耕作技術相關選擇因素的迭代分析結果顯示,集約化畜牧生產和勞動密集型生產降低改用有機農業的可能性[10]。只有限制技術變革產生的收益向下游轉移,才能改善坦桑尼亞湖區小規模棉農的收入和福利,并增加社區收入[11]。
前述研究較為系統、全面,為本文提供堅實的分析基礎,但仍存在一些尚待繼續探討的問題:一是對農產品質量的界定和分析較為單一,主要聚焦于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缺乏在外觀、品質和安全等多重屬性空間下的綜合分析;二是沒有從生產行為規范性角度分析其在技術支持和農產品質量提升間的中介效應,也未厘清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機理;三是經營性技術支持的相關分析較少,未區分主動和被動獲取農業技術的差異,導致技術支持政策制定的非“精準化”;四是對新型主體和普通農戶在農業技術支持、生產行為規范和農產品質量提升方面的差異研究較少,可能導致某些已實施的農業技術支持政策缺乏效率。為此,本文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三、研究假說和模型設定
(一)研究假說
1.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在農產品質量升級的關鍵階段,有效的農業技術支持可優化資源配置,發揮“工藝創新效應”,形成技術資本[12]。因此,農業技術支持在理論上對農產品質量提升具有正向效應,但可能因農業技術支持類型的不同而產生差異。為此,我們設定如下的五個假設:
H1a: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
H1b: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
H1c: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
H1d: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
H1e: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
2.農業技術支持對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作用。在農業技術推廣中,農戶需要的是集技術、管理和經營能力于一體的農業知識體系,標準化是這種知識體系的最佳載體。由于農業經營主體的技能水平不同,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技術含量和要求不同,現實中可能出現生產行為的異化現象。若加上生產行為規范性的激勵監管機制不足導致的道德風險,該異化現象必將被放大。為此,我們設定如下的五個假設:
H2a: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生產行為。
H2b: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生產行為。
H2c: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生產行為。
H2d: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生產行為。
H2e: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生產行為。
3.生產行為規范性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與施用化肥相比,施用生態肥促使農產品質量提高,實現農業系統和自然系統的良性循環[13]。田間管理的規范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產品的質量[14]。農藥施用的標準化大幅度提高農產品質量[15]。合理的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對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6]。為此,我們設定如下的四個假設:
H3a:施肥規范性有助于農產品質量提升。
H3b:田間管理規范性有助于農產品質量提升。
H3c:用藥規范性有助于農產品質量提升。
H3d:生態保護規范性有助于農產品質量提升。
4.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中介作用。農業標準通過應用推動農業發展,農業科技通過農業標準使其內能的釋放發揮到最大[17]。規范的生產行為可在農業技術支持提升農產品質量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為揭示不同類型農業技術支持的中介效應差異性,我們設定如下的五個假設:
H4a: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通過規范生產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
H4b: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通過規范生產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
H4c: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通過規范生產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
H4d: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通過規范生產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
H4e: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通過規范生產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
(二)模型設定
1.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總效應和相關作用。我們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總效應、農業技術支持對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作用及生產行為規范性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具體模型如下:
(1)
模型(1)主要用于檢驗H1a~H1e,考察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其中,n表示質量等級,quality表示質量,techsupport表示農業技術支持類型,α表示截距項,β表示斜率系數,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ε表示隨機擾動項。
(2)
模型(2)主要用于檢驗H2a~H2e,考察農業技術支持對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作用。其中,n表示生產行為規范性等級,normality表示生產行為規范性。
(3)
模型(3)主要用于檢驗H3a~H3d,考察生產行為規范性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
2.農業技術支持通過生產行為規范性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中介效應相關模型如下:
(4)

四、樣本數據、變量設定和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數據
本研究的基礎數據來源于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調研團隊在2016年8月~2017年2月對四川獼猴桃主產區種植戶開展的問卷調查。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的概率抽樣方法:選擇四川獼猴桃主產區域作為初級抽樣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PSU);隨機選定村作為次級抽樣單位(Secondary Sampling Unit,SSU);在每個村,通過獼猴桃技術專家選取部分質量認證的典型種植戶;采用簡單隨機抽樣方式,選取若干普通種植戶,與前述的典型種植戶一并構成樣本對象。調查區域覆蓋19個鄉鎮、44個村,共回收問卷351份,剔除填寫不完整的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27份。
(二)變量設定
1.因變量。部分學者從農產品的品質角度衡量農產品質量。Gillmeister和Buccola(2013)的研究表明生鮮乳生產者將根據市場需求調節乳脂、水分和非脂乳固體的含量[20]。借鑒耿寧等(2016)的處理方法[21],本文在梳理多個四川省無公害獼猴桃生產規范文本后,將外觀、品質和安全三個維度確定為獼猴桃質量屬性空間,并進一步明確質量控制的若干關鍵點及其評價標準,以關鍵點的達標程度刻畫農產品質量水平。其中,外觀包括是否損傷和果實縱徑兩個關鍵點,品質包括單果重量、酸度、維生素C含量和可溶性固形物占比四個關鍵點,安全包括農殘快檢這個關鍵點。當種植戶銷售驗收時某一關鍵點達標,其指標取值為1,不達標則取值為0。然后將所有關鍵點數量進行累加,構建綜合達標指標。
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樣本地區獼猴桃的質量達標程度總體上較低,表明質量還有較高的提升空間。其中,安全達標程度最好,外觀次之,品質最差。但安全達標程度的變異程度最大,種植戶質量安全達標的程度參差不齊,表明通過較長時期的治理,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提升較大,但實踐中該類治理呈現較顯著的區域性特征(1)限于篇幅,農產品質量達標程度的描述性統計已略去,作者備索。。
2.自變量。農業技術支持是農產品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嘗試從農業技術支持的主動和被動層面、經營性和公益性技術供給層面及新型主體層面進行深入分析。第一層面,通過調查問卷中“哪些種植環節咨詢了專家”的問題,獲取種植戶主動采納技術的相關信息。備選項包括“品種優選”“規范建園”“果園生草”“配方施肥”“授粉”“修剪”“灌水”“病蟲害防治”和“采收”共9項,構建“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自變量,將種植戶選取的總項數作為變量的取值。通過問卷中“過去一年參加過多少次技術培訓”的問題,構建種植戶“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自變量,將技術培訓的次數作為變量的取值。該層面的分析旨在探索農業技術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異及兩類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效應。第二層面,劃分經營性技術供給和公益性技術供給的步驟為:(1)問卷中詢問種植戶在“種苗”“施肥”“田間管理”和“病蟲害防治”4個環節中哪些生產環節實現了統一,并要求填寫統一的供給方,供給方的備選項包括“園區”“合作社”“龍頭企業”和“政府或第三方組織(如農技站、農發局和農業技術協會)”4個主體;(2)將每一個環節中種植戶填寫的單項或多項供給方按照4個主體分別進行匯總,如種植戶在“田間管理”環節選擇“合作社”和“龍頭企業”,則合作社和龍頭企業在該環節給予該種植戶的農業技術支持各計1次;(3)將每一個環節中合作社提供農業技術支持與該農戶參加合作社的收費進行匹配,篩選出“收費合作社”,獲得收費合作社農業技術支持的種植戶賦值為1(2)調研顯示,收費合作社往往提供更新、成效更顯著的種植技術。,其余的賦值為0。類似地,將每一個環節中從“園區”和“龍頭企業”獲得農業技術支持的種植戶賦值為1,其余的賦值為0。最后采用并集方式將前述兩個變量合并,構建生產環節“獲得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虛擬變量;(4)將每一個環節中從“免費合作社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和“政府或第三方組織”獲得農業技術支持的種植戶賦值為1,其余的賦值為0,構建“獲得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虛擬變量。該層面的分析旨在探索經營性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效應。第三層面,在第二層面的基礎上,將每一個環節中從“園區”“合作社”“龍頭企業”和“政府或第三方組織”獲得農業技術支持的定義為“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并賦值為1,其余的賦值為0。
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樣本區域內的大多數種植戶獲得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表明現階段通過新型主體提供農業技術服務的相關政策執行情況較好,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的發展態勢良好。主動和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呈現較大的變異性,不同地區提供專家咨詢和培訓的力度顯著不同。大部分種植戶并未獲得技術含量較高的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3)限于篇幅,各類農業技術支持的描述性統計已略去,作者備索。。
3.中介變量。根據問卷中問題的特點,生產行為規范性的測度包括:(1)施肥規范性,分別以基肥中是否使用尿素、含氯肥料和有機肥來測度。使用尿素和含氯肥料的賦值為0,沒有使用的賦值為1;使用有機肥的賦值為1,否則為0,加總后得到施肥的規范性水平;(2)田間管理規范性,以種植前翻土深度、開花后授粉時段、果實膨大期灌水頻率、采收時可溶性固體物占比來測度。其中,“種植前翻土深度”設置“全園深翻80cm”“部分深翻80cm”“深翻50~60cm”和“其他”4個選項,選擇第一個選項的種植戶符合標準規程并賦值為1。“開花后授粉時段”設置“1~2天”“3~4天”和“5天及以上”3個選項,選擇第一個選項的種植戶賦值為1。“果實膨大期灌水頻率”設置“7~8天灌1次水”“14~15天灌1次水”和“15天以上灌1次水”3個選項,選擇第一個選項的種植戶賦值為1。“采收時可溶性固形物占比”設置“4%以上”“6.5%以上”和“不清楚”3個選項,選擇第二個選項的種植戶賦值為1。同理,加總后得到田間管理規范性水平;(3)用藥規范性,分別以是否使用生物除草劑、是否使用復方殺菌劑、是否使用黃板、是否使用殺蟲燈來測度,選擇“是”的種植戶賦值為1。同理,加總后得到用藥規范性水平;(4)生態保護規范性,以是否進行秸稈還田、是否種植綠肥、是否增施有機肥和是否進行土壤修復來測度,選擇“是”的種植戶賦值為1。同理,加總后得到生態保護規范性水平。
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施肥規范性的達標程度最好,大部分種植戶都施用農家有機肥,但調研中發現施用新型有機肥的種植戶比重依然較少。田間管理規范性和用藥規范性的達標程度較好,生態保護規范性的達標程度相較較低,這與國家和省級相關項目的實施狀況密切相關(4)限于篇幅,生產行為規范性的描述性統計已略去,作者備索。。
4.控制變量。參照前述文獻綜述中的相關內容,本文選擇年齡、種植年限、種植面積、組織化程度和資源稟賦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組織化程度以“種苗是否統一”“田間管理是否統一”“施肥是否統一”和“銷售是否統一”來衡量,統一的項數越多,組織化程度就越高。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種植戶的平均年齡較大,農業生產老齡化問題依然突出,種植戶的組織化程度偏低,地理標志認證在四川獼猴桃主產區的覆蓋率較低(5)限于篇幅,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已略去,作者備索。。
五、實證分析結果及解釋
(一)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綜合達標程度的總效應
接下來,結合前述假設和模型,運用STATA12.0軟件進行實證分析(6)后續模型中均未報告常數項(cut1-cut8的估計值)。。首先是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綜合達標程度的總效應分析。

表1 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綜合達標程度的總效應
注:*、** 和*** 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下表同此。
表1顯示,M1~M5模型擬合度較好。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具有顯著作用,其余類型的農業技術支持均沒有顯著效應。從外觀、品質和安全三個方面分析分層總效應(7)由于模型個數較多且對后續分析意義不大,故在此省略模型,僅給出結論,作者備索。,發現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和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提升具有顯著作用,對外觀和品質的作用并不顯著,表明現有的獼猴桃種植技術可能更偏向于產量提高,在質量提升方面的作用尚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另外,年齡和種植面積的對數兩個變量在所有模型中均顯著,即種植戶年齡越大,農產品質量水平越低;種植面積越大,農產品質量水平越高,意味著提升獼猴桃質量應使生產者年輕化、種植面積規模化。
(二)農業技術支持對生產行為規范性的效應
我們分別分析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田間管理規范性、用藥規范性和生態保護規范性產生的效應。

表2 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的效應
由表2可知,M6~M10模型擬合度較好。經營性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的作用均顯著,但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的效應為負,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的效應為正,可能的原因是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更關注獼猴桃的產量,在尿素和含氯肥料的使用上并未加以限制,也未大力提倡使用見效較慢的有機肥。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起到較好的作用,其余類型農業技術支持的作用并不顯著。此外,種植戶年齡越大,施肥規范性程度越高。調研資料也顯示,年齡越大的種植戶更傾向于施用農家有機肥,而獲得地理標志認證區域的種植戶可能存在“揮霍自然資源優勢”的現象。
類似地,農業技術支持對田間管理規范性的效應分析模型顯示,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的效應顯著,但前者為正、后者為負,表明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有助于規范種植戶的田間管理行為,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在田間管理規范性方面表現較差。農業技術支持對用藥規范性的效應分析模型顯示,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和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對用藥規范性的正效應顯著,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的正效應更加顯著,其余類型農業技術支持的效應不顯著。規模化經營、較高程度的組織化有助于用藥規范,資源稟賦較好的地區用藥行為更規范。農業技術支持對生態保護規范性的效應分析模型顯示,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和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對生態保護規范性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其中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的效應最大且最顯著。隨著國家和省級層面的秸稈還田、土壤修復等相關工程的實施及農業科技公司對綠肥等新型生物肥料的推廣,生態保護規范性通過這三種農業技術支持得到較好的提升。組織化程度越高,生態保護行為越規范,資源稟賦較好的地區更加注重生態保護(8)限于篇幅,農業技術支持對田間管理規范性、用藥規范性和生態保護規范性的效應分析統計均已略去,作者備索。。
(三)生產行為規范性對農產品質量的效應
相關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樣本區內獼猴桃質量的提升主要依賴田間管理的規范性和用藥的規范性,特別是通過一些科技示范戶提供的生物除草劑和復方殺菌劑,對獼猴桃質量的提升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施肥規范性和生態保護規范性的作用并未體現出來(9)限于篇幅,施肥規范性、田間管理規范性、用藥規范性和生態保護規范性的效應分析統計均已略去,作者備索。。
(四)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中介效應
綜合前述分析結論,根據中介效應分析的要求,我們構建如下的模型。


表3 生產行為規范性的中介效應
六、結論與建議
前述分析表明,僅有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田間管理規范性、用藥規范性和生態保護規范性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被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生態保護規范性的正效應顯著;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但對生態保護規范性具有正效應;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對施肥規范性和用藥規范性的作用為正,但對田間管理規范性的作用為負;新型主體提供的農業技術支持在生產行為規范性方面沒有顯著效應。田間管理規范性和用藥規范性在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第一,促進新型經營主體與技術專家的深度融合,充分發揮主動獲取農業技術支持對農產品質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合理設計機制,推動新型經營主體向種植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可提升農產品質量的農業技術支持;第二,加強生產田間管理和用藥的規范性,進一步提升農產品質量;第三,在經營性合作社內積極推廣測土配方,減少化肥施用量,有效保障農產品質量,將經營性農業技術支持作為生態保護規范性實施的重要載體;第四,加強績效管理,強化公益性農業技術支持在施肥和用藥規范性方面的作用;第五,激勵各類農業技術支持提供主體大力研發將有助于推廣和使用農產品質量提升的農業種植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