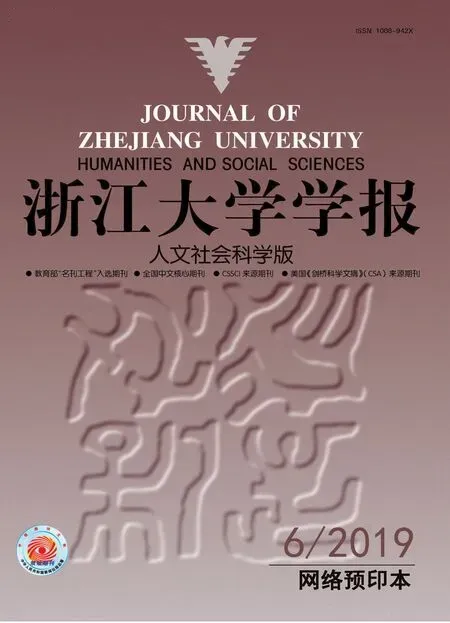基于話語分析的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建構
余瀟楓 張偉鵬
(1.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2.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國際戰略研究所,北京 100005)
國際安全研究中的哥本哈根學派以其建構主義立場與獨特的安全化理論,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安全分析帶來了安全研究范式的突破,特別是“去安全化”概念為探索實現積極和平與可持續安全的外交路徑提供了新的方法論視角。“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概念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其基本含義是“把安全議題移出緊急事件模式從而使其進入政治領域的一般性商談過程”[1]4。作為安全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安全化”概念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通常只是把“去安全化”視為“安全化”的逆向過程或衍生概念,并沒有建構出“去安全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哥本哈根學派雖然在擴大安全研究議題和發展安全研究路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沒有清晰地闡述國家行為體外交政策的“去安全化”特征及這種特征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這就導致了“去安全化”對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論指導與實踐意義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哥本哈根學派看來,“安全是一種‘話語形態’”[2]361,與安全化類似,“去安全化”也是運用“言語行為”[3]47的結果。國家行為體通過“文本表達”[4]201將議題轉移出安全領域來實現“去安全化”,而文本表達的關鍵是借助外交話語有效地傳播外交所承載的價值理念。因此,我們可以基于話語分析來重新解讀與識別外交話語中的“去安全化”特征,拓展其內涵與應用范圍,從而建構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及其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分析框架。
近年來,雖然中國周邊形勢趨于緩和,但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美歐關系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去安全化”是中國外交話語的主要特征,也是施行外交政策的理想方式。本文旨在基于話語分析重新審視“去安全化”的內涵,并從施事話語、價值認同和交往生態三個維度分析外交話語的“去安全化”特征,進而闡釋如何通過外交對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建構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策略。中國以強化經濟與文化合作為顯性模式,以“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1)參見習近平《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8年7月2日。為核心價值取向,努力打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建構體現話語安全且為國際社會所認可的“規范性力量”(2)規范性力量與觀念、認同相關,也可以被稱為“觀念性力量”,指一個國家對他國或世界事務的道德規范或道義觀念的影響力。這一概念最初被用來描述歐盟政策的規范性基礎,以及歐盟將其規范性原則推廣到世界的能力和影響其他國家政策及國際體系的能力。參見Manners I.,″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2(2002),pp.235-258;王正緒《中國崛起的規范性力量》,2015年2月7日,http://www.guancha.cn/Wang-Zhengxu/2015_02_07_308843.shtml,2018年7月2日。,這既有利于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有助于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理解與互鑒。
一、“去安全化”內涵再理解
公共問題的解決往往需要有政府設置議題、集成資源、操作應對的“政治化”過程,而“安全化”是一種較為激進或激烈的“政治化”,即直接把公共問題上升為安全議題,通過特別的政治程序與手段予以特別應對。在安全化理論的創始者,如奧利·維夫(Ole Wver)、巴里·布贊(Barry Buzan)和迪·懷爾德(Jaap de Wilde)看來,“當一項議題被表述為對某一特定參照對象構成威脅,它就是安全議題”[1]21。可見,安全化的實質是“安全議題化”。當然,安全議題的動態發展依賴于安全化行為體、參照主體、參照對象(3)根據布贊、維夫以及懷爾德的定義,“安全化行為體”是指“通過宣稱某些參照對象受到威脅而將議題安全化的行為體”,而“參照對象”是指“擁有合法的生存權利,然而看上去受到威脅的事物”。參見Buzan B.,Wver O.&de Wilde J.,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p.36-40。及受眾等因素,而安全化的完整過程則包括動機、實施過程及結果和影響三個部分。與“安全化”相比較,“去安全化”通常被認為是比“安全化”更理想的過程或狀態,這種認知偏好源于學者們對“安全化”成本的擔憂以及對“去安全化”可以“恢復將安全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的可能性”[5]251的判斷,也就是將安全問題降為公共問題,通過非軍事化、非特別程序的路徑給予解決以減少安全風險。
傳統安全研究的慣性思維對“去安全化”概念的認識所造成的局限是:僅僅把“去安全化”看作被動地去消除已經發生的威脅的過程,而忽視了在“安全化”事件發生之前分析“去安全化”動機的重要性。將安全議題移出安全領域這一過程本身與原安全議題和安全領域密切相關,甚至會引發新的安全問題,但“去安全化”動機則更多地與安全議題產生之前的預備狀態相關聯。菲利普·布赫博(Phillipe Bourbeau)和沃里·尤哈(Vuori A.Juha)注意到了“安全議題之前的動態性”[6],并通過將“安全”“彈性”[6]和“去安全化”進行整合分析,來說明“去安全化”先于安全議題出現的情況,但他們沒有指明這種情況會普遍發生還是只在特定領域發生,事實上,他們在對“安全化—去安全化”的動態性分析過程中引入了“彈性”這一概念,大大增加了論證的模糊性。如果說狹義的“去安全化”概念是針對已經實施的“安全化”進行消解,讓進入安全議題的安全問題還原或降格為非安全議題的公共問題,以消除和減少“硬權力”的使用,那么,廣義的“去安全化”還強調在“安全化”實施之前,努力使公共問題不被上升為進入安全議題的安全問題,或者使安全問題不進入需要使用“硬權力”的安全議題范圍,而是通過使用“軟權力”的方式或合作的方式解決。也就是說,“去安全化”更多的是運用“積極安全”的方式來消解威脅與解決問題,其中,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話語以及建構由這種話語構成的話語體系是“去安全化”的關鍵。
無論是“安全化”還是“去安全化”,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安全問題本身。但“安全化”的不當實施存在兩大誤區:一是“過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7]。公共問題通過特定的話語成為一種安全議題,進而上升為安全問題,往往能受到安全化行為體的重視;假如這一公共問題還不足以成為安全議題,但被過分認知,就會出現“過度安全化”,“中國威脅論”就是西方國家“過度安全化”的一種表現。二是“超安全化”(hypersecuritization)(4)“超安全化”概念由巴里·布贊提出,琳娜·漢森等將這一概念應用于網絡安全研究中,國內的劉楊鉞也曾從事相關研究。參見Buzan B.,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2004;Hansen L.&Nissenbaum H.,″Digital Disaster,Cyber Security,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3,No.4(2009),pp.1155-1175;劉楊鉞《國際政治中的網絡安全:理論視角與觀點爭鳴》,載《外交評論》2015年第5期,第117-132頁。。“超安全化”是指“安全話語依賴于假想的災難情境,使安全意象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遠高于現實安全威脅”[8]132。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威脅往往是已經存在的,“超安全化”的實施主體往往會夸大安全事件的威脅程度并訴諸對抗手段,但其宣傳的大規模、瞬時性的災難性后果還沒有發生。例如各國對網絡安全的認識往往會“超安全化”,由此加劇了國際社會中規則弱化、互信降低的狀況。為了防止國家行為體陷入“過度安全化”或“超安全化”的誤區,廣義“去安全化”理論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了,即糾正國家行為體對非安全問題的“過度安全化”和對安全問題的“超安全化”。
綜上,我們可以通過如下流程圖來展示廣義“去安全化”的演進路徑(圖1):

圖1 廣義“去安全化”的演進路徑
菲利普·布赫博和沃里·尤哈認為,“‘去安全化’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一是僅僅不在安全范疇內討論問題;二是對已經被‘安全化’了的議題做出回應以避免造成安全困境或其他形式的惡性循環;三是使安全議題回到常態政治領域”[6]256。琳娜·漢森(Lene Hansen)嘗試將安全政治的概念解釋與實現方式結合起來,試圖將“去安全化”概念的解釋及其實證應用聯系起來,并歸納了四種“去安全化”形式:“基于穩定的現狀改變”“替代”“重新表達”以及“沉默”[9]529。哥本哈根學派雖然明確解釋了“去安全化”的概念和實現方式,但在認識論層面存在明顯缺陷,即既無法確定“去安全化”概念的使用范圍,也不清楚安全領域與常態政治領域的邊界。這就導致學術界依然沒有就何時需要“去安全化”、“去安全化”的合法性依據以及“去安全化”程度與其效用的關系等問題達成一致。另外,蒂埃里·巴爾扎克(Thierry Balzacq)、霍爾格·施迪策(Holger Stritzel)、麗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和邁克爾·威廉姆斯(Michael C.Williams)等學者在這一領域也做出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成果,這些研究主要關注什么是“去安全化”(現象識別問題)、為什么應該“去安全化”(道德和規范性問題)以及如何實現“去安全化”(轉化性實踐問題)[10],但他們忽視了對另兩個重要問題的探討:一是塑造“去安全化”政治影響力的途徑是什么;二是在“去安全化”過程中,國家行為體間的善意互動能否解決驅動力不足的問題。討論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它們不是根植于“冷戰”思維,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挑戰了“去安全化”現有研究的議題和議題所處的語境。
至此,我們已經指明目前對“去安全化”的理論范圍與實現方式的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并引出對建構廣義“去安全化”理論的思考,但目前學術界還缺乏合適的研究視角來搭建起連接“去安全化”理論與實踐的橋梁。對話語分析理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通過分析話語可以“界定對象領域,定義‘知識’主體的合法性以及確定概念或理論闡述的規范”[11]199。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決策者通常除了在常態政治事件上升為安全議題之后考慮“去安全化”,也力求在“安全化”行為產生之前對其行為動機進行“去安全化”,而基于話語分析在外交政策領域建構廣義“去安全化”理論的分析框架,可以成為探索建構這一橋梁的重要嘗試。
二、“去安全化”理論再建構
哥本哈根學派運用建構主義的方法論和后實證主義的語言學分析視角,創立了包含“去安全化”概念的安全化理論,并通過深化與擴展話語安全這一非常特殊的安全領域以彌補原來客觀安全與主觀安全解釋力的不足。按照哥本哈根學派的理論立場,安全是話語的自我指涉,安全議題則是一種以言語行為為前提的社會性建構。那么,當一個安全問題不被列入安全議題時,其安全問題本身是否還存在?或真實的安全問題是否可能被真正地“去安全化”?這是實證主義安全學者最直接的質疑。換言之,安全問題被“去安全化”了,還是不是安全問題?這里存在著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間的方法論沖突。按實證主義立場,安全問題是客觀的,不管是否被列入安全議題,都是安全問題;后實證主義則認為,安全問題是被建構的,“去安全化”表明了安全問題的消解,在現實中原來被安全化的安全問題是否客觀存在意義不大,如果存在,那么,至多也是一個“沉默”的安全問題。本文闡述的重點不是對“去安全化”的建構主義方法論進行普遍意義上的理論分析,而是在建構主義方法論基礎上結合外交語境拓展與再建構“去安全化”理論,并從施事話語、價值認同和交往生態三個維度建構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及其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分析框架,進而通過打造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方略及外交話語體系,消解由別國的安全化行為所導致的外交困境,最終實現“去安全化”的外交目標。
(一)施事話語
言語行為理論是“安全化”與“去安全化”理論的核心支撐,而話語的施事行為則是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它是指話語不僅可以描述現實,也可以改變它所描述的現實,這其實也是話語安全與客觀安全、主觀安全相區別而得以成立的關鍵所在,因為安全議題在本質上是一種話語的建構,施動者可以借助話語的施事性對受眾的行為施加影響。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說,“去安全化”在本體論意義上可以被表述為各行為體在相互關聯的話語建構中消解“激烈對抗性”的過程,甚至“去安全化”具有“不僅改變主體本身及其敵人對事件的看法,而且從根本上改變敵我關系本身”[9]529的功能,這使得國家行為體在不同語境下甚至在異質性沖突十分明顯的狀態下構建新型關系成為可能。再從話語分析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將外交文本視為一種首要的“施事話語”(5)“施事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概念最早由約翰·朗肖·奧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提出,其本義是“說話就是施事”,不是脫離情境的單純孤立的話語,而是處于一定情境之中的話語,后發展為“言語行為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本文采用楊玉成和趙京超的翻譯方式,參見[英]J.L.奧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國家行為體通過制定并執行合適的外交政策,將由價值對立、利益沖突以及結構性矛盾所引發的爭端等轉化為常態政治中的一般議題,目的是在特定語境下將沖突“去安全化”,并實現以合作為目標的權力平衡與以消除對抗為前提的戰略導引。從廣義的“去安全化”立場來分析,“去安全化”不僅會發生在“安全化”行為之后,也有可能發生在事件被“安全化”之前。這也就為具有施事性特征的外交話語塑造了更多“去安全化”的現實可能與政治影響力。依據施事話語的視角,具備“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往往是一種“言后行為”或“語效性行為”(6)“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 act)是相對于言內行為與言外行為來說的,強調話語對受眾所產生的影響,因而也有將其譯為“語效性行為”“以言取效行為”或“取效行為”的。參見Austin 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01。。因此,對外交文本的“去安全化”特征的分析,不僅要考察其政治影響力,而且應重視國家行為體如何通過這種政治影響力使受眾對(潛在)安全問題的態度發生變化。
對外交領域中的施事話語進行深入分析,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外交文本中的“去安全化”特征。對施事話語的分析由四個方面組成:施事話語的自我反映、不同語境下施事話語不同特征的顯現、干擾施事話語的可能因素以及施事話語的準確展示。在外交實踐中,多項外交政策同外事宣傳往往會相互影響,外交文本間的多重互構關系在為建構共同語境奠定基礎的同時也提升了受眾誤解政策的風險,這會給言后行為目標的實現帶來隱患。雖然不同外交文本間的多重互構關系和流行文化的擴散可以在破裂和/或尚未鞏固的社會領域內使“去安全化”成為社會共識,但外交施事話語的運用只是“去安全化”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非全部。由于施事話語所達成的“共識”往往建立在暫時的共同利益基礎之上,因而它并不一定穩固,我們仍需要在國家行為體間建構起持久的價值認同,以實現“去安全化”的目標。
(二)價值認同
“去安全化”與“安全化”一樣,也是一種基于話語的安全議題建構與解構,此外,“去安全化”也注重強調主體責任、建構供受眾討論議題的公共領域以及真正消除威脅認同的重要性[9]。廣義的“去安全化”還強調防止未進入安全議題的問題被“過度安全化”或防止進入安全議題的問題被“超安全化”,那么,推進“去安全化”進程的持久的驅動因素可能是什么?如果視價值認同為其持久的驅動因素,那么建立“去安全化”持久的價值認同是否可能?又如何成為可能?可以說這既是再建構“去安全化”理論的重點,也是難點。
對廣義“去安全化”理論來說,在進行“去安全化”之前,我們必須提供具有說服力的理由說明安全事件或可能被“安全化”的事件不是安全威脅,同時也不具有成為安全威脅的潛在可能。在“去安全化”的施動方尋找共同利益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各國家行為體互動而形成“共有知識”,進而建構具有持久性的價值認同,從而使得“去安全化”的施動方能較大可能地獲得以建構語境、整合價值與促進合作為核心內容的規范性力量。這一建構性過程包括認知、判斷、界定、接受、回應與商談[12]等步驟。在外交領域,對“去安全化”的過程分析往往需要先截取這一過程中的若干“情節”,每一個“情節”都反映了一個獨立的因果關系,我們需要將提取自不同“情節”的因果關系聯結起來,以揭示具備“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戰略的重要意義。但這種聯結不是簡單的合并,而是要能闡明:施事話語如何與價值認同相聯系?為什么施動者會用這樣的表達方式而不用其他方式來建構并使用規范性力量?
人類發展至今,國際社會多多少少建構起了支撐世界運行的價值基礎,除了主權、和平、富強之外,民主、公平、正義以及尊重和保護人權等也是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國際關系價值準則,但由于各國家行為體的歷史傳統、現實國情不盡相同,各國對價值評判所處的語境存在許多差異,這就為“去安全化”帶來了不少障礙與前提性缺失。但認同的可能除了來自歷史與現實,還可來自未來與預期,況且對歷史與現實進行再理解與再建構仍然是獲得認同的重要方面,特別是“‘認同’是由話語構成的,國家(或國家的代表機構)可以通過指引和動員認同來實現其外交政策的合法化”[13]210,因而決定“去安全化”可能與否的是其背后體現價值認同的話語結構和話語環境。在后結構主義者看來,“外交政策是界定國家身份或其等同物的核心”[14]34,語境的差異導致決策者對合作產生了源于對本體安全(7)“本體安全”是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會認同理論中的一個關鍵詞,它是大多數人對自我認同的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物質環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恒心,表達希望獲得可靠和安全的體驗的愿望。吉登斯以此來解釋人們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而產生的脆弱性和恐懼的現象。的擔憂的危機感。國家行為體的決策者對安全的認知總是與該事件對國家主權和身份的重要性密切相關,這種認知建立在決策者維護國家利益責任的基礎上,是決策者對政權的存在和國民利益延續性的保護。“去安全化”以國家行為體間的互信為基礎,這種互信源于共同語境下的價值認同。國家行為體經常需要借助話語本身的政治影響力,通過塑造輿論以及提升本國文化的吸引力等方式壯大其在共同語境下的規范性力量。而話語的政治影響力受其表達方式的影響,與國家行為體對共同語境的定位與建構密切相關,這就為國家行為體在任何語境下建構“去安全化”戰略提供了可能,而對以“和平發展”為外交根本方向、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外交總目標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那么,如何消解中國與西方國家間存在的異質性沖突?這需要在外交施事話語與價值認同建構基礎上進行交往生態的再造。
(三)交往生態
學術界一直對包括“去安全化”概念在內的“安全化”模式能否適用于對非西方國家案例的分析存在爭議,因為多數學者固守“威斯特伐利亞式”的話語體系,一方面強調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念方面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又認為,在不同社會制度環境下民眾對決策者制定政策的影響力不同。很明顯,這一視角的片面性就在于僅僅考慮了“去安全化”在國家行為體內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對外交政策本身“去安全化”特征的分析。因此,理解“去安全化”的關鍵在于準確把握國家行為體通過制定外交政策所確定的立場與受眾對這一立場的理解之間是如何溝通的,以及在這種溝通過程中外交文本所體現出的“去安全化”特征,這就需要我們重視施事話語,推動價值認同的形成,通過理解、對話和溝通,建構良性的交往生態。
交往生態是交往發生時交往行為體所處的關系結構與總體環境狀態,即“溝通過程發生的背景”[15],它由共同語境和主體間互動的狀況構成。“去安全化”則是基于確保行為體和受眾的本體安全而對交往生態內部結構進行優化重組的過程,旨在平衡各種傾向于“安全化”的力量。在外交政策分析領域,交往生態的良性或惡性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國家行為體間關系的緊密度(同盟、伙伴關系、關系正常化、沖突);二是處于良性交往生態中的國家行為體針對突發安全事件而體現出某種應急能力的響應度;三是對共同價值的認可度。由于以“去安全化”為特征的交往行為傾向于獲得基于價值認同的相互理解,我們應該通過分析國家行為體的政治目標、受眾的期望和情緒訴求以及需要共同應對的問題來建構良性的交往生態。將交往生態概念引入“去安全化”研究有利于強化“去安全化”的理論邏輯,也“為進一步制定政策以及在這個方向上對技術、實踐和慣例的改善與進步搭建了框架”[16]52。當然,對“去安全化”的實現方式的研究既應包括如何對危機和沖突做出反應,也應包括國家行為體如何在長期塑造次區域、區域乃至全球結構中提升能力。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以“和合”為核心取向、以價值認同為持久性動機、以施事話語為有效方式、以“優態共存”[17]的交往生態為最終目標的廣義“去安全化”理論新架構。
三、廣義“去安全化”理論與外交話語策略的建構
廣義“去安全化”理論的運用涉及整體國家對外戰略的設定與實施,限于篇幅,本文著重對其在外交領域的運用進行研究,特別是基于話語分析,通過對外交對接、合法化和互文性三個維度的考察,為在外交工作中實現“去安全化”的目標提供新的視角與路徑。在廣義“去安全化”理論運用的實踐中,一些學者重視對“去安全化”概念的解釋,并將其應用于分析眾多具體的安全問題,包括中東地區的雙邊關系/沖突、核戰略、北極治理、少數族裔權利和民主制度等(8)參見Aras B.&Polat R.K.,″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Desecuritization of Turkey’s Relations with Syria and Iran,″ Security Dialogue,Vol.39,No.5(2008),pp.495-515;Jacobsen M.&Strandsbjerg J.,″Desecuritization as Displacement of Controversy:Geopolitics,Law and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Arctic,″ Politik,Vol.20,No.3(2017),pp.15-30;Roe P.,″Securitization and Minority Rights:Conditions of Desecuritization;Security and the Democratic Scene:Desecurit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p.279-294.;另一些學者則重視對“去安全化”實現方式的探討,比如杰夫·海斯曼(Jef Huysmans)提出了三種“去安全化”策略,包括客觀主義策略、建構主義策略和反建構主義策略[18]55。但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或是只聚焦于對概念的解釋,或是只聚焦于對抽象策略的分析,沒有將“去安全化”的話語與構建國家行為體的外交話語戰略結合起來分析。在當今國際體系中,安全形勢的不斷變化在給國家行為體的外交工作帶來復雜挑戰的同時,也為“去安全化”理論的拓展與建構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策略提供了新的語境,而其驅動力源自人們對當前國際社會權力分配關系變化的思考及對“威斯特伐利亞式”國際關系話語體系的質疑。
(一)外交對接:良性交往生態的建構
在“去安全化”理論的實踐運用中,外交決策者首先應該排除兩種觀念的“誘惑”,一種是無限擴大的“普遍主義”,另一種是絕對的“例外主義”。無限擴大的“普遍主義”是指將自己的文化強加于世界各地,而不顧其他國家行為體的特殊性,甚至濫用“安全化”來尋求介入他國事務的合法性,這實際上是一種源自文化帝國主義和意識形態帝國主義的極端路徑。同時,我們也需要防范絕對的“例外主義”,避免把自身的文化看作擁有“特殊體質”或“特殊稟賦”的文化基因。實際上,絕對的“例外主義”會降低民族文化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增大矛盾和沖突等安全問題出現的可能性。因而,實現“去安全化”需要國家行為體在建構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交往生態方面做出長期努力,這不僅需要在外交實踐中實現價值認同的對接,也需要國家間方略層面的對接。
外交對接是建構以“和合主義”[19]為核心的對外交往生態的主要方式,也是廣義“去安全化”理論運用的優先途徑。“對接”首先排除了軍事上的對抗性,其次消解了政治上的對立性。國家之間的外交對接有許多方面,價值認同的對接具有根本性意義,方略層面的對接具有目標性意義。對接過程一般遵循以下四個步驟:一是在“去安全化”的啟動行為體上自我定位,國家行為體結合實踐中的利益需要,尋找共同的價值偏好,并在跨越各國家行為體歷史文化和外交傳統藩籬的基礎上,針對“安全化”的潛在動機或“安全化”后的國際環境提出具有建設性和創新性的“去安全化”倡議;二是開創話語安全的新語境以推進“去安全化”的實施,國家行為體通過塑造輿論、正面回應及民眾交流等方式使倡議深入人心,不僅要政策溝通,還要民心相通;三是重視外交文本的互文性以整合價值,國家行為體通過主動發揮話語的施事性效應,結合各方對倡議的反應,整合各方的價值取向以符合時代背景及政策需要;四是建構良性交往生態以促進行為體間的方略對接,國家方略的對接一般首先體現在外交文本中對方略名稱及具體對策的話語整合上。事實上,各國的官方文件都有對本國發展規劃及外交政策的描述,對接方略就是指決策者在理解各國外交文本的用詞習慣、語體風格和語篇銜接邏輯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政府政策、政黨政治狀況及民意情況,對未來發展走向進行合理預測與話語建構。同時,方略層面的話語對接也需要充分考慮所在區域核心國家及重要國際組織的反應。
(二)合法化:規范性力量的獲取
無論是基于外交話語進行外交對接,還是基于施事話語和價值認同進行交往生態建構,如何將這些外交行為在國際社會中合法化是國家行為體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本文中,合法化的行為是指國家行為體通過獲取國際社會對其規范性力量的認可,或使其在良性交往生態中所建構的價值準則得到受眾的普遍認同,使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獲得足夠政治影響力的行為。國家行為體在特定語境下為尋求各方在合法性問題上取得共識而進行長期努力的過程,顯示了規范性力量的獲取與運用以及得到受眾支持的艱難性。范·魯文(van Leeuwen)認為獲取合法化可以運用以下四種方式:權威化(參照權威人物或傳統)、道德化(參考價值體系)、合理化(提及制度化社會行動的目標和用途)和創造神話(獎勵合法行為的敘事)[20]。雖然這四種方式為獲取合法化指明了可能的方向,但考慮到這四種方式的實施難度及其適用范圍的模糊性制約了其在分析復雜的外交實踐時的靈活性,我們需要探討更符合雙邊及多邊外交實踐特點的有效合法化方式。
有效的合法化方式包含四種路徑:第一,將本國的利益需要描述成其與雙邊及多邊外交合作的預期成果或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在建立價值及戰略兩個層面對接的基礎上,國家行為體在外交文本的表述中既要體現對接關系,又要體現其對維護共同利益的理性和責任,在建構價值認同的同時,強化規范性力量的利他性。第二,對合作方式進行清晰準確的定義。決策者要充分發揮外交話語的彈性,擴大制度邊界,積極融入各種社會力量,夯實參與行為的合法性基礎。同時,決策者也要注意塑造剛性外交話語,堅定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提升外交話語的可信度,推動戰略互信的建構。第三,維護國際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如果出現由經濟和社會政策導致受眾不能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而付出太多成本的問題,雖然政策的合法性似乎增加了,但流失的意愿和損失的支持基礎也會威脅到政策結構乃至區域結構的穩定性。換句話說,在推動“去安全化”的外交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決策者必須強調在國際社會中公平與正義的重要性。第四,避免“過度去安全化”和“欠缺去安全化”[7],對“去安全化”的濫用也會導致“信任危機”。決策者既不能忽視安全問題產生的潛在可能,也不能夸大安全威脅,要準確把握問題的實質及其所處的階段,同時通過外交話語的建構對實時的交往生態狀況保持清晰的認知,從而在決策中做出恰當的選擇。
(三)互文性:多重外交文本的疊加效應
要在多邊外交中倡導“去安全化”戰略,就得重視外交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帶來的疊加效應。一般來說,對外政策文本深置于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共享文本空間中,它與各國外交政策文本及各種媒體文本之間存在著互文性關聯[21]49。事實上,“文本具有特殊性和統一性的雙重特征:每個文本都建構各自獨特的身份,產生一系列并列和差異,并將它們與空間、時間和倫理維度的外交政策聯系起來”[21]49。在一個共享的文本空間范圍內,每一個文本都始終是其他文本解讀的產物,而對已具備合法性的文本的解讀也是建構文本本身合法性的過程。同樣,每一項外交政策都不能脫離特定語境,而應該在更大的文本網絡中由其他文本來解讀,從而在新的視角下將不同的表象與認同聯系在一起,得出新的“共有知識”。在外交領域中,“去安全化”應該被視為基于多重外交文本的疊加效應而賦予外交行為的“合法性”在各方共同塑造的交往生態中施加政治影響力的過程,而這種疊加效應的產生則源于話語的互文性。
對外交文本互動的研究不僅要重視官方文本對外交政策的權威宣傳,也要注意研究政策支持者與反對者關于安全議題的辯論。如果缺少互文性分析,我們很難從不同外交文本中找到最恰當的分析外交政策的角度和方式,這也是誤解外交政策目標的主要原因。琳娜·漢森提出了研究互文性的三個步驟:“一是分析認同和政策在初始文本中是如何被表達的;二是分析初始文本對于認同和政策的建構是如何被后來的文本呈現的;三是比較初始文本和后續文本。”[21]52制定“去安全化”外交話語戰略的過程包括對問題初始文本、將問題“安全化”了的文本以及當前對這些文本的解讀進行比較,通過對“安全化”話語的準確性、可信度、合法性等指標的考察,基于共同的價值基礎撰寫新的外交文本,在獲得國際社會其他行為體理解和認同的同時,闡明安全問題脫離安全領域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四、中美貿易摩擦:中國的“去安全化”外交實踐與前景分析
對“去安全化”理論建構、解構、重構的研究不僅要闡明理論本身如何發展的問題,也要反映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國際關系史、領導人行為方式以及國際體系的變遷所產生的影響。“去安全化”理論的發展不應局限于同質文化的內部互動,而應將其研究范圍擴展至異質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為我們重新認識外交政策、國家安全環境以及國際體系的變遷開辟了新路。具備“去安全化”特征的外交話語能提供給受眾什么樣的知識?知識是如何被有效表達、傳播和應用的?我們又應該如何對“安全化”的外交話語進行抵制、解構,同時重構廣義“去安全化”的外交話語體系?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積極學習世界、融入世界,并不斷努力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貢獻。但近年來,隨著“反全球化”思潮與貿易保護主義逆向泛起,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把中國視為“威脅”,極力將中國的和平發展“安全化”,鑒于此,中國運用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建構具有化解外交困境功能的新外交話語策略是當務之急。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作為經濟總量世界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雙方互為各自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隨著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美國外交政策決策模式與風格相比以往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最顯著的變化當屬傳統涉外部門,如美國國務院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相對弱化,而特朗普總統本人外交風格的重要性顯著提升。中美關系中的“施事話語”主要包括外交文書、外交部門公布的政策文件以及領導人講話等內容。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之前以及目前的“較量”中,雙方以往外交文書的作用相對減弱、美國外交政策文件的影響力“外溢”以及特朗普總統對“推特外交”的使用助推了“安全化”的發生,這極易混淆是非、誤導輿論從而迷惑我方決策,給我國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因此,剖析美方“施事話語”的變化不僅對調整我方原有的認知結構、避免認知固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尋找中美貿易摩擦的“去安全化”解決方式開啟了全新的視角。
(一)特朗普政府外交“施事話語”與被“安全化”了的中美關系
1.中美關系中外交文書的作用有所下降
自21世紀以來,中美關系幾經風雨,從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到就推動“元首外交”在中美關系中發揮戰略引領作用達成共識,再到中美雙方于2017年共同建立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在中美兩國間的外交文書所傳遞的大國合作精神指引下,雖然美國歷屆政府也曾觸碰中方底線并挑戰外交文書的權威性,但中美關系仍在由外交文書建立的框架內保持可控狀態,發展總體穩定向好。而在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后,外交文書在管控分歧和化解危機等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等口號的驅使下,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承認以往各項外交文書的內容,但另一方面又通過不斷觸碰或挑戰我方外交底線力求在博弈中獲得更高收益。其次,目前中美雙方建立的90余個對話機制沒有從根本上提升雙方的戰略互信,無法化解“中國威脅論”的不利影響。在中美關系中,外交對接的前提除了各自國家利益的平衡,還應包括在充分協調各自安全價值排序與倫理關聯的基礎上建構良性的交往生態。第三,面對新的國際形勢,現有外交文本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及不穩定狀態的應對手段不夠、管控力度不足。我國應該做好當中美關系出現因美方一意孤行而加速滑向并長期處于“危機不穩定狀態”的情況時的應對準備。
2.美國外交政策文件的影響力“外溢”
特朗普政府通過其2017年發布的任期內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連同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18美國國防戰略概要》(Summaryof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l2018)、2018年6月19日美國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OTMP)發布的《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全球的技術和知識產權》(HowChina’sEconomicAggressionThreatenstheTechnologiesandIntellectualPropertyoftheUnitedStatesandtheWorld)研究報告以及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JohnS.McCain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forFiscalYear2019)四份外交政策文件,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所面對的最主要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導致中美關系被加速“安全化”。特朗普政府通過在四份文件中頻繁使用“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s)、“竊取”(steal)、“侵略”(aggression)等國際關系中的“惡語”(bad words)詞匯制造話題,把中國塑造成“不公平的貿易者”“知識產權的盜竊者”,并將這一形象向世界傳播,利用文本的互文性引導輿論走向,從而不斷提高加征關稅的價碼,欲通過“霸凌主義”行徑向中國施壓,以維護其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者角色。惡語”指“攻訐性的、歧視性的、情緒化的語言現象”[22]33。美國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惡語”是一種“構成社會沖突的重要因素”[23]47。“惡語”的產生不僅會對“安全化”有催化作用,而且往往會導致“超安全化”。四份報告關于中國問題的描述既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國內通過“安全化”手段凝聚國內共識、推行強勢貿易政策從而攫取更高收益的理論依據,也是其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占領道義制高點的“宣戰書”。
3.特朗普總統的“推特外交”
“推特外交”(9)原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2017年6月6日的白宮記者會上在記者質疑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發布信息時回應說:“The president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ey are considered official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參見www.patheos.com/blogs/dispatches/2017/06/07/spicer-trumps-tweets-official-white-house-statements/,2018年7月2日。集中顯示了特朗普總統強化符合個人偏好的決策模式和外交風格,是其使用“惡語”向世界“煽風點火”,從而美化自身成就、宣揚所謂“讓美國再次強大”和“美國優先”的另一主要渠道。自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特朗普總統在其個人推特中頻繁使用“傷害美國經濟”“不公平”“邪惡的”等攻訐性“惡語”來形容過去幾年的中美經貿關系,同時使用“?”“!”等情緒化的標點符號渲染“安全化”氣氛。以推特、臉書等為代表的外國社交媒體雖然能夠拉進政治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感,但不應使它們成為誤導民眾,特別是抹黑他國國際形象的工具。特朗普總統對推特的靈活使用是其商業思維在外交事務中的延續,“推特外交”雖然可以在美國國內固化其支持力量的政治傾向,同時在與別國談判時為其增加籌碼,但他卻忽視了誠信與責任對大國在國際社會樹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意義。對“推特外交”進行“去安全化”,我們需要思考兩個問題:“應以怎樣的方略來制定符合國際根本利益追求的外交政策,并以怎樣的方式進行對外宣傳以配合既定的外交政策”[24]。與此同時,如何在新的語境下創新“施事話語”以推進對中美關系的廣義的“去安全化”議程,也是本文必須解決的問題。
(二)貿易摩擦前景分析與中國的“去安全化”外交話語策略
自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中國在由雙方外交話語構建起來的信息場域中對美方的不當言論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應,并通過這些回應向世界傳遞正義的信號,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中國總體上采用了“去安全化”戰略,在官方媒體刊發五篇宣言(10)五篇宣言分別為《緊緊抓住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人民日報》2018年1月15日)、《艱苦奮斗再創業》(《人民日報》2018年2月23日)、《為有源頭活水來》(《人民日報》2018年4月2日)、《風雨無阻創造美好生活》(《人民日報》2018年8月8日)、《改革開放天地寬》(《人民日報》2018年8月13日)。,并發表聲明強調在國際貿易中出現摩擦和沖突是正常的,但應通過WTO等國際貿易機制進行談判與磋商加以解決。在美國先發制人、頻頻出擊的情況下,中國仍強調“中方絕不打第一槍”(11)參見《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2018年7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0705.shtml,2019年6月30日。,“中美是一條船上的成員”(12)參見高石《崔天凱:中美依然在同一條船上》,2018年7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27/c1002-30174854.html,2019年6月30日。,“中方一直盡自己最大努力推動有關方面客觀認識、理性處理雙邊貿易中出現的分歧和問題”[25]60。在美國試圖逐步升級、全面與中國為敵的情勢下,中國一方面做好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準備,另一方面仍在盡最大努力以維護兩國關系。展望未來,達成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雙贏方案仍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本文擬提出以下話語安全策略:
第一,重建合作的價值基礎和良性交往生態,完善外交對接機制。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要通過談判、對話與溝通強化雙方的安全價值排序與倫理關聯,在共同的安全話語語境中建構以“和合共生”為價值基礎的中美兩國間良性交往生態,為判斷某個問題是否應從安全議程中剔除提供評判標準,并使其成為推動中美關系“去安全化”的持久驅動力。完善外交對接機制的具體路徑為:(1)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的引領作用,將雙方未來發展戰略進行對接,使雙方重回以談判與對話解決分歧的正確軌道,通過運用新的“共同話語”,建構起新的“觀念認同”,探討打造新型大國關系的可能性。(2)重新評估目前存在的90余種聯絡機制,并完善其分布結構,優化資源配置。我方應整合各部委職能,詳細制定針對每種對接機制的實施細則,商討并準確把握各領域聯絡機制的情況與條件,在充分保障話語安全的前提下,避免與美方產生錯位銜接。
第二,充分發掘外文社交媒體渠道的傳播潛力,強化多重外交“施事話語”之間的互構關系,并提升我方話語的精準性、權威性和延續性。我方在對外宣傳工作中應調整對宣傳方式的傳統認知結構,重視借助外交話語的互文性,運用多種流通廣泛的外語語種,在國外社交媒體的官方認證賬號中將特朗普政府出臺的四份政策文件及“推特外交”中出現的“惡語”放入全球維護自由貿易的語境中,與中國始終堅持“為了捍衛國家尊嚴和人民利益,捍衛自由貿易原則和多邊貿易體制,捍衛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13)參見《商務部發表聲明》,2018年7月1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2765543.shtml,2019年6月30日。的堅定立場進行對比解讀,強調貿易摩擦的“雙輸”結果及其對全球貿易復蘇的不利影響,并揭示特朗普政府反復無常的話語風格所導致的信任赤字,從而詮釋對中美貿易摩擦“去安全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降低“惡語”對“安全化”的催化作用,塑造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第三,超越“對稱式”話語策略,積極有效地應對話語的重復博弈。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美國已然將中國視為其維持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脅,因此貿易摩擦的加劇并不是偶然的,美國基于“冷戰思維”必然要采取“安全化”手段在各個層面遏制中國可能的超越。但對“安全化”行為的回應的最大作用是進行形象上的“止損”,而要實現對異質性話語管理能力的提升并沉著應對話語的重復博弈,不應僅僅完全按照對稱式思維做出被動回應,而應發揮自身優勢,運用創新思維及手段制定符合我國國情且被國際社會所認可的話語策略,防范“安全化”的衍生、轉移與擴散。(1)我國要始終保持立場堅定和戰略自信,通過縱向拓展歷史性的全局視野以及橫向分析特朗普政府在各領域的政策,準確把握美方的重點、要點以及當前存在的痛點、難點等。(2)我國應建構共同語境,增進多方共識,在國際社會中尋找更多的戰略支點,同時對新的“安全化”動機進行合理預測。(3)我國應結合美國政治生態的變化,即不同派別“施事話語”內容與價值認同的差異,有針對性地實施話語分層策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美國政府及參眾兩院中的對華遏制派保持“反擊回應”式話語,對保持對華接觸派等溫和力量的回應要運用“謹慎包容”式話語,而對因貿易戰而遭受損失的美國公司及民眾要運用“開放友好”式話語,最大限度地釋放中國的善意。(4)我國應持續發力建設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將立場的堅定性、內容的延續性、結構的嚴謹性、風格的多樣性與手段的豐富性有機結合。
五、結 論
廣義“去安全化”不僅是“安全化”的逆向過程,也是國家行為體通過創設以“和合共生”為核心的共同語境、建構適合雙方的價值認同和合作機制,進而將(安全)議題排除在安全領域之外或將其移出安全領域而歸置于常態政治的過程,更是一種“言語行為”的結果。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將對“去安全化”的分析范圍從僅在“安全化”之后拓展到包含“安全化”之前,糾正國家行為體對非安全問題的“過度安全化”和對安全問題的“超安全化”。通過建構施事話語、價值認同和交往生態三個維度重新認識“去安全化”概念,本文進而探討如何從外交對接、合法化和互文性三個方面實現外交政策的“去安全化”目標,從而建構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及其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分析框架。傳統意義上對“去安全化”理論的分析往往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鑒于許多非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將“去安全化”理論運用到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案例的分析中不僅有利于提升該理論的科學性和解釋力,也有利于推動不同地區間的經驗交流與文明融合。當前我們有必要拓展“去安全化”的研究議題,賦予這一概念新的理論內涵,即制定和運用具有“去安全化”特征的話語策略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也為建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開辟了新路。面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的復雜國際安全形勢,“去安全化”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有賴于中國外交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的全面提升,從而有效化解話語安全中的諸多難題,真正開創大國“大外交”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