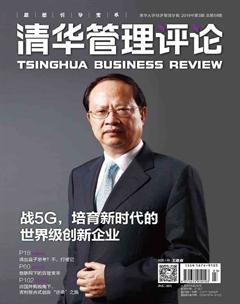謝德蓀談中國發展戰略——重在剛需,“美好”跟隨
張春晏

本次采訪中,謝德蓀教授提出了新的想法和理論。他把市場需求分為兩大類——剛需市場和“美好市場”——吃、穿、住、健康等人類基本需求之外,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都屬于“美好”市場。美國是一個非常善于以科技創新創造美好市場的國家。在中美關系非常緊張的現狀下,謝德蓀教授認為中國應該把重點放在滿足剛需市場上,從而培育更大的“美好市場”,亦應該重點把新技術應用于剛需,打造新的生態,從而實現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謝教授的觀點給我們提供了別樣的思考視角。
TBR:您在《源創新》一書中,將創新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科學創新,包括新的科學理論、產品和科技;另一類是商業創新,指創造新價值。您把前者稱為“始創新”,后者又可進一步分為“流創新”和“源創新”。流創新是指能改善現有價值鏈的活動;源創新是開辟新市場的創新。請您結合中國的創新介紹一下您最核心的觀點?
謝德蓀:就我的理論而言,常常我的第一句話是關于創新跟文化的結合——不同的文化中做事的方法不一樣。有些創新美國做得好,中國就很難,因為沒有美國的文化背景,因此做不到。但是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競爭力,美國也做不到。所以我主要研究文化背景跟創新怎么結合。
TBR:如果讓您提煉最核心的文化差異,中國拼不過美國的是什么?
謝德蓀:其實創新跟科技沒關系,跟技術好不好也沒有關系,核心在于你如何想事情。很多時候,創新是一種藝術,就是你如何去想去做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你想事情的方法不一樣。我管美國的創新叫做盒子之外的創新,美國人追求怎么打破盒子,跳出盒子來思考,你給他盒子,他不要,他要自己創造一個盒子,這跟整個美國的歷史、文化都有關系;而我們中國人,善于在盒子里面創新,給你一個盒子,一個框架,在盒子里面轉得很好,比美國人全世界人轉得都好。那誰給這個大盒子呢?權威、領導可以給一個大的盒子;人家已經做出了盒子,知道怎么做了,那我在里頭轉,例如中國互聯網的成功就是這樣。包括韓國、日本,要進行源創新也很難,這跟文化是有關的。所以如果我們要學美國跳出盒子來創新,我們很難做得到。
TBR:那么您是認為我們應該放棄您所定義的“源創新”嗎?
謝德蓀:不是,我認為連續源創新是持續經濟發展的動力,不只不可放棄,要堅持實踐。我最近有一個新的理論。我說所有的源創新,都是顛覆性改變,創造了新的社會的價值——不是指新的東西,不是新的技術,而是創造新的價值。源創新可以通過盒子之外創新的思維做到,也可從更大盒子里面創新的思維做到,所以關鍵是如何利用你思維方式的優勢,推動源創新,打造新的社會的價值,重點是什么新價值,這新價值從哪里來?
我說全世界的價值分兩類,一類是剛需的,一類是美好的。
剛需就是大家都一定需要的,水、吃飯、空氣、健康。但是,大家都知道剛需的東西是什么,但社會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剛需的需求沒有去解決呢?完全的市場經濟,講的是如何配置資源,獲取回報。沒有回報就不會去做。所以很多剛需,是有需求沒有人去做。比如說貧窮,脫貧這件事就無法依賴自由市場,而需要政府去做,政府去協調。中國第一次的最大的改變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個是解決剛需問題的源創新。
另一種需求是覺得美好的。美好是什么?你已經脫貧了,你已經有錢了,你便會想要一些從沒見過的好東西,這個完全可以由市場來提供。所以,很多這種“美好”的創新,大部分是科技來推動的,因為有科技就有新的可能性,有新的可能性你就想怎么樣去讓世界更美好一點。人們如果實現了剛需需求之后,就會有潛在美好需求了。所以剛需每個人都要,但是美好市場一定是有錢人的市場,沒錢的他不會追求美好。
TBR:吃不飽飯確實不會太追求美好。
謝德蓀:“剛需”如果解決之后,你就有“美好市場”了。所以剛需可以帶動美好。看中國的兩次源創新——第一次,改革開放是剛需的解決;第二次互聯網革命,互聯網是給誰用的?是給已經可以消費得起互聯網的人用的,有剩余的錢你才能有消費市場。所以我說,中國的第二次是美好源創新,成功主要是因為第一次剛需源創新的成功——第一次基本成功滿足了剛需市場,所以對“美好”有要求了,為第二次的成功提供了基礎。互聯網經濟是我們把美國的美好帶到中國去,根據中國的情況塑造了中國的互聯網。這對中國人來講,是最符合我們中國人的創新特點的。特點是什么?看到成功的大家很會學。你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盒子,已經成功了,我在這個盒子里玩,那能在盒子里玩得很好。中國過去的成功就是這個思維,這種文化——不斷找已經被證明出來的盒子。
TBR:如果文化制約創新,那么我們不是應該要改變這種文化嗎?
謝德蓀:文化是幾千年的積累,我認為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改過來。可能需要幾代人,涉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等一系列問題。中國的教育是要守規矩聽話,考試就是給你一個盒子;美國也有考試,但主要是讓你學會問問題,非常不一樣。中國很多很成功的人是叛逆小孩,但畢竟是很少數。
問題是我沒改過來的時候怎么創新呢?我認為這是很務實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不要去超越。中國要創新要繼續發展,還是要利用大部分人的能力。
所以我有一個理論——有創意的模仿。我模仿,但是我在其中創造新的價值, 這也是源創新。這就符合我們中國人的文化特點和能力結構了。我強調有創意的模仿與源創新是不沖突的。
看看韓國的成功,主要不是跳出盒子的想法,而是找一個大的盒子來發揮,完成源創新。韓國的三星、現代、LG都是那樣。這種模型中國肯定可以學得到,因為這跟中國的文化是相通的。
美國的IT產業為什么這么強?因為它的產業鏈連接著全世界,把全世界的資源整合起來支持一個或者幾個公司。英特爾是全世界的其他公司在支撐的。所以,我認為從長期來講,美國不會走極端。
在科技推動美好這點上,不可否認,全世界美國做得最好。但美國不是在做一個盒子,而是一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是很難與之競爭的,尤其是中國人沒有跳出盒子的思維。但是我們可以一點一點,嵌入到它整個生態中去。
TBR:美國的IT創新是一個生態,意味著它是有機的變化的,甚至是進化的,會源源不斷誕生出新的事物新的創新。
謝德蓀:每一個生態系統一旦形成是很難去靠一樣東西去競爭的,我也做研發去打破它的生態,做不到的。有思維、人才、配件等等,很多看不到的東西。但是美國的IT創新生態是鏈接是全世界的,全世界都在養活美國的這個生態。如果這個生態中沒有中國的支撐,它的生態會慢慢死的。現任總統川普是做房地產生意的,沒法理解IT產業的特點。美國的IT產業為什么這么強?因為它的產業鏈連接著全世界,把全世界的資源整合起來支持一個或者幾個公司。英特爾是全世界的其他公司在支撐的。所以,我認為從長期來講,美國不會走極端。
所以說,我們中國要做什么呢?我認為我們不要跟美國拼。我叫反思維。美國的都是“美好經濟”驅動的。那我們中國從剛需來解鎖,以源創新解決剛需的問題。我們把新的技術用在剛需源創新方面。AI新技術,你可以用在無人駕駛上,這個是“美好”的,但是如果AI用在污水處理上,這個是剛需的。AI用在新能源分布上,這個是中國剛需的。我們不要跟美國進行最直接的競爭,不要緊跟著熱門產業跑,美國做VR,我也做VR,美國做無人駕駛,我也做無人駕駛。不是說不做,但是我們可以把力量重點放在剛需方面。
我認為最主要是怎么解決我們中國貧困人口問題,把他們的生活水平拉上去。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一上去,就壯大了“美好市場”,美好市場越大,中國就越有控制力,美國就不會說不賣給你,因為市場大。最后說話的是市場——把市場搞好,掌握市場,你就是掌握什么技術我也不怕你。
TBR:中國現在還有四億貧困人口。
謝德蓀:一帶一路上還有很多。如果把所有落后國家的貧窮人口生活水平拉上去,這個市場有多大?如果造福貧困人口,他們生活水平走上來的時候,他們就會追求美好,這是不是我們中國的下一步呢?我說推動剛需源創新的解決機會比追求美好源創新的機會大多了。因為在追求美好有人要卡你對吧?那如果我把這個落后市場拉上去,整個市場會擴大,其實對美國也是有好處的,美國也可以分享這個市場。
TBR:那我們是要放棄追求“美好市場”的努力嗎?
謝德蓀:不是。美好還是做。美國做了我也跟著你來做。我們多一點BAT,京東,美團,這個是美好的,美國美好源創新做了我們跟著做,但不是完全是自己的新的東西。例如美國把無人駕駛做起來了,那中國很容易就應用對吧?但用無人駕駛代替現在的駕駛,這是美好市場,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交通不便,那放一個無人駕駛車去,幫助人們出行,這個就變為一個剛需市場。所以也可能在中國,是從三線四線城市來做,主要通過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做法不一樣,思維不一樣。
中國這樣慢慢做起來,就會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我就要把剛需源創新看為平臺的概念,其實互聯網平臺大部分是這種“美好的”,我認為剛需也可以有平臺概念——很傳統的產業進行思維改造之后,變為平臺,這是我在中國幫很多企業開始做的。
從一個產品或者服務怎么樣變為一個平臺,是思維的改變。我舉一個很簡單的案例。中石化在非洲一個國家有個天然氣工程項目——挖掘天然氣連接管道。剛去的時候,雖然跟這個國家簽了約,但是這個國家有不同的派別,常常搞事,當地人不合作,非常難做。這個工程的經理人研究之后,發現當地有很多的問題,例如沒水喝,很多小孩沒學上。于是他們幫他們打井,讓大家可以享受飲用水,還開辦學校,雇傭當地的人當員工。當地人做不好就培訓。然后當地人就改變了,覺得這個項目對我們是有好處的,那要幫他們一起來把這個項目做成功。當地人就把這個項目當成自己的項目來做。然后這個地方有穩定的電了,可以吸引很多人去投資,整個地區發展起來了。這個項目就變為了一個平臺。如果光是關注一個項目,那我用最便宜最好的方法把項目完成,就完事了。而源創新思維是我通過打造平臺,打造或帶動其他的價值,其價值不一定是項目本身。
如果用這個思維,我在一個地方建高鐵,高鐵本身可能會虧本。但如果高鐵修建的地方可以把當地經濟發展起來,和其他工業服務業掛鉤,那就不虧本。所有這種項目如果你用不同的看法,其中帶動的價值可以是很大的。我說,可以是顛覆性改變。如何顛覆性地滿足剛需市場,最后可能會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系統。我認為中國應該打造這個平臺。
我跟很多人說,污水處理的項目不要把它看成排污系統,因為沒人會為這個付錢給你,但是你要想到這個可以帶動什么?從這個思維,我們可以做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還可以做到全世界去。
TBR:您的想法很有新意。不過這里有非常多的挑戰,需要非常長期的心態,長期的規劃,長期的投資,這對于很多私人企業是巨大的挑戰,企業如果長期無法盈利,是生存不下去的。
謝德蓀:是有很多挑戰,但是沒有挑戰也就沒有什么好做的,對吧?這是非常長期的觀點投資。但是這個投資是需要的,現在我們資金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關鍵是你要投到哪里去?投資做一個比美國還先進的芯片,你說這個投資大不大?
TBR:那相當大,取得成功應該說會極其艱難。
謝德蓀:那這個錢是不是可以投到剛需那里去?芯片我并不是不投資了,是不是我跟在美國后面就行?我們不可能所有東西都是第一,對吧?要選個最主要的方向。

TBR:您的想法比較與眾不同。
謝德蓀:我覺得我們需要平靜下來,想想什么是我們的優勢。如果要做世界科技推動美好的領導者,第一個,從文化方面,我們沒有創新優勢;第二,美國已經走在前面去了,我們沒有領先優勢。我們的優勢在于,我們的文化在發展利用科技滿足剛需市場方面有優勢,我們知道剛需市場怎么做,可以在盒子里轉。美好一定是你現在不知道存在的,不知道是什么樣的,但一定不是現在的盒子里。
TBR:您說的美好是指創造新的需求。
謝德蓀:創造新的美好需求。美國的文化是對于創造“美好”市場是有優勢的。所有的東方文化有不同的優勢,因為我們的想法就是那么一個特點。中國有另外的優勢是什么?我們市場大,所以我們可用自己的市場來嘗試,做完之后再推廣。對于韓國來講就不一樣了,韓國市場太小了,必須要走到外面去。我們的高鐵為什么那么快超過日本,超過其他國家?國家大,我們現在建的高鐵比日本的多得多了。
我認為最主要是怎么解決我們中國貧困人口問題,把他們的生活水平拉上去。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一上去,就壯大了“美好市場”,美好市場越大,中國就越有控制力,美國就不會說不賣給你,因為市場大。最后說話的是市場——把市場搞好,掌握市場,你掌握什么技術我也不怕你。
所以現在中國就可以滿足很多剛需的需求。我預測新能源,中國會比美國跑得快,新能源用在中國很多還需要發展的地方,形成新的能源結構,而去替代舊能源是很難的。我們做好了,再引進到落后國家,最后我們的市場會比美國的市場大。
TBR:但是剛需市場的消費能力會不會太有限?企業是要追求回報的。
謝德蓀:所以剛需一定要和政府結合,開始的時候用政府的力量。推動剛需源創新,我們一定要用羊毛出在狗身上的思維。因為得到好處的人不一定是付錢的人。其實也不一定一定是政府付錢,可能你可以找到那個狗,把羊、狗各種要素結合起來發展。
TBR:然后您認為在這個最前沿的科技方面不要去趕上超越美國,而是跟隨,重點應用在剛需的滿足。
謝德蓀:在IT領域,美國已建立強大的生態系統,不要去在美好方面硬性競爭。在美好方面,我退下來好了,跟在美國后面。我解決剛需美國不會反對吧?因為我解決的問題可能有一天就幫助你的。我不是要替代你,我解決剛需市場,最后是一個互補和共贏的結果。如果我要靠你的技術,你要靠我的市場,那我們兩個就是死黨了。你需要我的市場,你是跑不掉的。因為越是高端市場,就越是必須往全世界走。在其他高科技方面,美國還未建立強大的生態系統,那雙方都處于平等的競爭環境中,最終的贏家是誰先建立更強大的生態系統,這方面中國有優勢把其他高科技領先應用于剛需源創新,在美好源創新方面,美國有優勢,那我便跟在美國后面。
TBR:跟隨戰略會不會跟不上呢?可能落后一步再也跟不上了。
謝德蓀:不會。跟隨不是跟到美國去,而是跟到中國來。你要開拓美好,你一定要跟這個市場很接近。我們離美國太遠,對美國的文化也不太了解,怎么去給它美好呢?同樣,中國的美好市場,美國也很難滿足我們,因為文化不一樣,大家的需求不一樣。所以我們中國的美好市場我們一定比美國有優勢的。所以我學你就行了,你先做完我就知道了,我再把它帶過來就行了。
TBR:但是芯片就帶不過來呀。
謝德蓀:芯片帶不過來。但是,從長遠來講,芯片是一定要賣給我們的,第二,我們可以研發特定功能的芯片。要做到英特爾那樣,我們中國很難做得到,市場也已經比較飽和。我們不要競爭這個。華為的做法是對的,我市場有了,那可以自己來做比較窄及自己可用的應用芯片。
(本文僅代表被訪專家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