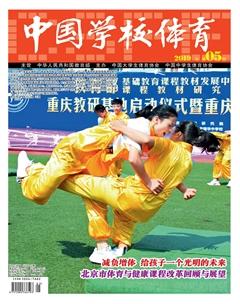讓身體“動起來”的意義:想怎么“動”就能怎么“動”
孫喜和 陳昌福
不同概念范疇下的運動其價值屬性是不一樣的,以健身為目的的運動,體現的是鍛煉價值;以競技為目的的運動,其價值在于競爭和獲勝;而以教育為目的的運動,則是追求運動文化的真意。從教育學意義上來說,運動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認知過程,也是運動技能的形成過程。反思以往所謂的“運動技術”教學,往往看到的大多是“單個動作”的教學,即使是學過了,也不知所學的是什么,有什么用。這樣的教學實質上是一種形式化的教學,結果是學生喜歡體育卻不喜歡體育課。本文不在于探究學生為什么不喜歡體育課的原因和理由,而是從另一個視角來說體育課應該給予學生什么樣的“技能”和這些技能可以以什么樣的形式表現出來。
本期研討的主題認為“體育教學不是讓學生學會1~2個技術動作,也不是學會1~2個技術,而是對運動文化的整體把握”,如果按照對“運動文化”整體把握這一前提下思考運動學習和體育教學,與“身體”活動有關的問題必然納入討論的范圍。那么掌握“運動技術”形成“運動技能”的新視野就可以從“動起來”的身體上進行探討。筆者認為運動技術的把握及運動技能的形成應該是“我”在一定的運動場域下,“我”的身體應該是想怎樣“動”就能怎樣“動”的。如,籃球的持球突破,不管防守者多么強悍,在屬于“我”的技能水平范疇內,“我”可以突破并且能夠突破對手。
從研討結果來看,也有許多一線體育教師對這一點有足夠的關注和認識。
一、固定思維模式下的“投擲”到類的投擲的觀念轉變
很顯然,以往一旦提到“投擲”時,人們往往想到的就是基本運動和田徑運動中的投擲項目,如,投實心球、投鉛球、擲標槍、擲鐵餅等具體內容。山東蔡延廣用教學實踐經驗對此進行了詮釋,他認為,對于投擲的理解,以前只是認為投擲項目才是投擲,而今天看了投擲的單元設計,才知道以前對投擲的理解太片面了。河南李時時認為,以傳統項目觀為主線的教學一般是從水平一就開始學習投擲壘球,水平二學習投擲實心球,水平三學習投擲鉛球,水平四學習各種投擲,雖然質疑并提出了案例的設計沒有突破傳統模式,但還是可以看到受傳統觀念本身根深蒂固的影響。江蘇姚饒認為,以往的投擲教學,無外乎是投擲項目的教學,或者歸納為“投遠”和“投準”的教學,學習內容諸如投擲壘球、實心球、鉛球、標槍、鐵餅等,但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傳統觀念這一提法的成立。
盡管研討中有許多體育教師對投擲內容還持有“傳統觀念”,但更多的教師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認為本次“案例研析”話題研討的“投擲”動作的系列單元更具有“投擲”的典型代表意義。
吉林高華偉對投擲動作給了最樸素的解釋,“投擲就是用手將某個物體拋出去,諸如投擲是身體將某種物體通過拋、扔、踢、投等形式的動作,使其離開身體的某類技能”,也具有這種含義。而山東侯靜的“投擲動作是體育活動中常見的操作性動作技能,是大肌肉動作技能,將全身不同部位相互協調用力,最終將力量轉化到手上,向一定的方向和目標投出或者擲出器材”觀點,則是對“投擲”動作從整體上進行歸納分析的結果,是一種新認識和突破。江蘇張建則列出了幾乎所有的投擲動作,包括“用單手或雙手將物體扔、甩、投、擲、推、傳、拋、挑、撇向目標的動作方法都可以稱為投擲,單手和雙手投準或投遠,原地、(單雙腳)跳起、(快、慢速)跑動中、擰轉體、向各個方向、正面、側面、背面、頭上、肩上、胸前投”。這種分類整理,對于體育教師重新思考投擲動作具有積極意義。黑龍江吳勇從投擲的構成要素方面理解和分析,“力量、角度、時機、準度、遠度、姿勢等都是相關要素,根據這些要素解剖,可以集中聚焦某個要素,也可以同時針對幾個要素”,則是教學和訓練中要考慮的關鍵要素,對提高教師的認識有積極的借鑒作用。正如浙江姜年軍所說,“不管是動作文化還是運動文化,本質上都是教育目的達成的載體,載體能夠直通目標,也可能與目標背道而馳,因此如何精準把控需要一個清晰的邏輯,如,目標·內容·教材·方法·評價一體化,或者為什么教—教什么—用什么教—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連貫一致”。精準把控,可以說是對“投擲”再認識的邏輯基準。
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從教學含義上對所要傳授的投擲動作的思考,一線教師的認識也在變化著,青海馬長虹的“案例更側重類的概念”觀點,實際上是本次案例研討中對動作認識的一個高度概括和總結,也是一種認識的新高度。當回到運動現實時,對投擲動作的認識也還只能是第一步,但這種認識的提升,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浙江施世想的“George Graham等的運動構圖的這些特征反映了由動作的名稱、構成開始,到這種動作可能的各種變化和組合,再到運動的意識、行為變化的運動整體觀,也就是從微觀的動作到運動思維的整體顯性化,避免了只見動作不見運動的狹隘動作觀(或者說是避免了狹隘的運動技術動作教學觀)短見,為體育教師重新認識體育教學中的運動教學提供了新的視點和開拓思考的可能性”,同樣他的“當旋轉運動構圖,也就是從動態狀態下對George Graham等的運動構圖進行解讀時,又對運動形式這種無限變化的狀況,如何應對呢?這恰恰是運動構圖對于單元構建的魅力所在,那么,如何選擇1個出發點,又如何設立1個歸結點,不僅僅是理解運動的本源所在,更是如何利用好它,形成運動技能的最佳思考點所在”的認識,也為體育教師進行再思考提供了一種思路和想法。
二、“投擲”動作學習的認知與“動”
從“類”的角度對“投擲”動作的解讀與分析,為運動學習提供了認知的前提和保證,對教學的有效開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山東徐江善認為,“投擲運動是全身各部分肌肉參與的運動,體現在主動用力和輔助用力,如果研究正確了,出成績是一定的”。很顯然,山東徐江善的“全身各部分肌肉參與的運動”從身體活動的角度對運動教學和學習的理解具有現實意義。因為以操作技能形成為主要目的的體育教學,應該是在一定運動背景下的身體表現,這種表現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技能水平的呈現,換句話說就是“想動”和“能動”。如,“我想將球傳給對對手最有威脅的球員”,在2名隊員意識一致的前提下就能將球傳給最有威脅的球員。那么,如何能夠做到“想動”就“能動”呢?本次研討許多教師對此也發表了個人的觀點,讓參與研討的教師們看到了體育教學未來的“動態”場景。
山東李革新認為,“案例給出的從水平一最基本的能力開始,在能力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上位的動作,再依據動作技能輪進行旋轉,同時讓學生體驗投擲內隱的各種信息,包括不同姿勢、不同角度等”“從更高、更快、更遠的角度分析,投擲是為了通過更遠的距離,獲得更好的成績。而在籃球的單手肩上投籃中,又是以投準為目的,所以,在不同學段,既要讓學生體驗投遠時身體肌肉的感覺,也要有投準時的對比體驗”“籃球轉身投籃是開放的有對抗的,投擲標槍是封閉的無對抗的。所以,在平時的練習中,要為學生創造相應的運動場域,為以后學生走向專項打下基礎。在未來的生活、運動中,他們很少用到或幾乎用不到投擲標槍的動作,但一定會用到投擲動作”“投擲時‘我的目標是什么,‘我與目標之間的空間是怎樣的,時間是怎樣的,要根據這些外在條件的變化控制‘我的肌肉,以及各部位運動時的感覺是怎樣的,這些都是需要一步步完成的,而不僅僅是投擲時的協調用力”“籃球的學習是在學生能夠較好地完成含有投擲特性的動作基礎上的,是在判斷、空間、意識等更高要求的應用,所以必須有好的基礎才能夠完成”“不同姿勢的投擲、不同遠度要求的投擲,其內隱的信息都是在讓學生體驗出手的角度,不同姿勢下的身體肌肉的感覺。在此基礎上,可以旋轉動作技能輪,如,設計快速投、移動投、連續的不定點擲準等,這些都是基于投擲基本能力下高要求的體現。再一層層地提高要求、組合,就出現了持器械的、有對抗的投擲等”。
山東侯靜認為,低年級應該以感知動作為主,中年級應為了達到更好的目標,嘗試不同的方式和手段,高年級借助助跑或者其他方式達成目標,整個過程是一個感知——嘗試——提高的過程。山東尹耀認為,從水平一教學目標來說,要增加“投擲”動作的多樣性,使該階段學生獲得豐富的動作體驗。浙江翟夢杰認為,在體育教學中如何讓學生較好地感知到自己做的動作什么樣是非常重要的。如,排球發球時,球拋的高度是否合適,那么,學生如何感知呢?這就需要教師知道學生在拋球時需要什么樣的感知力。通常,這些能力包括:手的方位的感知、空間和速度的感知、安全控球區域的感知、對器械的控制(手型和用力程度)、不同感官的綜合及三維空間的感受等能力,這些感知在時間和空間上應形象化和具體化,然后增強機體的控制能力,達到將球準確地擊出的目的。浙江鄭飛認為,體育教師不應忽略最基本的運動概念,如,方向、路徑、高度、姿勢、時間、力量等,從投擲的分類可以分為肩上投擲和肩下投擲,有物體的肩上擊打、肩下擊打等。力度、距離、精準度是投擲目的。應讓學生學會對物體的控制,獲得身體經驗和運動感知。在以后具體的運動場域中的“會”,應是將所學動作運用起來。山東付國超認為,動作學習的遞進是由對動作的基本認知到動作的基本體驗,再到利用投擲動作完成基本課題(運動任務),最后到在復雜條件下相關動作的應用,在這里面除了動作之外,意識的完善也是一條主線。
如對上述內容進行提煉,可獲得這樣的一些關鍵字或者句子:“體驗投擲內隱的各種信息”“體驗投遠時身體肌肉的感覺”“控制‘我的肌肉,以及各部位運動時的感覺”“投擲特性的動作基礎上,在判斷、空間、意識等更高要求的應用”“體驗出手的角度,不同姿勢下身體肌肉的感覺”“感知——嘗試——提高”“動作體驗”“感知力”“身體經驗和運動感知”“基本體驗”。這些關鍵詞恰好反映了運動學習的本質,身體認知和身體反應是動作把握和技能形成的基礎,是“動覺”的前提所在。那么,如何給出恰當的方法,讓學生學會“動”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由此來看,對“投擲”動作的正確理解和給予學生恰當的“感覺”“體驗”“經驗”,才會讓學生有“感知力”,才會體驗到動作的真意,形成身體經驗。
雖然,“想動”“就能動”是一種理想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動”的形成,決然不可能“想動”“就能動”的。“動”的學習是第1個層次,是體育教學的首要任務。
三、反思與小結
案例的主題是讓身體“動起來”,設計了從水平一(小學一、二年級)開始到水平四(初中3個年級)的具體內容,然而,只能說這還是最淺顯的一種構思。因為,單純的“投擲”動作與各種運動中的“投”與“擲”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投擲”的動作學習與投擲動作的運用與技能表現又不同,所以不能視為一回事。在案例研討中,筆者曾舉例說“基本動作技能的形成與發展,是身體能力形成的基礎,身體能力是更高級別運動能力形成的保證。NBA選手是一個典型案例。CBA呢?身體能力是一個方面,但基礎的薄弱、意識的缺乏等較多原因造成的結果是不能與NBA相比”,為什么這樣說呢?實際上身體能力和身體表現能力還是2個不同層次上的概念,體育教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身體能力和表現能力,但表現能力需要根據對抗水平變化,這就是舉例的真實意思所在。
研討中,也有教師提出了疑問,如,浙江王金龍的“這樣構建的理論依據是什么?效果好不好有沒有證據證明?是理論假設還是實踐結果?這個方向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它的劣勢是什么”。山東尹耀的“案例的單元設計中考慮的力量、方向、角度、用力方式(推、撥、甩)、單人、雙人等因素,從豐富性來說,是否全面?技能輪中哪些因素還沒有充分運用上?”“從技能輪由內向外來看,與‘投擲并列關系的還有持球、撿球、踢、運球、截球、用網球拍擊球、用長柄工具擊球等。體育教師在進行‘投擲單元設計時,如何更好地把握這種并列關系。換言之,這個‘投擲是徒手嗎?如果不是,那一定有具體器材的問題”等等,都具有較好的建設性建議,如何進一步深入思考和展開,對于《案例研析》欄目的發展具有價值,值得思考。
但,讓身體“動起來”的研討,從方向性來說,具有積極的引導意義,盡管還處在理論研討階段,但一旦成熟,必將為體育教育教學帶來根本性的轉變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