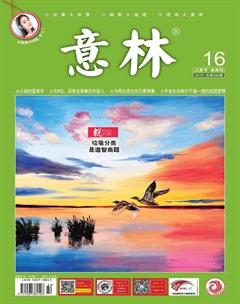送別
榛生
從小我就喜歡雜志。稍長一點,上了中學,我試著給雜志投稿。后來在我快畢業時,有一天,有人給我發電子郵件,說我就是他們要找的人。那是一本大牌雜志,他們要我寫專欄。像這樣的事后來經常發生,我漸漸就成了“雜志業的人”,但我另一個身份是一家昆蟲科研所的員工,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工作,有一位領導和一位同事。

我分到那家科研所的第一天,領導說:“大榛同志,你在右邊這間辦公室。”又對另一個剛分來的男生說:“大樹同志,你在左邊的辦公室。”
領導給我們倆一人一張飯卡,然后就回中間的辦公室睡覺去了。
何大樹走進來說:“咱倆今天要擦標本室!”他拿著雞毛撣子。他比我有責任心多了,先進去擦了一個小時我才去。標本怕蟲蛀所以在玻璃盒里放了樟腦精,年代久遠,樟腦精汽化再凝固,在昆蟲針上結晶成六邊的雪花、奇麗的鉆石或者美妙的冰塊兒。冬天下午,天黑得早,我們開著燈,在燈下看著那一盒一盒晶瑩的標本。那是我終生難忘的記憶。
“這一盒大蟲子是蠶嗎?應該不是中國的。”我說。
“印度的野蠶,吐的絲也能紡線,千年不朽。”何大樹說。
那是雜志業興旺蓬勃的零零年代,我的稿子登在各種暢銷雜志上,經過一間書報亭,十本雜志里七本都有我的愛情小說。
很多人喜歡我的文章,特別是那些少男少女,有一些知道了我地址的粉絲堵在科研所的門口,見我和何大樹一起走出來,她們發出粉紅色的尖叫。
何大樹就像我的兄弟、我的手足。兄弟同心,手足情深的那種。他連我吃面條打噴嚏面條從鼻孔里掛出來的德行都看到過,連我被領導狠批時哭出鼻涕泡的丑樣都看到過。
工作第六年,辦公樓改造,據說要把所有害蟲、育種、昆蟲類都排在大格子間里,我們一邊抱怨一邊盼望新樓的落成,裝修的時候領導安排我倆出走。“你倆出差去,內蒙古,四川,海南,東北,你倆選吧。”我說我去四川,何大樹說他去內蒙古,所以這就是我們倆,我們倆怎么可能戀愛呢?
去四川出差,當地科研所請客吃飯,在所有人中有一個人看上去有點特別,原來他是那家科研所請來的客人,是一位昆蟲學家。他比我年長一些,沉穩又溫和,在我唱 K 的時候,我知道他在看我,不看他也知道他在看我。
我怎么唱得這么好呢?我一首接一首地唱,直到連唱了十首歌快要斷氣時,那個人終于跟我說話了:“你頭發上有個瓜子皮……”他幫我把瓜子皮摘掉。
但就算有瓜子皮的阻撓,我和他還是一見鐘情了。回到武漢,一下飛機,手機里就看到他發來的短信。我的心差點從腔子里跳出來,硬給咽回去。就這樣,我戀愛了。
我這個戀愛談得可真不容易,遠隔千里,牽扯著一脈紅線。他有時候在國外,會在我的中午、他的半夜跟我視頻。這種時候,何大樹你為什么不滾回你的辦公室,跑來跟我瞎叨叨什么呢?
“酒精燈煮面條,面條帶著酒味,我吃一碗要醉啦醉啦。”何大樹說。
“胡扯,別發羊角風了。”我轟他走。
光有視頻是不夠用的,我用盡一切辦法和男朋友見面。在馬六甲海峽遠望著海面上的云,近處紅色的屋頂,有一只貓懶洋洋地走過來,睡在我的腳邊。我和我的愛人曬著暖暖的太陽,我們真的不想分開。“結婚吧。”他說,“買一所房子,生一個小孩,養一只貓,我們安定下來,一起度過一生。”
知道我要結婚了,領導不無惋惜地說:“這下我們小何落單了。”何大樹在隔壁辦公室說:“請別提我!”
為了慶祝我結婚,幾個同事一起出去喝點酒。他們說:“何大樹啊何大樹,你把窩邊最美的獨角仙放歸了森林啊!”
“不對不對,大榛還是比較像一只竹節蟲,坐那里能一上午不動。”
“試試說她是蜣螂看她會不會發火?”
他們極盡所能地開玩笑,因為知道榛姐今天一定不會發火。何大樹一滴酒都沒喝。
喝醉的,桌子底下躺著好幾條。他挨個扶起來,他們又倒到桌子底下。
法布爾來接我了。
何大樹對我說:“你先走,我來搞定。”然后孤身處理一群醉鬼,我想,兄弟嘛,兄弟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心里唯一一點兒過意不去也就煙消云散了。
從大學畢業到工作的第七年,從二十三歲到三十歲,這是我青春時代最蔥蘢的回憶。三十一歲,我和法布爾移民去了新西蘭。在新西蘭醫院的產房,滿身大汗但又渾身發抖,全身的骨頭縫兒都撐開了,頭上冒蒸汽,舌頭冷得打結。洋護士體貼地往我身上灑滿冰塊……那個時候,忽然想起小辦公室的酒精燈,那么小,但是那么溫暖,想起那些和大樹同志吃著熱乎乎方便面的中午。
孩子出生后,我和中國漸漸失去了聯絡,那些年,我很少寫作,也難得看到一本中國的雜志。我曾經那么喜愛雜志,時間的洪流追逐它消亡,任何人都挽留不了,就如同青春一定會從你的身上離去。
“我也要離開科研所了,這兒還有些你的東西,你還要不要?”何大樹在微信上問我。
不久后我收到從中國寄來的包裹。一本我在各種雜志上刊登的小說的剪貼集。什么時候做的?為什么做?何苦要做?我想既然寄來此物的人沒有附上留言解釋,那么我也就沒有必要再問。
用一幅布料包了封面——只有常年擺弄蝴蝶的翅膀、草蛉的觸須或是夜蛾、螳螂、白蟻、天牛標本的手,才能如此靈巧,做得了這樣細致的手工活兒。
布料細薄帶韌性,灰褐色,不是染的,天然就是那個顏色。
我認得出那是野蠶的絲。大樹一定去過印度了。這種野蠶只有印度才有,幼蟲綠色,渾身長毛,蠶繭拳頭大。不必像家蠶那樣燙繭抽絲,野蠶會咬破繭變作團扇大的蛾子飛走,所以取來的蠶絲是斷的,細碎的,做出的布料是粗糙起毛的。何大樹,他居然去了印度!
我想象他在某棵大桑樹下,野蠶爬滿了頭發,取到幾個繭,揣進衣兜。而那時我在新西蘭,也許正在喂自己的小孩吃南瓜泥。
我是談一次戀愛就成功結婚的幸運女生,但我心中也有一個微小的惆悵,關于一個我從未愛過,但對我一往情深的兄弟。
我忽然明白他為什么要將這本剪貼集寄給我,并不是“不寄不更好嗎”那么簡單,必須要寄,一定要寄,因為這也是他的儀式,是他在跟他的青春作別。從此他經秦嶺,過藍關,渡瘴江,再到惶恐灘、零丁洋,最后去往海外另一座島嶼安家,就像我們每次出差那樣,同時出發,但不同時歸來,我們有各自的人生,各自的行程,各自的山河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