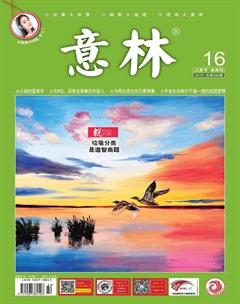高考過后,校門口的小吃就都過期了
姜思達
我對高二時的高考季印象深刻,那會兒我們面臨著兩件事:一是隨著高三考生即將離開,我們要搬教室;二是我們要打掃好他們遺落的空蕩蕩的教室,以作考場用。
我們掃完是下午三點來鐘,藍天被烤熟了,我們出去吃冰棍。

我們被班主任養成了愛吃冰棍的惡習。尤其到大半年后的高考沖刺季,班主任總是薅走班級里某兩個壯男,抑或是閑來無事的末位生,去北門外的小賣店買冰棍。兩大箱幾十根,分為“冰的”和“奶的”各一半。
學校的食堂基本沒有人去,極少聽說誰在學校食堂吃飯,無論是午餐還是晚餐。
在我家和學校中間的位置,有一家韓式料理,叫云平,很正經地面對顧客的那種餐廳,炒菜、拌面、鍋包肉。那個拌冷面,我在其他地方就基本沒有見過了,很私有的配方,很難忘的味道。
另外兩家,是難得一面和新羅酒家。難得一面就是刀削面,牛肉刀削和涼拌刀削,配一些辣菜。后來我才意識到那些辣菜比如豆泡、干豆腐皮可能均來自延吉。
每個中午,都是聊八卦的時間。根本就是不談及學業,也不討論考試。所謂的八卦無非是今天誰上課聽見誰跟誰說啥了表示匪夷所思,要不就是你知道嗎昨天晚自習的時候誰偷偷跟誰去干啥了。無聊到回想當日,什么都想不起來。
復讀那年在大慶,讓胡路區,其實跟我老家還挺不一樣的,周圍一切都為了這個學校。老家那會兒,中午還能溜達去買個肯德基帶回來吃吃,大慶這邊,基本得在食堂。不過食堂挺好吃的,早上有蝦漢堡可以吃,出操的時候,總有人會去買兩包泡椒金針菇。
大慶實驗中學的校門口有一個烤串很驚人。就是流動攤販那種,一塊錢一根烤串。一般會買十串。這是我目前吃過的唯一一個會撒糖的烤串,肥得要命,香得要命。晚上就買一把,那會兒我的室友會吃四個,讓我吃六個。
另外一邊的大門,對著幾個小餐館。有一家叫媽媽拌飯館。如果不想去吃食堂,基本就是去那兒。媽媽拌飯館里固然有一些拌飯,但都不是很好吃,最好吃的是炸醬面,有點甜面醬的感覺,黑乎乎的,非常非常黑,有煎雞蛋可以碎在里面。后來這家店老板換人了,不再好吃了,我們就叫它“后媽拌飯館”。吃完飯,我會跟我的室友去旁邊的一個浴室洗澡。洗完澡回去上晚自習。從某些角度說,大慶實驗中學還挺好的,人才輩出,清華北大扎堆往外送,高考結束我在學校排出一二百名之外。
年輕人啊,你高考后,校門口的那些美食,就一一過期了。
它們過期了,因為你很有可能不會再去了。你會很想念它們的味道,但新的刺激遠遠比記憶的誘惑更有煽動力。這些餐廳只是日復一日記載著學生們不斷重復的史料,大同小異——緊張、無聊、貧窮、炫耀、朋友吵架、戀人分手、你過生日、他進醫院。校服上的馬克筆,腳上踩的三葉草,低賤的奶茶香精,目中無人的滾滾油煙。一沓沓的面坨子和一盆盆的大米飯,它們喂飽了這些饑餓的年輕人,它們卻永遠抓不住這些年輕人。哪怕年輕人,不會輕易忘記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