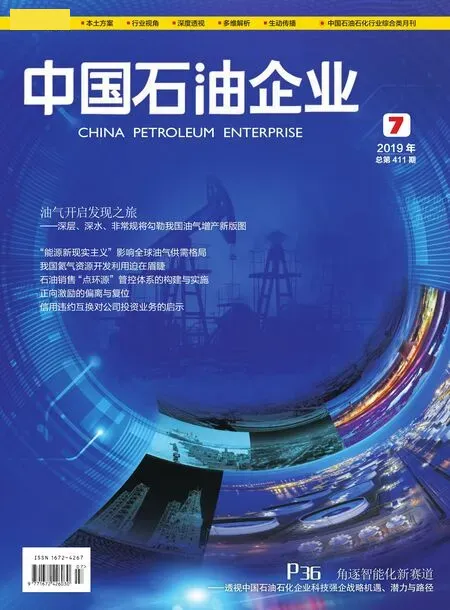我國石油石化產業轉型戰略機遇與選擇
全球能源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智能化、一體化、微型化、低成本為主要特征的技術革命加速產業化,極大地改變未來石油市場競爭格局。由于智能化技術在現有井下工具系統中整合大量前沿技術要素,未來石油市場格局、業務模式、成本變化在油氣資源技術革命推動下可能被顛覆性改變。從主導性能源轉換歷史來看,這場圍繞數字化新賽道大博弈持續時間可能到2035年前后。其間,勝者將占據產業鏈頂端,主導油氣版圖劃分;失敗者將卷縮一隅,被動接受油氣產業秩序位置。
大數據是油氣產業關鍵技術要素,它將在傳統工藝流程中99%未被利用的數據集中釋放,從源頭上提升產業鏈價值。IBM公司認為,未來10年,從采集頻次到刻畫精度,互聯設備和分析技術可產生10000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效益。率先采用新技術、新工藝的企業,將通過大數據獲得技術壟斷。
與國外領先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國石油企業在地震勘探技術應用領域,基本處于同一水平;在地震勘探技術創新領域,物探技術進步主要以集成創新為主,但自主創新能力仍然不足;在轉換波勘探中處理解釋技術有了很大進展,但多波勘探處理解釋技術仍在試驗階段,四維地震油藏監測技術也在試驗階段。因此,應跟蹤前沿、加強基礎研究,強化采集、處理、解釋關鍵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而要發展解釋新技術,提升計算機運算能力、圖形處理和相應軟件升級是前提條件。
目前,我國石油企業各大探區面臨地面與地下地震地質條件差異大、勘探難度系數大等難題,而在有利凹陷區,大多已完成三維地震二次覆蓋和多輪次處理。如渤海灣一些盆地,近年來已完成二次三維地震采集,今后可否借鑒國外小面元、高密度、寬頻帶、寬方位地震采集和各向異性逆時偏移處理技術,來提高復雜斷塊和小斷裂成像精度;針對塔里木油田碳酸鹽巖非均質儲層,可否借鑒國外小面元、高密度、寬頻帶、全方位地震采集技術、各向異性逆時偏移和全波形反演處理解釋技術,來提高縫洞型儲層定量雕刻精度。這就要求在技術配套上,向高精端疾進:在地震裝備上,陸地裝備應向10萬道以上帶道能力發展,海上地震裝備應向20纜以上能力發展,未來裝備向百萬道發展;在采集技術上,陸上、海上采集應向寬方位、高密度、寬頻帶可控震源、雙檢電纜等技術發展;在地震處理上,應向各向異性逆時偏移、全波形反演等先進技術發展;在地震解釋上,應向多波處理解釋、四維地震、巖石物理等解釋技術發展。
在2009年頁巖氣革命推動下,世界石油市場初現立體博弈格局。美國依靠頁巖油氣繁榮帶動實體經濟復興,輔以成品油/原油出口政策調整,在原油、成品油、石化產品三個市場領域驟然打破了世界供需平衡;油氣行業利潤中心沿產業鏈下移,煉化產品市場可能成為大國油氣博弈的正面戰場。受原油與天然氣價格間的比值長期且持續擴大影響,全球,特別是歐亞地區75%以石腦油為原料的乙烯生產商,不得不沿著成本曲線向上攀援,進而在全球掀起一場下游化工產業價值從歐亞洼地向美國價值高端轉移浪潮。僅2011年以來,就有550億美元新增投資,陸續在美國50個石油化工新項目上集中上馬,并有望在4—5年內形成產能。2014—2018年,美國已連續4年都有新煉油裝置建成投產。屆時,將沖擊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石油化工企業,也為化工產品供需結構失衡預留了空間。

當前,我國石化和化工產業價值觀正在發生變化,成為產業體系重構的核心動力之一。這主要體現在社會體系對化工發展成功與否的判定標準和取向。我國石化和化工產業需求已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生活型階段,下一步將要進入到生態型階段,需求層次、需求內容、產業映射和核心價值等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我國石化和化工產業正在努力,盡快進入生態型階段,這需要更多高端技術和清潔資源的保障。
煉油行業要認識到產能過剩的嚴峻性,一定要推進部分產能退出或者企業轉型。綜合考慮未來國內經濟增長率、汽車保有量、天然氣及電動汽車替代率等多種因素影響,預計2020年國內成品油需求量為3.7億噸。按照65%的成品油收率和80%的開工率計算,屆時合理配置煉油能力應為7.1億噸/年。而2020年全國一次加工能力預計將達到8.2億噸/年左右,過剩能力將維持在1.1億噸/年,產能過剩形勢依舊嚴峻,對于煉油產能的增加一定要慎之又慎。
烯烴行業需注意原料輕質化迫切性的增加及多元化發展呈現的新格局。應立足國內資源稟賦特點,加強行業管理,合理引導煤/甲醇制烯烴等新原料路線烯烴工業有序發展,充分認識其產品競爭力和區域市場要求,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在產業定位和布局上與傳統石腦油裂解制乙烯工業實現錯位發展。擬發展乙烷裂解制烯烴或丙烷脫氫制丙烯或碳四資源綜合利用等低碳產業,應深入研究資源來源條件和分層次的產業競爭力,不可造成過熱或者一哄而上。芳烴行業則需注重調整優化布局,結合煉化一體化統籌發展。
高端專用化學品和戰略性新興材料產業占有率極低,是制約我國石油化工產業向需求頂端移動的“命門”。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化工品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一直沒有解決精細化工發展問題,這與國有石油石化企業將自己定位于能源化工公司有關。一方面通用產品產能過剩;另一方面高端產品大量進口,石油和化工行業產品結構向精細化的轉型迫在眉睫。
智能化轉型是我國石油化工行業未來發展方向,但在具體實施層面還有許多功課要做。首先,與世界石油化工強國相比,我國在化工信息化建設方面資金投入不足,這也是大而不強的原因之一。智能制造基礎是CPS(虛擬-物理系統),而CPS建設是需要足夠投入來推動的,沒有這一前提,智能化無從談起。其次,目前我國制造服務業服務能力十分有限,特別是針對石油和化工行業的IT技術服務更是羸弱不堪。雖然國內網購和電子商務很發達,但制造業和IT產業還是兩張皮,還沒有看到有影響力的制造服務商。石油化工行業復雜性,讓許多IT公司望而卻步,國內鮮有專業軟件/互聯網等IT公司愿意深耕這一領域。幾家特大型石油化工企業雖有內部IT隊伍,但其母公司均沒有想將其徹底進行體制改造,打造成面向行業提供社會化、專業化服務的公司。與之相反的是,國際一些知名軟件/互聯網等IT公司跨界延伸服務已深入到實體制造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