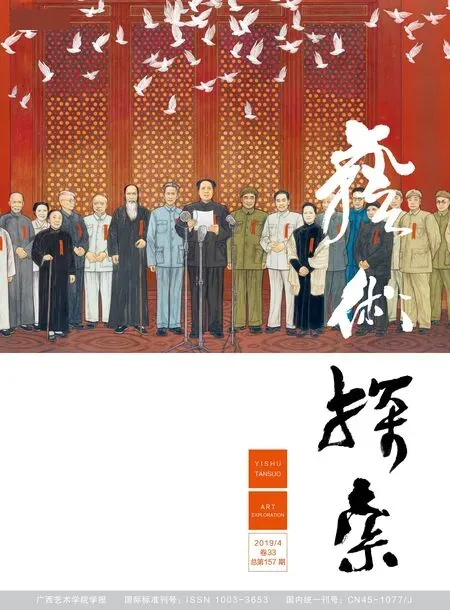從喬治·奧特看超現實主義藝術話語在美國早期現代藝術語境中的延異
聶皓雪
(廣州美術學院 藝術與人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1400)
引言
作為美國早期現代藝術中一位被歷史淹沒的藝術家,并不長壽也并不多產的喬治·奧特通常只是作為藝術史敘事中的一個短小的腳注出現。然而,其短暫的藝術生涯中所創作的面向及其豐富的作品,跨越了包括精確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等不同藝術流派與運動在美國本土的發展軌跡。對喬治·奧特藝術作品的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補足美國早期現代藝術史敘事中存在的論述不足、語焉不詳,甚至相互抵牾的狀況。喬治·奧特與超現實主義美國化之間的關系,正是一個值得切入的角度,幫助我們進一步厘清超現實主義運動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沉潛之后,是如何輾轉騰挪、轉換調停,最終得以抵達60年代以降的全面復興的。
一、浪漫主義與政治議題:奧特的取與舍
在與超現實主義藝術運動存有交集的眾多藝術思潮中,浪漫主義也許是最為核心的部分之一。我們今天提到浪漫主義時,多是將其視為一種19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文學與藝術運動。而實際上,它有著更為廣泛與普世的意義——就是作為席卷各個文藝領域的一種思潮。其核心的部分,是以過去某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或社會價值來反對現代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文明,充滿著一種對失卻天堂的懷舊感,對資本主義商業價值觀的懷疑與否定。布列東曾經從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①諾瓦利斯是德國浪漫主義詩人、作家、哲學家格奧爾格·哈登伯格(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1772—1801年)的筆名。其著有詩歌《夜之贊歌》(1800年)、《圣歌》(1799年),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1899年)等。處得到靈感,引申其“魔幻藝術”(Magic Art)的說法,提出“藝術是否有改變生活的魔力”的問題。諾瓦利斯曾經稱“浪漫化這個世界,就是使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的魔力,領略它的神秘與神奇之處,就是教育我們的感官去感受,使得尋常之物變得不尋常,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平凡的事物變得神圣,有限的事物變得無限。[1]294可以說,這段話完美地預示了超現實主義運動中的浪漫與幻想的傾向。當代藝術史家英格麗德·夏弗納(Ingrid Schaffner)也曾經將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①新浪漫主義一詞用來表述自浪漫主義運動之后(尤其是20世紀以降),所有在哲學、文學、音樂、繪畫與建筑等領域均與其產生交集的創作媒介。新浪漫主義的審美取向,在19世紀40年代以降曾在不同的時期被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或現代主義的作家,畫家與音樂家運用。叔本華和尼采等哲學家都對新浪漫主義思潮的形成與完善做出很多貢獻。總體來說,在新浪漫主義的框架下,存在著一種對于現代文化生活重新定位的主張;新浪漫主義者們認為人類的靈魂始終在召喚生活的意義與內容,這或可減輕現代生活的碎片化帶給人們的失重感與焦慮感。在此處,新浪漫主義傾向于指涉出現于20世紀30—50年代的一個松散的繪畫流派,它導源于英國。實踐這一風格的風景畫藝術家們,一方面回溯19世紀的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和塞繆爾·帕爾默(Samuel Palmer)等人具有敘事性與浪漫抒情性的風格;同時也受到了如畢加索、馬宋、謝利仇恩等法國現代主義藝術家的影響。具體地說,這次運動是對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精神壓力的回應。該運動的主要藝術家有保羅·納什,約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拉漢姆·薩瑟蘭(Graham Sutherland)。與魔幻現實主義(Magic Realism)②藝術史家阿納森(H.H. Arnason)在其專著《現代藝術》(Modern Art)中曾經這樣定義:“總的來說,魔幻現實主義者的直接導師是基里柯,他通過并置的方法創造一種神秘與使人驚異的視覺效果,使得觀者在辨認繪畫中的對象時感到無所適從。魔幻現實主義者雖然不似原教旨意義上的超現實主義者那樣沉溺于弗洛伊德式的夢境建構中,卻也對將日常的經驗轉換為陌生與神秘有著極大的興趣。”稱之為“超現實主義的兩個表親”[2]122。
奧特相當一部分風景畫作品的趣味,正停留在浪漫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交集之中。當朱利安·列文的私人畫廊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出超現實主義者的繪畫作品時,奧特也是其中的常客——其實,奧特也曾經邀請列文到訪自己的畫室評鑒他的作品,不幸的是,列文稱自己從不上門拜訪藝術家,而是需要他們親自帶著作品前往畫廊拜訪——這在生性敏感的奧特看來也許是不友善的信號,他亦大約就此錯過了與列文畫廊之間建立更多聯系的機會——從他在列文畫廊展覽名單的缺席中就可以看出。但奧特并未因此放棄自己同超現實主義繪畫的聯系,[3]39而且,居停伍德斯托克的早期,即便迫于生計的奧特不得不更加緊密地參與聯邦政府的藝術救援計劃,他對此活動的參與也并不積極,始終感到自己的創作受到公共題材的限制,超現實主義風格作品的創作也一度受到擱置與妨礙。[3]39這種牽引力,也是奧特始終未能在超現實主義里超脫現實的部分走得更遠,而總是流露出浪漫主義晚期浸淫著幽暗與頹廢情緒的,帶有一種末世感的現實色彩的原因。當然,這種現實,也多半是奧特構想出的“現實”,一種看似現實的“超驗現實”——與社會超現實主義那批關心社會議題的藝術家不同,奧特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表達過任何的社會現象,或者說,他無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展開對超現實主義政治維度的開掘。然而他所處的階級與所受的教育還是使他對社會與政治事件始終抱持獨立的立場與高度的自覺——他并非不關心政治,只是他不將此訴諸于藝術創作之中——而且,某種程度上,他刻意避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政治與社會主題,這反而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在分析奧特這個類型的藝術作品之前,我們需要先進入奧特所處的政治環境,這會幫助我們理解奧特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的創作心態。作為一個有著良好政治素養的公民,奧特不但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也充分利用了結社與集會的自由。在路易斯看來,“奧特一生都是社會歷史事件的積極關注者,對有關人類發展的社會民主、公民平權、政治選舉等議題高度關注,甚至十分沉迷”[3]39。這種入迷,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在奧特的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最后幾年中,也就是在伍德斯托克寓居時,路易斯與奧特的通信往來證明了這一點,奧特在信中大量提及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并且訂閱了德懷特·麥克唐納德(Dwight Macdonald)的雜志《政治》(Politics)③《政治》(Politics)系德懷特·麥克唐納德創立,并作為主編的政治期刊,發行時間為1944—1949年。麥克唐納德曾在1944—1949年為雜志《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編輯,但之后便與之發生分歧,從中退出,創辦了《政治》雜志作為其對手出版物。和紐約左翼報紙《工業與經濟》(PM.)④《工業與經濟》是美國作家與編輯拉夫·英格索爾(Ralph Ingersoll)在紐約創辦的,于1940年6月到1948年6月發行的自由派報紙,由芝加哥百萬富翁馬歇爾·菲爾德三世資助。。同麥克唐納德一樣,奧特敏銳地察覺到斯大林社會主義者的集權傾向,政治觀點傾向于麥克唐納德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盡管他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美好的愿景”,像宗教一樣。[4]1211奧特更曾在信中指“骯臟的FBI(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像一個“美國蓋世太保”,認為戰時的行政機關是“大商業帝國主義者的新政權”,稱這是之前的斯大林主義對于美國的影響。[4]24-26根據路易斯回憶,某次她與奧特走在紐約街頭,看到一個男人因為饑餓“快要昏死在路旁”,“之后,奧特毫不猶豫地走到紐約共產黨總部,注冊成為一名黨員,希望付出時間與精力了解參與政治事務——這對于奧特而言,并不完全是沖一時動。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他便意識到了法西斯鐵蹄的迫近,而他認為只有共產主義者能夠解決這些問題”[4]1119。路易斯記得奧特加入共產黨的時間是1935年,但她已經不記得確切的日期;她同時稱奧特在1933年秋天曾擔任約翰·里德俱樂部藝術學校的素描老師[5]224。1935年,奧特與包括斯圖爾特·戴維斯(Stuart Davis)在內的藝術家一起在美國藝術家協會(American Artists Congress)①美國藝術家協會成立于1936年,當時是從屬于美國共產黨大眾戰線的一部分,作為團結藝術家來抗爭法西斯主義擴張的中介。該協會匯聚的主要是紐約的現代藝術創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組織最終并入了“為勝利而戰藝術家委員會”(Artists’ Council for Victory)。為左翼雜志《新大眾》(New Masses)十月一號的發刊做準備。然而,加入之后的奧特卻顯得與這個圈子格格不入——在該組織于1937年舉辦的第一次年度成員展覽中,奧特的參展作品是與政治主題毫不相關的《伍德斯托克的夏天風景》(Summer Landscape,Woodstock,1937年)。如此“去政治化”的作品,在一眾爭先恐后表達社會現實與人文關懷的主題中跳脫了出來,顯得很不協調。[4]1036-1037事實上,在與戰后方興未艾的抽象繪畫潮流擦肩而過之前,奧特這種內向觀的,從不直接在作品中反映社會現實的傾向,讓他首先錯過了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現實主義的繪畫潮流。在“美國群體”(An American Group)②“美國群體”(An American Group)是一個有左翼政治思想傾向的藝術家作品展覽機構。與海上工人委員會聯合創建的,由社會研究新課堂舉辦的“海濱藝術展覽”(Waterfront Art Show)中,奧特再次展出了他創作于20世紀20年代的作品——又一個“形式”重于“內容”的,與社會現實完全不相關的《離開港口》。奧特并非一個待在象牙塔中的藝術家,他只是刻意在自己的創作主題與社會政治事務之間劃上界限,不像其他的同輩畫家一樣直接在作品中反映鮮明的時代主題。他十分希望自己在對抗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主義的浪潮中貢獻個人的力量,并且極其耐心地忍受所有組織性政治團體操作與運行方面的笨拙與不成熟。整個20世紀30年代,奧特與路易斯都參加了這個時期的典型政治活動,比如參加藝術家聯盟(Artists’Union)組織的會議。③藝術家聯盟位于紐約,是一個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短暫存在的紐約藝術家聯合組織,對1933年12月份開始的公共藝術計劃與1935年開始的聯邦藝術救援計劃的施行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20世紀30年代,為藝術家的集會活動提供便利條件,對藝術家參與社會事務有很大推動作用。該聯盟于1942年解散。1935年末,他們一同觀看劇院聯盟組織排演的戲劇,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④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898—1956年),德國現代戲劇家、詩人。他的劇作在世界各地上演。布萊希特創立并置換了敘事戲劇,或曰“辯證戲劇”的觀念。的《母親》(Mother),對法西斯在西班牙的暴行感到痛心疾首。[4]1009-1010
這種不合作的立場,是因為奧特的藝術主張與左翼共產主義者們是完全不相諧和的。1936年11月,奧特曾經在聯邦劇院的電臺部發表了一次名為“藝術創作的主題”的講演。開篇他即援引了唯美主義者畫家惠斯勒作為例子:“在我看來,以目前藝術的發展狀況,就‘大寫’的藝術這個概念來說,只有當其能夠被用來激發一個藝術家創作出一件真正意義上的藝術作品的靈感時,才具有重要性。而且,為了能夠達到啟發藝術家的效果,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藝術家的情緒本能以及他的個人審美取向聯系在一起,成為可感知的東西時,才具有重要性。”為了進一步說明他的觀點,奧特將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Eug ène Delacroix)⑤歐仁·德拉克羅瓦(1798—1863年),19世紀法國著名浪漫主義畫家。曾師從法國古典主義畫派畫家皮埃爾·蓋因(Pierre-Narcisse Gu é rin)學習繪畫,但卻非常欣賞荷蘭畫家彼得·保羅·魯本斯繪畫中的色彩表現力,并受到同時代畫家籍里柯的影響,熱心發展色彩的作用,成為浪漫主義畫派的典型代表。與拉斐爾前派畫家約翰·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⑥約翰·米萊(1829—1896年),19世紀英國畫家與插圖畫家,拉斐爾前派創始人之一。進行對比,稱德拉克羅瓦“選擇題材,依據的是他擅長創作的大型繪畫的尺幅——因為這有助于他表現作為藝術家的情感”,而米萊“并沒有選擇他的主題。他僅僅在描繪歷史畫,這個題材在當時的英格蘭十分流行——因為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社會是可以管控藝術家們的創作題材的”。之后,他將目光轉向自己所處的時代,當“那些突然成為了關懷社會與經濟現狀的人堅持認為藝術家應該扮演‘圖畫宣傳者’的角色”,這樣的人便成為了“決定藝術家應該創作何種題材的獨裁者”,而這種行為同“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獨裁者告訴藝術家應該創作什么”是一個性質。他接著說道:“以相似的方式,我們有一群教條主義的審美者,他們的教條主要是以政治化而不是以藝術審美為先的——我覺得這種思維毫無意義。在藝術家選擇繪畫主題的時候,他應該被放在一個獨立的環境中,而不是被驅使與擺布。而任何一個熱愛藝術的人都會明白,他對一件藝術作品的欣賞不會僅僅是因為它的主題——只要這件作品是以形式與色彩之和諧的組織布局為基礎完成的。在此之后,觀者方才會展現出自己對其主題的看法。”[6]3-5
在此前提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反駁克勞斯·曼(Klaus Mann)①克勞斯·曼(1906—1949年),現代德國作家,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與妻子卡提亞的兒子,主要撰寫戲劇評論與短篇小說。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捍衛超現實主義表達之正當性的舉動了。1943年,奧特致信《藝術文摘》(Art Digest),控訴克勞斯發表在《美國精神》(The American Mercury)中對超現實主義進行猛烈抨擊的文章。[7]174-181奧特認為克勞斯的攻擊完全是粗魯的政治偏見,并且稱“超現實主義已經開啟了全新的表達世界的方式,這個世界充滿了奇異與美妙的想象力。這與喬托對他所處時代做出的貢獻,印象主義者與后印象主義者在藝術史的轉折點處做出的貢獻是相同的”[8]27-28。

圖1 喬治·奧特《法國海岸的回憶》,1944年,伯明翰藝術博物館
二、現實之外:形而上世界的建構
雖然拒絕在作品中直接呈現政治與社會性的內容,奧特在作品《法國海岸的回憶》(Memories of the Coast of French,1944年,圖1)中,還是含蓄巧妙地將自己的感時傷懷投射到了作品之中。畫面里,奧特描繪了一個海岸線的風景:畫面中景處是一個鋪滿砂礫的半島,延伸到海域內,連貫的場景被一些風化的石頭阻隔成曲折的線條,逐漸彎曲為“達利作品一樣的形狀”[9]30。奧特告訴路易斯,“我有一種極度的不真實感,尤其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這真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世界”[10]54。畫面的背景是一些失事船只的殘骸,由沙灘上立起的桅桿可以分辨出來。畫面的前景則是一個裸女坐在石頭上,伴隨著潮汐的起落,這個裸女形象的出現,就是畫面中超現實的部分。而這件作品完成的1944年,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法交戰最為激烈的時候。路易斯對這件作品做出過一些說明,她曾回憶,當奧特聽到法國被占領的消息時,“雙手顫抖,低頭啜泣”。[4]127-128他當時已經情緒失控,無法作畫,等到情緒平復后來到畫架前開始創作,便有了這幅作品。奧特對法國的感情,正如這件作品的名字所指涉的那樣,來自于他的“回憶”,也就是他青少年時期美好的歐洲時光,他與家人一起無憂無慮的、此后終其一生的日子里都在追憶的時光。法國之于奧特就像精神故鄉一樣重要,20世紀20年代初期,他幾次在巴黎度假,參觀藝術展覽,與兄弟們一起外出游玩寫生。[4]耶魯大學教授納莫魯夫稱這件作品中的云彩“以箭頭和雞冠帽一樣充滿敵意的進攻的姿態出現”[9]30。路易斯也曾指出“這件作品有著不易察覺的暴力觀念”[9]127-128。而畫面中仿佛超塵遺世的裸女,不僅是古典藝術概念中唯美典雅的化身,還有自己永不復還的往昔時光的暗示——所有脆弱而易逝的美好的總和。畫面中環境的失重感,暗示了一個也許來自于記憶,而甚或是夢境的場景,襯托出整個場景的孤冷與絕望。如路易斯所指出的那樣,整個畫面的情緒是關乎憂郁與悲痛的,而且它不應完全被理解為一個孤獨避世者對過去的追憶,它更像是一曲挽歌——那個藝術家曾經陶醉其中的世界,正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4]38

圖2 喬治·奧特《電纜箱》,1944年

圖3 喬治·奧特《月亮與云》,1945年
《電纜箱》(The Cable Box,1944年,圖2)的創作背景與《法國海岸的回憶》相似,也是與二次世界大戰和奧特的法國記憶有關。這幅作品的構思來源,是奧特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的法國海岸旁一個軍事基地的照片——這再次勾起了他兒時的記憶。在這幅作品中,象征著現代景觀的電纜箱被放置在茫茫的海岸中,畫面中前現代與現代的景觀都感到絕望——正像天空里漂浮的那朵形狀奇異的烏云——奧特很關注天空中云朵的形狀,他曾經“讓路易斯觀察草地與山間上方的天空中云彩的形式”[4]53,也曾多次對著天空中變幻多姿的云彩寫生與創作——奧特對云的迷戀,包裹著他始終不變的“賴德情結”,還體現在他1945年創作的炭筆素描作品《月亮與云》(Moon and Clouds,圖3)中。這顯然屬于奧特作品中與自然相通的部分,畫中的云彩在強烈的明暗對比中形成一股攻擊波,它們向著右邊進發,聚集起強大的勢頭,彌漫在整個畫面中構成壓倒性的力量;它不是歲月靜好的風景,而是來勢兇猛的反作用力,而處于弱勢的月亮則被包裹在緊密的漩渦之中。《電纜箱》中傳達出的冷漠與隔絕的氛圍,與奧特斯萊德學院曾經的同窗保羅·納什(Paul Nash)表達戰爭主題的作品也有異曲同工之處。路易斯記下了奧特構思這幅作品的過程:
當喬治看到了《紐約時報》刊登的一幅法國海岸線旁電纜箱的照片,他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建筑形式,之后將它用在了一幅新作品的構圖中:一個電纜箱,一個帶有電線卻突然斷掉的電線桿,神秘的浪漫化的云彩和一片海。他幾乎是癡迷而歇斯底里地渴望著一個有秩序的,和平與民主的世界,然而他看到的卻是為戰爭構建起來的電纜箱。文明的世界危在旦夕。前路究竟在何方?[4]97
路易斯接著又感慨道:“‘電纜箱’似乎是他表達自己與所處時代之斷裂感的頂峰。這個人對于自己所處現代生活中的如此不自然的敏感,以致于在畫布上,它必須表達出一種和諧有序的自然世界。”[4]96奧特對法國的愛,或者說對他青少年歲月的自由與快樂的追憶,顯然加強了這種情緒。他時常與路易斯談起自己在法國的時光,“他憶及自己童年的時光,在布里塔尼、諾曼底和皮卡爾迪消夏,奧特一家住在一戶法國人家中。在這里,他們住在一個有著四百年歷史的家庭農場,他對當地的玉米輪種體系和植物耕種有著濃厚的興趣。那里的生活十分美好,愉快的田園生活成為他一生難以忘懷的回憶。他在法國創作的風景作品中描繪紅色瓷磚覆蓋著的屋頂,海岸的山崖與河道。他還保存著一塊坎佩爾瓷器的殘片——來自那個時光,那個地點,那個法國農場的餐桌”[4]95。此外,1924年赴法國度假時,已經結婚的奧特還在此地展開了一段婚外情,時隔多年之后憶及此事,奧特仍然無法自已,“當他心情好的時候,會告訴我他都去過哪些地方,他的目光轉向我,眼光灼灼,想要告訴我1924年他的法國之旅。當他低聲說出‘蒙帕爾納斯’時,他的聲音好像在召喚一個溫柔的戀人”[4]117。所有這些有關法國的浪漫經驗,最終好像都化為《電纜箱》中仿佛象征著奧特自我人格的,好像在暗示與全世界都失去了聯系的,那幾縷戛然而止的、憑空消失的電線。
在奧特對“難以置信”世界的描述中,《卡茨基爾的十一月末》(Late November in the Catskills,1940年,圖4)也有著獨特的分量。畫面中,一個包著頭巾的農婦立在暗淡蕭瑟的秋景中——畫面中雖然一反常態地使用了具有冷暖色彩傾向的翠綠與赭石,卻因為天空中層疊的灰色讓人對眼前的秋日光景意興闌珊。這個場景同時呈現出真實與非真實的二元對立的情況,畫面中的女性似乎立在了山間小道中,同時又是與她周圍的景觀脫離的。看起來,她更像是一個疊加在場景中的角色——好像是在已然完成的畫面中于最后的一瞬間加上去的一個符號,在關注另外一個世界。她的姿態如此的猶疑不定,好像在思考:“或者我是真實的,或者這個世界是真實的,但我們兩者不可能同時是真實的”[9]10。
奧特作品之中這種蕭瑟的孤獨感,并不因為畫面當中存在的人物形象而產生絲毫的減損。事實上,畫面中人物的出現往往更加劇了這種孤獨感。奧特在伍德斯托克幾乎離群索居,在熱鬧的藝術家村子里是一個異數。[4]46-47他曾經告訴路易斯:“試圖跟一個與你價值觀相左的人交談,就好像嗓子里卡入了一根頭發一樣難受。”[4]135他在此地交往的為數不多的朋友似乎都與藝術圈無關:有曾經在《費斯特斯·揚普樂和他的牛》中出現的賣牛人凱姆布里基·拉舍爾,制作畫框的工人,運送冰塊的人,房屋油漆匠亞歷山大·皮考克——所有這些人,奧特欣賞他們簡單真率的性格,這大約與他對谷倉造型的欣賞出于相似的原因。

圖5 喬治·奧特《山澗溪流》,1945年
將背景設置在冬季的《山澗溪流》(Brook in Mountains,1945年,圖5)也表達了奧特某種隱秘與懷舊的情緒——這幅畫曾經被路易斯選為她為奧特撰寫的《藝術家在伍德斯托克:獨立歲月》(Artist in Woodstock:the Independent Years,1978年)的傳記封面。一次,奧特在暴雨中走到了附近的山澗旁,他徹底地被湍急的回旋所吸引,認為這“充滿了大自然的力量”[4]53。對于路易斯來說,這件作品更是意義非凡。奧特曾將這幅作品托付給伍德斯托克畫廊出售,可是當路易斯某一天經過這個畫廊再次看到自己丈夫的這幅作品時,“想到這個精心構思的、靜謐的風景作品,伶仃地孤懸在畫廊里,她動搖了”。路易斯當下產生一股強烈的沖動,認為這件作品不該輕易轉手給畫廊,在得到奧特的允許之后,她鼓起勇氣與畫廊協商,最終要回了這幅作品。“我想要留下這幅作品的沖動……就好像我想跟他一起生活的沖動。”[4]148-150這幅作品一如既往地延續了他之前冬季作品的風格,有一種天真的美國風俗畫的趣味,噴涌的瀑布汩汩流出,看起來卻冷靜而富于秩序。
三、形式主義話語反思:話語間隙中難以被覆蓋的隱秘維度
奧特死后一年左右,這幅作品于1950年在米爾克畫廊(Milch Gallery)展覽時受到了批評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關注,在路易斯邀請格林伯格參觀的這次奧特作品回顧展上,①路易斯在寫給格林伯格的信中提及奧特對后者的藝術觀點“十分在意”,“完全同意您對藝術的看法”。提到奧特也曾經在繪畫上做過完全非再現的表現主義的藝術實驗。在《紀念一顆薊》(Remember a Thistle)中,路易斯也提到,奧特在1942年左右開始透過一些先鋒藝術雜志關注到抽象表現主義的部分作品。后者認為奧特的作品“十分有趣”,盡管“搜尋中的情緒比要表達的情緒更多”,他稱贊奧特“每一寸畫布上都表現出其作為藝術家的天賦”。稱這次展覽“對觀察這些在法國繪畫傳統之外的一個更大的藝術脈絡,試圖尋找更多自主性的美國畫家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即便奧特“最終并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11]我們無從知曉格林伯格是否從奧特的身上看到了后者尊崇與膜拜的賴德(Albert Pinkham Ryder)的影子,不過格林伯格對于賴德的評價不可謂不高,1947年,格林伯格在惠特尼博物館舉辦的賴德個展[12]后的評論,充分證實了格林伯格對于賴德在美國藝術史上地位的肯定,他認為這位藝術家完全可以擔當得起美國本土繪畫先驅的稱號,并且認為他幾乎自外于歐洲的傳統,并未真正參與喧嘩躁動的歐洲繪畫的表現方式。他可以通過在畫面掌控一種普遍的、包容的色調的統一來達到一種珍貴的、由不確定性所帶來的下意識的笨拙與生澀。從始至終,不論是作品創作介質的自主性、表現手法的多樣化、情感傳達的私密化與美學趣味的建構上,這位藝術家都是完全獨立的,他確乎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風格。[13]178-180
其實,格林伯格對奧特的這番評論,很可能是出于對一個丈夫新死的遺孀的安慰,而格林伯格與奧特的藝術立場也恐怕并沒有路易斯以為的那樣接近——盡管奧特與格林伯格都各自對唯美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精神抱以支持的態度,同時對受到政治意識形態污染的藝術創作理念表現出不屑。20世紀20年代美國興起的現代主義文化這個奧特也曾卷入的浪潮中,如精確主義 (Precisionism)②精確主義(Precisionism)是美國本土的第一場現代藝術運動,緊隨其后的就是現代主義在美國的興起。精確主義藝術首次出現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達到高峰,題材主要是新興的美國大廈、橋梁和工廠等建筑物,其風格也被稱作“立體現實主義”。一樣,存在著一類在更為普遍與廣泛的意義上,涉及心理學維度與受到社會文化風潮暗示的形象化(此處指側重寫實手法的創作)繪畫表達——但這些作品卻是格林伯格的批評體系無法覆蓋的地方。③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和安德魯·懷斯(Andrew Wyeth)等藝術家顯然突破了形式與內容、意識形態與個人表達之間的界限,他們的作品在個人經驗與社會進程中找到了表達的平衡,越過了以藝術風格和表達手法來劃分藝術運動之領地的層面。對于后者來說,現代藝術所描繪對象的價值,是建立在其賴以表達的既定媒介上的——尤其當它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時。而對于奧特來說,這些限制并沒有那么嚴格,藝術作品的價值與意義是通過藝術家在作品中釋放出的神秘與充滿想象力的觸動觀者的效果產生的。相比于格林伯格對于形式主義④形式主義藝術(Formalist art)所秉持的美學觀點有如下幾個方面:1.繪畫是由最基本的幾個元素組成的:色彩、線條、構圖與肌理,這些元素組成了繪畫作品最基本的語言結構,也是形式主義藝術批評家用以分析藝術作品的基本工具;2.不論一件藝術作品是純粹的抽象作品還是再現性作品,一位形式主義者所追逐的始終是繪畫中基本的元素,并且以此為標準來評判一件作品的藝術價值;3.形式主義者們認為,如果一件藝術作品被認為缺少藝術價值,那便是因為藝術家沒有能夠在形式化的繪畫元素上找到視覺的平衡。克萊蒙特·格林伯格是美國20世紀中葉風頭最勁的形式主義批評家,其對于藝術作品的評判主要建立在去除社會語境與主題意識的,純粹的形式理論上。其1939年發表于《黨派評論》的《先鋒與媚俗》一文,為形式主義藝術的接受語境掃清了障礙,也為抽象表現主義在美國的發生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的極致推崇,奧特或許更傾向于耽溺在一種接近潛意識狀態下的,形式與其所暗示內容之間形成張力的此消彼長之中——形式本身并沒有在奧特的作品中占據壓倒一切的位置,他所表現的形式中總是負載著個人情感。此外,格林伯格對20世紀40年代初期畫壇泛起的,與社會文化物質生活緊密相關的、空洞而虛妄的商業主義傾向十分反感,認為他們“完全沒有反抗權威與既有束縛的精神”——我們可以在1944年他對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名為“浪漫主義繪畫在美國”(Romantic Painting in America)①此次展覽的意圖,在于“在美國藝術與歐洲藝術的傳統中建立對話機制”。對策展人巴爾來說,這次展覽還代表著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一次機會,使得最新的美國藝術的趨勢進入到類別劃分中來,并且將其放置到一個藝術史的語境中:“ 歷史化”在此處是加引號的,因為對于博物館來說,藝術史僅僅就是昨天的故事;而更近于我們的過往中,正在發生變化的藝術現場,相比于我們稱之為當下的不久的過去來說,又成為了離我們較遠的景觀。兩位策展人巴爾和藝評家索比(James Thrall Soby)都認為,這次展覽是一次試探性的而非定義性的展覽。在抽象表現主義已經處于醞釀時期的1944年,索比這樣描述過去不久的一段美國藝術史:“很明顯,長期以來,批評家還沒有嚴肅地思考過浪漫主義這個概念,因為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它們持續不斷地在關注抽象繪畫和表現主義繪畫趨勢,不管其是多么的富于活力,現在的勢頭都不如十五年前那樣迅猛了,‘美國浪漫主義繪畫 ’中展覽的藝術,很顯然就是1943年以來的先鋒藝術。”顯然,從此處可以看出的是,在有關美國本土現代藝術的定義方面,各路評論家的觀念存在很大分歧。而索比和巴爾等人與格林伯格意見的相左,并不在于“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之爭,而在于對“現代藝術”本身之定義的爭論。的展覽評論中看出他的態度:
這些來自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新的“浪漫主義者”(Romantics)以及新浪漫主義者們(Neo-romantics),他們回望過去,以尋找某種情感與形式上的支撐,在此基礎上確認他們作品的完整性與最終效果。他們從前立體主義者的語匯中借用特定的創作方式——自由的筆觸和明亮的色調——他們的方法則取自樣式主義者,巴洛克、德國與法國之浪漫主義的作品——然而最終的結果是導向一種墮落的品位。只有放棄對于這種效果的追求,去征服新的經驗,才會使得繪畫與情感得到真正的統一。[14]157
顯然,格林伯格對20世紀40年代作為“沉渣泛起”的浪漫主義風潮感到鄙夷與不安。在這種保守的浪漫主義風格上,奧特雖然沒有克里斯蒂安·貝拉爾德(Christian Berard)與帕弗爾·謝利仇恩(Pavel Tchelitchew)等人的傾向性更為明顯,他在伍德斯托克創作的大部分風景作品中的浪漫主義情緒,同格林伯格的趣味也是相去甚遠的。而令奧特心醉神迷的超現實主義,則在1944年被格林伯格貶損為“死灰復燃的學院主義”,有以“文學性的”主題與方式威脅現代主義繪畫自主性的威脅——這也說明了兩個人審美傾向的錯位。②1939年,格林伯格在《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上發表了《先鋒與媚俗》(Avant Garde and Kitsch)一文,指出媚俗藝術包括“大眾商業藝術與文學,出現在各種形式的彩色照片,雜志封面,插圖,通俗小說,廣告,踢踏舞,好萊塢電影”。藝術史家蒂莫西·克拉克(T.J. Clark)認為,格林伯格之所以認定媚俗藝術是無聊與索然的,是因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大眾消費情境下的復制藝術品已經成為了其卑鄙的所謂民主的一部分;但當局們卻還在制造一個大眾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主宰者的假象。媚俗藝術為大眾消費服務,同時也迎合了后者淺薄的自我滿足——而格林伯格所痛斥的超現實主義,則在很大程度上尊重這些形式,或者將其改頭換面——盡管其一開始具有革命理想。格林伯格認為超現實主義是一種不純粹與墮落衰頹的學院主義代表。造型藝術中的超現實主義則是一種對試圖恢復‘以社會情境為基礎的’藝術趨勢的反映”。有關格林伯格對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看法,還可參見Surrealis Painting(The Collected Eassay and Criticism, Vol.1, pp.225-256) ; Pictures and Prattle: Review of Abstract and Surrealsit Art in America by Sidney Janis(The Collected Eassay and Criticism, vol.1).對于1947年在阿奎維拉畫廊舉辦的籍里柯作品展,格林伯格更是以誡慎與苛刻的眼光看待這位奧特的精神導師,認為其作品對于20世紀初期的歐洲現代主義繪畫流派是一個誤導,甚至無法稱之為完整的架上繪畫;只能被認為是某種程度上的裝飾作品,是一種極度悲觀的,并沒有多少創新的模仿,僅僅是對現代生活中某些現實的中肯卻無能為力的反映。[14]134-137可是,這其中被忽視的重要方面是,奧特的超現實主義與格林伯格所竭力批判的外向觀的、工于技巧的、商業化與市場化的超現實主義相去甚遠。然而,尚在形成時期、未定格局的美國早期現代主義話語體系還未能察覺這種差別。格林伯格所主張的純粹的、依賴藝術創作媒材的,形式主義為主導的先鋒藝術話語體系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全面勝利,而與通俗文化和商業文化走得更近的巴爾,顯然也無法在他所制定的框架內將奧特囊括其中。即便是1944年,收藏家西德尼·賈尼斯(Sidney Janis)在其策展的名為“美國抽象藝術與超現實主義藝術”(Abstract and Surrealist Art in America)①這次展覽在舊金山、辛辛那提、西雅圖和紐約等多地舉辦。策展人賈尼斯的意圖,乃是彌合超現實主義與抽象藝術之間的裂縫,企圖另辟蹊徑,將超現實主義視為一種文化趨勢,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潮流;提出超現實主義文化是美國現代文化中有力的養分之一。在實際的布展中,賈尼斯也有意將超現實主義畫家與抽象畫家的身份混同起來,模糊其原本的界限;強調一種綜合的,作為文化趨勢的超現實主義的概念。而正如桑德拉·澤爾曼(Sandra Zalman)在《美國文化對超現實主義的化用》(Consuming Surrealism in American Culture)一書中的觀察,隨著“美國的超現實主義的概念從先鋒姿態轉道商業化,從心理上的沖擊轉為社會學意義上的陳詞濫調,象征性的超現實主義也逐漸退出藝術界的主流格局了”。的,試圖彌合超現實主義與抽象藝術之裂痕的展覽中,其成效亦是曇花一現——而奧特也依然無法進入其為超現實主義編織的合法化語詞中。直到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后,不懈致力于超現實主義在美國現代藝術史話語合法化的威廉·魯賓,試圖在形式主義話語與抽象藝術實踐為主導的語境下,通過將一部分超現實主義者列為抽象表現主義與波普藝術的啟蒙者為其在主流藝術史敘事中正名。②參見威廉·魯賓于1968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策劃的名為“達達,超現實主義及其遺產”(Dada, Surrealism and their Heritage)的展覽。長遠地看,醉心于形式的奧特無疑與側重圖繪和象征性的超現實主義的關聯十分有限,然而他的作品與聲名,早已在形式主義更為風靡的前一個十年中潮退人散。其作品中自外于商業化與政治化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超現實主義,架空了原教旨意義上超現實主義的內核;而其作品對形式本身的執著,又因為他固守的浪漫與唯美主義情結,難以真正進入純粹的形式主義范疇。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奧特超現實主義傾向作品進一步被邊緣化的事實。③總體來說,雖然巴爾與格林伯格為不同程度的形式主義者,然而巴爾從未放棄為格林伯格所鄙棄的超現實主義發聲,始終致力于超現實主義在美國本土的合法化的話語經營,主張的是一種外向的、與每日生活相聯系的藝術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