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書畫視角看攝影
盛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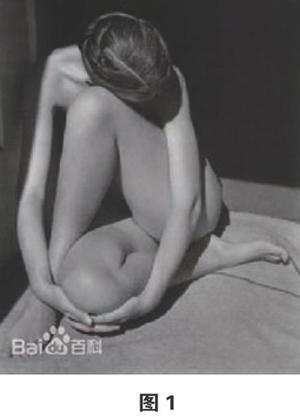

中國書畫與攝影同為平面造型藝術,都具有類似的審美功能。攝影誕生至今雖走過了170余年的歷程,但相對于中國書畫源遠流長的發展歷史以及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特質,攝影還有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由于兩者物質載體與基本特征的不同,這就決定了攝影很難從物態化層面上與中國書畫一并而論,但在當今多元化的藝術理念語境下,攝影與其他藝術門類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這就為攝影藝術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討論空間和創作空間。
其中,攝影中的極簡風格深受不少攝影師的喜愛,“少即是多”,以“少”帶出更“多”的內容,極簡風格的攝影作品與其他類型的作品相比構圖更為純粹,用極少的畫面元素傳達特定的信息,對空間的運用更為考究,從作品內涵、審美觀念、構圖形式的角度來說,正與中國傳統書畫高度契合。早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老子《道德經》就有云:“萬物之始,大道至簡,衍化至繁。”“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書畫一直深受儒、道文化的影響,更包含著“一花一葉一世界”的人生哲學,而極簡風格的攝影作品也將這種“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禪意美學發揮到了極致。
一、中國傳統書畫與極簡風格攝影的創作思考
攝影對生活的反映不是被動的、隨意的、無目的性的,攝影具有抽象性、凝練性。攝影大師布列松曾說過:“在拍攝的時候,我總是閉著一只眼睛,我用這只眼睛觀察自己的心靈;我又總是睜著一只眼睛,我用這只眼睛觀察整個世界。”(《決定性瞬間》)這段話充分地說明了當照片拍攝經驗積累到一定階段時,人們必然將自己的思考和審美理念借助現實中被拍攝場景傳達出來。這種主觀能動的表現動機,筆者認為就是攝影者將自我意識與圖片現實抽象內在審美意義的連接。
與中國書畫相同,攝影藝術同樣需要深刻的認知度和攝影經驗去審視暗藏在作品中不可言喻的抽象美,這種抽象美的內涵遠遠超出了作品的表面意義,需要通過觀者自身的審美經驗引導、激發出來。例如在愛德華韋斯頓的作品(圖1)中,流暢優美的線條和細膩的構圖意味深長地刻畫出了世上最基本的和諧與統一,美國著名攝影師安塞爾亞當斯在評價韋斯頓對攝影藝術的貢獻時說道:“人類在不斷探索和尋求著最完美的精神境界,韋斯頓的作品,照亮了這條道路。”他的后輩同行厄斯特哈斯由他的作品看出了“攝影里面有詩”。極簡風格攝影作品的表現能力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攝影師的作品中有更為直接的詮釋但這并不是說西方不具備這種審美意識拾恰相反,“二戰”以后這種高度抽象、簡約的攝影思維越來越被今天的西方藝術家所關注。
這種攝影創作思維看似無為,但實則有大為在《道之攝影》一書中,阿蘭華茲有這樣的解釋:“無為是追隨道的人的生活方式,必須主要以智慧的形式理解,就是說,了解人類和自然事物的原則、結構和趨勢,以及如何用最少的能量去對付它們。”“無為不應解釋為懶散,相反是一種非常有效、熟練完成事情的方式。以無為的原則行事,你必須保持接受的狀態 不是被動麻木,而是放松而警覺,與生命無休止的變化保持同步。這種與生命的流動對內對外的和諧使圣賢與創造攝影師能夠自然自發地行動。”這種放松的創作狀態正與中國書畫及極簡風格攝影作品的創作狀態幾乎完全契合。
二、中國傳統書畫與極簡風格攝影的構圖方式
在中國書畫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也曾經歷過由繁至簡的轉變,例如在書法中由筆畫繁多復雜的篆書逐漸向簡化的草書轉變,在國畫中由細膩寫實的工筆畫向灑脫簡練的大寫意風格轉變等。中國書畫的發展趨勢從大范圍看來幾乎是在做減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追求的是形而下的技法、墨法、章法,受制于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一直理性地書畫,但其實書畫美學的較高層面應該是寥寥數筆于方寸間勾勒天地,于無畫處頓生妙境。例如八大山人的《行草題魚圖軸>《芍藥圖》等,空寂明凈的畫面凸顯了作品的意境和格調。
美學大師宗白華有云:“中國畫最重空白處。空白處并非真空,乃靈氣往來生命流動之處。且空而后能簡,簡而練,則理趣橫溢,而脫略形跡。”(《藝境》)這種空、無的哲學思想體現在中國書畫里就是留白這是中國書畫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說是對極簡主義的最佳詮釋,也正是極簡攝影內在審美的表現形式之一。
中國書法家邵巖的現代書法作品(圖2),黑色的墨痕與白色的宣紙產生了鮮明的對比,似乎又是中國陰陽哲學理念中黑白互化過程的一個瞬間體現。墨跡由右向左逐漸加重,筆觸由輕盈轉為雄壯;與此同時,節奏感和力量感逐漸加強,為了突出這種沖擊力和感染力,作者最后的墨跡沖出了作品畫幅之外,給觀者以無盡的向左下方沖擊的動勢。整幅作品簡約而抽象,但給觀者的視覺感受和印象又是那么的強有力。同樣的視覺感和構圖感在日本攝影師筱山紀信的黑白攝影作品(圖3)中也能找到。兩個人像堅實、肯定的形象構成了畫面的視覺中心,向右延伸的影子與遠處的山,就好像邵巖書法作品中虛靈的細線條,反襯了左下方強有力的視覺點及其分量感。由此可以看到書法與極簡攝影在構圖上也體現了一定的契合點。雖然也許兩位藝術家從未謀面,也未進行過任何的藝術探討,但是兩幅作品在構圖形式上卻有著非常顯而易見的共通性。類似的例子在極簡主義攝影作品中不難尋覓,再如邵巖作品(圖4)與杉本博司的作品(圖5)比較。
三、中國傳統書畫意境在攝影藝術中的運用
攝影術在19世紀40年代傳人中國時,風光攝影成為國人最早拍攝的題材之一,中國風光攝影興盛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特有的傳統山水文化。中國的攝影人在攝影創作中,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運用著書畫藝術中的理論知識和表現手法,將其中強烈的主觀情感和意境融人攝影創作中,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影響著中國攝影藝術的發展。
“影中有畫,畫中有影。”許多人對郎靜山攝影作品的第一感覺常常是“這分明就是中國水墨畫!”郎靜山是中國最早的攝影記者之一,也是將中國繪畫原理運用到攝影這個舶來品之中的第一人。他將中國傳統美學與西方科技融為一體,通過仿國畫、重意境、師古法的原理并運用西方攝影技術承載東方意境,形成其特有的藝術風格
集錦攝影。他的作品營造出虛實相生、淡泊幽遠的意境,熟練地運用類似于中國水墨畫中的黑白灰三色措鑒傳統繪畫藝術的‘六法,融氣韻、神為一體,形成世界攝壇獨樹一幟的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攝影風格。
緊隨其后,陳大志的水墨攝影、姚璐和楊泳梁的數碼山水攝影以及孫郡的新文人畫攝影,都受到中國傳統繪畫審美文化的影響,并使之有機地融入風光攝影的語境之中,開辟出不同于他人的攝影之路,拍攝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攝影作品。
攝影師光與影的藝術,書畫是筆與墨的藝術。源遠流長的中國山水畫、文學詩詞和傳統文化審美意識對中國攝影藝術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中國書畫從審美和構圖上對風光攝影的藝術在民族文化傳承和藝術表現創新上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綜上所述,中國書畫作品與極簡攝影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藝術,其實存在著諸多共通點,這將促進兩種藝術門類互學互用、借鑒發展,同時也會帶來各自創新發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