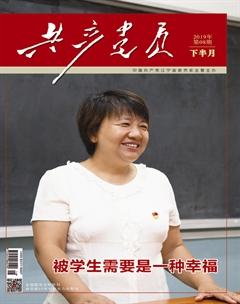科爾沁草原的守護者
張大庸 尚金州 牛澤群
廣袤的科爾沁草原,無邊無際的草木匯成綠色的海洋,鳥兒與牛羊合奏著大自然的交響樂。當地牧民告訴我們,“科爾沁”是蒙語,有“弓箭手”“護衛”等意。千百年來,科爾沁草原有效阻擋了寒流和風沙的長驅直入,是東北、華北生態安全的一道天然屏障。
然而,近幾十年來,由于在不恰當的地理條件下實行農耕化和高耗水企業的入駐,科爾沁草原生態遭到嚴重破壞,部分土地沙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人民訴求,以全新的理念指導生態文明建設,吸引了無數志愿者投身于治理沙地、恢復草原生態的事業中。
在沈陽,就有這樣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十幾年的時間自費走遍科爾沁草原各地,為沙地治理出謀劃策,為保護草原奔走呼吁,與伙伴們一起將植被覆蓋率接近于零的100公頃沙地恢復成植被覆蓋率達99%的草原,其生態理念和治理經驗被廣泛傳播。他就是沈陽化工大學退休副教授、現年75歲的李慶祿。
把茫茫沙地變成綠色草原
是他最滿意的“論文”
“老萬老萬,干賠不見賺;老李老李,愛講大道理。”這是十幾年前,吉林省通榆縣新合屯的村民們編的順口溜。
“老萬”,名叫萬平,2000年辭去公職,在通榆縣條件最艱苦、環境最惡劣、經濟最落后的流動沙丘上建起了一個方圓100公頃的生態示范區。苦干兩年,積蓄耗盡,栽下的2.7萬棵楊樹僅成活30%,萬平還是不服輸。“老李”就是李慶祿,早就對草原沙化憂心忡忡,2005年了解到萬平的事跡后,主動找上門來為萬平出謀劃策。
“沙地治理必須是生態治理,生態治理不等于綠化,綠化不等于栽樹”“楊樹的耗水量是榆樹的59.4倍,要適地適樹”……一席話,既有先進理論指導,又有實際數據支撐,讓萬平茅塞頓開。從此,李慶祿成為萬平創建的通榆縣環保志愿者協會的核心成員,負責教學、科研等工作,與萬平在沙地治理、恢復草原生態的征程上并肩前行。
上世紀70年代,李慶祿在清華大學就讀期間,學的是化工專業。清華大學嚴謹的學風,在課程設置上可見一斑——李慶祿當時不僅要學化工相關知識,還要學地質、氣象、建筑等所有與化工“沾邊兒”的課程。為了進一步做好治理沙地、恢復草原生態的工作,李慶祿又捧起景觀生態學、草原生態學、環境政策學、社會學、民族學、人地關系等學科的書籍進行研讀,成為名副其實的草原專家,對生態示范區的發展起到了把關定向作用。經過十多年的探索與奮斗,李慶祿和萬平等人在這片植被覆蓋率幾乎為零的沙地上成功地重建起以羊草、冰草、榆樹等為頂級植物的疏林草原生態系統,植被覆蓋率達到99%,生長植物250余種,動物40余種,到處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2011年9月,北方地區森林、草原荒漠化防治與保護交流會議在生態示范區召開,與會專家在示范區內進行了大范圍實地考察。昔日的茫茫沙地上,長出了羊草、冰草、杠柳、黃芪、針茅、香蒲等植物,野雞、跳鼠、狗獾、野兔、狐貍和各種鳥類不時穿梭其間,讓所有參會人員備感驚喜。與會專家一致認為,生態示范區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對整個科爾沁沙地區域來說均有代表性,對科爾沁沙地治理、草原生態系統恢復及保護有著典型的示范作用,凸顯出顯著的生態效應和社會效益。如今,生態示范區的成功經驗已產生很大影響,與其相鄰的8000公頃沙地,植被覆蓋率已達50%以上。2019年6月,通榆縣環保志愿者協會被生態環境部授予“中國生態文明獎先進集體”稱號,是所有獲獎單位中唯一一個志愿者組織。
而對當地生態環境變化感受最深的,無疑是新合屯的村民。當年,生存環境惡劣的新合屯是全縣最窮的村屯,村民們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孩子們去上學要用頭巾甚至塑料布包住頭臉遮擋風沙。如今,由于示范區及周邊自然生態的恢復,區域小氣候發生明顯變化,風沙小了、降雨多了、地皮綠了,村民的農牧業收入逐年增加,家家戶戶蓋起了磚基鋼瓦房,成為全縣最富裕的村屯之一。村民們又流傳起新的順口溜:“老萬老萬,埋頭苦干;老李老李,堅持真理。”
從國際學術會場到硬座車廂
都是他的“課堂”
沙地變草原,生態示范區彰顯的示范指導作用吸引了眾多環保志愿者和科研人員的到來,將生態示范區作為科研、教學、社會實踐的基地。近年來,示范區迎來了20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和學生,其中還包括來自8個國家的外國留學生。每一撥“取經者”到來,李慶祿都會熱情講解、有問必答,不遺余力地傳播生態文明理念。他還先后應邀到全國5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中學進行專題講座、經驗交流、環保宣傳教育,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研討會,被多個國內環保組織聘為講師或顧問。
有一次,他應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邀請,作題為《美麗的科爾沁草原演變成為沙地的深層次原因》的講座。他縝密的推理、翔實的數據、充滿感情的演講,深深打動了北大學子。講座從晚上7點開始,一直到教學樓清樓時,他的身邊仍然圍著一群熱情的大學生在連續發問。在保安的再三催促下,大家又簇擁著李慶祿走出教學樓繼續交流,一直到晚上11點多鐘,聽眾才陸續散去。
十多年來,李慶祿自費走遍了科爾沁草原的每一個角落,足跡遍及內蒙古、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四省區,光差旅費就花了二三十萬元。有人問他這樣做圖啥,他堅定地回答說:“習近平總書記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捍衛綠水青山,沒有局外人!”
幾年前,李慶祿在蒙東某盟,發現當地正在施工興建前期煤化工、有色金屬冶煉、重金屬深加工工業企業,立即意識到這些高耗水、重污染的大型企業進駐該地區會給當地帶來無法修復的災難性后果。于是,他用5個月時間,對當地進行了氣象、水文、地質、草原濕地等全方位的調研,又到水利部、中科院、國家氣象局等20多個相關單位進行調研,奔走呼吁停止該項目。
與內蒙古某盟接壤的吉林白城對李慶祿的建議高度重視,邀請他和省內外相關領域的10名專家進行研討論證。李慶祿指出,高耗水、重污染企業要入駐該盟,一是要有豐富的水資源,二是這些大型企業必須沒有污染,三是要符合《全國國土功能區規劃》有關法規的規定。實際上,這3個條件在此地都不具備。叫停該盟在建工程并撤項,可避免大興安嶺地區生態災難發生,也可使處于內蒙古該盟下位的吉林白城居民免受污染水的毒害。時隔不久,這項投資額達數百億元的項目停止施工,退出內蒙古某盟。
奔走于科爾沁草原的旅途上,李慶祿總是選擇硬座車廂,一是票價便宜,二是方便與普通百姓交流,以宣傳生態文明理念。2012年,他在火車上與大興安嶺五岔溝林業局退休干部楊有寬結識,從此攜手為保護當地森林做了大量工作。2018年5月,在回沈陽的火車上,吉林省雙遼市的幾名村民告訴李慶祿:“市領導到我們村里來了,說必須走出沙地治理的誤區,不要再栽種楊樹。”李慶祿欣慰地笑了。
“總書記說,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保護草原生態,對建設生態文明、促進民族團結、推進文化繁榮都有深刻意義。為此,我愿做科爾沁草原一名永遠的守護者!”李慶祿深情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