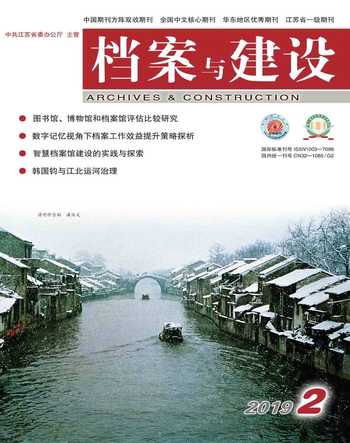在路上 努力著
林越陵
“二百多年前,清代詩人袁枚筑園小倉山,取名‘隨園’。1958年,江蘇省檔案館成立,后來落戶隨園。”這兩句話,經常出現在我的文章中,也出現在我們組織的大型活動中,成為描述我們江蘇省檔案館大院的代表性語言。
時光穿越30余年,當我于20世紀80年代中葉踏入這個大院的時候,并不了解這塊土地的厚重和她所蘊含的寶藏。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在大學四年所學專業的從業時間只有三年,可在這個大院里的時間則是長長的33年。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懵懵懂懂來到這個大院,我進入的第一個部門是江蘇省檔案館管理部,學習管理檔案實體。時間不長,但所做工作不少。管理檔案、調卷、抄卡片、抄檔案、為編纂《江蘇省大事記》摘抄史料。也許有人會說,抄東西簡單啊,會寫字就行啦。別說,還真不簡單。就說抄革命歷史檔案吧,許多戰爭年代的標語是手寫的,有行書、草書,還是繁體字。如我這種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教育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那就是認“天書”啊。好在有老同志指點,咱年輕好學,孺子可教,很快便獨立工作,加上手快字好,還經常受到表揚。初來乍到就受到表揚,心里很得意,竟沒有去深究這項工作意義何在,也沒有仔細端詳那些經過戰爭年代的洗禮,泛黃的紙張里所承載的歷史。第一次面對面近距離接觸檔案實體的機會就這樣大大咧咧地錯過了。
不久,我被調到江蘇省檔案局綜合處,學習檔案事業管理。我幸運地趕上了中國檔案事業恢復整頓的好時機,在領導和老同志的帶領下,見證了一項項工作從無到有,恢復發展。專業技術職務評審、教育、法制、宣傳……十幾年里,在學習本領、得到鍛煉的同時,參與很多填補空白、首開紀錄的工作,也為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86年,繼高校、科研院所恢復職稱,開始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后,檔案專業也開始進行職稱改革,由原來職稱的評聘一體改為評聘分開。我在領導的帶領下,參與起草了和專業技術職務評審相關的文件材料,開啟改革開放后江蘇檔案系列專業技術職務評審。這期間,我有幸結識了吳寶康等老一輩檔案工作者,和他們一道開會、調研,近距離聆聽他們的教誨。當時,一個縣檔案局局長申報研究館員職務。縣級檔案部門的工作人員是否具備研究館員所需要的業務水平和研究能力,專家們心存疑惑。但他們沒有簡單否定,而是驅車至現場,實地了解情況。經過調查研究,專家們一致認為,該同志雖然身處縣級檔案館,但從業數十年,熟悉檔案管理業務,研究檔案館藏,工作業績和編研成果均真實可見,符合任職條件。于是,他成為職稱改革后獲評研究館員職務的縣級檔案館第一人。吳老等前輩為我樹立了檔案工作者認真嚴謹、以人為本、高度負責的職業形象。
恢復整頓期間,各項工作千頭萬緒,人才培養是關鍵。從1986年開始,我在領導的帶領下,又奔波在教育部門和相關學校間。1986年,南京大學先后設立科技檔案專業本科和科技檔案第二學士學位班。在省教委的大力支持下,1989年、1990年省檔案局與揚州師范學院聯合舉辦專業證書班;1988年蘇州大學承辦檔案專業自學考試;1986年省檔案局與省輕工廳聯合在常州輕工業學校開設檔案專業。江蘇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從雙學士到中專完整的檔案專業教育體系。那時候,每年一度的華東六省一市檔案教育協作會,其他六家都是檔案局帶一所學校參會,江蘇呢,南大、蘇大、揚州師院、金陵職大、常輕校……雙學位、本科生、大專、中專、自學考試……讓其他省市好生羨慕。1997年國家檔案局在長沙召開教育工作會議,江蘇作為典型作大會交流。盡管我那次發言之后的數十年一直被朋友們戲稱是“毛丫頭上臺”,但江蘇的檔案專業教育工作可是杠杠的呀。

那個時候提起檔案局,社會上很多人理解為“辦共產黨案子的地方”,開發票抬頭單位寫的是“黨案局”,看你的眼神充滿著戒備,甚至肢體語言告訴你要保持距離。
改變的契機源自一次國際會議。1996年9月5日,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在北京召開。為了迎接大會的召開,那一年檔案部門開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一時間,“電視上有圖像,廣播里有聲音,報紙上有文章”成為檔案宣傳必須做到的三要素,滿大街都是標語、彩旗,甚至還有拱門氣球。如今檔案宣傳的規定動作——廣場宣傳咨詢活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整整一年,我們都在組織辦展覽,辦宣傳咨詢活動,在電視臺錄制三檔節目:全省檔案知識競賽、領導電視講話和“大寫真——讓檔案造福人類”專題節目。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電視臺專業人員一道制作專題片。那個時候的“大寫真”欄目,12分鐘,仿佛是江蘇版“焦點訪談”,從拍片到播出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開始了人生第一次體驗:撰寫腳本、解說;陪同攝制組到科研院所、工廠、檔案館等,采訪中科院院士、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檔案工作人員,拍攝了大量現場素材;參與編輯剪片。我不懂操作,但熟悉素材,什么位置放什么內容,在第幾個素材帶、時長多少,都能準確地報出來,編輯進度大大提高。開播前,欄目負責人對我說,稿子是你寫的,我看你普通話還可以,干脆你來主持吧。這可嚇壞我了:我參加拍攝、編輯剪片、撰寫解說,是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當主持,那可是要給全省電視觀眾看的呀,萬萬不行!沒出息的我,錯過了唯一一次可以上電視主持節目的機會。
1997年9月5日—1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頒布十周年之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海軍原副司令員、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政委張序三中將率領全國人大檔案執法檢查組到江蘇省檢查《檔案法》貫徹落實情況,那是我們第一次迎接最高級別的執法檢查組。這樣的檢查活動,我等小輩自然沒有參與的機會,但向檢查組匯報的材料卻是由我完成的。記得那天晚上,已經下班的我被處長召回辦公室。領導們正在會議室研究迎接檢查的事情,我和處長就在會議室對面的辦公室里趕材料。處長幫忙找資料,我寫稿子。那是我第一次承擔如此緊張且重要的文字任務,壓力山大,以至于今天回想起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細節的東西全部忘記,只留下兩個字——緊張。
《檔案法》的頒布實施,系列宣傳活動產生的效應,終于讓社會對于封閉的檔案館和檔案工作有了一定的認知,開發票的時候不再出現“黨案局”了。
離開綜合處,我先后在局辦公室、《檔案與建設》編輯部工作,主要是和文字打交道。說實話,一個學理科的,在文史人才聚集的部門負責文字工作,那得多么無知無畏啊。好在領導信任,給我一句話:“握筆三分主”;也非常體諒:“你就是見識少,很多文稿起草對于你來說都是第一次。”讓我有勇氣承擔了大量全局綜合文稿的起草任務,也為近十位分管檔案工作的省領導代擬過講話稿,政策水平、站位意識大大地得到了提升。
人生易老天難老戰地黃花分外香
我在大院的前十幾年工作是在檔案圈里,屬于被動的“自娛自樂”,從2003年9月我到省檔案局征集接收處,就把目光放到全社會,放到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學習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思考檔案資源建設問題。這樣的經歷也讓我看到了別樣風景。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張家港原市委書記秦振華獲得“改革先鋒”稱號受到表彰。當我打電話向他表示祝賀時,老書記哈哈大笑,連說了三聲“高興”,聲音洪亮,中氣十足。
在江蘇改革開放進程中,秦振華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他所創立并實踐的“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于爭先”的“張家港精神”是張家港發展之魂、力量之源,也成為新時期實現“兩個率先”過程中要發揚光大的江蘇精神。

2011年6月,我們開始聯系秦振華,打算錄制“張家港精神”創建口述史。老書記非常高興,欣然答應。那時,正值由全面小康向基本實現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中央再次肯定“張家港精神”在改革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意義,秦振華受邀到各地作報告,與我們的約定一拖再拖。2012年2月一個星期天中午,我接到了他的電話,告知第二天有空,在張家港等我們。機會面前,顧不得其他,趕緊通知團隊、落實車輛,第二天一早出發。11時10分到賓館,秦振華已經等在那里了。一般到了這個點,都是先用餐,然后下午再工作。可老書記要求我們用5分鐘的時間放下東西,立即到會議室開始工作。緊緊張張趕到了會議室,下意識地趕緊把手機調到震動,這個小動作被秦振華看到了,他馬上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手機關掉”。初次見面,我就領教了他的威嚴和效率。那一天,老書記講了五個小時,一氣呵成,沒有停頓。濃濃的鄉音傳遞著深深的鄉情,揮舞有力的手勢果斷干脆,毫不拖泥帶水。面對面,在已經離開職場多年,已近80歲的秦振華身上,依然能看到那種效率、激情、認真、嚴謹。我理解了為什么張家港能夠成為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典型,為什么沒讀多少書、沒有太高學歷的秦振華能夠成為一種精神的創始人,成為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人物。
2017年11月2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發布消息,我國申報的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征集甲骨文研究資料的經歷不斷在我腦海中閃回。從2004年開始,我們征集了我國第一位女外交官袁曉園的檔案資料。在她的2000多個編號的檔案資料中,有153個編號是她收集的建國前中國大陸、中國臺灣、日本等地出版的許多大家研究中華民族文字演變的圖書,相當一部分和甲骨文有關,包括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的著作。201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甲骨文研究專家,時任江蘇省甲骨文學會會長的徐自學。徐老先生儒雅謙和,在海內外甲骨文研究領域頗有影響。在他的娓娓道來中,一幅甲骨文的歷史畫卷在我腦海中展開。我們和徐老先生一拍即合,決定在江蘇省檔案館建立“甲骨文研究檔案資料庫”。徐老先生一方面將他的計劃、設想與甲骨文學會顧問溝通,獲得理解支持;一方面與海內外甲骨文研究學者、專家聯系,以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倡議大家將研究成果捐贈江蘇省檔案館,大家共建甲骨文研究者的精神家園。在徐老先生的引見下,我們結識了韓志強、王本興、謝兆崗、張大順、吳向明等海內外甲骨文研究專家、學者,館藏也由少而多地積累了甲骨文研究成果,更因徐老先生的捐贈義舉收藏了甲骨“四堂”之一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作品。在與老先生們的交往過程中,親見他們為人類最古老的文字傳承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館藏保存著他們為甲骨文申遺征集的萬人簽名。終于,老先生們多年的付出獲得了回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從她的“母體”出發,穿越數千年,成為世界文明的瑰寶,成為人類共同的記憶遺產。
金陵刻經技藝檔案資料是我征集的第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檔案。那個位于南京新街口鬧市區卻神秘、沉寂的院子,因為傳承著中國古老的木刻水墨雕版印刷技藝,在世界印刷史上占重要地位,被譽為“活的古代印刷博物館”。清同治五年(1866),我國近代佛教文化復興的奠基人楊仁山等有識之士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傳承我國古代佛經、佛像木刻雕版印刷技藝,是我國著名的佛教文化機構,也是融古代經書、經版收藏,經書雕刻、印刷、流通及佛學研究于一體的佛經出版機構,百余年來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我們收集了那里保存的經版印刷的經書,金陵刻經處創始人楊仁山家族照片,中央電視臺拍攝的《金陵刻經技藝》專題片,申報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材料,金陵刻經處創建140周年紀念大會暨入選首批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慶典大會等7160件檔案資料。其中,《乾隆版大藏經》俗稱“龍藏”,是清代唯一官刻漢文大藏經,從清雍正十三年(1735)正式開雕至今,印數累計不超過150部,在歷代大藏經編纂刊印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2006年,為準備中國文化遺產日宣傳資料,中央電視臺選擇金陵刻經處拍攝專題片。那一個星期,金陵刻經處從制墨、刻版、印刷到裝訂等環節,還原了金陵刻經技藝的完整流程,呈現在專題片中那種為紙張點數的“刷刷”聲都清晰可聞。有意思的是,我們跟隨攝制組,用攝像機記錄了整個專題片的拍攝過程。最后,中央電視臺的專題片和我們拍攝的《紀錄片是這樣拍成的》一并收入了省檔案館中。2009年9月,《中國雕版印刷技藝(金陵刻經印刷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倏然而已。
欣慰嗎?多多的!
十數年時間,我和同事們如螞蟻搬家一樣聚沙成塔,圍繞江蘇大地書寫歷史的人和人創造的歷史,征集了大量檔案史料,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江蘇、改革開放以來江蘇重大事件重大活動、江蘇文化遺產、社會記憶等檔案資料。有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活化石”吳江開弦弓村和費孝通檔案,泗洪上塘農村改革檔案,全國文明村華西村、蔣巷村檔案,江蘇援建四川綿竹檔案,江蘇援建新疆檔案,全國“五個一”工程獲獎項目、江蘇參加上海世博會、全國十運會、西南服務團等專題檔案……在省檔案館建立了“江蘇名人檔案庫”“江蘇書畫名家檔案庫”“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庫”“改革開放以來江蘇重大事件檔案資料庫”“甲骨文研究資料庫”“江蘇鄉鎮企業家口述史資料庫”“江蘇省口述史資料數據庫”。為改善館藏結構,豐富館藏內容作了積極的嘗試和努力。
感動嗎?滿滿的!
原南京軍區政委方祖岐將軍80高齡,親自整理個人檔案,分門別類、分期分批捐贈省檔案館。檔案見證了一位共和國將軍由戰場上走來,成長為高級將領的不凡歷程,退而不休、筆墨丹青、不斷進取的晚年。
江蘇省原副省長吳瑞林將幾十年積累的日記、文稿等個人檔案資料全部捐給省檔案館。這讓我們感受到一個領導干部的磊落、境界和胸襟。
畫家喻繼高老先生每次見面總會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說個沒完,還會和作家龐瑞垠老先生一道“突然襲擊”打個電話來聊天。新華日報社幾代攝影人接力幫助我們積累重大活動圖片資料。攝影愛好者用十年的時間,拍攝數萬張記錄自然風貌、城鄉變化的照片幫助我們豐富館藏。記者朋友主動在《新華日報》撰寫文章報道檔案工作,讓我對所從事的職業產生敬畏和自信。
收獲嗎?大大的!
這樣的經歷,開闊了我的視野,增長了我的見識,豐富了我的閱歷,讓我得以在更高的平臺上看待歷史,回往我們走過的路。走近那些時代、歷史的風云人物,靈魂會得到洗禮,境界會得到升華。當然,還有許許多多與我一樣的普通人,職業不同,因檔案結緣,成為數十年的朋友。靠近你,溫暖我!
近四十年,見證了檔案從遠離生活,用于宣示王權的合法性或宗法血緣關系的工具,到今天成為社會人作為獨立主體的存在和維系社會經濟秩序必不可少的日常;也見證了檔案由居于廟堂、束之高閣,到今天進入拍賣行,完成了中華文明之檔案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的普及。
有資料顯示,職場中有80%的人做的是單調重復的工作,只有20%的人會面對新的工作和挑戰。我很幸運,在這個崗位上,每一次面對征集對象都是學習的機會,沒有一個征集故事是可以重復的。我的職業為我打開了一扇扇門窗,我得以徜徉在江蘇歷史的長河中,觸摸那些人創造的歷史,和歷史事件中的人。不同的人間際遇或悲或喜,往事鉤沉皆是經歷。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見證著,體驗著,記錄著,收獲著……我本凡人,但我的職業生涯因此而豐富多彩。
神奇嗎?妙妙的!
很多曾經的經歷、記憶深處的人和事,或者偶然的際遇,在若干年后因為職業產生交集。
小時候,我曾經從長江北岸的浦口火車站擺渡到南岸,站在南京長江大橋南堡下面,對正在建設的大橋充滿了好奇和期待。幾十年后,我和大橋建設的親歷者面對面,記錄那些和大橋建設有關的點滴……
皖南事變的歷史人人知道,可我沒想到有一天,袁國平烈士之子會來到我的辦公室里,談父輩為信仰慷慨赴義精神的學習和傳承……
每每夏日炎炎,行走在綠樹成蔭的南京大街上,享受著懸鈴木帶來的清涼,便想起了傅煥光。他的名字許多人不知道,但他播下的種子卻滲透到每一位南京人的生活里。他在擔任中山陵園主任技師、園林組長兼設計委員會委員期間,用十年時間,綠化紫金山,有了今天惠澤南京城的“綠肺”。這是一個值得南京人感恩的人。他的檔案讓我時時想起那句古語: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一個偶然的電話,讓我接觸到一個群體——西南服務團。那些新中國第一批奔赴西南的熱血青年,從富庶的江南義無反顧地挺進大西南,參與剿匪、建設。巧合的是,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我曾經在大西南生活了15年。與老人們面對面,聽他們訴說歷經磨難卻青春無悔的歲月,那些熟悉的地名和山山水水,感慨萬千……
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陳虹教授——劇作家陳白塵教授的女兒。在征集檔案資料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她說說歷史往事,劇作家的抗戰、烽火中的文人,還有家族數十年的命運經歷。她講述的國事、家事,絲毫不亞于文學作品……
曾經因為在南部邊疆上學的經歷,喜歡上歌曲《兩地書母子情》。若干年后,作者的家人成了我的征集對象……
三十多年職業生涯,點點滴滴,背景是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是如火如荼的檔案事業發展。全社會各行各業一個個“微觀社會”的記憶匯聚而成的,是記錄國家興盛、民族復興的檔案。見證這樣的時代是我的榮幸,保存這樣的記憶是我的光榮。
匠人之大者,莫過于以心守護。
匠心之大者,莫過于敬畏傳承。
于我,在路上,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