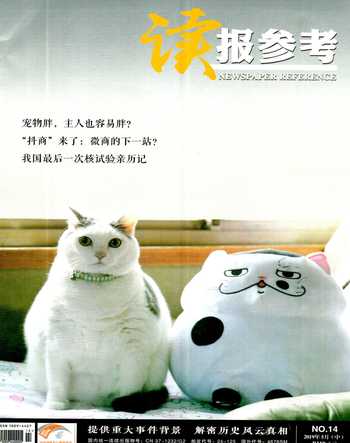淞滬會戰中的國軍高層眾生相
馮杰
1930年代,上海是中國工業、金融中心及西方國家在華利益的核心所在。“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全部動員全面抗戰”,為了牽制、分散華北日軍,喚醒國際列強干涉,蔣介石主動出擊上海,從而打響了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會戰。本文主要關注淞滬會戰中的國軍高層是如何指揮運作的,從而揭開了派系齟齬的“幕后秘辛”。
張治中:“我一直在前方,委員長究竟要怎么樣”
1936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準備對日作戰,劃全國為數個國防區,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兼任京滬區長官。戰備工作需要秘密進行,張治中用心良苦,在軍校辦公室的邊上設置了一個高級教官室,對所有工作人員有一個很嚴厲的規定——絕對不許對外泄漏工作的機密。因而,沒有一個外人知道,這個小小的機構,竟是日后揭開全面抗日戰爭序幕的司令部。秘密機構后來移駐蘇州獅子林、留園,對外號稱“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以繼續掩入耳目。
盧溝橋槍響,張治中正在青島養病,聞訊后急忙返回南京,出任京滬警備司令官。8月9日,日軍駐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與水兵齋藤要藏強闖虹橋機場,被機場保安隊開槍擊斃。8月12日晚上,蔣介石電令張治中星夜進軍上海,駐扎在京滬線上的第87師、第88師等部頓時忙碌起來。宋美齡邀請來的空軍顧問陳納德碰巧遇上了這一幕:火車在駛往南京的半途中停下來,所有的乘客被趕下車,中國部隊擁進車廂,火車掉轉頭折回上海。第二天清晨,上海居民從夢里醒來,看見遍地頭戴德式鋼盔的中央軍,驚喜交集:“你們從哪里來的?為什么這樣神速?”
中央軍的首要任務是“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結果事與愿違,幾天進攻下來,收效甚微。軍政部次長陳誠、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視察淞滬戰場,建議張治中改攻匯山碼頭,向敵中央突破,先截成兩段,再分別掃蕩。適逢第36師從西安趕到上海,第216團團長胡家驥身先士卒,連續沖過東熙華德、百老匯路,但無法摧毀匯山碼頭堅固的鐵柵門,進攻再次受阻。8月22日,蔣介石調整戰斗序列,任命陳誠為第15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擔任由京滬警備司令部改編的第9集團軍總司令。據陳誠日記記載,當晚他由南京、蘇州轉南翔,找到張治中“重商總攻部署”,次日又因前方通訊困難,“回蘇州處置一切”。
令人不解的是,張治中似乎并不了解戰斗序列出現的明顯變化,8月24日從太倉趕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軍軍長羅卓英的疑問:“張總司令為什么會跑到我們這里來?”據張治中的說法,仔細一問,他這才知道,“自蘊藻浜以北地區的防務,統歸陳誠指揮了”。于是又找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了解情況,豈料引來一場軒然大波。
蔣介石在電話中質問張治中為什么不在前線,跑到蘇州后方?張治中本來就一肚子氣,回復聲音也不小:“羅卓英歸我指揮,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劃歸陳誠指揮了!”蔣介石越發厲聲責問:“為什么到蘇州?為什么到蘇州?”張治中再也按捺不住:“我到蘇州是與顧祝同商量問題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員長究竟要怎么樣?”
懷著委屈的心情,張治中提出辭職。9月4日,陳誠電呈蔣介石,替張治中說盡好話:“文白兄兩旬以來,在前方指揮作戰,異常奮勵,夜以繼日,至為辛勞。唯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機關組織,未臻完善,種種準備,未能周密,而成現在之局。職意用人在用其所長,可否使文白兄擔任大本營總務部長?”張治中本人也給南京寫了一封長信,懇切表示辭職的至誠,但總黽不蒙批準。原來蔣介石征詢了顧祝同意見,顧保留自己看法:“現在乃整個問題并非某一人之過錯,似可不必調回也。”軍委會副參謀長白崇禧巡視前線,張治中托其轉達辭職之意,最終以身體狀況不適合為由,調離前方指揮崗位。回到南京,張治中提出回家休養一段時日,蔣介石和藹地說:“好,但你先就了新職再走。”
結合相關文獻,蔣介石主要是反感張治中過于“注重宣傳”“屢向新聞界發表意見”,為此還專門通令前方各軍官不得任意發表言論。曾振時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部參謀處科長,他說:“張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戰時,喜歡在報紙上發表戰況。委員長見報,便屢次告誡,不要發表談話。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記者,偏偏每天必來。委員長來電話斥責,張在電話中答復說,報告委員長.我明天不說了。但是第二天的報紙上仍然有張發表的談話,這樣一斥一答有好幾次。”曾振同時認為,張治中一腔熱血,確實盡心盡力,“整日忙于指揮作戰,也沒有理發,夜間睡眠不足,蓬頭垢面,甚是狼狽”。
陳誠:“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1937年盛夏,軍政部次長陳誠兼任廬山暑期訓練團教育長,工作忙得不可開交。8月15日,蔣介石打來電話“催即回京”,交代了三個任務:“即擬整個戰斗序列,調整華北部隊之部署,至上海一行,計劃解決日租界之敵。”事不宜遲,陳誠、熊式輝連夜乘汽車由南京赴南翔,“與文白商掃蕩上海之計劃”。8月18日深夜,兩人又同車返回南京,熊式輝問:“對領袖報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陳誠不加思索就說:“各就所見報告,可使委員長多得一份參考,似可不必一致。”翌日上午,熊式輝“極言將領及部隊之不能戰”,建言蔣介石“不能打”。而陳誠意見相反:“滬上官兵之不能戰,誠然!但此時非能戰不能戰,問題是在當戰不當戰。若不戰而亡,孰若戰而圖存?”蔣介石則態度堅決:“打!打!一定打!”陳誠很興奮:“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當時援滬大軍早已上路,陳誠系統第18軍原本計劃參加保定方面作戰,先頭列車駛過鄭州時,軍長羅卓英突接蔣介石電令:“原車南下,開蘇州待命。”日軍不甘落后,亦從國內調兵猛撲獅子林至吳淞口一線,憑借艦炮掩護和空中優勢,第3、第11兩個師團登陸首日僅僅死傷40余人,損失相當輕微。隨著第18軍的全線投入,戰場情勢陡變。8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日記顯示,傷亡數字急劇攀升:“第11師團自登陸以來,已傷亡人員約四百余名。師團參謀下坂少佐也在登陸后即被敵軍飛機擊中身亡。第3師團死傷總數達三百余名。”松井石根報告東京:“值得注意的是,該方面使用了中國軍中最精銳的陳誠指揮的第11師、第14師,我軍兵力最小限度要五個師團。”
盡管難度極大,陳誠立場仍然堅定:“淞滬在戰略上對我極為不利,但在政略上絕不能放棄,亦不可放棄。 欲達持久戰之目的,只有取積極之手段(以攻為守),與抱犧牲之精神,斷然攻擊。以全盤情形觀察,敵除海軍炮艦及飛機炸彈外,其陸軍絕難發展,其困難情形只有比我為甚。”9月6日,日軍攻占寶山縣城,第98師第583團第1營自營長姚子青以下大部陣亡。陳誠痛心之余批評國軍人事:“此次組織之不健全,系統之不清楚,各級因人設位,而應負責者僅掛名而已,實際負責者則無名義。”
應負責者系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雖居名義,事實上無法得心應手指揮中央大軍作戰。實際負責者是指自己,明明獨當一面,麾下部隊遠遠超過一個集團軍,卻無合適名義。都說“名不正,言不順”,蔣介石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有意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陳誠反倒猶豫起來,“余以現在情形以不居名義為妥”。9月21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左翼總司令仍兼第15集團軍總司令,在符合淞滬戰場實際態勢的同時,又同步解決了“名義”難題。
上海戰事持久不下,日軍再增三個師團,其中第9師團于10月8日突破了蘊藻浜南北兩岸國軍陣地。蘊藻浜原屬中央作戰軍總司令朱紹良指揮,顧祝同認為朱甚少把握,提出左翼軍和中央作戰軍均歸陳誠指揮。陳誠有些擔心“侵犯權限”遭人嫉妒,但想到“不能負責、不肯負責,則又將如何”,遂挑起重任。適逢廣西軍隊開到,顧祝同、白崇禧、陳誠會商使用辦法,決定“先占領大場至陳家行之線(守勢待機)”。10月16日,蔣介石偕宋美齡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抵達蘇州,強令取消“守勢待機”,蘊藻浜必須主動出擊。促使蔣介石不惜犧牲的重要因素,或許來自美國方面的關切,陳誠日記明白寫著:“下午三時(10月17日),謁委座,談如何使上海戰事維持至明春(因羅斯福有問及此)。”
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北岸金山衛,淞滬形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指定陳誠赴青浦臨時指揮右翼,顧祝同“以系統不明,恐責不專,報告委座,以陳誠任前敵總司令”,倚重之深,躍然紙上。11月9日拂曉,孫元良、桂永清等部先后撤至昆山,陳誠從容不迫,命令孫部暫守鐵橋,前敵總司令部人員取水道往宜興。而他本人并不著急先走,“獨與少數官佐分別至各要路口,令各部隊長至指定地區收容整頓待命”,等到一切部署妥當,“則至昆山一寶塔內坐鎮,又三日,始乘小艇繞道回蘇州”。
馮玉祥:“我曾作一月無言之司令長官”
8月上旬,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作戰區域包括江蘇省長江以南和浙江全省。張治中和馮玉祥是安徽巢縣同鄉,第一時間表示歡迎,馮復電:“此后共在一區,抗敵救國,互相策勉,尤愿一致在大元帥(蔣介石)領導之下,犧牲小我,而謀民族復興。”
僅僅過去幾天,抗戰熱情高昂的馮玉祥就把所見、所想和盤托出:“此次對日作戰,恐非短期間所能結局,即預備一千萬后備軍,亦不為多,至少應先成立二百萬方能足用。各地環境不同,人才因之而異,各有長短,各有需要。例如江蘇一帶財富之區,人文蔚起,謀略有余,對于征兵,反有所懼。最好北由冀、魯、豫、皖等省,南由滇、黔、桂、湘等省,迅速招兵,不至誤事。各地方因軍事長官開往前方應戰,以致后方多負責無人,防空、防奸,及后方醫院,均未能周備,極應指定專員辦理。”蔣介石曾有一次從南京打電話給馮玉祥:“前方的將領都太年輕,勇敢有余,經驗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氣。”馮說:“決不客氣,現在我們前方的各將領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戰的革命青年。他們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方的任務就是作幾首歪詩,再一個就是等死罷了。
馮玉祥覺得“對敵抗戰,非喚醒民眾不可”,草擬了“抗日救國問答十條”供蔣參考,文字通俗,極具推廣性,比如:“不抗日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要當亡國奴了。怎樣才能不當亡國奴呢?只有信仰我們的政府,信仰我們的軍隊,信仰我們的軍事領袖,大家一致抗日,才能不當亡國奴。”民國時期教育普及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比比皆是,粗淺的大白話比起深奧的大道理,容易灌輸給大眾快速接受。蔣介石想想蠻有道理:“所陳各節甚當,已令飭各有關機關,參酌情形,負責進行辦理。”
然而無需諱言,因為歷史和地緣的關系,馮玉祥與中央軍將領素少淵源,指揮調度并不順暢。白崇禧往來淞滬前線,據其觀察,馮玉祥“白天不在戰區長官部,住在離上海約150華里之宜興張公洞,除偶爾夜間到戰區長官部,白天就把私章交給顧祝同,公事由顧處理”。公開場合,馮玉祥胸懷坦蕩:“我們只要能抗日,不必軍隊一定要聽我的指揮;我們只要能救國,不必一定自己處很高的地位。此間軍隊,我都不甚熟悉,若必處處聽我指揮,必致敗了大事。”但私下不免流露郁悶心情:“三戰區為人家(指蔣)直屬部隊,我曾作一月無言之司令長官。”
白崇禧察覺其中微妙,與軍政部長何應欽商量:“我以為西北部隊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孫連仲、劉汝明、馮治安等有愛國之熱誠,又是馮一手造成之部隊,他們對程潛之指揮不大接受。不如在黃河以北、山東北部、河北等地,開辟一新戰區——第六戰區,由馮負責,兵力若連同韓復榘部至少有十五萬人以上。”蔣介石采納建議,但自己不方便出面,便委托白崇禧問問馮玉祥的意思,馮倒挺爽快:“在抗戰的時候,只有唯命是聽,統帥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從。”9月11日,軍事委員會劃津浦線為第六戰區,正式任命馮玉祥為司令長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北軍舊部已集體“變心”,都不歡迎馮玉祥光臨指導,也就一個多月時間,第六戰區撤銷,馮玉祥只好繼續當他的副委員長。
顧祝同:“你們準備怎樣來實踐統帥的意旨”
張治中無法完成既定任務,馮玉祥又名不副實,8月24日晚上,蔣介石毫無預兆地任命顧祝同為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負責指揮一切。顧祝同感到無比詫異,一來早先預定他負責徐州方面的作戰任務,二來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之外,又設立副司令長官部,這也是一種特殊的、不尋常的組織。
事出突然,身邊的幕僚人員尚未到齊,大部分還在重慶行營和西安行營,顧祝同只好一面電話通知,一面先行赴滬就任,“我來戰區,只是臨時決定,僅帶有隨從一名,只得暫借張治中總部的人員及設備。我的辦公室,也就暫設在張治中辦公室的隔壁,只裝了兩部電話機,以應付前后方聯絡的需要”。
其實,無論誰居名義,毋寧說都是高度重視上海的蔣介石親自擔任總指揮,顧祝同心甘情愿扮演傳聲筒角色。史說時任第9集團軍作戰科長,晚年記憶猶新:“顧祝同每天早晚與蔣介石通電話,報告情況,由蔣在電話中指示,某師調往哪里,某師如何作戰,顧作了傳令兵。”
馮玉祥調離之后,蔣介石干脆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事無巨細,親力親為。顧祝同亦不嫌煩,報備戰況,樂此不疲。不過也有史料說明,顧祝同并非一味言聽計從。10月下旬,國軍主力退守滬西,蔣介石要求留下第88師死守閘北,喚起國際列強同情。師長孫元良意見相左:“我們孤立在這里,聯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不值得。”參謀主任張柏亭面陳顧祝同,強調第88師老兵所剩無幾等種種難處。顧祝同反問:“那么,你們準備怎樣來實踐統帥的意旨呢?”張柏亭說:“既然是出于政略考慮,似乎不必硬性規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權部隊自行處理。”顧又問:“孫師長電話中,也曾提到這些,但沒有說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守備何種據點?”張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認為選拔一支精銳部隊,至多一團左右兵力,來固守一二個據點,也就夠了。”最后落實的方案是,由中校謝晉元帶領第524團一個加強營,固守蘇州河畔靠近租界的四行倉庫。由此可見,顧祝同倒也不失為蔣介石溝通前方將領的合適人選。
11月14日黃昏,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部開始撤退。顧祝同與曾振等人同時離開蘇州,只見“一路充塞,部隊亦絡繹西進,秩序混亂已極”。晚年撰寫回憶錄,顧這樣寫道:“過去戰地情景,我雖已見慣,而此時一幅亂離慘痛的畫面,深印腦際,歷久竟不能磨滅。”11月15日晨,顧祝同赴京述職,司令部同仁則經溧水轉往皖南。
蔣介石后來檢討淞滬會戰,坦言自己犯下大錯:“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于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布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平心而論,金山衛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淞滬鏖兵三個月,國軍疲憊不堪,如果能夠適時撤至江蘇境內的既定國防工事線,或許更有利于持久抵抗。可惜,蔣介石過分考慮政略,遲遲不愿意放棄上海,導致撤退階段狼狽不堪,這才是真正應該檢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