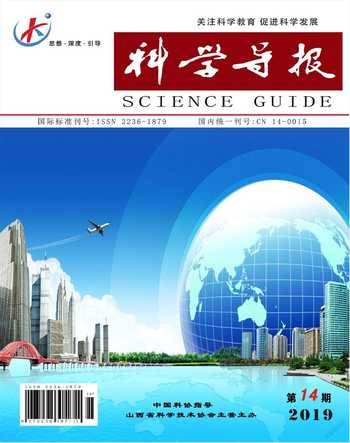《竹林》的靜寂,《蕭蕭》的偶然
趙麗
摘要:廢名與沈從文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一直被認(rèn)為是有著近似風(fēng)格的兩個(gè)小說(shuō)家,同樣的淡化情節(jié),同樣的詩(shī)意,但是他們對(duì)人事的態(tài)度卻是迥然不同的,廢名的清凈帶有的是一種對(duì)人事的冷漠,有一種拒絕的塵世的獨(dú)立。而沈從文的清凈中有著熱鬧的一面,有著更多的人間煙火氣,在一種必然之中處處顯現(xiàn)出偶然的痕跡。而這種不同在《竹林的故事》和《蕭蕭》中最為突出。
關(guān)鍵詞:《竹林的故事》;廢名;《蕭蕭》;沈從文;靜寂;偶然
廢名與沈從文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一直被認(rèn)為是有著相似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兩位小說(shuō)家。他們?cè)诙兰o(jì)二三十年代創(chuàng)作的小說(shuō),以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的淡化、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人物形象的白描、詩(shī)性的孜孜以求贏得了讀者的青睞。盡管他們的創(chuàng)作傾向與風(fēng)格大體一致,但在細(xì)微處卻還有著各自的異同。從整體風(fēng)格上來(lái)看,沈從文所邁的步子是溫文爾雅、自然無(wú)雕飾的,其以湘西農(nóng)村為題材的作品總籠罩在如同那一片經(jīng)久不散的煙雨朦朧般的溫柔、熱情且必然中又有著偶然的凸顯,《蕭蕭》便是這一風(fēng)格的最佳體現(xiàn)。而廢名的足音多少有些冷漠、寂寥且一切順其自然,他的作品即便是抒寫田園風(fēng)光也“以沖淡為衣”,較為“閃露”,《竹林的故事》便是這一風(fēng)格的最佳體現(xiàn)。
《蕭蕭》給我們展示的是一幅不著色彩的淡淡的湘西山村的山水圖,平平常常的山和水,一代又一代似乎有規(guī)律而毫無(wú)波瀾的生活,沒(méi)有濃烈的色彩,只有春來(lái)秋走的時(shí)間如流水,只有春后一個(gè)秋的狗尾巴草、南瓜、毛毛蟲、,山間無(wú)名的野花,,一切的事情都平常樸實(shí)得如同我們自己的生活一樣,時(shí)間在悠悠的春秋中走了又來(lái),只是這個(gè)時(shí)間中有著自然的必然,卻有著小小的偶然的波瀾。作者取人物唇吻間的話語(yǔ),簡(jiǎn)單自然的舉動(dòng),天真在眉目言動(dòng)之間流露,這蕭蕭如她所在的那一片碧水,任情而無(wú)所顧及的流淌著,即便偶有思慮也是山川草木的問(wèn)題,小說(shuō)在寫了十二歲:蕭蕭過(guò)門(交待其童養(yǎng)媳的生活內(nèi)容),夏夜乘涼,祖父戲說(shuō)女學(xué)生,蕭蕭的女學(xué)生之夢(mèng)的產(chǎn)生;十三歲:秋收摘瓜,花狗挑逗,情欲初萌;十五歲:春日野合懷孕,逃跑未遂,生子被恕;十年后:圓房,生次子,為大兒娶童養(yǎng)媳;在《蕭蕭》中,時(shí)間體現(xiàn)出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意義尤其明顯。因?yàn)槊恳粋€(gè)時(shí)間對(duì)應(yīng)著蕭蕭獨(dú)特的一段生命景觀。不僅如此,文本中的季節(jié)還具有深層的隱喻意義。小說(shuō)中每一個(gè)季節(jié)對(duì)應(yīng)著一個(gè)蕭蕭生命中的特定事件。如春的萬(wàn)物滋生對(duì)應(yīng)著蕭蕭與花狗的野合;冬的調(diào)零、空蕪對(duì)應(yīng)著蕭蕭童年期的提前完結(jié)以及最后蕭蕭情欲和夢(mèng)的消失。而四季的循環(huán)往復(fù)又象征著一個(gè)固定的、封閉的生命結(jié)構(gòu)模式,即蕭蕭這個(gè)符碼所代表的鄉(xiāng)間女子的整體命運(yùn)模式,因而,沈從文筆下的人與自然的節(jié)律是相宜的。作者在這種純凈中體現(xiàn)著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一種相融。
翻開(kāi)《竹林的故事》,盡管是精簡(jiǎn)、樸素的兩三句描述,卻呼之“已”出的是幽幽竹林園的自然、美麗、清凈。“出城一條河,過(guò)河西走,壩腳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作者盡管只用了“河”、“竹林”、“茅屋”、“菜園”等幾個(gè)簡(jiǎn)單的詞匯,卻勾勒出了一幅小橋流水人家的田園圖景,傳遞著恬靜清幽的溫馨,充滿了生機(jī)與活力:“林里的竹子,園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綠得可愛(ài)”。“雨之后,河里滿河山水”。“因?yàn)樘?yáng)射不到這來(lái),一邊一顆樹(shù)交陰著成一座天然的涼棚,水漲了,搓衣的石頭沉在河底,剩現(xiàn)綠團(tuán)團(tuán)的坡,剛剛高過(guò)水面,廢名所描寫的大自然,盡管處處是小橋流水、疏林修竹、桃紅柳綠,但沒(méi)有騷動(dòng),沒(méi)有風(fēng)波,人與自然盡管交織匯融,回歸到渾然一體的原始之初,但作者并沒(méi)有寄情感于自然萬(wàn)物中。所以,在《竹林的故事》中,人與外界、心靈與自然產(chǎn)生了距離,他們彼此獨(dú)立,因?yàn)樽髡叩膬?nèi)心早已皈依自然,所具備的是超然塵外的自然人格。書中對(duì)與老程死了以后是這樣說(shuō)的:“然而那也并非是長(zhǎng)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樣勤敏,家事的興旺,正如這塊小天地,春天來(lái)了,林里的竹子,園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綠得可愛(ài)。老程的死卻恰好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lái)。”人物的內(nèi)心與環(huán)境是相互獨(dú)立的,人的生死與自然是自成一格的,自行其道。
沈從文專家凌宇在《從邊城走向世界》中,提到此篇小說(shuō)是“常與變交織,必然與偶然錯(cuò)綜”,并認(rèn)為蕭蕭面對(duì)許多“偶然的因素”,包括:出現(xiàn)過(guò)一個(gè)讀過(guò)“子曰”的人;有人家買蕭蕭;生下的是兒子,他的結(jié)論便是:“情節(jié)的發(fā)展指向一個(gè)明確的思維方向:蕭蕭這類善良、純樸的山村兒女,生命在一種無(wú)法預(yù)測(cè)其結(jié)果的人生浪濤里浮沉,任何一種偶然的因素都可能使她們的人生命運(yùn)改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無(wú)可否認(rèn)的偶然與變數(shù)并沒(méi)有影響整個(gè)生命循環(huán)的自然規(guī)律。鄉(xiāng)下人生活中不斷出現(xiàn)的“規(guī)矩”,即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禮法制度,或者稱為“偶然”和“變數(shù)”,同樣也不曾禁錮他們善良的心靈。小說(shuō)中蕭蕭的失貞、懷孕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事情了,它必然會(huì)引起軒然大波,這個(gè)必然的出現(xiàn)在其他作家那里絕對(duì)是重筆,會(huì)以血、淚、火來(lái)體現(xiàn),但是在文中卻出現(xiàn)了一個(gè)“子曰”的伯父決定發(fā)賣而不是沉潭,然后生了一個(gè)“團(tuán)頭大眼”的男嬰,“大家把母子而人照料的好好的,照規(guī)矩吃蒸雞同江米酒補(bǔ)血,燒紙謝神,一家子都喜歡那兒子。這個(gè)男嬰長(zhǎng)大了叫蕭蕭的丈夫‘大叔’,‘大叔’從不生氣,并讓男孩長(zhǎng)到十二歲時(shí)照樣給接了親”這樣一個(gè)結(jié)局是出乎意料的,在蕭蕭的小丈夫嘴巴里唱著花狗教的情歌時(shí),我們可以預(yù)料到蕭蕭與花狗會(huì)發(fā)生故事,這是常也是人性中的必然性,但是當(dāng)這件事情就這樣順其自然的落幕的時(shí)候,一種人生偶然就在自然中融化了,一切的不合理都在它自己的規(guī)律之中合理了。這就是沈從文的靜,他的靜不是死寂,有著最貼近生活的原來(lái)面目,熱情中有波瀾,只是這種波瀾并不會(huì)打破生活原有的平靜,沈從文的小說(shuō)有水的色彩,透明澄凈,卻是流動(dòng)的,有著小小的跳躍,最后有靜靜的流到它應(yīng)該到的位置。
廢名的小說(shuō)《竹林的故事》則是波瀾不驚,是一潭死水,承載的生活沒(méi)有煙火人心,是所有的東西都在靜靜的流淌,連愛(ài)憐都是如風(fēng)的清新,帶有失音的鞋印。三姑娘的爸爸不知不覺(jué)地死了,“綠團(tuán)團(tuán)的坡上從此不見(jiàn)了老程的蹤跡”,一筆帶過(guò)。這種風(fēng)格若以詩(shī)比,則近于韋應(yīng)物的“春潮帶雨晚來(lái)急,野渡無(wú)人舟自橫”的那份淡雅;若以畫比,則近于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那種地老天荒似的寂寞的美麗。小說(shuō)的敘述者是帶著愛(ài)戀的對(duì)三姑娘但是卻處理的波痕都沒(méi)有一點(diǎn)。對(duì)三姑娘的回憶是從“我”十二年前的讀書生活開(kāi)始的。“我”曾經(jīng)在那個(gè)村莊的私塾讀了六年書,那段時(shí)間也正是“我”的青少年時(shí)期。然而在十二年后“我”還對(duì)一個(gè)鄉(xiāng)村少女如此念念不忘,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作為一個(gè)青年男子的“我”對(duì)三姑娘所產(chǎn)生的特別情愫。最初的“我”作為回憶者以全知角度敘述的只是三姑娘在河邊嬉戲、幫爸爸捉魚的歡快場(chǎng)面,以及三姑娘一家溫馨的生活場(chǎng)景,那時(shí)的“我”也只當(dāng)她是一個(gè)小孩子,常常借割菜來(lái)逗她玩笑。在此,他們之間的情感只是純潔無(wú)邪的童真童趣。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guò)去,三姑娘己經(jīng)長(zhǎng)成一個(gè)十二三歲情竇初開(kāi)的少女。他們之間也開(kāi)始形成了男女兩性世界的對(duì)立,三姑娘也處于“我”這位男性目光的追尋和看視之下。在“我”眼里,總覺(jué)得“見(jiàn)了三姑娘活潑潑的肩上一擔(dān)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為什么那樣沒(méi)出息,不在火燭之下現(xiàn)一現(xiàn)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樣的面龐呢?”由此可見(jiàn)“我”對(duì)三姑娘是有著愛(ài)慕之情的。當(dāng)三姑娘多抓了一把青椒給“我”,我取笑她將來(lái)碰上一個(gè)好姑爺,而她卻害羞地逃走時(shí),可見(jiàn)三姑娘對(duì)我也是有著綿綿情意的。然而“我”還是“我”,既不敢向她表白,也不敢向她求愛(ài)。只是將這份愛(ài)存入心底,直至一句“從此我沒(méi)有見(jiàn)到三姑娘”道出了后來(lái)自己對(duì)她的思念與惋惜,并最終讓“三姑娘低頭過(guò)去”平淡地完成了“竹林”里的這個(gè)“愛(ài)情故事”,似有若無(wú),沒(méi)有什么熱情,沒(méi)有偶然和波瀾,歲月無(wú)聲的流失中什么都走了,沒(méi)有怨,沒(méi)有恨,只有歲月如歌。
廢名是坐在柳蔭下,平靜悠然地看著人間景致的,而沈從文則是劃著一張?zhí)以捶ぷ樱蹨喌厍斑M(jìn)有風(fēng)有浪更有生命的激情。他們都在構(gòu)建屬于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然而他們所站立的姿態(tài)不同,一個(gè)是孤獨(dú)的、缺乏斗志的,而一個(gè)卻在描繪如詩(shī)如畫的自然美景時(shí),一個(gè)是在他的“竹林世界里封閉自我,來(lái)逃避現(xiàn)實(shí)世界而尋找自身的,而另一個(gè)是以一個(gè)有追求、有愛(ài)心、有理想,希望人們愛(ài)自己,也希望人人愛(ài)別人的形象出現(xiàn)的。曾經(jīng),沈從文將自己與廢名進(jìn)行了比較,他認(rèn)為廢名“所顯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xì)微雕刻……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筑到‘平靜’上,有一點(diǎn)憂郁,一點(diǎn)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duì)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ài)有憎,———但……這些靈魂,仍然不會(huì)騷動(dòng)……”而認(rèn)為自己“使社會(huì)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機(jī)會(huì)在作者筆下寫出……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qiáng)烈的愛(ài)憎,有悲憫的情感……”。沈從文在人間生活,廢名在真空中生活。
(作者單位:昆明幼兒師范專科學(xué)校(昆明市中等職業(yè)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