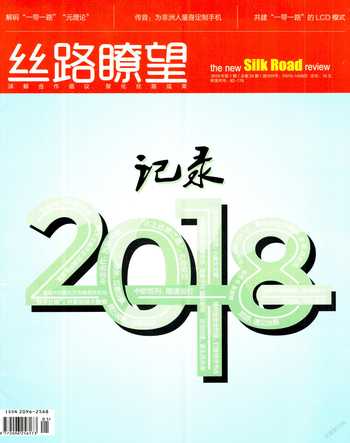“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理論
趙柯
從1980年到2006年,全球經濟經歷了一個被稱之“大穩健”的經濟繁榮周期,高速增長、低通脹率和低失業率是這一階段的特征。2007年的全球金融風暴讓世界經濟發展從“大穩健”轉換為“大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深度調整期。全球經濟復蘇脆弱、不均衡,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說法,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拐點:它可以一直保持低增長——進入“新平庸時代”。這種風險是存在的。所以,當前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一帶一路”建設正是要為經濟增長提供這樣一種新動力。
經濟增長,說到底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首先需要貿易,也就是人與人之間通過交易“互通有無”。對此,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給出了強有力的論證。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國民財富從哪里來?
《國富論》洋洋灑灑數十萬言,幾乎涉及了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他開明宗義放在第一章的是“論分工”,這是斯密對增長最為深刻的洞見。他認為經濟增長源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因為有了分工和專業化,而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則有賴于市場規模的擴大。這就好比一個村子,如果只有三五戶人家,家家都得自給自足。但如果有了三五十戶,甚至三五百戶,那么分工就會出現:一些家庭可以只專注于種糧食,另外一些則可以制造農具、釀造美酒或者開設餐館。村民相互交易自己的勞動成果,結果是村莊的整體福利得到提高。
斯密所描述的這個增長模型告訴我們:只有市場規模擴大才能容納更多的分工和專業化,進而使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才會出現。簡單說就是:市場規模很重要,經濟增長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
“一帶一路”最基本的經濟學邏輯,就在于通過各國間的互聯互通,全球市場規模極大地得到了拓展,這讓提升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成為可能,世界經濟的增長才能獲得更為持久的推動力。“一帶一路”建設是解決當前全球經濟長期增長瓶頸的一個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