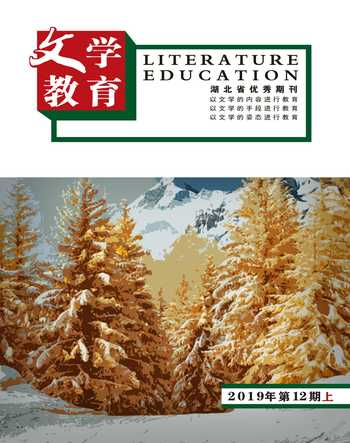莫言自稱再也寫不出《紅高粱》了
2019-09-10 04:19:02
文學教育 2019年12期
莫言日前在“第二屆會稽山論壇”接受采訪時說:“如果現在讓我重新寫一遍《紅高粱》,肯定寫不出那個樣子了,肯定是按部就班地遵循語法規則,會把語言雕琢打磨得很美,會把人物寫得很圓滿,會把人物身上很多過分丑陋的東西適當美化,這就是我目前的狀態。”對于《紅高粱》那種“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敘述語調,褪去年輕時的張狂后的莫言笑稱,這實際上只是年輕時的一段狂言,“現在讓我寫,我肯定不會這樣去寫,我肯定會寫故鄉太可愛了,我永遠想念你”。莫言現在認為,《紅高粱》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尤顯離經叛道,不僅是主題上的突破,在結構和語言上也力求不同。于是這才有了《紅高粱》那種“頭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跳躍式寫法,這種藝術上的創新在當時同樣被視為是一種對傳統的挑戰。莫言說:“現在我回過頭來讀《紅高粱》,讀到某些片斷時,我也覺得有些過分,把動詞當名詞用,把名詞當動詞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詞搭配到一起。《紅高粱》如果讓中學的語文教師來讀的話,他會在上面畫滿了紅叉,會說不通順要改正,用詞不當,或者邏輯錯誤等。但我覺得,也正是因為這種寫法才使我的這種強烈情感得到了釋放,正是這種寫法對語言的破壞,也使讀者受到了感染。”莫言還深情地懷念中國30年前的那個“80年代”。他說:“那是一個黃金時代,如今回頭看,那個年代無論是美術界、文學界,還是舞蹈、音樂,都涌現了一批年輕人,大家都有自己長期積累的情感和生活,對幾十年來沒有變化的這種藝術秩序進行沖擊,試圖實現突破,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
猜你喜歡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家庭醫學(下半月)(2020年4期)2020-05-30 12:42:50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小太陽畫報(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期)2016-12-01 03:59:30
發明與創新(2016年6期)2016-08-21 13:4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