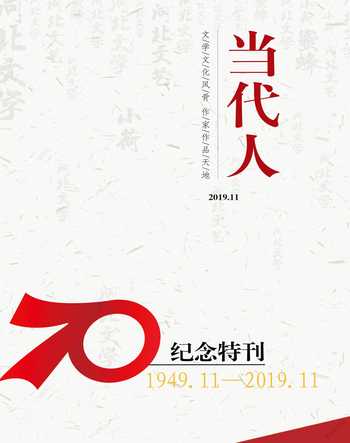他的詩(shī)心即是獲救
詩(shī)人一枝草及其詩(shī)歌,似乎一夜之間躥入詩(shī)壇。實(shí)則,他是回歸。只是,一枝草與三十年前河北文壇新銳顧超圻及今日港媒資深記者顧大鵬是一人,鮮為人知。
記者的職業(yè)和“歸來(lái)”的身世,注定了他詩(shī)歌的獨(dú)特之處。歸來(lái)的詩(shī)者不以詩(shī)人自居,他的詩(shī)無(wú)匠氣,不從眾。他“不以詩(shī)為詩(shī)”。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詩(shī)歌,是他獻(xiàn)給世界的另一種報(bào)道文本,一切源自生命經(jīng)驗(yàn),是自省與批判,是突圍、冒犯、解構(gòu)以及新的和解。
發(fā)現(xiàn):在新的高度回望
一直以來(lái),詩(shī)歌介入現(xiàn)實(shí),重返現(xiàn)實(shí),干預(yù)現(xiàn)實(shí),呈現(xiàn)現(xiàn)實(shí),調(diào)整現(xiàn)實(shí),各種命題千奇百態(tài),在順應(yīng)著時(shí)代大潮不斷翻涌和更迭中起起落落。但真理恒在,很多時(shí)候,詩(shī)歌前行之路,只需探索,只需發(fā)現(xiàn),沖破人云亦云的桎梏,呈現(xiàn)出一種展望的勇氣。
一枝草的詩(shī)以其迥異的表達(dá),既混合著韻律與文化的暗指,又在直白中呈現(xiàn)著觸目驚心的現(xiàn)實(shí):“喝下這杯抹香的茶,/ 半睜著一雙肉眼,/ 覬覦整個(gè)世界,/ 貪婪吞噬無(wú)限的地平線”(《地平線》)。他因“回望”而發(fā)現(xiàn)了“覬覦”之肉眼,這便形成了一種對(duì)峙的關(guān)系,詩(shī)人與現(xiàn)實(shí)的對(duì)峙。與其說(shuō)是一種偶然遭遇的抗衡,莫若說(shuō)是一種有預(yù)見(jiàn)性的廝殺。“理性”和“高度”成為一種巨大的磁力,或百慕大的漩渦,不遺余力地蔑視著那些所謂的“自我加冕”“光明之神的夜宴”,并在“以正義之名向正義宣戰(zhàn)”的驚人發(fā)現(xiàn)中,讓它成為一個(gè)腹語(yǔ)的表演者,成為受試者自己精神地圖之內(nèi)的陌生人。
一枝草的詩(shī)常常有著暗沉的底色,這里有閉塞和絕望的生存現(xiàn)場(chǎng),也有幽暗的自我和刺骨的疼痛:“這次滿懷希望的旅行,/ 沒(méi)有看到自由的田垅,/ 沒(méi)有聽(tīng)到麥場(chǎng)里的低語(yǔ)。/ 沒(méi)有聞到五谷的草香,/ 沒(méi)有摸到小魚的泥滑”(《今夜,再次向小鳥(niǎo)講述》);“年復(fù)一年的七月,/ 烤焦過(guò)我良知的紅薯,/ 還常常降下斗大的冰雹”(《我的七月簽》)。生存的苦難與荒涼,現(xiàn)實(shí)和理想的矛盾,讓以記者為職業(yè)的詩(shī)人一枝草一邊行走,一邊回望,他知道,一名詩(shī)人最重要的是面對(duì),是真實(shí),是擔(dān)當(dāng),他無(wú)意去做隔靴搔癢的呻吟,更無(wú)意去采擷勻稱的歌調(diào),他只是憑著 “懇切、透徹、熱烈與誠(chéng)實(shí)”的品性,堅(jiān)執(zhí)地涵育著他那善于發(fā)現(xiàn)的詩(shī)眼和詩(shī)緒,在緊張的對(duì)峙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力量和批判。一枝草用“以正義之名向正義宣戰(zhàn)”的荒誕,作為透視世界和生存的鏡像,他不僅發(fā)現(xiàn)了外在的荒原,也發(fā)現(xiàn)了內(nèi)在的干渴:
我居于鳥(niǎo)巢,/ 卻沒(méi)有翅膀,/ 如果黑云擲下閃電,/ 擊垮了這個(gè)水泥森林,/我有什么值得傳承?
——《今夜,再次向小鳥(niǎo)講述》
“我有什么值得傳承?”這是一種生命的干渴中對(duì)精神甘霖的渴求,“傳承”即是對(duì)人類不可喪失思想和信仰的強(qiáng)烈信念。一枝草詩(shī)歌中融合了古代和現(xiàn)代、東方和西方的物與人的現(xiàn)實(shí)景觀,他既樹(shù)起了一種否定的、不認(rèn)同的發(fā)現(xiàn)者的姿態(tài),又隱含著一個(gè)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憂患的、沉思的形象。這是一個(gè)富有自我意識(shí)的抒情主體,他游走在現(xiàn)實(shí)和心靈內(nèi)外,以客觀的眼睛和超然的態(tài)度鑒照著人生,也鑒照著自己。
追問(wèn):能否尋回失去的本我
當(dāng)詩(shī)歌確立了它的歷史情境,我們就能夠清晰認(rèn)知,文學(xué)并不是一個(gè)獨(dú)立的文學(xué)場(chǎng)。詩(shī)本體在于追問(wèn)與求索。
一枝草也在審視,在反思,在追問(wèn)。他追問(wèn)了什么?
我是誰(shuí)?/ 誰(shuí)是我?/ 在扭捏的地平線上,/ 能否尋回失去的本我?
——《地平線》
宇宙生命的本真意義,作為個(gè)體的人的獨(dú)立、真實(shí)的本我。一枝草何嘗不知道這是一個(gè)非解的答案,自柏拉圖提出后,人人都在追問(wèn)。他的勇氣就在于他敢于老調(diào)重彈。他重彈是因?yàn)樗钪獎(jiǎng)?chuàng)造本身就是在不斷的反思和追問(wèn)中。他無(wú)畏審視著“星際大戰(zhàn)遺留下的斑駁血痕”(《你即是那一切》),審視著“文明奴役愚昧的陰謀?”(《陰謀》),審視著“老樹(shù)枯藤為土造的鋼爐殉葬”(《清明》),審視著“死寂的性愛(ài)和喧囂的歌”(《突然坍塌的我》),從認(rèn)識(shí)論和本體論兩個(gè)層面去體驗(yàn),他讓客體和主體互為他者,既有有距離的觀察的凜然,亦有合一的感同身受的驚悚,他獲得了不可或缺的生命體驗(yàn),“我是誰(shuí)?/ 誰(shuí)是我?”,他以他自身選定的主題保持了自身與思想的完整性。
如果說(shuō),詩(shī)不能給予,只能是喚起。那么一枝草的追問(wèn)就成為必然。他追問(wèn)活的意義,包括詩(shī),包括語(yǔ)言,當(dāng)然也包括心跳:“借宙斯發(fā)出的雷鳴和擲下的閃電,/ 一次又一次地隆重加封續(xù)命?”(《我無(wú)心芒種和收割》),他也追問(wèn)死的啟示:“看看先人的天藍(lán)不藍(lán),水又清不清?/ 看看先人是不是追趕時(shí)尚,/ 喜歡金山銀山和水泥森林。”(《清明》),他更追問(wèn)著自身的潔凈:“那我問(wèn)你,那不是你是誰(shuí)?”(《突然坍塌的我》)一枝草在生命體驗(yàn)中獲得了最深切的感受,他將自己化為熾熱鋼水,在情不自禁的追問(wèn)中,在無(wú)所顧忌的追問(wèn)中,他鑒照了世界和自己,也鑒照了現(xiàn)實(shí)和夢(mèng)境,他在詩(shī)話的言說(shuō)中超越了自我,救贖了自我。一枝草不是一個(gè)逃離的人,他的發(fā)現(xiàn)即是面對(duì),他的詩(shī)心即是獲救。
一枝草找到了本我,那就是“只求人鬼之間有真情!”(《清明》)的一個(gè)“真”。
頓悟:你即是那一切
作為記者的顧大鵬善于甄別偽善真假,作為詩(shī)人的一枝草始終培育著心底的成熟與充盈。他的詩(shī)不從眾,他讓他的語(yǔ)言有自己的維度和發(fā)聲,他的句式可長(zhǎng)可短,全部是隨心所欲,為內(nèi)心的情感之流而奔涌。他的節(jié)奏有舒有緩,意味有顯有隱,他不刻意布道,他只說(shuō)出真實(shí)。他的自語(yǔ)性瀝膽剖心,他的整體性乃有頓悟之味。
他的詩(shī)作不談悲憫卻潛隱著生命的倫理,不談禪宗卻歸隱著自然的圣殿。他毫不掩飾地指認(rèn)著自我:“我曾傻傻地分別白天和黑夜,/ 我曾傻傻地相信自詡光明的人,/ 我曾傻傻地憎惡黑暗,擁抱光明。”(《黑暗與光明》)
這種指認(rèn),讓他在貼近先鋒精神的深刻內(nèi)省中,獲得了黑暗與光明雙生雙刃中的自由。這自由讓他的詩(shī)心深入萬(wàn)物的靈魂,深入生活的底蘊(yùn),深入生命的本源。他“從夢(mèng)中慢慢蘇醒”(《地平線》);“遙望宇宙那閃爍的星云”(《你即是那一切》);“我時(shí)常從我的脊背上飛起,回望”(《今夜,再次向小鳥(niǎo)講述》);“我測(cè)試著我的運(yùn)勢(shì)”(《我的七月簽》);“我想自由自在地去踏青”(《清明》)。詩(shī)人從外場(chǎng)景至內(nèi)宇宙的回歸和頓悟,沒(méi)有讓他虛無(wú),而是更加豐富;沒(méi)有讓他頹廢,而是讓他更見(jiàn)從容;沒(méi)有讓他退縮,而是更見(jiàn)修為。
你即是父親,/ 又是兒子和孫子,/ 你即是那一切。
——《你即是那一切》
我是那風(fēng),/ 我是那雨,/ 我就是那風(fēng)雨中的雷電。/ 其實(shí)呀,你就是我,他就是我,這個(gè)世界就是我。
——《突然坍塌的我》
真正的詩(shī)人,總是能夠毫不留情地解構(gòu),同時(shí)也能創(chuàng)造性地建構(gòu)。詩(shī)美的奧秘恰恰在于兩者相互滲透、深入、構(gòu)成,渾然一體。一枝草的這組詩(shī),成就了它們互為出發(fā)點(diǎn),又互為歸宿。
(薛梅,滿族。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師范學(xué)院教授,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承德市作協(xié)副主席,《國(guó)風(fēng)》常務(wù)副主編,魯迅文學(xué)院22期少數(shù)民族學(xué)員。有專著《承德詩(shī)歌簡(jiǎn)論》《與面具共舞——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詩(shī)歌現(xiàn)場(chǎng)研究》。曾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jiǎng)、河北文學(xué)評(píng)論獎(jiǎng)、《詩(shī)選刊》年度優(yōu)秀詩(shī)人獎(jiǎng)、承德市文藝繁榮獎(jiǎng)。)
編輯:郭文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