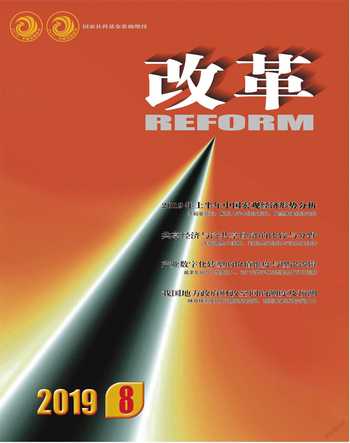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效應(yīng)評(píng)價(jià)與路徑選擇
俞嵐



內(nèi)容提要:開(kāi)放是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徑。只有選擇符合自身實(shí)際的開(kāi)放道路,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中國(guó)的開(kāi)放經(jīng)驗(yàn)表明,選擇漸進(jìn)式開(kāi)放,走先試點(diǎn)后推廣的開(kāi)放路徑有其合理性,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堅(jiān)持。下一步,中國(guó)要由國(guó)際規(guī)則的適應(yīng)者、接受者逐步轉(zhuǎn)變?yōu)閲?guó)際規(guī)則的參與者和建設(shè)者,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jì)和系統(tǒng)性安排,勇于涉足改革開(kāi)放的深水區(qū)。
關(guān)鍵詞:對(duì)外開(kāi)放;經(jīng)濟(jì)全球化;對(duì)外貿(mào)易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720?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文章編號(hào):1003-7543(2019)08-0071-12
開(kāi)放、創(chuàng)新和市場(chǎng)化是全球化三大驅(qū)動(dòng)力。全球化在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增進(jìn)福利方面的正面效應(yīng)已經(jīng)充分體現(xiàn),與此同時(shí),其負(fù)面沖擊和矛盾也逐漸顯現(xiàn),如財(cái)富分配不均、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不平衡、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續(xù)等。與此同時(shí),全球化背景下的國(guó)際秩序受到質(zhì)疑,基于西方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則的自由貿(mào)易規(guī)則和秩序遭遇挑戰(zhàn),多邊合作機(jī)制和全球治理架構(gòu)亦面臨沖擊。
中國(guó)是全球化的積極實(shí)踐者。中國(guó)推行改革開(kāi)放的目的之一就是積極參與全球化,融入多邊經(jīng)濟(jì)體系,以開(kāi)放促改革、以改革擴(kuò)開(kāi)放,進(jìn)而推動(dòng)高水平開(kāi)放、高標(biāo)準(zhǔn)改革、高質(zhì)量發(fā)展協(xié)同進(jìn)步。當(dāng)下全球化進(jìn)程受阻,但方向和趨勢(shì)不可逆,國(guó)家間經(jīng)濟(jì)開(kāi)放與融合乃大勢(shì)所趨。
一、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相關(guān)理論演進(jìn)
人類(lèi)并非從一開(kāi)始就對(duì)擴(kuò)大開(kāi)放的益處有系統(tǒng)性的認(rèn)識(shí),而是經(jīng)歷了一個(gè)相當(dāng)長(zhǎng)的過(guò)程。
(一)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理論的歷史演進(jìn)
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理論緣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及貿(mào)易的全球擴(kuò)張。十五世紀(jì)初至十七世紀(jì)末,隨著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航海技術(shù)發(fā)展,西歐封建制度解體,全球貿(mào)易和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飛速發(fā)展,歐洲國(guó)家間競(jìng)爭(zhēng)日趨激烈。作為應(yīng)對(duì)當(dāng)時(shí)世界貿(mào)易和國(guó)家競(jìng)爭(zhēng)的一種學(xué)說(shuō),重商主義應(yīng)運(yùn)而生。重商主義認(rèn)為,對(duì)外出口是財(cái)富的源泉,擁有金銀的多寡是衡量國(guó)家富裕程度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因此需要通過(guò)政府的力量維護(hù)本國(guó)貿(mào)易優(yōu)勢(shì),使貿(mào)易順差最大化。在重商主義學(xué)說(shuō)指導(dǎo)下,開(kāi)放具有明顯的雙重標(biāo)準(zhǔn):一方面,要求他國(guó)開(kāi)放市場(chǎng),促進(jìn)本國(guó)出口;另一方面,對(duì)本國(guó)實(shí)行保護(hù)主義,維持貿(mào)易順差和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因此,重商主義必然帶來(lái)開(kāi)放的“囚徒困境”和保護(hù)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進(jìn)一步發(fā)展,重商主義越來(lái)越難以指導(dǎo)國(guó)際貿(mào)易活動(dòng),亞當(dāng)·斯密的國(guó)際分工和絕對(duì)優(yōu)勢(shì)貿(mào)易理論開(kāi)始主導(dǎo)經(jīng)濟(jì)開(kāi)放理論和實(shí)踐。在其代表作《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中,亞當(dāng)·斯密對(duì)重商主義予以批判:一是金銀等貴金屬的流入不能直接提升國(guó)內(nèi)供給能力,反而會(huì)導(dǎo)致物價(jià)上升,最終降低競(jìng)爭(zhēng)力并導(dǎo)致金銀外流;二是衡量一國(guó)財(cái)富的標(biāo)準(zhǔn)不是貴金屬的儲(chǔ)存量,而是居民能夠購(gòu)買(mǎi)的國(guó)內(nèi)外商品總量[1]。在批判的基礎(chǔ)上,亞當(dāng)·斯密提出了國(guó)際分工和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理論,其主要觀點(diǎn)包括:第一,增加國(guó)家財(cái)富的根本在于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主要路徑在于加大資本積累和擴(kuò)大專(zhuān)業(yè)化分工;第二,各國(guó)都擁有具備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特定商品,通過(guò)開(kāi)展專(zhuān)業(yè)化分工生產(chǎn)和貿(mào)易交換,參與國(guó)際貿(mào)易的各國(guó)都能獲益。根據(jù)這一理論,開(kāi)放將帶動(dòng)市場(chǎng)擴(kuò)大和分工深化,對(duì)外開(kāi)放的合理性和貿(mào)易的互利性得到驗(yàn)證。
在繼承亞當(dāng)·斯密學(xué)說(shuō)的基礎(chǔ)上,英國(guó)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派的大衛(wèi)·李嘉圖進(jìn)一步創(chuàng)立了比較優(yōu)勢(shì)理論,在更廣泛的領(lǐng)域論證了開(kāi)放的合理性[2]。根據(jù)亞當(dāng)·斯密的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理論,如果一個(gè)國(guó)家在任何領(lǐng)域都不具備絕對(duì)優(yōu)勢(shì),就無(wú)法參與國(guó)際分工并分享貿(mào)易帶來(lái)的好處。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shì)學(xué)說(shuō)指出,國(guó)際貿(mào)易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并不限于絕對(duì)優(yōu)勢(shì),全面落后國(guó)家通過(guò)參與全球分工也能促進(jìn)本國(guó)發(fā)展。該理論認(rèn)為,各國(guó)在不同產(chǎn)品生產(chǎn)技術(shù)方面存在相對(duì)差別,導(dǎo)致不同產(chǎn)品價(jià)格不同,因此絕對(duì)成本普遍高的國(guó)家也能因產(chǎn)品價(jià)格相對(duì)便宜而實(shí)現(xiàn)相對(duì)優(yōu)勢(shì),從而獲得比較利益。比較優(yōu)勢(shì)學(xué)說(shuō)進(jìn)一步揭示了國(guó)際分工的必要性和開(kāi)放的互利性。
瑞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創(chuàng)立的要素稟賦理論,繼承并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比較優(yōu)勢(shì)學(xué)說(shuō),認(rèn)為要素稟賦差異是造成各國(guó)比較優(yōu)勢(shì)不同的主要原因[3],即商品價(jià)格差異緣于成本不同,而成本差異來(lái)源有二:一是生產(chǎn)要素的供給,即要素稟賦不同;二是生產(chǎn)不同產(chǎn)品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生產(chǎn)要素的相對(duì)稀缺性和技術(shù),是比較優(yōu)勢(shì)差異的重要成因。因此,要素稟賦不同的經(jīng)濟(jì)體之間通過(guò)彼此開(kāi)放和互相貿(mào)易也將帶來(lái)巨大收益。
(二)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競(jìng)爭(zhēng)力與開(kāi)放的關(guān)系
誕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的古典貿(mào)易和開(kāi)放理論,在“二戰(zhàn)”后的前30年并未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實(shí)踐中成為主流。普雷維什、辛格、繆爾達(dá)爾、納克斯等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提出了“初級(jí)產(chǎn)品長(zhǎng)期貿(mào)易條件惡化論”、發(fā)展中國(guó)家“出口悲觀論”[4-5],認(rèn)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主要出口初級(jí)產(chǎn)品,而初級(jí)產(chǎn)品出口的長(zhǎng)期貿(mào)易條件持續(xù)惡化,因此擴(kuò)大對(duì)外開(kāi)放、擴(kuò)大初級(jí)產(chǎn)品出口會(huì)導(dǎo)致出口購(gòu)買(mǎi)力持續(xù)惡化,使其在國(guó)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很難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蘇聯(lián)依靠?jī)?nèi)生發(fā)展迅速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的成功案例,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追趕發(fā)達(dá)國(guó)家提供了一個(gè)可資借鑒的樣板。這個(gè)時(shí)期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大多認(rèn)為,應(yīng)建立以保護(hù)主義為特征的進(jìn)口替代工業(yè)化戰(zhàn)略,推動(dòng)本國(guó)幼稚工業(yè)發(fā)展,建立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相類(lèi)似的工業(yè)化結(jié)構(gòu),實(shí)現(xiàn)自身富強(qiáng)。
這種保護(hù)主義和進(jìn)口替代工業(yè)化的理論思潮20世紀(jì)70年代以前在很多新獨(dú)立國(guó)家或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在拉丁美洲,出于保護(hù)本國(guó)民族工業(yè)的需要,大部分政府限制外國(guó)直接投資涉足國(guó)內(nèi)特定工業(yè)部門(mén),對(duì)進(jìn)口工業(yè)品征收高額關(guān)稅或?qū)嵤┡漕~,對(duì)出口初級(jí)產(chǎn)品征收出口關(guān)稅,并通過(guò)補(bǔ)貼和各種市場(chǎng)扭曲支持本國(guó)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的發(fā)展,實(shí)行進(jìn)口替代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由于資本相對(duì)不足,這些經(jīng)濟(jì)體主要依靠對(duì)外舉債解決資金短缺,采取了以外債促增長(zhǎng)、借增長(zhǎng)還外債的發(fā)展模式。中國(guó)和印度等經(jīng)濟(jì)體則推行了內(nèi)向型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政府通過(guò)工農(nóng)業(yè)“剪刀差”或分配機(jī)制扭曲,對(duì)工業(yè)部門(mén)進(jìn)行大規(guī)模補(bǔ)貼,實(shí)施行政計(jì)劃、財(cái)政補(bǔ)助等政策措施,以期在短期內(nèi)建立起國(guó)有工業(yè)體系。
以保護(hù)主義為特征的進(jìn)口替代戰(zhàn)略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lái)受到了理論和實(shí)踐的雙重挑戰(zhàn)。在基礎(chǔ)理論上,一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從理論邏輯和前置條件出發(fā)質(zhì)疑保護(hù)主義,論證了開(kāi)放是促進(jìn)發(fā)展的關(guān)鍵手段。克魯格等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不斷質(zhì)疑進(jìn)口替代戰(zhàn)略,包括質(zhì)疑初級(jí)產(chǎn)品長(zhǎng)期貿(mào)易條件不斷下降的假設(shè),認(rèn)為通過(guò)開(kāi)放和出口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shì)可以獲取出口剩余和貿(mào)易利益,出口帶來(lái)資本積累,改善基礎(chǔ)設(shè)施、要素結(jié)構(gòu)、勞動(dòng)力技能,使經(jīng)濟(jì)實(shí)績(jī)不斷提高。
在實(shí)踐上,采取進(jìn)口替代工業(yè)化戰(zhàn)略的拉美地區(qū)和普遍采取出口導(dǎo)向工業(yè)化戰(zhàn)略的東亞地區(qū)差距不斷拉大,讓以?xún)?nèi)向型特征為主的保護(hù)主義思想和實(shí)踐逐漸失去市場(chǎng)。拉美各國(guó)由于政府過(guò)度干預(yù)經(jīng)濟(jì)和市場(chǎng)機(jī)制嚴(yán)重扭曲,缺乏消費(fèi)和生產(chǎn)的良性循環(huán),外債壓力越來(lái)越大,補(bǔ)貼導(dǎo)致政府不堪重負(fù),經(jīng)濟(jì)陷入高債務(wù)、貨幣貶值和高通脹的困局,最終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而采取出口導(dǎo)向工業(yè)化戰(zhàn)略的“亞洲四小龍”,經(jīng)濟(jì)沿動(dòng)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階梯逐步升級(jí),形成了亞洲特有的外向型發(fā)展模式。
(三)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路徑的相關(guān)理論
一百多年來(lái)的經(jīng)濟(jì)史和經(jīng)濟(jì)思想史表明,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邁向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的必要條件,但如何開(kāi)放、選擇什么開(kāi)放次序,是擺在各國(guó)決策者和理論界面前的難題。20世紀(jì)80年代,隨著拉美國(guó)家陷入債務(wù)危機(jī),傳統(tǒng)計(jì)劃經(jīng)濟(jì)運(yùn)轉(zhuǎn)失靈,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開(kāi)出一劑“藥方”,即以“華盛頓共識(shí)”為指導(dǎo),推動(dòng)基于市場(chǎng)和規(guī)則的宏觀緊縮、自由化以及私有化改革的方案[6]:一是緊縮財(cái)政支出,改革稅制,防止通脹;二是推動(dòng)金融自由化、匯率浮動(dòng)化和貿(mào)易自由化;三是實(shí)現(xiàn)國(guó)企私有化,開(kāi)放外國(guó)直接投資;四是取消管制和對(duì)競(jìng)爭(zhēng)的限制,保護(hù)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這一方案實(shí)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jī)爆發(fā)后,一些出口導(dǎo)向型經(jīng)濟(jì)體陷入困境,也引發(fā)了開(kāi)放的同時(shí)如何解決好新舊動(dòng)能轉(zhuǎn)換問(wèn)題的討論①。
基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實(shí)踐和破解理論困境的需要,關(guān)于開(kāi)放和自由化路徑的反思在學(xué)術(shù)和實(shí)踐層面同步展開(kāi),大致形成三類(lèi)較為典型的觀點(diǎn):第一類(lèi)全盤(pán)否定自由化和開(kāi)放;第二類(lèi)依然堅(jiān)持自由化理念,認(rèn)為導(dǎo)致危機(jī)爆發(fā)的主要因素并非自由化過(guò)度,而在于政府干預(yù)過(guò)度;第三類(lèi)觀點(diǎn)折衷,不否認(rèn)自由化和開(kāi)放是各國(guó)追求的長(zhǎng)期目標(biāo),但同時(shí)也承認(rèn)要注意節(jié)奏和策略。持這一觀點(diǎn)的典型代表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和羅德里克等經(jīng)濟(jì)學(xué)家[7-8],與巴格瓦迪②、麥金農(nóng)的“經(jīng)濟(jì)自由化次序”主張有共通之處[9-10]。
一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提出了所謂“后華盛頓共識(shí)”,修正了“華盛頓共識(shí)”將目標(biāo)當(dāng)作手段的錯(cuò)誤。他們指出,盡管穩(wěn)定通脹和赤字水平很重要,但充分就業(yè)、穩(wěn)定生產(chǎn)和促進(jìn)長(zhǎng)期增長(zhǎng)也應(yīng)作為宏觀調(diào)控的內(nèi)容。在推進(jìn)金融改革方面,重建監(jiān)管體系而非自由化和私有化才是優(yōu)先手段。此外,還應(yīng)鼓勵(lì)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加速技術(shù)轉(zhuǎn)讓?zhuān)苿?dòng)貿(mào)易政策自由化;加強(qiáng)政府能力建設(shè),根據(jù)不同職能進(jìn)行重組和重建。“后華盛頓共識(shí)”的進(jìn)步之處在于認(rèn)為市場(chǎng)的形成需要一個(gè)過(guò)程,市場(chǎng)的發(fā)育需要在“干中學(xué)”。
高盛公司前顧問(wèn)雷默對(duì)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的經(jīng)驗(yàn)作了總結(jié)和提煉。雷默認(rèn)為,中國(guó)極其謹(jǐn)慎地處理私有化和自由貿(mào)易,并積極通過(guò)經(jīng)濟(jì)特區(qū)等大膽實(shí)踐和主動(dòng)創(chuàng)新,按照循序漸進(jìn)原則努力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具體體現(xiàn)在:創(chuàng)造允許實(shí)驗(yàn)和失敗的環(huán)境,實(shí)現(xiàn)本土化以及與其他國(guó)家互利共贏。其中,創(chuàng)新和實(shí)驗(yàn)是靈魂,務(wù)實(shí)靈活,因事而異,不搞“一刀切”。
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效應(yīng)評(píng)估:基于多維度的視角
開(kāi)放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積極作用不僅為理論所證明,而且有廣泛的實(shí)踐支撐。
(一)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效應(yīng)的總體評(píng)價(jià)
對(duì)開(kāi)放效應(yīng)進(jìn)行基于理論模型的量化評(píng)價(jià)有一定難度,基于實(shí)證的效應(yīng)評(píng)價(jià)雖非最優(yōu)選項(xiàng),但也不失為滿(mǎn)意解。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效應(yīng)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第一,促進(jìn)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形成了連續(xù)的帕累托改進(jìn)。得益于1978年打開(kāi)國(guó)門(mén),中國(guó)認(rèn)識(shí)到與世界的差距,堅(jiān)定了學(xué)習(xí)和追趕的決心。在改革開(kāi)放早期,中國(guó)基于資本和技術(shù)稀缺而勞動(dòng)力和自然資源相對(duì)充裕的國(guó)情,走出國(guó)門(mén)開(kāi)拓新的市場(chǎng),引進(jìn)外資和技術(shù)大力發(fā)展加工貿(mào)易③,既解決了就業(yè),引導(dǎo)勞動(dòng)力從農(nóng)業(yè)向工業(yè)轉(zhuǎn)移,又將潛在資源轉(zhuǎn)化為了現(xiàn)實(shí)的生產(chǎn)力和競(jìng)爭(zhēng)力。在擴(kuò)大對(duì)外開(kāi)放過(guò)程中,中國(guó)充分發(fā)揮自身比較優(yōu)勢(shì),積累了大量外匯,加快了資本積累進(jìn)程,使比較優(yōu)勢(shì)不斷向更高層次邁進(jìn)。
第二,帶動(dòng)了體制機(jī)制轉(zhuǎn)型,推動(dòng)了國(guó)內(nèi)效率變革。對(duì)外開(kāi)放不斷激發(fā)對(duì)改革的要求,從貿(mào)易企業(yè)自主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涉外經(jīng)濟(jì)經(jīng)營(yíng)體制的改革,到市場(chǎng)配置資源的相關(guān)體制機(jī)制改革,再到對(duì)外開(kāi)放背景下經(jīng)濟(jì)體制和宏觀運(yùn)行環(huán)境的改革,改革開(kāi)放同步向縱深推進(jìn),帶動(dòng)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不斷提升。微觀經(jīng)營(yíng)體制的放開(kāi)和搞活增強(qiáng)了企業(yè)活力,解決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企業(yè)缺乏自主權(quán)、政企不分、集中過(guò)多和統(tǒng)得過(guò)死等一系列問(wèn)題,逐步推動(dòng)形成了市場(chǎng)引導(dǎo)、盈利驅(qū)動(dòng)的市場(chǎng)化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機(jī)制。在資源配置上,從“引入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市場(chǎng)發(fā)揮主要作用”到“市場(chǎng)起基礎(chǔ)性作用”,再到“市場(chǎng)起決定性作用”,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升。對(duì)外開(kāi)放的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經(jīng)營(yíng)機(jī)制的形成,推動(dòng)政府逐步退出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直接干預(yù),國(guó)家資源配置模式也不斷轉(zhuǎn)變,逐漸建立起基于財(cái)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間接調(diào)控體系,市場(chǎng)機(jī)制進(jìn)一步發(fā)育和完善。不斷擴(kuò)大的市場(chǎng)需求,從產(chǎn)品到要素的市場(chǎng)機(jī)制變革,促進(jìn)了外貿(mào)、物資、財(cái)稅、外匯等方面的持續(xù)改革,以?xún)r(jià)格信號(hào)為核心的市場(chǎng)機(jī)制不斷完善,宏觀調(diào)控體系日趨成熟。
第三,推動(dòng)了技術(shù)變革和產(chǎn)業(yè)升級(jí)。增長(zhǎng)的本質(zhì)是經(jīng)濟(jì)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在技術(shù)進(jìn)步和制度變革帶動(dòng)下不斷升級(jí),進(jìn)而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發(fā)展中國(guó)家受現(xiàn)實(shí)條件約束,無(wú)法投入大量物資和人力資本進(jìn)行研發(fā),即使自主研發(fā)也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且需要較長(zhǎng)周期。對(duì)外開(kāi)放在推動(dòng)資本積累、改善要素稟賦結(jié)構(gòu)、促進(jìn)制度改革、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時(shí),擴(kuò)大了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技術(shù)選擇空間并加速了產(chǎn)業(yè)升級(jí)步伐。發(fā)展中國(guó)家結(jié)合自身優(yōu)勢(shì), 對(duì)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技術(shù)進(jìn)行甄別,選擇適合自身發(fā)展的適宜技術(shù)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創(chuàng)新,加快本國(guó)技術(shù)進(jìn)步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促進(jìn)經(jīng)濟(jì)較快增長(zhǎng),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逐步加大科學(xué)、技術(shù)和教育投入,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技術(shù)來(lái)源和動(dòng)力機(jī)制從外部引進(jìn)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新轉(zhuǎn)化到以自主創(chuàng)新為主。
改革開(kāi)放之初,中國(guó)就高度重視科學(xué)技術(shù),始終強(qiáng)調(diào)“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和科教興國(guó)戰(zhàn)略[11],通過(guò)發(fā)揮低成本勞動(dòng)力優(yōu)勢(shì),結(jié)合此前重工業(yè)發(fā)展帶來(lái)的工業(yè)基礎(chǔ)和系統(tǒng)配套的優(yōu)勢(shì),廣泛引進(jìn)外資和港澳臺(tái)資本,抓住有利時(shí)間窗口承接國(guó)際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發(fā)展加工貿(mào)易,成功嵌入全球價(jià)值鏈。開(kāi)放不僅帶來(lái)了資本,更帶來(lái)了知識(shí)、理念和技術(shù)。在外資企業(yè)與本地產(chǎn)業(yè)競(jìng)爭(zhēng)、合作過(guò)程中,中國(guó)積累了大量人才和技術(shù),國(guó)內(nèi)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理念和能力也得到提升。通過(guò)開(kāi)放實(shí)踐,中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迭代式轉(zhuǎn)型升級(jí),在全球產(chǎn)業(yè)鏈、價(jià)值鏈中所處的地位不斷提升,出口的附加值也持續(xù)增加。
中國(guó)的發(fā)展歷程為評(píng)估開(kāi)放效應(yīng)提供了較好的實(shí)證分析樣板。1978年以來(lái),中國(guó)推進(jìn)改革開(kāi)放,堅(jiān)持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建立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機(jī)制,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積極參與國(guó)際分工和交換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2018年底,中國(guó)GDP總量占全球比重從改革開(kāi)放之初不足2%上升到接近16%,出口總量躍居全球第一(見(jiàn)圖1、圖2,下頁(yè))。
(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效應(yīng)的多維度評(píng)估
1.需求面的評(píng)估
1978年以來(lái),凈出口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貢獻(xiàn)累計(jì)達(dá)到7.3%,尤其是20世紀(jì)90年代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確立后,凈出口直接推動(dòng)GDP年均增長(zhǎng)0.91%(見(jiàn)圖3,下頁(yè))。
然而,從綜合影響效應(yīng)看,這一數(shù)字大幅低估了開(kāi)放的需求效應(yīng)。一方面,忽略了外商直接投資帶來(lái)的新增需求對(du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另一方面未能精確反映出口引發(fā)的乘數(shù)效應(yīng)。中國(guó)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1981年僅為約6億美元,2018年達(dá)到1350億美元,增長(zhǎng)224倍(見(jiàn)圖4,下頁(yè))。陳浪南等的研究表明,20世紀(jì)8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需求面的直接貢獻(xiàn)度每年略低于0.1%,20世紀(jì)90年代每年貢獻(xiàn)達(dá)到0.5%[12]。若考慮出口乘數(shù)效應(yīng),林毅夫等認(rèn)為,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外貿(mào)出口每增長(zhǎng)10%,基本上能夠推動(dòng)GDP增長(zhǎng)1%[13]。由于在20世紀(jì)90年代和2000年后出口年均增長(zhǎng)達(dá)到22%和18%,這意味著出口從需求面對(du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在這兩個(gè)時(shí)間段年均分別達(dá)到2.2%和1.8%。
2.供給面的評(píng)估
開(kāi)放對(duì)供給面也會(huì)產(chǎn)生重要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是加快技術(shù)跨境轉(zhuǎn)移的重要途徑,也與人力資本提升直接相關(guān),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貢獻(xiàn)較為顯著。開(kāi)放和出口導(dǎo)向型增長(zhǎng)進(jìn)一步加速了技術(shù)擴(kuò)散,有助于加快推動(dòng)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升級(jí)。
此外,開(kāi)放推進(jìn)了國(guó)內(nèi)改革,也提升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潛力。一些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1979~2016年的增長(zhǎng)作了分解和核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盡管在2000年前后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對(du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趨勢(shì)有所不同,但剔除勞動(dòng)和資本等要素積累的影響后,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對(du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超過(guò)30%,年均增長(zhǎng)貢獻(xiàn)達(dá)3.0%[14](見(jiàn)圖5,下頁(yè))。根據(jù)對(duì)區(qū)域增長(zhǎng)數(shù)據(jù)的非參數(shù)分解分析,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貢獻(xiàn)大部分是由技術(shù)進(jìn)步推動(dòng)的。若考慮到技術(shù)進(jìn)步的間接效果,如推動(dòng)資本回報(bào)增加、加速資本深化和人力資本積累,開(kāi)放帶來(lái)的技術(shù)進(jìn)步對(du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將更加顯著。
3.產(chǎn)業(yè)和出口結(jié)構(gòu)的視角
中國(guó)比較優(yōu)勢(shì)和出口競(jìng)爭(zhēng)力在開(kāi)放和改革帶動(dòng)下明顯提升。
一方面,出口結(jié)構(gòu)不斷升級(jí)。改革開(kāi)放之初,中國(guó)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的產(chǎn)品以資源、原材料和低技術(shù)產(chǎn)品為主,經(jīng)過(guò)深化改革與擴(kuò)大開(kāi)放,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的產(chǎn)品在各類(lèi)不同技術(shù)含量產(chǎn)業(yè)間的分布更加合理。在出口中占比最高的低技術(shù)產(chǎn)品正逐步被中等技術(shù)甚至高技術(shù)產(chǎn)品所取代,中等技術(shù)工業(yè)制成品成為中國(guó)第一大出口產(chǎn)品類(lèi)別。與此同時(shí),高技術(shù)類(lèi)產(chǎn)品的比重逐步增加[15](見(jiàn)表1,下頁(yè))。根據(jù)Wind數(shù)據(jù),2000~2018年,中國(guó)出口商品中高新技術(shù)商品占比已由15%上升至30%(見(jiàn)圖6,下頁(yè))。盡管近10年來(lái),該比例總體在相對(duì)高位保持穩(wěn)定,但考慮到中國(guó)出口規(guī)模持續(xù)擴(kuò)大,這一比例保持穩(wěn)定本身就表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持續(xù)發(fā)展作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化的一個(gè)新特征已經(jīng)穩(wěn)定下來(lái)。
另一方面,出口不同技術(shù)產(chǎn)品的比較優(yōu)勢(shì)正不斷升級(jí)。顯示性比較優(yōu)勢(shì)指數(shù)是度量比較優(yōu)勢(shì)的關(guān)鍵指標(biāo),是指某種商品在一國(guó)出口中的份額與其在世界出口中份額的比率。一些學(xué)者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在低技術(shù)制造業(yè)顯示性比較優(yōu)勢(shì)不斷下降[16],而在高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產(chǎn)品顯示性比較優(yōu)勢(shì)不斷上升(見(jiàn)圖7,下頁(yè))。作為制造業(yè)子行業(yè),機(jī)電產(chǎn)品和交通設(shè)備等技術(shù)含量相對(duì)較高,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比較優(yōu)勢(shì)快速上升(見(jiàn)表2,下頁(yè))。
出口復(fù)雜度和相似度從另一個(gè)角度度量了開(kāi)放對(duì)出口競(jìng)爭(zhēng)力的影響。出口復(fù)雜度計(jì)算方法是對(duì)其所有出口產(chǎn)品求加權(quán)平均。一般而言,高收入水平國(guó)家出口總體復(fù)雜度較高,而低收入水平國(guó)家出口較多的產(chǎn)品總體復(fù)雜度較低。出口復(fù)雜度分為三個(gè)層面,即國(guó)家、行業(yè)和具體產(chǎn)品的出口復(fù)雜度。國(guó)家層面的該指標(biāo)主要反映了一國(guó)出口商品中所含的要素稟賦以及產(chǎn)品構(gòu)成等。行業(yè)層面的該指標(biāo)度量同一行業(yè)的技術(shù)層次以及在跨國(guó)產(chǎn)業(yè)鏈中的地位。從國(guó)家層面看,中國(guó)的出口復(fù)雜度明顯高于同發(fā)展階段和類(lèi)似收入水平的其他國(guó)家。徐斌利用中國(guó)在世界貿(mào)易尺度下的出口復(fù)雜度來(lái)度量出口升級(jí),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相對(duì)出口復(fù)雜度呈快速上升趨勢(shì)[17](見(jiàn)圖8,下頁(yè))。出口復(fù)雜度的升級(jí)與開(kāi)放高度相關(guān),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出口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的推動(dòng)力亦表現(xiàn)強(qiáng)勁。在出口復(fù)雜度提升的同時(shí),中國(guó)與主要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出口相似度增強(qiáng),工業(yè)品與美國(guó)的出口相似度上升至約0.4[18](見(jiàn)圖9,下頁(yè))。更細(xì)顆粒度的比較發(fā)現(xiàn),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技術(shù)含量較高的部門(mén)如機(jī)電和電子產(chǎn)品等行業(yè)的分工從以前的產(chǎn)業(yè)間分工逐步向產(chǎn)業(yè)內(nèi)分工形態(tài)轉(zhuǎn)變,在采掘、紡織尤其是服裝制造業(yè)等技術(shù)含量低的行業(yè),中國(guó)的專(zhuān)業(yè)化能力明顯增強(qiáng)[19]。
4.價(jià)值鏈的視角
在貿(mào)易規(guī)模快速增長(zhǎng)的同時(shí),也不乏對(duì)中國(guó)出口代工較多、國(guó)內(nèi)價(jià)值增值有限的擔(dān)憂。根據(jù)商務(wù)部的統(tǒng)計(jì)和分析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以總出口還是以增加值核算,出口對(duì)GDP的重要性盡管略有下降,但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影響仍占據(jù)重要地位(見(jiàn)圖10、圖11,下頁(yè))。2010年,中國(guó)出口總值為1.75萬(wàn)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28.9%;2018年,出口總值增長(zhǎng)到2.48萬(wàn)億美元,但占GDP的比重下降至18.2%。2010年出口增加值為1.1萬(wàn)億美元,相當(dāng)于當(dāng)年GDP的18.2%;2018年增長(zhǎng)到1.9萬(wàn)億美元,占當(dāng)年GDP的比重下降至14.2%。特別是近年來(lái)加工貿(mào)易在總出口中比重逐步下降,反映勞動(dòng)力等要素成本優(yōu)勢(shì)下降,一般貿(mào)易的競(jìng)爭(zhēng)力和比較優(yōu)勢(shì)逐步上升。
從價(jià)值鏈的視角更有助于分析中國(guó)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變化,觀察價(jià)值鏈變化對(duì)全球和中國(guó)投入產(chǎn)出表的分析亦十分必要。在考慮加工貿(mào)易影響后,庫(kù)珀曼等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出口的國(guó)內(nèi)增加值不斷上升,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的貢獻(xiàn)逐年增加,生產(chǎn)活動(dòng)正逐步向全球價(jià)值鏈高端攀升[20]。盡管加工貿(mào)易所占比例降低,但中間產(chǎn)品在世界市場(chǎng)的份額不斷增大,加工貿(mào)易的附加值不斷上升,在全球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中的地位也不斷上升(見(jiàn)表3)。
從不同行業(yè)在全球價(jià)值鏈的相對(duì)變化,可以清晰觀察到開(kāi)放帶動(dòng)中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斷升級(jí),企業(yè)在全球生產(chǎn)鏈和價(jià)值鏈的地位也明顯上升[21](見(jiàn)表4)。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中國(guó)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的貢獻(xiàn)逐年增加,在價(jià)值鏈中的地位不斷邁向高端,尤其是制造業(yè)和服務(wù)業(yè)中知識(shí)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貿(mào)易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第二,初級(jí)產(chǎn)品出口增加值降低,表明初級(jí)品出口國(guó)內(nèi)增值部分的占比減少。第三,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品出口的國(guó)內(nèi)增加值占比下降,表明從價(jià)值鏈角度來(lái)看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比較優(yōu)勢(shì)減弱。第四,中國(guó)服務(wù)業(yè)出口的國(guó)內(nèi)增加值比重不斷增加,服務(wù)業(yè)整體比較優(yōu)勢(shì)和競(jìng)爭(zhēng)力逐步提升。
5.區(qū)域演進(jìn)的視角
中國(guó)對(duì)外開(kāi)放在區(qū)域上呈現(xiàn)明顯的漸進(jìn)性。沿海地區(qū)首先啟動(dòng)對(duì)外開(kāi)放,此后開(kāi)放逐步從沿海向沿江、沿邊和內(nèi)陸拓展。通過(guò)設(shè)立出口加工區(qū)、高新技術(shù)開(kāi)發(fā)區(qū)、保稅區(qū)、自由貿(mào)易試驗(yàn)區(qū)等一系列經(jīng)濟(jì)功能區(qū),開(kāi)放區(qū)域和開(kāi)放形式上不斷深化。
研究表明,對(duì)外開(kāi)放的先后、開(kāi)放的形式和內(nèi)容都對(duì)一個(gè)區(qū)域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李言、高波、雷紅的研究表明,東部沿海地區(qū)由于開(kāi)放較早,技術(shù)水平提升快,經(jīng)濟(jì)中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明顯較高[22]。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規(guī)模和開(kāi)放程度高度相關(guān)[23-24]。不同開(kāi)放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功能區(qū)在人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上呈現(xiàn)明顯差異,開(kāi)放越早,開(kāi)放程度越高,經(jīng)濟(jì)積聚效應(yīng)越強(qiáng),技術(shù)水平越高。
三、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路徑選擇與啟示
開(kāi)放對(duì)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作用已經(jīng)為理論和實(shí)踐所證明,但開(kāi)放并非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充分條件,更不是有利無(wú)弊。對(duì)外開(kāi)放路徑選擇不同,對(duì)一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發(fā)揮的作用也不同。
(一)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差異化路徑
從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歷史經(jīng)驗(yàn)看,對(duì)外開(kāi)放主要有三種方式: 一是國(guó)際貿(mào)易往來(lái),二是從國(guó)際金融市場(chǎng)融資,三是獲得國(guó)際直接投資。單純依賴(lài)敞開(kāi)國(guó)門(mén)發(fā)展對(duì)外貿(mào)易并非最優(yōu)的開(kāi)放路徑。受資源稟賦等限制,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初期只能以出口附加值較低的初級(jí)產(chǎn)品參與國(guó)際貿(mào)易往來(lái),進(jìn)口機(jī)械設(shè)備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yè)制成品。若無(wú)法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或產(chǎn)業(yè)升級(jí),陷入“資源詛咒”或低水平陷阱的概率較大,或淪為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的原材料附庸,或由于貿(mào)易條件惡化、國(guó)際收支失衡和資本流向逆轉(zhuǎn)引發(fā)金融動(dòng)蕩或危機(jī)。而依賴(lài)外債融資的第二條路徑,風(fēng)險(xiǎn)同樣不可忽視。由于對(duì)外舉債主要以外幣計(jì)價(jià),隨著外債負(fù)擔(dān)增加,一旦匯率波動(dòng)或外部流動(dòng)性趨緊,本國(guó)將由于償債壓力增大而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引發(fā)“債務(wù)陷阱”或債務(wù)危機(jī)。如拉美債務(wù)危機(jī)、亞洲金融危機(jī)等就是由于開(kāi)放路徑和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不當(dāng)所致,試圖超出自身能力和發(fā)展階段,大量舉借外債的開(kāi)放實(shí)驗(yàn)普遍不成功。如2015年美聯(lián)儲(chǔ)開(kāi)始加息并引發(fā)美元大幅升值,出現(xiàn)資本大量外流,一些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還債壓力急劇增加,陷入外匯或美元流動(dòng)性危機(jī),進(jìn)而引爆債務(wù)危機(jī)。
中國(guó)對(duì)外開(kāi)放在充分吸收國(guó)際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并結(jié)合自身國(guó)情的基礎(chǔ)上,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發(fā)展道路。
一是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shí)俱進(jìn)、求真務(wù)實(shí)。充分借鑒別國(guó)的開(kāi)放實(shí)踐和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尤其一些國(guó)家因?yàn)殚_(kāi)放路徑選擇不當(dāng)而出現(xiàn)危機(jī)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不唯書(shū),不把目標(biāo)當(dāng)作路徑,避免一蹴而就的開(kāi)放“急躁癥”。
二是走漸進(jìn)式道路。從開(kāi)放進(jìn)程來(lái)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引入外來(lái)壓力,優(yōu)先擴(kuò)大制造業(yè)對(duì)外開(kāi)放形成發(fā)展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推動(dòng)對(duì)外貿(mào)易部門(mén)等外向型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逐步從鼓勵(lì)“引進(jìn)來(lái)”為主到“引進(jìn)來(lái)”和“走出去”相結(jié)合,從鼓勵(lì)出口為主到出口和進(jìn)口并重,從鼓勵(lì)傳統(tǒng)制造業(yè)出口為主到推動(dòng)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出口。從市場(chǎng)開(kāi)放來(lái)看,根據(jù)可貿(mào)易程度由簡(jiǎn)單到復(fù)雜,從制造業(yè)漸次拓展到服務(wù)業(yè),從消費(fèi)品漸次拓展至生產(chǎn)資料等資本品市場(chǎng)。在加大實(shí)體部門(mén)對(duì)外開(kāi)放基礎(chǔ)上,結(jié)合支持和服務(wù)實(shí)體部門(mén)需求,有步驟開(kāi)放國(guó)內(nèi)金融及資本市場(chǎng)。從產(chǎn)業(yè)來(lái)看,結(jié)合發(fā)展階段和競(jìng)爭(zhēng)狀況,對(duì)各行業(yè)采取有差別的過(guò)渡期和開(kāi)放節(jié)奏,有序降低關(guān)稅等相關(guān)貿(mào)易壁壘,鼓勵(lì)競(jìng)爭(zhēng)。從地域來(lái)看,對(duì)外開(kāi)放實(shí)現(xiàn)梯次有序推進(jìn)。
三是處理好開(kāi)放、改革和穩(wěn)定之間的關(guān)系。漸進(jìn)式開(kāi)放能取得成功的關(guān)鍵在于在開(kāi)放取得增量效應(yīng)的前提下積蓄進(jìn)一步開(kāi)放的動(dòng)力,在配套改革取得效果的前提下創(chuàng)造進(jìn)一步開(kāi)放的條件,從而實(shí)現(xiàn)開(kāi)放、改革和穩(wěn)定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漸進(jìn)式開(kāi)放本身也有助于平穩(wěn)過(guò)渡,先試驗(yàn)再推廣是開(kāi)放穩(wěn)定可控的重要模式。中國(guó)早期的經(jīng)濟(jì)特區(qū)就是在缺乏參照的情況下對(duì)外開(kāi)放的重點(diǎn)突破,有助于控制風(fēng)險(xiǎn)、達(dá)成共識(shí)。此后的國(guó)家級(jí)開(kāi)發(fā)區(qū)、海關(guān)特殊監(jiān)管區(qū)域和邊境經(jīng)濟(jì)合作區(qū),以及自由貿(mào)易試驗(yàn)區(qū)和自由貿(mào)易港都是在開(kāi)放不同階段進(jìn)行政策試驗(yàn)和復(fù)制推廣的平臺(tái)和載體。這些特殊政策區(qū)域有助于充分發(fā)揮地方的主觀能動(dòng)性,避免政策“一刀切”帶來(lái)的風(fēng)險(xiǎn),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從而在獲得可復(fù)制的良好經(jīng)驗(yàn)后快速推廣至全國(guó),顯著放大對(duì)外開(kāi)放的正面效應(yīng)。
(二)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kāi)放的啟示
經(jīng)濟(jì)開(kāi)放特別是大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開(kāi)放能有效增進(jìn)經(jīng)濟(jì)效率和社會(huì)福利,促進(jìn)國(guó)際貿(mào)易和國(guó)家間經(jīng)濟(jì)往來(lái),推動(dòng)全球化在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盛行之際繼續(xù)發(fā)展。從國(guó)際發(fā)展視野看,封閉不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現(xiàn)代化的備選項(xiàng),開(kāi)放才是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邁向發(fā)達(dá)國(guó)家行列的唯一途徑。拉美國(guó)家陷入債務(wù)困境,部分東亞國(guó)家面臨權(quán)貴資本主義困擾,這些開(kāi)放的教訓(xùn)并不是開(kāi)放效應(yīng)的反證,反而凸顯開(kāi)放路徑和模式選擇的重要性。
如果沒(méi)有選擇適合自身發(fā)展的道路和有效模式,開(kāi)放風(fēng)險(xiǎn)可能大于收益。拉美國(guó)家的教訓(xùn)是路徑錯(cuò)誤,即在開(kāi)放環(huán)境中扭曲國(guó)內(nèi)要素環(huán)境,通過(guò)外債推動(dòng)進(jìn)口替代戰(zhàn)略,導(dǎo)致陷入債務(wù)困境。部分亞洲新興國(guó)家的教訓(xùn)則是超越階段,在制造業(yè)開(kāi)放取得成功而匯率未實(shí)現(xiàn)完全市場(chǎng)化之前,過(guò)早開(kāi)放資本市場(chǎng)和資本賬戶(hù),導(dǎo)致在外部流動(dòng)性劇變背景下國(guó)內(nèi)發(fā)生金融危機(jī),致使經(jīng)濟(jì)陷入困境。
中國(guó)的開(kāi)放與改革并行,漸進(jìn)式開(kāi)放是主基調(diào),開(kāi)放模式和路徑選擇應(yīng)兼顧經(jīng)濟(jì)全球化要求、自身國(guó)情和要素稟賦。中國(guó)的開(kāi)放經(jīng)驗(yàn)表明,經(jīng)濟(jì)開(kāi)放的路徑無(wú)定式,需要依據(jù)自身的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自然條件,選擇適合自身特點(diǎn)的道路。其要點(diǎn)包括:一是始終堅(jiān)持漸進(jìn)開(kāi)放,把握好改革和開(kāi)放之間的關(guān)系和良性互動(dòng),通過(guò)開(kāi)放促進(jìn)市場(chǎng)化改革,通過(guò)改革配套為進(jìn)一步開(kāi)放創(chuàng)造條件,使開(kāi)放實(shí)現(xiàn)波浪式前進(jìn)。二是先試點(diǎn)再推廣的開(kāi)放邏輯具有實(shí)踐方面的可操作性,能較好地平衡開(kāi)放、改革和穩(wěn)定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控制風(fēng)險(xiǎn),放大效益。三是在具體路徑上,按照優(yōu)先開(kāi)放制造業(yè)走出口導(dǎo)向型模式,然后開(kāi)放服務(wù)業(yè),先開(kāi)放經(jīng)常賬戶(hù)為出口導(dǎo)向模式創(chuàng)造條件,再開(kāi)放資本賬戶(hù)為服務(wù)業(yè)開(kāi)放奠定基礎(chǔ)。四是將人民幣國(guó)際化進(jìn)程與經(jīng)濟(jì)開(kāi)放相互配合。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開(kāi)放在金融體系市場(chǎng)化之前,實(shí)體經(jīng)濟(jì)開(kāi)放和金融市場(chǎng)開(kāi)放在人民幣自由兌換之前,資本項(xiàng)目開(kāi)放在實(shí)行浮動(dòng)匯率制之后,人民幣儲(chǔ)備貨幣職能在貿(mào)易貨幣職能和投資貨幣職能之后。
展望未來(lái),我們必須看到,在中國(guó)這樣一個(gè)大型經(jīng)濟(jì)體融入全球產(chǎn)業(yè)鏈的過(guò)程中,漸進(jìn)式改革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面對(duì)和應(yīng)對(duì)以下兩方面的問(wèn)題:一是隨著經(jīng)濟(jì)體量的增長(zhǎng)和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躍遷,中國(guó)需要由國(guó)際規(guī)則的適應(yīng)者、接受者逐步轉(zhuǎn)變?yōu)閲?guó)際規(guī)則的參與者和建設(shè)者[25]。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中國(guó)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就是這一轉(zhuǎn)變的很好嘗試,未來(lái)中國(guó)需要在國(guó)際規(guī)則研究和制定方面做好充分的知識(shí)積累和人才儲(chǔ)備。二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在融入全球產(chǎn)業(yè)鏈分工的過(guò)程中,必然由高速增長(zhǎng)逐步轉(zhuǎn)變?yōu)楦哔|(zhì)量發(fā)展。這一新的發(fā)展階段對(duì)經(jīng)濟(jì)體系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制度安排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如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jì)和系統(tǒng)性安排,勇于涉足改革開(kāi)放的深水區(qū)等。
未來(lái)關(guān)鍵領(lǐng)域的改革措施包括:一是進(jìn)一步深化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在非關(guān)鍵領(lǐng)域?qū)崿F(xiàn)由管企業(yè)向管資本的過(guò)渡;二是促進(jìn)各種所有制企業(yè)活力的爭(zhēng)相迸發(fā),促進(jìn)對(duì)內(nèi)、對(duì)外雙向開(kāi)放;三是有效厘定政府與市場(chǎng)、社會(huì)的邊界,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機(jī)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shí)現(xiàn)政府的“歸位”且不越位;四是有效推進(jìn)法治和財(cái)稅改革等,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這些領(lǐng)域的改革彼此相關(guān),需要有頂層設(shè)計(jì)的智慧和篤定前行的勇氣。
參考文獻(xiàn)
[1]亞當(dāng)·斯密.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72.
[2]大衛(wèi)·李嘉圖.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及賦稅原理[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62.
[3]伯爾蒂爾·俄林.地區(qū)間貿(mào)易和國(guó)際貿(mào)易[M].王繼祖,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6.
[4]賈根良,沈梓鑫.普雷維什—辛格新假說(shuō)與新李斯特主義的政策建議[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4):46-54.
[5]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J].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1962, 7(1): 1-43.
[6]JOHN WILLIAMSON. 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J]. World Development, 1993, 21(8): 1329-1336.
[7]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duì)資本和金融市場(chǎng)的自由化要謹(jǐn)慎[R].(2014-03-23).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403/23/t2014
0323_2534006.shtml.
[8]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6, 14(5): 1-19.
[9]JAGDISH N. BHAGWATI, ANNE OSBORN KRUEGER. Exchange contro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419-427.
[10]羅納德·I.麥金農(nóng).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化的次序[M].周庭煜,尹翔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陳勁,王璐瑤.新時(shí)代中國(guó)科教興國(guó)戰(zhàn)略論綱[J].改革,2019(6):32-40.
[12]陳浪南,陳景煌. 外商直接投資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影響的經(jīng)驗(yàn)研究[J].世界經(jīng)濟(jì),2002(6):20-26.
[13]林毅夫,李永軍.出口與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需求導(dǎo)向的分析[J].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03(4):779-794.
[14]楊志云,陳再齊.要素生產(chǎn)率、資本深化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基于1979~2016年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核算[J].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18(5):41-51.
[15]王聰.我國(guó)出口產(chǎn)品比較優(yōu)勢(shì)及貿(mào)易結(jié)構(gòu)分析——基于附加值統(tǒng)計(jì)口徑[J].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評(píng)論,2017(3):46-60.
[16]孫玉琴,郭惠君.中日制造業(yè)出口技術(shù)結(jié)構(gòu):衡量與比較[J].國(guó)際經(jīng)濟(jì)合作,2018(3):20-24.
[17]XU BIN. T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Is China special?[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21(3): 482-493.
[18]丁小義,胡雙丹.基于國(guó)內(nèi)增值的中國(guó)出口復(fù)雜度測(cè)度分析——兼論“Rodrik悖論”[J].國(guó)際貿(mào)易問(wèn)題,2013(4):40-50.
[19]黃永明,張文潔.出口復(fù)雜度的國(guó)外研究進(jìn)展[J].國(guó)際貿(mào)易問(wèn)題,2012(3):167-176.
[20]ROBERT KOOPMAN, ZHI WANG, SHANG-JIN WEI.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178-189.
[21]樊茂清,黃薇.基于全球價(jià)值鏈分解的中國(guó)貿(mào)易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演進(jìn)研究[J].世界經(jīng)濟(jì),2014(2):50-70.
[22]李言,高波,雷紅.中國(guó)地區(qū)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遷:1978~2016[J].數(shù)量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2018(10):21-39.
[23]任思雨,吳海濤,冉啟英.對(duì)外直接投資、制度環(huán)境與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基于廣義分位數(shù)與動(dòng)態(tài)門(mén)限面板模型的實(shí)證研究[J].國(guó)際商務(wù)(對(duì)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3): 83-96.
[24]劉敏,黃亮雄,黃翔.全要素生產(chǎn)率、融資約束與企業(yè)對(duì)外直接投資[J].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2):31-41.
[25]陳偉光,王燕.全球經(jīng)濟(jì)治理中制度性話語(yǔ)權(quán)的中國(guó)策[J].改革,2016(7):25-37.
Abstract: Opening-up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Only by choosing an open road that conforms to its own reality, can we achieve good results. China’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choose gradual opening-up and follow the path of opening-up, which is first pilot and then promotion,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it. Next, China should gradually change from the adapter and acceptor of international rules to the participant and builder of international rules,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dare to step into the deep-water are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 words: opening-u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eign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