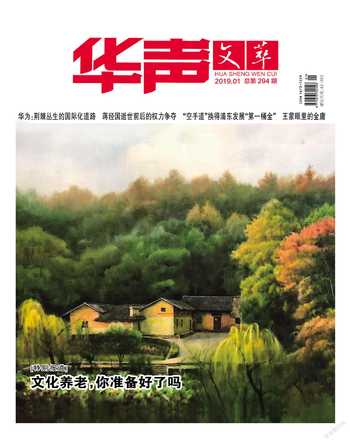老年“學霸”的開掛人生
老年人只會在路邊下象棋、打麻將?老年人落伍、跟不上時代?這也許是你對老年人的誤解。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學習熱情。他們不僅會用電腦軟件制作電子相冊,還會制作H5,也有人可以閱讀英語原版《哈姆雷特》。很多老人已經在老年大學“寒窗苦讀”十多年,依然每天堅持去聽課。學完一門課程畢業后又重新報名,繼續學習或換門課程再學。有人拿了3本結業證書,卻依然不想畢業。
老人們學習如此全情投入,是因為年輕時錯過了太多大好光陰,現在想圓自己的大學夢,“活到老,學到老。”
2018年2月,天津大學衛津路校區,一場普通的畢業典禮備受關注。
滿頭白發,面容清癯,當81歲的薛敏修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言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過去四年,這位高齡學生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努力,完成了所有專升本課程,終于順利拿到天津大學現代遠程教育的本科畢業證書,實現了自己追逐半個多世紀的大學夢。
“別叫我奶奶,叫同學。”這是已到耄耋之年的薛敏修經常跟她的老師和同學強調的。
4年前,當薛敏修走進天津大學網絡教育學院院本部報名處時,所有人都以為她是來替忙碌的孫輩報名的。“奶奶,您……”沒等工作人員把話說完,薛敏修就認真地糾正道:“別叫我奶奶,我來這兒是學習的,請叫我薛敏修同學。”
4年后,薛敏修同學畢業了。在畢業典禮上,她作為畢業生代表上臺發言:“有的人會想,像我這個年紀的老人更適合在家里種花養草,度過安逸的晚年時光。但我不甘于這樣的生活,我覺得生命的意義就在于不斷挑戰自己、完善自己,所以我要感謝天津大學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把年少時未完成的夢想變成現實。”
上大學,是薛敏修追逐了半個多世紀的夢想。她曾三次參加高考,卻因各種原因與大學失之交臂——
薛敏修1936年12月出生在天津,后考上鐵道部哈爾濱衛生學校藥劑學專業(中專),畢業后分配到位于西安的鐵道部臨潼療養院工作。
1957年,已參加工作的薛敏修參加了高考,并被西北大學錄取。然而由于一些原因,她沒能如愿入學。1959年,她第二次參加高考,因一些變故,仍沒能被錄取。
不過,薛敏修并未因此放棄學習。她曾負責藥品管理,所有的進口藥品說明書通用語言都是英語,而她中學時學的是俄語,讀衛校時學的是俄語和拉丁語,此前從沒接觸過英語,“我只能拿英文名稱對照拉丁文,把分子式結構查清,再給醫務部門下通知,這是什么藥、怎么用,這就逼著我去學英語。”
薛敏修說,當時學英語很困難,“我每天早上5點起床,廣播里有一個臺專門教英語,我就跟著學。”后來,她又專門去英語培訓班學習,并參加了老年大學的法語課程,“英語和法語有一定相通之處,我也是想借法語來理解英語。”
2001年,教育部公布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新舉措,取消了考生“未婚、年齡不超過25歲”的限制,埋藏在薛敏修心中多年的大學夢再次復蘇。2013年,薛敏修報名參加了當年的高考。不過,她的成績不理想,沒有達到本科錄取線。
當時,薛敏修已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讀完了電子商務專業大專課程。她不甘于此,仍希望繼續讀本科。2014年,薛敏修報考天津大學網絡教育學院電子商務專業(專升本)并被錄取,夢想終于照進現實。
在過去4年里,薛敏修共學了18門課程,包括大學英語、計算機應用基礎、應用統計學、網絡營銷學和電子商務系統分析與設計等。由于學習努力,她還獲得了2014-2015年度天津大學“現代遠程教育學習之星”稱號。
過去4年里,薛敏修每天早上5點起床后,都要先打開電腦學習一會兒,再去洗漱、吃早點。每天除了吃飯和鍛煉,其他時間都花在鉆研學習上。甚至因為害怕看電視劇浪費時間,家里的電視已經4年不開機了。“反正我一有時間就學習,吃飯都去外面隨便吃點,生活上除了洗點衣服就沒有別的事,我的任務就是學習,跟學生時期差不多。”薛敏修說。
因為網絡學習的特點,平時作業可以通過“刷題”的方式得到好成績,薛敏修基本是不刷到滿分不罷休,有一次為了做對一道題,她甚至刷了70多次考題。
盡管學習認真、執著,但薛敏修在學習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她說,第一次上高等數學課時,剛開始還能聽懂一點,“后來公式一變化我就聽不懂了,我回家就把高中課本翻出來學,甚至有時還要把初中數學拿出來看。”第一學期下來,薛敏修5門功課就有2門不及格,她對此很坦誠,“考不過就補考唄,反正我不帶小條 ,我可不做違紀的事。”
盡管已從天津大學畢業,但薛敏修并不打算停止學習的腳步。她笑言:“一旦停止學習,大腦就衰退得非常快。如果我現在徹底不學了,那么一年后你再見我,我恐怕一句‘你好’的英語都不會說了,甚至還有可能老年癡呆呢。我可不敢這樣試,學習必須堅持。我覺得,人不能重在享受,一定要多學習多用腦。”
今年69歲的吳莉莉穿著一件紅色上衣,戴著墨鏡,十分時尚,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她的生活方式十分新潮。除了經常到國外旅游,她還會用“會聲會影”自己制作視頻相冊、制作H5,還會用PS、美圖秀秀進行圖片加工。“我主要是心態好,所以看起來年輕,腹有詩書氣自華嘛。”吳莉莉笑著說。
如今,每周一三五到廣州市老干部大學上課,成了她退休生活最大的精神寄托。
吳莉莉的老家在上海,家境殷實,是家中的長女。上世紀60年代,隨著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吳莉莉被分配到江西尋烏的大山中干農活,也錯過了自己的“大學夢”。上世紀80年代她來到廣州,進入廣東省百貨公司上班。
“我從小就喜愛詩詞和文學,初中時讀的是上海的知名初中,即便沒有上大學,后來參加工作,在單位干的也是筆桿子的工作,幫忙寫財務報表,寫總結報告。”但沒能上成大學,一直是吳莉莉的心結,揮之不去。“我有時路過大學校園,看到年輕的大學生穿著漂亮的裙子,背著書包,夾著書本在校園里走過,真的好羨慕他們。”
于是,2004年,退休后的第二天,她便來到位于中山七路的廣州嶺海老年大學。當時她想報考古詩詞專業,結果名額滿了,她便“厚著臉皮”跑去蹭聽古詩詞課程。剛好一位老學員去了香港,吳莉莉便頂了她的位置。沒想到,才聽了幾堂課,她就迷上了古詩詞,從此一發不可收拾。2008年,當教授古詩詞的那位名教授去世后,吳莉莉又來到位于下塘西路的廣州市老干部大學,繼續學習古詩詞。
“我上老年大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拿學位,而純粹是興趣。更重要的是圓夢,把我過去曾經錯過的大學夢圓了。”吳莉莉說,女兒和老伴都非常支持她上老年大學。為此,老伴還主動承擔起了接送孫子和給全家做午飯的任務。
吳莉莉對上課甘之如飴,不管天晴下雨,風雨寒暑,她從不缺課,也從不遲到。從她居住的江灣路小區到老干部大學需要40多分鐘的車程,還要換乘一次公交車,但她依然樂此不疲。
吳莉莉經常在朋友圈曬出她參加各種詩詞學會的學術研討活動,以及京劇賞析會的現場活動照片,這讓小區的老人們都羨慕不已。“我覺得這比曬在外地旅游的照片高了一個檔次。”她笑著說。她的手機中還珍藏著一張2012年與京劇大師梅葆玖的合照,原來,她和梅葆玖是上海一所中學的校友。每當她把這張照片給同齡的老人展示時,總能引來羨慕的目光。
14年“寒窗”,吳莉莉也有了滿滿的收獲,她先后學習了近10個專業的課程,包括聲樂、舞蹈、電腦制作、攝影、樂器、書法等,先后拿了3本結業證書。在她書房的紙箱里,堆滿了各種榮譽證書。
吳莉莉說,每次到老年大學,和年齡相仿的同伴在一起交流,尤其是和詩詞方面的專家教授討論詩歌創作心得,這讓她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并沒有被這個社會淘汰,依舊和這個社會的脈搏一起躍動。“現在是一個信息時代,很多人覺得老年僵化、封閉、跟不上時代,但我想告訴大家,廣州的老人不是這樣的,他們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也很愿意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古詩詞非常講究韻律,要講究押韻,所以,我每創作一首古詩詞,都要反復修改好多次。”吳莉莉邊說邊到書房翻出自己的詩集。其中一首《途經從化流溪河畔》寫道:清涼鳥道盤山嶺,滴翠流溪入眼中,雖是岸梅香雪掃,飛泉百丈例稱雄。
自從迷上寫古體詩之后,吳莉莉更是“啃”起了古典詩詞的“大部頭”。廣州圖書館如今可以一次性借閱15本書,她經常去借回很多“大部頭”,看書看到深夜。“有時候已經躺下了,腦中閃過一個句子或一個詞,又起身亮燈,拿筆記下,生怕第二天忘了。”
至今,她還保留著一個習慣,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子,凡是想起好的詞句,都會第一時間記在小本子上。雖然是業余寫詩,但吳莉莉對自己的詩歌要求很高,頗有“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執著,有時,為了一句好詩的下半句,她愁眉苦臉,茶飯不思,把自己關在書房幾個小時。甚至有時連一旁的丈夫都有些“看不過去”了,勸她說:“你又不是專業詩人,有必要這么較勁嗎?”而當她突然想出一個妙句,則又喜不自勝。
吳莉莉還經常參加全國各地的老年社團組織的詩詞創作活動。迄今為止,她先后寫出古詩詞上千篇,廣州和國家級的不少期刊、報紙上都有刊載她的“大作”。吳莉莉準備出一本詩集,將自己這十多年來從事古詩詞創作的詩歌都收集在一起。
“古詩詞讓我變得年輕”,吳莉莉說。
除了薛敏修、吳莉莉,還有很多老人一樣又酷又認真——阿里40萬年薪招聘60歲以上老人做淘寶調研員,3000名大爺大媽投了簡歷,最后阿里選出了10位進行初選,而這10位初選者的簡歷非常亮眼。
62歲的黃爺爺,人稱“IT小鮮肉”,能夠熟練運用PS、office辦公軟件,還會運營微信公眾號,制作H5手機動畫。最厲害的是,他還組織了多次老年防騙課堂。
83歲的李路奶奶,清華大學畢業,退休后開始學電腦,三四年前開始使用智能手機,有6年網購經歷,是十幾個微信群群主;她會五門語言、會制作表格、會用Photoshop處理照片;目前還在不斷學習比特幣、區塊鏈、機器人等新鮮事物。
而在青島老年生活大學文學研修班里,不少老人受益匪淺,華麗蛻變實現了“文學夢”。學員史在新四十多萬字的《醫者筆耕錄》可與專業作家比肩;僅上了五年小學的學員王芝云的《過年》《纏足》等作品登上《工人日報》等國家主流媒體;年近九旬的學員張迪勛的三部小說傳記《我趟過的歲月》《老嫂》《老伴》每部小說都有20多萬字;學員陳琦的《夢溪詩詞》30萬字;學員趙玉珍的 《我的四個家庭》20多萬字,均由正規出版社出版。
人們常常會以年齡節點,來定義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間,卻被年齡的框架所限制,暗暗“殺死”了自己的夢想。其實,這已經是一個越來越“無齡感”的時代。在偏見里,人到老年,一定是無所事事的、跟不上時代的,可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告訴我們,那些敢于對抗“年齡偏見”的人,有多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