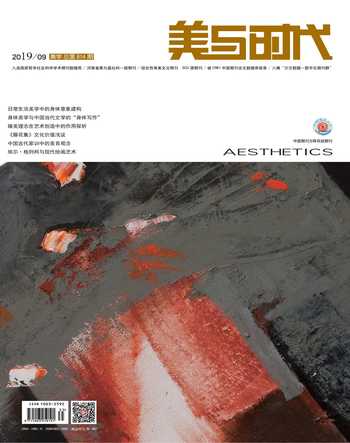論《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傾向
摘? 要:19世紀(jì)中葉,達(dá)爾文創(chuàng)立了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這一理論發(fā)展為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在上部《清晨》中建立了一個(gè)遠(yuǎn)離現(xiàn)代文明的化外世界,在現(xiàn)代文明對應(yīng)下的鄂倫溫克人和諧自足的生活構(gòu)成了對于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一種無聲的反抗;在下部《黃昏》及尾聲《半個(gè)月亮》中處處顯露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至今自身所顯露出來的種種焦慮感,瓦解了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中部《正午》中顯示了作者對于傳統(tǒng)現(xiàn)代共融的美好構(gòu)想,表達(dá)了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huì),我們應(yīng)推崇的應(yīng)該是一種更加多樣和包容的世界觀,而非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指向的無休止的爭斗。
關(guān)鍵詞:《額爾古納河右岸》;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現(xiàn)代焦慮;自然回歸
文藝復(fù)興之后,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理性思維逐漸確立,達(dá)爾文于此時(shí)提出優(yōu)勝劣汰、自然選擇的進(jìn)化論。該理論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逐漸演變?yōu)樯鐣?huì)達(dá)爾文主義,即將整個(gè)社會(huì)看作叢林,遵循叢林法則運(yùn)轉(zhuǎn),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遲子建依據(jù)自己的生活閱歷和生命體驗(yàn)創(chuàng)作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流露出對浪漫自然詩意生活狀態(tài)的向往,對原始的生命強(qiáng)力的崇拜以及對人性中體現(xiàn)的巨大溫暖包容的肯定,構(gòu)成了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無聲的反抗。文本還表達(dá)了對鄂溫克人在現(xiàn)代文明入侵下萬般無奈地求生存過程中的悲痛,對現(xiàn)代文明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的忽略深深的遺憾,透露出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推崇的現(xiàn)代文明的弊端正在逐漸瓦解自身。而在中部則表達(dá)了對于現(xiàn)代文明和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而構(gòu)成的和諧共生局面的向往,這實(shí)際上也是對于人類文明向前發(fā)展的美好構(gòu)想,對于宣揚(yáng)優(yōu)勝劣汰的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強(qiáng)烈的質(zhì)疑。
一、清晨——化外世界建立構(gòu)成
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的無聲反抗
對于一件事物的反抗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激烈的咆哮,一種是無聲的反抗。前者看似更具爆發(fā)力和沖擊力,實(shí)際上也更容易淪為一種話語的發(fā)泄;后者看似表面風(fēng)平浪靜、脆弱無力,實(shí)則在經(jīng)過對事物和局勢認(rèn)真的分析之后,更能洞悉事物本質(zhì),最終實(shí)現(xiàn)真正的反抗。在《清晨》一章中作者集中表現(xiàn)了鄂溫克人的生活方式、習(xí)俗傳統(tǒng)、人情倫理等各個(gè)方面,以一種冷靜客觀的視角審視這個(gè)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生發(fā)展,字里行間流露出對于這個(gè)遠(yuǎn)離城市喧囂的化外世界的欣羨,仿若世外桃源的淳樸質(zhì)厚世界與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指向的無休止淘汰世界兩相對照,從而對后者產(chǎn)生了一種無聲卻蘊(yùn)含著力量的反抗。
在鄂溫克人原生態(tài)的生活中,人們處于一個(gè)凝固的人群體系里,對周圍的人事變遷有著長時(shí)間的觀察,因而對于人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當(dāng)老達(dá)西從為周圍人厭惡憎恨,到被人們心疼理解,到最后復(fù)仇成功安詳?shù)仉x去;當(dāng)伊芙琳從平易近人簡單善良,變得絕望掙扎惡毒,在瑪利亞死后彷徨無措,消解掉仇恨帶著鮮花離開;當(dāng)尼浩一次次為了那些“別人的孩子”而忍痛讓上蒼帶走自己的孩子;當(dāng)尼都薩滿心懷愛、壓抑愛、放棄愛穿上神袍,到等待愛、追求愛、失去愛在舞蹈中葬送自己的一生……一幕幕都體現(xiàn)出人性中巨大的包容,人們對于苦難的承受和消解,對于幸福的追求和釋然,對于生死的理解,都充滿了無限的意味。帶著溫暖的希望降臨,又平靜歸于灑滿陽光鮮花盛放的山坡。伊蓮娜生活于這樣的環(huán)境中,聽風(fēng)的呼嘯,和月亮星星說悄悄話,她較長時(shí)間里克服了在人群中的慌張和焦慮,把精力更多地專注于畫畫,專注于對人的發(fā)現(xiàn)和理解。對自然的敬畏與崇拜,很好地彌補(bǔ)了迅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文明的一種缺失,并形成了一種良性的互補(bǔ)。因此,她的畫,她畫中的色彩及色彩的沖擊力令人震撼。正如作者在采訪中所說的:“對于作家來說,在一個(gè)相對安靜的環(huán)境里,有利于他們的寫作。因?yàn)檫h(yuǎn)離喧囂,會(huì)讓文學(xué)的情感純度更高。”[1]這世界上偉大的人往往不是去發(fā)現(xiàn)和迎合他人、服從世界,而是用最大的力氣來發(fā)現(xiàn)自己、認(rèn)識(shí)自己并守住自己,凸顯出了其區(qū)別于眾人的獨(dú)特性,并由此超越時(shí)代,成為歷史星空的閃亮星斗。因此,與其耗精費(fèi)神地在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的引導(dǎo)下明爭暗斗消除差異融入主流,不如認(rèn)真審視自己的內(nèi)心和周圍的人事,將惶恐焦慮轉(zhuǎn)化為花開的從容。
作者以客觀冷靜的視角對鄂溫克人進(jìn)行了描寫,不限于單方面的頌揚(yáng),還夾雜著自己的冷峻的審視和質(zhì)疑。作者在描述鄂溫克人淳樸的民風(fēng)民俗的同時(shí),也描寫了人們的愚昧迷信、自私冷漠。但與現(xiàn)代文明相對照,每一種缺失又都帶有一種寶貴的品質(zhì)。因?yàn)橛廾翢o知所以對自然和生命充滿敬畏,而所謂的自私冷漠如達(dá)西則顯示著人們單純的愛憎分明的價(jià)值觀,看似迷信實(shí)際上是弱小民族對自己神靈堅(jiān)定的信仰。遲子建曾提到:“在我自幼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我明白了一個(gè)最樸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2]對于簡單的自然變化,如春去冬來、花謝花開,作者消失在文本背后,讓讀者自己進(jìn)行論斷。而讀者最終會(huì)發(fā)現(xiàn),看似冷漠無情、自私自利的人在內(nèi)心深處也有溫暖柔軟的角落。人物形象立體厚重,整體的故事敘述也變得更加真實(shí)可觀,更具可信性。遲子建以一個(gè)接近真實(shí)世界的建構(gòu)來論證兩種世界共生的包容,論證了差異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從而對消除差異的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學(xué)說構(gòu)成一種對立關(guān)系。
在激烈的社會(huì)變革過程中,幸福和痛苦實(shí)際的承擔(dān)者是作為組成社會(huì)的具體的人,這個(gè)社會(huì)可以給出一萬種理性的理由來解釋變革的時(shí)代中炮灰的飛濺是一種必然,但是作為研究人發(fā)現(xiàn)人體察人的文學(xué),有責(zé)任來正視炮灰的聲音,來傾聽那些來自底層喑啞的悲鳴。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舉著為現(xiàn)代文明更好發(fā)展的大旗,卻恰恰忽略了現(xiàn)代文明中平等自由的本質(zhì)。
二、黃昏——現(xiàn)代文明自身焦慮構(gòu)成
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自我消解
科技的進(jìn)步為生活帶來方方面面的便利,人們的民主、獨(dú)立、自由意識(shí)不斷提高,但也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從早年我們說的因自然原因造成的人類貧窮、饑餓和疾病,轉(zhuǎn)變成了今天因?yàn)榘l(fā)展和追求發(fā)展而造成的因改變自然而出現(xiàn)的災(zāi)難和人類新的生存境遇。”[3]75現(xiàn)代文明以一種強(qiáng)大的不容反抗的力量迫使少數(shù)作出讓步并努力融合其中,但是我們“等來的不是那些豎著美麗犄角的鹿,而是裹挾著沙塵的風(fēng)。”[4]大興安嶺上消失的一片片茂密的叢林、逐漸失去生命靈性的馴鹿、夏季越來越稀疏的雨、冬季逐年稀薄的雪,都足以讓我們認(rèn)真反思文明的當(dāng)下進(jìn)程。遲子建在下部《黃昏》中飽含遺憾與凄涼地描述了鄂溫克人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的夾縫求生存,在時(shí)代變換下的顛沛流離,現(xiàn)代文明所體現(xiàn)出的焦慮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完成了自我消解。
城市社會(huì)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醫(yī)療、教育、公共設(shè)施的健全,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為人們對于自由的追逐、對于生命價(jià)值的追求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物質(zhì)基礎(chǔ)。但與此同時(shí),人際關(guān)系也愈加冷漠,現(xiàn)代人的戒備感逐漸增強(qiáng),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逐漸物化。遲子建筆下鄂溫克人的自然生活狀態(tài)籠罩著一種神秘的安寧。對自然詩意浪漫生活的追求,對淳樸平淡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的向往,對生命靈性自由意志的選擇,這些來自于生命的原始的強(qiáng)力給人一種別樣的觸動(dòng)。現(xiàn)代化進(jìn)程飛速前進(jìn),現(xiàn)代人卻又頻頻深情回望,從本質(zhì)上來講這是因?yàn)樯鐣?huì)達(dá)爾文主義隱約蘊(yùn)含了一種終極烏托邦。這種學(xué)說認(rèn)為,我們處于進(jìn)化之中,只要進(jìn)行不停地淘汰和“選擇”,就能夠邁進(jìn)一個(gè)完美的時(shí)空。但這更像是一種永遠(yuǎn)無法抵達(dá)的美好可能,讓我們能夠面對現(xiàn)實(shí)的無奈帶著希望前行。社會(huì)改革發(fā)展進(jìn)步必然面臨陣痛與犧牲,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說為了將來的幸福可以犧牲掉現(xiàn)在,“不惜以個(gè)人為貢獻(xiàn)”,則反而造成魯迅所說的“愈趨于惡濁,庸凡涼薄,日益以深,愚頑之道行,偽詐之勢逞,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于草莽,辱于濘涂,個(gè)性尊嚴(yán),人類之價(jià)值,將咸歸于無有”[5]的局面,這樣的改革就背離了其本來的宗旨,令人質(zhì)疑改革的出發(fā)點(diǎn)究竟是人民幸福,還是僅僅國家機(jī)器的強(qiáng)大。
縱觀人類發(fā)展的歷史,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更像是一種對達(dá)爾文思想的異化,曲解了達(dá)爾文的本意,反而為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社會(huì)不平等提供了合理化的溫床,直接指導(dǎo)了人類史上的幾次大屠殺,被后來的一些政治軍事分子所利用,導(dǎo)致了人類歷史上一次次的災(zāi)難。日之夕矣,馴鹿在夕陽下的剪影由模糊到清晰,又由清晰變得模糊,被圈養(yǎng)的它們在山腳下目光迷亂,看不懂世間的風(fēng)起云涌,參不透時(shí)代的瞬息萬變,它們等待著明天會(huì)有新的太陽從東方升起。
三、正午——和諧共融的悅納
而非血流不止的爭斗
褪去晨光的新生和稚嫩,正午的陽光有一天中最飽和的溫度和熱情,雖然免不了日薄西山的命運(yùn),但此時(shí)此刻達(dá)到的物我交融、萬物和諧運(yùn)轉(zhuǎn)使這個(gè)時(shí)候的平靜多了一種對過往的滿足和對未來的蓄勢待發(fā)。遲子建在《正午》一章中對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的和諧交融的描繪,也是對于現(xiàn)代社會(huì)及未來社會(huì)發(fā)展的美好構(gòu)想,并非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指向的血流不止的爭斗,而是萬物相攜相生、生生不息的悅納共生。
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它將整個(gè)社會(huì)比作一個(gè)叢林社會(huì),弱肉強(qiáng)食,如果想要存活就必須遵從這個(gè)規(guī)則,如果不去和其他人競爭并成為獲勝者,就必然走上被成功者取代并滅亡的道路。但是,理智思考就可以發(fā)現(xiàn),成功和失敗并非不可折中。鄂倫溫克人在草原森林的原生態(tài)生活提供了另外一種生存、生命和生活的可能性,人們對生活感到自足,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令人心生敬畏。如果我們只待在科學(xué)能夠認(rèn)識(shí)的狹小但安全的范圍內(nèi),而不去探索模糊的邊緣地帶,作哪怕是徒勞的假設(shè),我們就只能發(fā)現(xiàn)我們所能看到的現(xiàn)象,并且局限于這種發(fā)現(xiàn)。我們?nèi)绻麅H僅以已有的知識(shí)基礎(chǔ)來認(rèn)知這個(gè)世界,那么得出的結(jié)論往往是不成熟的,這個(gè)世界還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要做的不是消除差異實(shí)現(xiàn)成功者的趨同,而需要在一個(gè)不斷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在制度、法律的逐漸健全下用一種足夠包容尊重的眼光來面對世界的差異性,而不是以戰(zhàn)爭、武力征服的方式來實(shí)現(xiàn)文明的一體化。每當(dāng)我們征服一個(gè)種族、征服一種文化,實(shí)際上我們也喪失了一種美好,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要想融入到另一個(gè)世界或者變成另一個(gè)世界,就必須接受和服從另一個(gè)世界的原則,在和之前幾乎全然不同的叢林法則下,人們一以貫之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維方式等必須隨之改變。但在這種劇烈的轉(zhuǎn)變過程中扭曲的是人性。“農(nóng)村社會(huì)所保有的那點(diǎn)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shí)際社會(huì)培養(yǎng)成功的一種唯實(shí)為利的庸俗人生觀。”[6]在農(nóng)村社會(huì)短短幾十年的發(fā)展中,人們的價(jià)值逐漸翻轉(zhuǎn)到一個(gè)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似乎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jià)值。我們之所以生活條件呈上升狀態(tài)的時(shí)候幸福感卻呈下降狀態(tài)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在社會(huì)快速發(fā)展時(shí),人性中一些美好的元素因不適應(yīng)新壞境被殘忍地閹割了。到最后,正如不停地游走在城市和鄉(xiāng)野、在兩種具有差異性的文化中所顯現(xiàn)出的痛苦焦慮不安的伊蓮娜。人們身上既不具備城市所需要的文明,又失卻了鄉(xiāng)下人的淳樸,變成了游蕩在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邊緣人。我們所呈現(xiàn)的,不是一種重視長時(shí)間積累、凸顯本質(zhì)性民族性的獨(dú)特存在,而是一種渴望立即見效的速成拼貼文化,混血和變異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本質(zhì)。“文明在進(jìn)步,而鄉(xiāng)村的詩意,卻正在這進(jìn)步中消失殆盡,或者發(fā)生著巨大的更替與墮落。”[7]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在進(jìn)行所謂的“優(yōu)勝劣汰”的過程中,原本期待的美好并未實(shí)現(xiàn),反而導(dǎo)致和不斷加劇人和社會(huì)的畸形異化,使邁向現(xiàn)代文明的進(jìn)程更加步履維艱。
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宣揚(yáng)優(yōu)勝劣汰,但是在人類社會(huì)倫理觀的衡量下優(yōu)劣本身就是無法定義的,當(dāng)一種存在形態(tài)以不傷害任何人的方式自然存在的時(shí)候,就沒有高貴和低賤之分。“生物界進(jìn)化規(guī)律和人類倫理的進(jìn)化是截然不同根本對立的過程。”[8]如果把自然界生存斗爭的規(guī)律套用到人類社會(huì),那就必然嚴(yán)重削弱甚至毀滅使社會(huì)結(jié)合在一起的紐帶。鄂溫克人的生活方式和我們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與我們的生活又有潛在的關(guān)聯(lián),簡單粗暴地以“力”為準(zhǔn)則來改變原有社會(huì)運(yùn)行的“禮”的原則,對于整個(gè)社會(huì)以及人類文明進(jìn)程的發(fā)展的作用不容樂觀。遲子建在采訪中提到:“當(dāng)初我們試圖把他們變?yōu)槎际腥耍o他們在城鎮(zhèn)建造了同一模式的房屋,讓他們帶著馴鹿下山后,沒有多久,這些骨子里流著山泉水的鄂溫克人,紛紛擺脫束縛,帶著他們的馴鹿回到山林,又過起了老日子。”在他們的世界里,有自己向往的幸福歡樂,雖然生活方式、思維形式與現(xiàn)代社會(huì)有所不同,卻也沒有對城市的生活產(chǎn)生侵?jǐn)_,反而還與現(xiàn)代社會(huì)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我們可以時(shí)時(shí)刻刻從他們的生活中來拷問、訓(xùn)誡自己的良知,形成一種良好的共存。
參考文獻(xiàn):
[1]遲子建.慣于長冬[J].南方人物周刊,2015(15):94-98.
[2]遲子建.文學(xué)的“求經(jīng)之路”[J].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2):7-11.
[3]張清華.中國當(dāng)代作家海外演講[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
[4]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0.
[5]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6]沈從文.長河[M].長沙:岳麓書社,2010.
[7]張清華.中國當(dāng)代作家海外演講[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
[8]翁美琪.赫胥黎對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的否定——讀《進(jìn)化論與倫理學(xué)》[J].讀書,1983(6):72-75.
作者簡介:郭璐璐,廣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寫作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