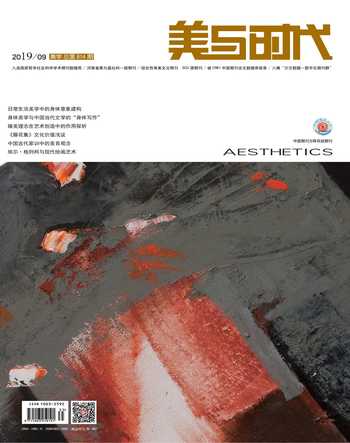2014年以來大陸犯罪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 要:自2014年的《白日焰火》一片以來,大陸犯罪片呈現出新的創作模式,藝術與商業的結合是其最大的特色以及成功的要素,人性的挖掘則是其一貫主題,人物的吸引力提到了與敘事并肩的高度。犯罪片作為一個極具市場潛力的類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在面向市場時也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通過對《白日焰火》《心迷宮》《暴雪將至》《爆裂無聲》四部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梳理,總結了三種類型的女性:被利用的女性、賢妻良母式女性以及被污名化的女性。這三類型女性中,一方面,有著電影中對女性的傳統表達,另一方面,女性人物的反抗,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的自我要求、自我認識、自我獨立的女性意識的生長。這些影片在保持其深刻的人性挖掘主題不變的基礎上,呼喚著與男性平等的女性形象的繼續書寫,也呼喚著更豐富的女性形象的表達。
關鍵詞:類型電影;大陸犯罪片;女性形象
2014年,《白日焰火》一片摘得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員兩個大獎,成為當年的話題性電影,獎項的助力加上適當的營銷,使這部文藝氣質濃厚的影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自此之后,涌現了一批融合作者思考和商業色彩的犯罪片。與《盲山》《盲井》這一類借助犯罪事件深挖社會黑暗現實的影片不同,新的犯罪片側重表現個體在極端環境中的煎熬與自我反思,直指人性的幽微之處。這類犯罪片主要以男性為主人公,女性大多作為男性的對立面或附庸出現。
一、 被利用的女性
在犯罪片中,有一類女性是長期的書寫對象,她們外表美麗,兼之強大的性吸引力,往往作為欲望客體出現在銀幕上,成為男性的凝視對象。這類女性的代表人物有《白日焰火》的吳志貞和《暴雪將至》的燕子。
《白日焰火》的女主人公吳志貞周旋于多個男性之間,與男性角色的關系揭示了她作為欲望客體的悲慘命運。男主人公張自力接近吳志貞,一方面有著“破案-人生成功”的動機,另一方面源于對神秘有魅力的吳志貞的探究欲和征服欲。勞拉·穆爾維指出,在兩性尚未實現真正平等的社會語境下,男性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掌控電影的生產與接受過程,從而創造出各種女性形象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和無意識的欲望。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被處理成了一種符碼,在銀幕上成為“被看”的對象。在看與被看的“權利-欲望”關系中,張自力與吳志貞分別處在看與被看的位置,影片中多次表現張自力對于吳志貞主動的“看”。吳志貞第一次出現在鏡頭中時,并未直接展示她的面部,而是運用了一個對裸露腿部的搖拍,既有著“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主義,又將女性的身體奇觀化。直到張自力介入吳志貞的生活、投射出凝視的目光時,觀眾才第一次看清這個女人的面龐。在接下來過肩拍攝張自力背部的鏡頭中,張自力成為畫面的前景,吳志貞背對著畫面的身體成為后景,這個鏡頭連結了銀幕上的男性與銀幕前觀眾的視線,確立了張自力觀看的主動權,同時提醒著銀幕下觀眾的視線投射。
影片中,吳志貞兩次反抗過張自力的跟蹤行為,第一次,吳志貞偷偷遞給張自力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別再跟著我”,張自力不以為然;第二次,吳志貞遭到洗衣店老板的猥褻,張自力將她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這件事成為吳志貞內心防線的第一個突破口,張自力得到接近她的機會,車站前吳志貞又一次對張自力說“別再跟著我了”,這一次張自力同樣無視了她的要求,轉而向她提出邀請,而實際上他正密謀著如何利用吳志貞。吳志貞的兩次反抗都帶著無法自我說服的無力感,與其說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行為,毋寧說是弱者形象的深化。在與張自力的交往中,吳志貞從抗拒到接受再到信任依靠,展現了一個女性從無望的反抗中最終走向失敗的過程。
洗衣店老板與吳志貞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和影片中流浪漢與他收留的馬形成對照,收留與被收留之中,主被動關系一目了然,這意味著吳志貞必須常年忍受老板的猥褻,才能使自己免于被丟棄的困境。洗衣店老板作為一個性無能的人,是男權社會的他者,他無法通過正常的方式獲得快感,被他欺辱而無力反抗的女性因此顯得更加悲慘。
活死人丈夫梁志軍與吳志貞,他們之間呈現占有與逃離的對抗。梁志軍的社會身份已經不存在,這令吳志貞脫離了“梁志軍妻子”這個身份,語言上的解脫并沒有為吳志貞帶來實際的自由,梁志軍強烈的占有欲促使他殺死一個個接近她的男人,也將危機加諸于她。背叛梁志軍使吳志貞完成了一次逃離,不過這只是一次短暫的逃離,不久她又陷入了張自力的掌控與背叛之中。在片中,皮氅這一反復出現的物象,直指男性對吳志貞的控制,這件象征著男性權利與金錢社會的皮氅,先后經過白日焰火夜總會老板和張自力的手,正是掌握了這件東西,這兩個男人逼迫她做出了獻身。吳志貞作為欲望客體,在對三個男性的絕望反抗中走向失敗。
《暴雪將至》的燕子,特殊的裝扮和霓虹燈閃爍的空間暗示了她的妓女身份,這一社會身份加諸于她的是“不純潔”“低賤”等詞匯,因此,她成為了余國偉抓捕針對女性犯罪的嫌疑人的誘餌。燕子是一個想象視域中的受害者形象,始終處在余國偉、想象中的犯罪者和觀眾的三重視線之下。
對于燕子的分析也可以引入關于黑色電影中蛇蝎美人的描述,大部分黑色電影和犯罪片對蛇蝎美人身體的展現是充滿窺視欲的“奇觀化”審美,勞拉·穆爾維把這稱為男性視角對女性身體的“戀物癖”式的表現方式。男性對女性的戀物傾向,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玩偶之家》式的,將女性變成父權或夫權的漂亮玩偶。另一種是狹義“戀物癖”式的,男人們對女人飄逸的金發、性感的紅唇、時尚的皮鞋、閃亮的珠寶都有著火熱的激情。燕子經常以紅唇形象示人,再加上紅色皮衣和皮裙,構成了片中男性的戀物實體,強化了“戀物癖”式的男性窺視的目光,在不斷重復的化妝動作中,一個潛在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就出現在余國偉和銀幕前的觀眾面前。
片中總是利用物像的并置暗示燕子的命運,燕子貼在墻上的照片是余國偉將她當成誘餌的開端,在這個場景中,燕子貼在墻上的照片和警察局墻上的女性受害者的照片相對照,燕子第一次與那些女性受害者建立了聯系。在燕子發現真相的段落中,她的照片與那些受害者裸露的身體的照片放在一起,燕子等于受害者的結論更加清晰。
黑色電影中的蛇蝎美女都是這樣的女性:有著獨立的意識,并且在實際行動中對片中的男性發出沖擊,但是她們往往在與男性的交往中產生真情,而無法達到自己的目的。與這類女性有相似之處,燕子盡管干著看不到明天的工作,但一直堅持著去香港的夢想。她愛上了余國偉,但當她發現余國偉并不愛她而是把她當成誘餌時,她說“好像做了一場夢,忽然間一切都不真實了”,愛的夢破碎了,她縱身一躍,以悲痛的方式反抗了余國偉的利用和“背叛”。吳志貞和燕子代表著被男性觀看、被男性利用的一類女性,她們也曾有反抗的意識,但反抗行為總是和失敗并存。
二、賢妻良母式的女性
這一類女性在影片中的身份通常設定為母親或妻子,其形象與中國傳統的富于母性的女性形象一脈相承,其關鍵詞可以是含辛茹苦的、相夫教子的、維系家庭的,她們認同男權社會的運行方式,是男權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這一類女性包括《心迷宮》中肖衛國的妻子,《暴裂無聲》中張保民的妻子,她們成為片中男性的撫慰力量,并不構成敘事的動力。
《心迷宮》中的母親這一角色,作為肖衛國的妻子,肖宗耀的母親,是兩父子緊張關系的調停者。在可見的場景中,她都與廚房和家務事聯系在一起,苦口婆心地勸導兒子聽從父親的安排,盡管如此,肖宗耀真正理解、接納父親卻是在自身陷入殺人案之后,母親的意志在本片中是被忽視的。這類女性是最傳統的中國女性形象,她們并不參與到男性的話語中,并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男性的主導地位。
《暴裂無聲》中男主角張保民的妻子翠霞是另一典型人物,她總是和許多藥瓶處于同一畫面中,這直接宣告了她身體的脆弱,腿上的疾病使她喪失了行動力,最常見的動作是幾乎靜止地坐在炕上,不多見的行動中也總是佝僂著肩背,搖搖欲墜。盡管翠霞自身已經十分虛弱,但她還是不吝惜對張保民的維護,當張保民的母親忍不住抱怨張保民之前的沖動行為時,她站出來維護了張保民的尊嚴。
這一類女性并不參與到影片的主要敘事進程中,她們是失意男性的撫慰者。
三、被污名化的女性
這一類女性總是受到男權社會評判標準的壓迫,她們生活在男權社會之下,只要違反了男性主導社會之下的女性標準,總會受到男性角色的言語侮辱。這類女性包括《心迷宮》中的黃歡和麗琴。
在《心迷宮》的第一條敘事線中,王寶山在流水席上見到黃歡,兩人因王寶山表弟的死發生沖突,王寶山將表弟的意外死亡歸咎于黃歡,斥責黃歡是賤貨,這一情節體現了男權社會中將錯誤推到女性身上的習慣性做法,而男性在這一行為中得到想象性解脫。黃歡在片中的主要身份是肖宗耀的女朋友,除愛情之外,肖宗耀選擇黃歡的行為一定程度上被他當做反抗父權的工具。黃歡是肖宗耀反抗父權的一個犧牲品,正是因為在戀愛中處于弱勢地位,她需要用孩子來穩固戀情,從肖宗耀的話語中,也直接將她與傳宗接代的工具掛鉤。《心迷宮》中的農村社會,即使在新的時代,也將父系宗法制貫徹到了每一個人的心里,女性受制于它,也認同它。
《心迷宮》中的另一個女性麗琴是第二條敘事線的主要人物,她也屬于男權規范下被污名化的女性。麗琴年輕時與王寶山的戀情遭到男方家庭的反對,遭到拋棄的麗琴被村里人唾棄,導致她只能嫁給現在的瘸子丈夫,受到丈夫毒打后,她只能將痛苦轉化為對丈夫的背叛。在情人王寶山被當成殺人犯之后,王寶山為證清白不惜犧牲她的名節,在眾多男人面前,她冷靜地否定了昨晚與王寶山在一起的事實,“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做法為這個人物添上了無情的色彩,也再次證明了一個事實:在男權格外穩固的農村社會,婦女的名聲就是一切。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范,返還給男性個體以災難,不得不說這是對男權社會的諷刺。
麗琴這個角色是有著反抗色彩的,早年的經歷為她帶了污名,使她陷入困境。但是伴之而生的潛意識下的反抗精神,雖然并沒有將殺夫的意圖付諸實踐,然而將丈夫的骨灰與拐杖一起埋葬正是她獲得新生的體現。與王寶山斷絕關系,拒絕心儀她愿意為她殺人的大壯,都代表著受到男性傷害和男權社會壓迫的她認清了事實,并主動斷絕了這種不對等的關系。
在這一類女性身上體現了一個事實:男權社會形成了諸多女性規范,女性或遵循這一規范,或違反規范以致被污名化處理;而男性總是將過錯推到女性身上,幻想在對女性的污名化中脫困。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白日焰火》《心迷宮》《暴雪將至》《爆裂無聲》四部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梳理,總結了三種類型的女性:被利用的女性、賢妻良母式女性以及被污名化的女性。這三類型女性中,一方面,有著電影中對女性的傳統表達:女性的地位始終次于男性,或是欲望客體,或是撫慰男性的角色,這是女性形象塑造中不變的一面;另一方面,女性人物的反抗,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的自我要求、自我認識、自我獨立的女性意識的生長,這是變的一面。犯罪片作為一個極具市場潛力的類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在面向市場時也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在保持其深刻的人性挖掘主題不變的基礎上,呼喚著與男性平等的女性形象的繼續書寫,也呼喚著更豐富的女性形象的表達。
參考文獻:
[1]周憲,主編.視覺文化讀本[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宋鑫,朱潔.2014年以來大陸犯罪題材電影的創作轉向探析[J].文教資料,2017(32):204-206.
[3]祖紀妍.簡述蛇蝎美人的歷史溯源與發展變遷[J].當代電影,2015(4):68-72.
[4]吳洪娣,管仁福.論我國百年電影女性形象的嬗變[J].電影文學,2007(21):19-20.
[5]張藝凡,陳富為.《心迷宮》的敘事結構和人性主題解析[J].大眾文藝,2016(19):188.
作者簡介:張莉,上海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