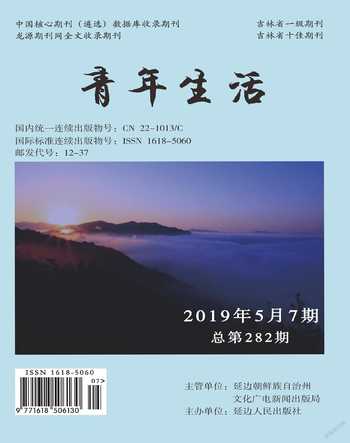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障礙分析
何惠

【摘要】:失地農民的對策研究多數是單向研究,如征地補償問題、失地農民就業問題、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和失地農民市民觀培育等問題。實際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之路與征地補償、就業和社會保障是內在的有機統一體,當然這種內在的有機聯系也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筆者在可持續生計理論模型的基礎上,結合新余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的實際情況,對其進行一個全面而系統的分析,這有利于我們更清楚地看清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障礙因素。
【關鍵詞】:經濟開發區? ?失地農民? ? 市民化? ?障礙分析
失地農民融入城市轉變為市民,不僅僅只是戶籍上的農轉非,他們在職業、生活方式、思想意識和價值觀也要經歷更難的轉變。失地農民市民化不僅僅包括物質層面,更包括精神層面,可以說物質層面的保障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基礎與前提,而精神層面的融入更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實質,這兩者缺一不可,不然失地農民市民化不能得以真正解決。
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物質層面有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與安置問題、就業與培訓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精神層面主要有其市民觀的培育,包括思想觀念、市民意識和價值觀等。但是我國失地農民市民化是在毫無準備、社會保障嚴重不足、市民待遇沒有確立的情況下被動接受身份和角色轉變的,是一種被動城市化。在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市民化現狀并不是很理想,從新余市經濟開發區農民市民化的現狀可見一斑。這里除了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的缺陷外,大多數失地農民在短時間內難以學會并內化現代城市環境下的市民價值觀念、行為規范以及生產、生活技能等,造成他們長期游離于市民與農民角色之間而不能融入城市,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持續發展。
為有效解決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市民化問題,筆者根據可持續生計理論模型,結合新余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的實際情況,對失地農民市民化的整個過程進行一個系統的梳理,對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利于我們更清楚地看清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障礙因素,以便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
根據可持續生計理論模型,結合新余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的實際情況,建構了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框架模型。其框架模型如下:
第一,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要素說明
可持續生計途徑框架圖是一種理解多種原因引起的貧困并給予多種解決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而我國失地農民作為一個邊緣化群體或弱勢群體,用可持續生計框架圖來分析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是可行的,但是由于失地農民的具體情況和特殊背景,可持續生計模式圖應有所改變。
首先,生計資本“三角形”的形成。隨著政府征地的發生,被征地農民失去了農耕地和山林,自然也就沒有了農作物和林木業的收成,所以失地農民的生計資本出現了自然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缺失。而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主要是影響失地農民就業的因素,所以筆者把他們合并成一個資本,即就業資本。而金融資本改成資金資本,是因為失地農民的收入大多數來自工資收入,而由于農民的保守心態,很少有人會拿去投資,所以來自投資資本、財產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的金融資本就很少。另外筆者認為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失地農民市民觀的轉換,也將其作為一個因素列入市民化資本中,所以就業資本、資金資本和市民關程度構成了市民化資本的三要素,而且在不同情況下,三種要素可以相互影響和轉化。
其次,脆弱性背景的內涵。可持續生計理論模型是以貧困農戶為單位進行的可持續生計出路分析的理論框架,而失地農民因為失去土地,所以他們受到自然災害沖擊和季節性變化的影響會比較少,但是失地農民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必須承認其脆弱性的存在,結合失地農民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們的脆弱性背景主要表現在失業、缺保和市場價格變動等方面。而結構和制度方面,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的主要有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政策制度、社區的服務水平和文化氛圍、企業的用工政策和各種相關法律政策等。而失地農民的市民地位主要表現在收入增加、就業穩定、生活水平提高、可持續升級能力不斷增強等,而失地農民的邊緣化地位表現則相反。筆者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路重構了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框架的各要素。
第二,框架模型各要素的相互機制分析
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框架圖是由脆弱性背景、市民化資本、政府和社區的政策措施、市民化表現等因素組成。這些組成成分以復雜的方式互相作用,箭頭只是表示一個組成會影響另一個組成的一些因素。
首先,市民化資本的三個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條件下相互影響和轉化,就業資本可以通過就業實現資金資本的積累,資金資本又可以反過來使就業資本得到提升;資金資本的積累可以作為市民觀實現的經濟基礎,而市民觀的轉變又可以拓寬資金資本積累的渠道;而就業資本和市民觀轉變可以作為相互之間的加速器不斷加速積累和轉變。
其次是失地農民市民化資本的影響機制,我們可以把失地農民看作是在一個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謀生的群體,其中脆弱性背景既可以創造資本又可以毀壞資本。比如金融危機引起的就業難和高失業率,會直接影響到失地農民的就業競爭力,從而使失地農民的市民化資本降低;同樣的,如果政府能給失地農民建立一個良好的就業服務體系和完善的工作環境,那失地農民的市民化資本就會得到加強。另外政府機構投資與管理水平、社區服務水平以及政策與制度的建設對資本創造過程也起著積極或消極影響,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脆弱性背景。正是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失地農民采取的不同生計措施,造就了不同的市民化結果,市民化結果又反作用脆弱性背景和資本狀況,形成一個循環過程。
而結合新余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把邊緣化看成是失地農民的市民化結果。失地農民因為就業不穩定、工資收入低,征地補償標準低,造成資金資本來源少;由于失地農民大多數文化水平低、技術水平缺乏,使得他們的就業資本也沒有競爭優勢;而且由于傳統文化和小農思想的根深蒂固,短時間轉變思想是很困難的,所以失地農民是建立在脆弱和不平衡的市民化資本組合基礎上的,加上近年來金融危機和物價上漲的影響,失地農民的脆弱性背景是加強的,又由于政策的剛出臺和剛試行而得不到政策、機構和制度的支持,使其不能有效地使用他們本來可能使用的資產,市民化之路構成了一個不可持續的生計策略,最后導致了被邊緣化的惡性循環。
根據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的框架模型的分析可見,其障礙因素來自經濟、制度、文化與社會網絡等多方面的社會排斥,使得失地農民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面臨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嚴重阻礙了其向市民角色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