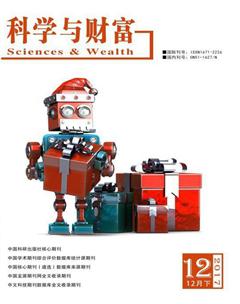工程項目上的財務管理
石嵐
工程財務是指在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財務活動,具體表現為與工程建設相關的企業和單位的資金運動,以及通過資金運動所體現的經濟關系。財務管理是指對財務活動所進行的計劃、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活動。
施工企業在施工過程中,將涉及一系列的財務活動,其中包括對計量支付材料的審核等。財務人員在支付方面工作主要表現在:
1.對計量支付程序檢查
(1)對計量支付程序的執行情況
主要檢查的內容是采用的計量支付型式與合同約定是否相同。對于一般監理項目,為了加快支付速度,并保證計量工程的質量,一般均采用監理工程師和承包商共同計量的方式。
(2)現場計量的程序
對填發了《檢驗申請批復單》或《工程檢驗認可書》的項目才可計量,每月計量前監理組做好有關計量的準備工作,包括計量部位的圖紙和其他有關資料、計量時所需的儀器設備。采用監理工程師和承包人共同計量的方式,一般由監理工程師與承包商委派的負責計量支付的人員到現場進行計量,然后將計量記錄及有關資料報送現場監理工程師核對確認。
(3)填寫中間計量表
中間計量表是計量的憑證,在進行現場計量時由計量人員填寫,經監理工程師核對確認后,作為中間付款的依據。
采用的表格中除了表明被計量項目的清單編號、工作內容及所在位置或部位外、還要繪制計量簡圖、列出計算公式及計算結果,以便各級監理工程師審查核實。
(4)駐地監理工程師對計量結果的審查
駐地監理工程師審查計量的工程質量是否達到合同標準,對審查過程中發現未達到質量標準的項目,均應進行修補或返工,達到標準后再重新予以計量。
(5)財務人員對計量結果的審查
財務人員審查計量的過程是否符合合同條件,包括計量簡圖、計算公式及最終計算結果。發現計量過程中的錯誤要及時通知承包人進行修正。
2.對合同條款執行情況的檢查
(1)質量合格的已完成工程才可以支付
只對承包商按照合同條款已經完成的工程項目才予以支付,對于未完成或雖然完成但工程質量未達到合同規定的項目,一律不予支付。承包商的一切活動必須達到監理工程師滿意的程度。因此,即使某項工程的質量已達到合同標準,但承包商其他方面的工程活動未使監理工程師滿意,監理工程師也有權對合格工程拒絕支付。
(2)變更的項目必須有監理工程師批復的變更指令才可以支付
合同條款規定,承包商沒有得到監理工程師的變更指令,不得對工程進行任何變動。因此,未經監理工程師的批準,對任何施工項目的改變都是不允許的。不管這種改變是否必要,一律不予進行任何支付。這是因為任何工程的變更,均需由監理工程師對變更后的工程標準是否能夠達到原合同規定的標準進行審定,變更的費用也需由監理工程師確定。因此,在工程支付的管理過程中,拒絕對未經監理工程師批準的變更項目予以付款,對保證工程質量是非常重要的,否則,監理工程師將失去對工程的控制。
(3)財務人員審核各項支付款是否符合合同條款的規定
無論是工程量清單中工程項目費用的支付,還是清單以外各項費用的支付,均需符合合同條款。例如,動員預付款額要符合投標文件附錄中規定的數量,支付的條件應該符合合同條款的規定,即承包商在完成下屬工作之后才予以支付動員預付款:
1)簽訂合同協議書;
2)提供履約擔保;
3)提供動員預付款的保單。
承包商在未完成上述工作之前,動員預付款將不予以支付。
(4)支付金額必須大于階段證書的最低額
根據有關規定,承包商每月可以對他完成的永久性工程的價值和工程量清單表中其他項目的費用以及按合同規定的承包商有權得到的任何其他金額提出申請,然后由監理工程師簽發付款證書。但是承包商每月得到的支付金額,必須等于或大于合同中規定的階段證書的最低限額才予以支付。如果支付的金額小于最低限額時,則不予以支付。在這種情況下所證實的金額將按月結轉,直到批準的付款總額達到或超過最低限額時才能予以支付。
3.調整價格情況及調價的有關申報和批復
施工合同工程價款調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工程數量增減引起的工程價款調整
1)工程數量自然增減,此類價格調整只需將增長或減少的工程量乘以相應的項目單價即可。
2)工程變更引起的工程數量增減,此類價格調整關鍵在于單價及價格的確定。這里單價的確定分為兩種情況。
(2)工程變更引起的工程數量增減,此類價格價格調整關鍵在于單價及價格的確定。這里單價的確定分兩種情況:
①合同中已包括工程變更項目的單價,應該以合同規定的單價為準,予以調整。
②合同中未包括可直接適用于變更項目的工程單價,如合同中相似項目的單價合理,亦可作為工程變更項目的價格調整基礎。若套用不合理,則由施工單位提出或監理工程師提供一個變更價格,經與施工單位及建設單位協商后,由監理工程師決定一個較為合適的單價或價格。若協商不成,在未取得一致意見前,由監理工程師確定一個合適單價或價格,報工程造價管理部門裁定。
(3)由于工程變更和工程量清單上實際工程量的增加或減少(不包括暫定金額、計日工和價格調整),使合同的價格增加或減少超過有效合同價的15%時,監理工程師應與施工單位和建設單位協商后,在款額超過或低于有效合同價15%的那一部分基礎上加上或減去雙方及監理工程師協商后的那一筆款額,若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則由監理工程師確定。
4.后繼法規引起的工程價款調整
如果在工程投標文件呈遞截止日期前28天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程所在地的法律法規發生變更,致使施工單位在施工中的費用發生了除了價格調整規定以外的增加或減少,則此項增加或減少的費用應按法律和法規的規定予以調整,合同價格應按此相應增加或減少。
5.資源價格變動引起的工程價款調整
合同執行期間,施工單位所需資源價格由于市場供應等因素的影響常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度工程費用的增減有著直接的影響,監理工程師應根據工程合同規定,對這些材料差價(包括工資差價及設備臺班費差價)同意或不同意補差。若工程合同不是閉口的,則監理工程師應掌握市場動態及當地物價部門的有關規定,注意價格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以便依據合同及有關規定準確而公正地處理好價格調整,通過調整,是原來的合同價予以增減。
(1)價格調整計算,應按投標截止日期前28天,當日政府規定的價格與現行價格的差值加到合同中或從合同價值中減去,或按投標截止日期前28天所在地的當日縣政府公布的物價指數與現行物價指數計算出的金額加到合同價值中或從合同價值中減去。
(2)價格調整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公式法,另一種是票證法。
①公式法是利用合同文件中規定的一種或幾種公式進行調整,這些公式在合同專用條款中給出。它把合同總價分成幾個要素(如人工費、鋼材、水泥、木材、地方材料、機械設備、油料等),然后根據統計局公布的價格指數對每一部分的價格進行調整。這一方法主要難點在于價格指數的取得和確認。
②票證法是根據供應單位或施工單位所提供的票據來進行調整。票據包括實際的發貨票。票證法的難點主要在于票據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