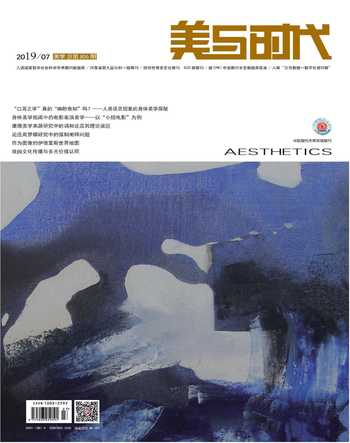藝術之丑的美學闡述與價值實現
摘? 要:生活丑通過藝術美的形式呈現,是藝術家通過“化丑為美”“以丑襯美”的方式讓丑在藝術生活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呈現方式,從而實現其特有的審美價值。這一過程凝結著藝術家對于“丑”與“美”的理解,從本質上來說生活丑和藝術美在審美的終極意義上是內在統一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辯證關系。通過表現生活丑,從而實現藝術美,這不僅可以強化美,還可以給人帶來與美不同的審美體驗。
關鍵詞:藝術之丑;藝術美;以丑襯美;化丑為美
一、“丑”的美學闡述
美學史上對丑的討論遠少于對美的研究,往往是在討論美的過程中為了表現美的多樣性而附帶地談及丑,丑在美的表現過程中只是美的陪襯,襯托著美。但任何事物并不是單純地表現丑或是單純地表現美,它都是矛盾的集合體,善惡、美丑亦然。我們在認知一個事物是美或是丑的過程中,其實是對于事物內在矛盾的認知,而矛盾雙方又是相互轉換、相互依存的,這也就使得美與丑之間相互轉換、相互依存,在美與丑的矛盾中,通過表現生活丑從而實現藝術美,其實質是通過丑造就超越其本身的藝術美。
美學之父鮑姆加登曾說:“Aesthetics(美學)是研究感性(sense)的學科,其對象就是對于感性認識的完善,也就是美;而與此相反就是感性認識的不完善,也就是丑。”在美學史上,雖然對于“丑”的探討不及“美”,美學家們對于“丑”也有著不同的認知,例如“卑劣”和“怪誕”,前者偏向于道德觀念中的低下、鄙俗,傾向于人內在情感的體驗。后者則偏向于外在形象上的古怪,更付之于人的外在感知。
英國著名美學家荷迦茲曾用賽馬和戰馬的例子來證明丑是自然本身的一種基本屬性,表現恰當則可以產生美,反之則會變成丑。他寫到“賽馬的馬的周身上下的尺寸,都最適宜于跑得快,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美的一貫的特點。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設想把戰馬的美麗的頭和秀美的彎曲的頸放在賽馬的馬的肩上……不但不能增加美,反而變得更丑了。因為,大家的論斷一定會說這是不適宜的。”[1]荷迦茲認為,表現恰當可以產生美,而違背客觀規律的隨意改變則會使本身美的東西缺乏了美感,變成了丑的東西。不過,作為審美范疇的“丑”,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談及的“丑”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我們日常生活所談及的“丑”,單純地指某一事物外在所呈現出的“丑”的形象,而審美范疇上的“丑”是具有否定意義和否定價值的,其外在所表現出來的“丑”的形象是被賦予某種特定內涵的,在此范疇中它成為一種“藝術丑”。
關于美與丑的闡釋,杜書瀛在其所著的《文藝美學原理》中這樣寫道:“美是和諧,丑是不和諧、反和諧。從排斥丑到吸收丑、重視丑,從丑服從美、襯托美到美襯托丑、丑逐步取得主導的地位,便成為近代藝術沖擊、代替古典藝術的轉折點,也成為近代藝術的主要審美特征。”[2]西方美學界在美丑關系的討論中,更強調美與丑之間的對立與沖突,而中國傳統美學認為美或丑并不孤立存在,美的存在需要丑的襯托,同樣在表現丑的過程中往往也會滲透著美,從而使美與丑相互協調、相互滲透。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關于美的討論不勝枚舉,例如孔子所講的“盡善盡美”、孟子的“充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等,但關于丑的討論相對較少,主要體現在儒家“丑即是惡”的觀點。儒家認為社會的正常運轉需要社會契約,凡是違背社會契約的行為都是丑的。除此之外,莊子也曾對“真”與“丑”進行對比。莊子認為美并非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美與丑是“應時而變”的。《莊子·知北游》中有一段話: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腐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圣人故貴一。[3]336
莊子這段話是說,世間萬物都是氣,好的東西、奇妙的東西、丑陋的東西、甚至于腐爛變質的東西都是氣。把世間的美好都看作是奇妙的,而把世間另外一些被人厭惡的東西看作是腐臭的。但奇妙的事物和腐臭的事物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即美與丑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莊子不僅使“丑”這個概念進入審美領域,也是美成為審美范疇的開端,同時提出了一個關于“美”和“丑”的本質規定:“美”和“丑”的本質都是“氣”。“美”與“丑”之間可以相互轉化,這不僅在于人們對于美丑的理解不同,也和人們在某一條件下對于美丑的認知有關,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和“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莊子·山木篇》中: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3]229
這段是想說,美與丑是相互依存,本質沒有差別。莊子告訴我們,丑中包含著美,他認為外表的丑陋不重要,人格的美才能使人得到尊重,因而突出的人格之美可以讓人忽視其外在的丑陋,而傾心于其內在的美,從而使外在所表現出的丑陋形象得到升華。當然這并不是說莊子就忽視了外在所表現出的美的形象,但他認為精神的、內在的美更為重要。
達·芬奇在《論繪畫》一書中寫道:“美和丑因相互對照而顯著。”其含義就是說,美與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相融,美的呈現需要丑的襯托。同樣,丑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表現丑的過程中同樣需要美來對其進行襯托。美與丑總是在相互對照中顯現出超越其自身的審美價值。德國美學家德蘇瓦爾曾寫道:“丑是一種背景,用來增強美的光輝。”他認為,在審美的過程中,丑也是必不可少的,若將美比作光,那丑就是影,在光影的世界中,光與影是并行的,光若離開了影,那么光也就索然無味,影若是沒有光的襯托,那也將會黯然失色。在美與丑的世界中,美同樣也需要丑作為背景來增強它的光輝。因而,在藝術創作中,通過美與丑之間的相互對比可以使藝術家想要表達的精神之美更為絢爛。
丑的定義是多種多樣的,每個個體關于丑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總體來說我們會把社會生活中那些給人帶來不舒服體驗的或使人內心產生恐懼或厭惡的現象定義為丑。因而丑總能讓人對積極、樂觀、向上的生活產生厭倦,使得本應前進的事物受到阻礙。丑與美總是處于對立面,若美被定義為和諧,那么丑就是所謂的不和諧。人們對于美丑的認知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認知水平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有時甚至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藝術丑作為藝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必然存在的一種審美經驗。通過丑來發現美,也是藝術家們進行藝術創作的一種常見方式,中西藝術史中有無數的藝術實踐證明了這一點。生活中丑的形象要轉化為藝術美,其審美價值主要通過以下兩種表現形式——以丑襯美和化丑為美——得以實現。
二、丑的價值實現途徑之一:以丑襯美
以丑襯美,可以更加突出美,使美更醒目、深刻。法國著名文學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運用以丑襯美的原則給讀者描繪出了典型的美與丑的藝術形象。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個有著四角鼻子、馬蹄形嘴巴、瘤子長在臉、牙齒參差不齊、嘴唇無比粗糙,可謂世界文學史上外貌最丑的卡西莫多的形象,雨果用這種夸張又生動的方式,把卡西莫多的丑和吉普賽姑娘愛斯美拉達的美進行了直觀上的對比。對于愛斯美拉達,雨果寫道:“整個身段細巧纖弱、靈活如黃蜂……兩肩裸呈,裙子不時掀開,露出秀美的小腿;何況黑發如漆,明眸如火。”[4]《巴黎圣母院》中也塑造了像副主教克羅德和衛隊長弗比斯這種外表看似和善,實則道貌岸然、自私自利的藝術形象。卡西莫多就是“丑”的典型代表,他與愛斯美達拉形成了一丑一美、一陰郁一絢麗的鮮明對比。但雨果并非單純地表現卡西莫多外在的丑陋,也并非想要簡單地描繪愛斯美拉達的美,而是通過對卡西莫多丑陋外表的描述來襯托愛斯美拉達的美,通過對克羅德和弗比斯英俊外表的描繪來反襯他們丑陋的內心,使他們的“丑”更為深刻,通過美與丑的對比,讓讀者從中獲得不同的審美體驗。
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根據法國著名詩人維龍的詩歌《美麗的歐米哀爾》創作了雕塑《歐米哀爾》,羅丹塑造了一個年老色衰、身材干癟的老妓女“歐米哀爾”的形象,雕塑中歐米哀爾彎著身軀、低頭無力地看著自己干癟的身體和枯癟的乳房,幾十年的風月場生活,使她的肚皮滿是皺褶。倘若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會對這樣的一個女人說美,可是當觀賞者面對羅丹的這件偉大的藝術作品的時候,卻遲遲不愿離開,心中泛起層層漣漪,或是對羅丹技法的感嘆又或是對歐米哀爾的同情,總之這是“丑”的形象所帶來的審美體驗。葉朗先生曾在《美在意象》一書中提到丑的審美價值主要集中表現在兩點,其中一點即為“丑可以顯現生活的本來面目”。因為現實生活中不僅存在美好的、積極的、向上的、光明的東西,也存在著與之相反的惡俗、消極以及陰暗的一面。正如雨果在《克倫威爾序言》中所講的,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與惡并存,黑暗與光明相共。
三、丑的價值實現途徑之二:化丑為美
化丑為美是藝術作品審美價值體現的另一種方式,也是藝術作品意識性的深刻體現。在《拉奧孔》雕塑中,大蛇用它致命的絞纏來扼殺拉奧孔和他的兒子們,拉奧孔的神情中充滿了痛苦和恐怖,他費力掙扎,想要擺脫蛇的纏繞。雕塑中,三人的身體已經在蛇的纏繞下痛苦到扭曲,身上肌肉的運動已經達到了極限,三人的身體都已經被痛苦填滿,在痛苦的籠罩之下,氣氛也異常慘烈而緊張。阿格桑得羅斯將現實中的“丑”通過藝術創作能動地轉化為藝術美,雖然事物本身“丑”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但作為藝術作品它已經具有了審美價值。正如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寫到:“我要讓丑惡陰暗的世界,開放出美麗的藝術之花。”[5]
朱光潛先生曾在《西方美學史》中寫道:“繪畫能不能用丑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畫能不能表現反面形象的問題。如果真正不能,繪畫就不能作為揭露丑惡的工具。”[6]就整個藝術史的發展來看,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不管是近代還是古代,單從藝術史上所留下來的畫作看,藝術創作并不排斥丑的素材,甚至會把丑的素材運用到藝術創作過程中。羅丹對此也有過表述, 他認為藝術作品描寫丑更能顯露出它的性格。也就是說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我們不僅僅表現美的形象,同時也需要表現丑的形象,通過表現丑的形象從而呈現出不同于美所帶來的愉悅的審美感受,而這種通過欣賞丑所感受到的審美感受更容易使藝術作品與眾不同。克羅齊在《美學原理》一書中寫道,丑的本質就在于對象以其形式狀貌對主體實踐效果的否定,喚起主體情感對對象存在的否定。也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丑,通過藝術家能動性的創造,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是可以形成其特有的審美價值的。如果藝術作品中的形象都能達到“因為丑反而變得更美”的效果,那么這種美的價值就得到了升華,達到善美與真美統一的境界。當然,如果藝術家自身審美趣味低下,或是創作技巧欠佳、表現手法不當,那么其所創作出的藝術品只能形成藝術丑,也就只具有消極意義,也就無法實現由生活丑到藝術美的轉化。
在一些優秀的藝術作品中,化丑為美的方式并不是單純地將生活丑通過藝術創造的方式使其具有審美價值,這就好比在一些優秀的影視作品中,美與丑是同時存在于同一個藝術形象身上的。人的本性是多元的,并不能簡單地用善惡美丑當中的一種性質來評價人物形象。例如在文牧野執導的影片《我不是藥神》中徐崢扮演的程勇、在斯皮爾伯格執導的影片《辛德勒名單》中連姆·尼森扮演的辛德勒都是化丑為美的典型代表。影片《我不是藥神》中,中年的程勇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長發,賣著“神油”,酗酒、家暴、亂發脾氣,所有當下社會男性的惡習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一副無所事事又頹廢的樣子,讓他的生活不見天日。因為程勇的種種惡習加上他又無比貪財,因而影片中黃毛對其怒吼“我看不起你”,此時程勇的人物形象就是“丑”的化身。而程勇從“丑”到“美”的轉化是在其被迫走上藥販子的道路之后,程勇一開始做藥販子,單純地為了賺錢,這與他剛開始的人物設置如出一轍,但在與那些白血病病人的不斷接觸中,他深感白血病病人生活的不易,從而逐漸蛻變,從最初唯利是圖的藥販子到最后傾其所有幫助白血病人的“藥神”。程勇的蛻變,不僅僅是個人的蛻變,也是影片中所塑造的藝術形象由“丑”化“美”的過程。程勇在迷失和尋找中完成了自我認知的轉變,從而得到了人性的救贖,在褪去其丑陋外殼的同時也塑造了一個真善美的人物形象,從而使影片中程勇的個人形象得到了重新建構,也使得影片主題得到升華。電影《辛德勒名單》中辛德勒最開始希望通過猶太人廉價的勞動力來給自己創造財富,但當其親眼目睹了納粹黨對于猶太人毫無人性的屠殺,尤其是當穿紅衣服的小女孩穿過人群走上樓梯的時候,辛德勒的內心被深深地震撼到,紅色代表著生的希望,小孩代表了民族的希望,導演以此恰當地刺激了辛德勒的神經,使其內心開始轉變,繼而開始下意識地去救助苦難中的猶太人,雖然這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但其內心深處的善良已經開始通過其行動而表現。后來當辛德勒在焚尸廠第二次看見那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時,小女孩已經去世,這給了辛德勒內心深深的刺激,使辛德勒愿意傾盡所有來救猶太人。影片之初,辛德勒是一個好色又貪婪、唯利是圖的商人,而當影片結束的時候,辛德勒已然成為猶太人心中的英雄。辛德勒身上這種美與丑、善與惡的融合使人物形象更加飽滿,從而散發出人性的魅力,實現超越形象自身的審美價值。
四、結語
古人云:“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美丑與共,瑕不掩瑜。”先人們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看到了美與丑不可分割的審美關系。無論是現實自然還是人文藝術,都不是絕對美的,而是美中有丑、丑中有美。尤其藝術中更不可偏廢,倘偏廢一方,就會顯得不完整,甚至會導致藝術創作的失敗。就取材來說,無論哪種藝術形式都不是單純地表現美而摒棄丑,一部發人深省的藝術作品是在美與丑的融合與矛盾沖突中實現其審美價值的。如果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只表現美好的事物,而摒棄不好的東西,就無法構成沖突,表現出的結果也就不那么有吸引力,對藝術作品來說就難以引起觀者的共鳴了。
藝術家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只有充分認識到生活丑向藝術美轉化的意義,才能將“丑”的審美內涵和審美價值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才能擺脫藝術作品的假大空,從而提升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西方美學家論美與美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02.
[2]杜書瀛.文藝美學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3]莊子.莊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4]雨果.巴黎圣母院[M].鄭克魯,譯.北京:中國宇航出版社,2016.
[5]波德萊爾.惡之花[M].郭宏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付曉鵬,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系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