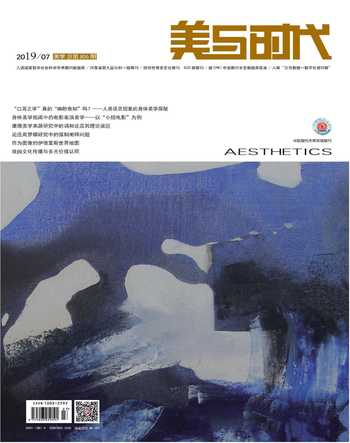淺析西北民間音樂之“花兒”

摘? 要:民間諺語中有“陜西的亂彈,河州的少年”一說(這里的“少年”即是“花兒”)。花兒是產生和流傳在甘、青、寧三省交界地帶的一種民歌。花兒以及其相關的習俗、生活環境構成了民間歌唱的文化空間。花兒于2009年作為中國申報的22個項目之一,成功當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張世界級文化名片的得來需要我們向成千上萬的花兒創作者以及傳承者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他們,同時也是這片廣袤神奇的大地孕育出了花兒這朵光彩照人的藝術。結合課程內容并通過文獻綜述選讀,對各個地區的花兒、不同類型的花兒、不同民族的花兒、花兒會以及花兒的傳承做一個系統的梳理。
關鍵詞:西北民間;音樂;花兒;河湟花兒;傳承
花兒歌手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來頭割下,不死了還是這個唱法。[1]40”從這句話中,我們能看出花兒的演唱已經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深深扎根于當地人的心中。花兒作為一種口頭傳承的文化符號,流傳于民間的歌唱習俗中,以一種強大的生命力存留著。
一、綜述各地區的花兒
花兒的發源地是河湟地區,河湟花兒是在湟水與黃河一帶交匯處所盛行的花兒。因其地理位置和所轄范圍與明代的河洲郡基本一致,故河湟花兒也被稱作“河洲花兒”。河湟花兒在漫長的流變過程中擴大了自身的生存空間,它還與其他地區的文化習俗相融合,形成了新興的“地方花兒”。花兒按照地域進行劃分,主要有“甘青花兒、寧夏花兒、新疆花兒以及中亞花兒”[1]4。
(一)甘青花兒
我們今天所說的河洲特指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甘青花兒這一區域與河湟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人文環境十分接近,它是花兒發源地的自然擴展并順勢流傳到青海的海西地區。可以說,甘青花兒是河湟花兒的延伸,兩者相似的環境以及風土人情使甘青花兒很容易被當地各民族的人民所接受。
(二)寧夏花兒
從發展的源流上來看,寧夏花兒是甘青花兒的一個分支,這可以從寧夏花兒的基本調式上看出。1.從分析寧夏花兒的調式來看,徵調式較為常見。而這也是河洲令型花兒的基本調式。因此,我們可以由此得出這是明清時期由甘肅河洲遷徙前往寧夏的回族人民帶來的[1]19。2.它的基本調式中含有大量的商調式,即下四川令型花兒。這是甘肅花兒經由商人旅客人口流通所帶回的。另外,寧夏本地還有山花兒。它在衍變過程中不僅吸收了河湟花兒的精華,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陜北“信天游”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很多寧夏山花兒的作品中會聽出些許陜北味。
(三)新疆花兒
所謂歌隨人走,河湟花兒隨著人群聚居區的遷徙逐漸流傳到天山一帶,現在主要流傳于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洲。河湟花兒傳入新疆后,與當地民歌(即西北地區的民歌)相互融合并有所發展。同樣,在新疆花兒中也會發現許多陜北民歌“信天游”的詞曲引子,這些花兒既保留了河湟花兒的特點,也吸取了西北地區民歌的風格。
(四)中亞花兒
中亞花兒的發展背景是在清朝的光緒年間,陜甘寧地區的回族人民遷移到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坦,并在此定居生活。因此花兒民歌也隨著回族人民的流動在國外生根發芽。另外,花兒民歌曾盛行在蘇聯集體農莊時代的回族聚居地區,這一考據可以從蘇聯時期東干語文獻中查詢花兒民歌得知[2]191。
二、闡述不同類型的花兒
現今,學術界習慣將花兒以三種類型劃分:河湟型花兒、洮岷型花兒、隴中型花兒。
(一)河湟型花兒
可以說,河湟地區既是花兒的源頭,也是花兒最流行的集中地,在這里演唱的民族最多。隨著河湟花兒的衍變,在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又衍生出了數十個流派。河湟型花兒曲令豐富,歌曲內容以愛情居多,其特點是只允許在外面唱而不許在室內家里演唱。此外,在演唱河湟花兒時,還會帶有樂器伴奏。
(二)洮岷型花兒
洮岷型花兒主要在甘肅的渭源、康樂、臨潭、臨洮等八個地區。傳唱的民族主要是漢族和藏族兩個民族。它的流行地域與河湟型花兒相比較小,但有別于河湟型花兒的是,它可以在家中演唱且隨帶伴唱。它的內容題材以敘事居多。洮岷型花兒在發展的進程中不斷改進,以娛樂化、生活化居多,“出現了交誼歌、賀喜歌、對答歌、生活歌等多種生活題裁的花兒”[2]192。
(三)隴中型花兒
從反映的內容來看,隴中型花兒比較雜亂,它的形式主要以娛樂為主。在大量隴中型花兒作品中,“有的以花兒的基本音調,配以花兒的歌詞格式;有的以花兒的基本音調,配以非花兒歌詞格式;有的以非花兒音調,配以花兒的歌詞格式;有的以非花兒音調,配以非花兒的歌詞格式”[1]22。隴中型花兒在形態上與傳統的河湟花兒相較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三、歷史發展中不同民族的花兒
目前,花兒主要在回族、漢族、藏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以及蒙古族等9個民族中傳唱,本文主要圍繞漢族、回族、土族三個民族做一個綜述整理。
(一)漢族花兒
漢族長期受儒家文化主導,因此漢族花兒在歌詞表達上多含蓄且采用隱喻的手法。在漢族花兒的創作中人們還會加入名著故事(如《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為其起興的內容[1]23。此外,漢族花兒受當地游牧民族的影響,其曲調多為高亢、豪放的基調,但在情感表達方面又保留著漢族人民委婉、哀怨的特點。
(二)回族花兒
回族在形成過程中吸取了一定的漢文化,在傳唱花兒上,回族對花兒的形成發展起著重要作用。首先,回族人口的增多是花兒生成的一個重要條件;其次,在歷史的衍變過程中,回族逐漸將漢族語言作為本民族的共同語言,這也是花兒生成的又一重要條件。
(三)土族花兒
土族是中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他們視歌唱為生活必需品。在土族有一句俗語,“飯可以一天不吃,歌一天不唱不行。”[1]23對土族人民來說,歌唱已經深深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另外,土族有很強的牡丹情結,他們酷愛牡丹。例如,“房子里掛的、畫的、插的都是牡丹。”他們也喜愛將自己的情人稱為“牡丹”,在花兒的曲令上也喜歡以“牡丹”命名,例如“白牡丹令”或者“紅牡丹令”[1]24。
譜例1:
譜例1是典型的流傳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的花兒——《尕妹是園里的白牡丹》。這首花兒的曲令為黃池令(以流傳的地方命名),是一首F宮G徵五聲調式。樂曲中主要采用宮、商、羽、徵四個音,其中徵音是構成調式的核心音,宮音和羽音的使用僅次于徵音和商音。從譜例中可看出,在此調式中角音起著輔助性的裝飾潤色作用。曲式結構上,該樂曲采用的是上下兩個樂句所構成的單樂段。結構上采用“斬斷腰式”,即在頭尾齊式的上下兩句中加進了一句半截句。
四、花兒的載體——花兒會
花兒會,即大規模的花兒演唱活動,它是花兒的載體。在花兒興起的地方必有花兒會,而在花兒會上所盛傳的神秘傳說以及宗教禮儀等,讓人們將視野投向花兒會與宗教信仰活動之間。
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就是“松鳴巖花兒會”。“松鳴巖花兒會”是人們對信仰追求的具體表現。它“是作為宗教活動的衍生而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以至于我們在它的身上始終能夠看到它與宗教千絲萬縷的聯系”[3]。關于松鳴巖花兒會產生的傳說版本不一,地方文獻的記載也不能科學全面地反映松鳴巖花兒會的起源和流變,但我們可以從中歸納、獲取一些與松鳴巖花兒會相關的信息。首先,松鳴巖花兒會舉行的時間就是歷史上舉辦龍華會的時間,兩者在時間上是一致的,主辦地點多在佛教寺廟附近。寺廟在古代可以說是一個地方社會的中心。花兒會就是這個中心地帶社會化的節日活動。在流傳發展中,由于松鳴巖花兒會自帶傳奇的神話色彩,因此官府利用這一特性來凸顯花兒會的合法性、合理性,并鼓勵當地百姓積極參與。花兒會作為一種群眾自發性的演唱花兒的集會形式,歷經歲月成為當地特有的民俗活動。歷時四天,從農歷的四月二十六至二十九結束。此外,松鳴巖花兒會還會與當地的廟會結合。在這段時間里,人們不僅可以以歌會友,進行文化、宗教信仰交流,還能利用廟會進行物資交流、商業活動。
花兒會的源頭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聯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問題。有學者認為,這些去參加廟會的年青人在唱神頌佛的同時,也有對愛情婚姻的祈禱。這種對神靈的祈禱經由歲月演變,最終成為異性之間用歌聲含蓄或直接的對唱表達。隨著歷史的變遷,宗教迷信的思想在人民群眾中逐漸減弱,出于迷信功利化演唱花兒的成份變少,取而代之的是單唱、發自內心的歌唱花兒。因此,原先的宗教活動就變成男女表達情感、專唱花兒的活動。
五、花兒的傳承與發展
在當今社會,花兒的傳承和發展可以說不容樂觀,其生存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人們不得不深思并實施搶救性保護。但是人們在保護花兒這一傳統民間藝術時也面臨一些問題。首先,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大環境的缺失。環境的變化使人民在創作花兒的生活氣息上大打折扣,其藝術內涵膚淺單薄。由此,“它正在從充滿個性的‘野花’變成取悅觀眾的‘瓶花’”[1]2。新創的花兒有別于以抒發情感為目的的傳統花兒。它的內容過于時尚化,原有的藝術特性逐漸消退。我們知道,傳統的花兒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延續至今,是因為它體現了數代人民的精神思想以及情感內容,對演唱的場所也有特別嚴格的規定(如河湟型花兒)。但是變異的花兒卻成了一種單純的娛樂工具,它打破了所有的條條框框,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戶外,茶室還是酒吧都能演唱花兒。有人甚至把古老的花兒和流行歌曲,甚至同搖滾樂混雜在一起,這樣的變異使它的原本面貌日漸模糊。不禁感嘆,我們保護的還是花兒嗎?還是在再創“新花兒”?
其次,花兒的藝術內涵不僅接受著巨大的挑戰,它的展演以及傳播也受到了強烈的商業沖擊。花兒會作為一種大眾化的民俗活動,對花兒的傳承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以一張文化名片讓世人了解花兒、走近花兒。“花兒最隆重的傳統演唱形式——花兒會,是花兒的展演和傳承平臺”[1]2。然而,如今的花兒會卻是以“傳統的文化交流向經濟效益不斷妥協”的現狀而繼續發展著。在某些組織的商業目的下變成了公司招攬商戶的活動,“隨著商家的加入又同時成為了商品交易會”[1]2。商業化的目的徹底改變了傳統花兒會以歌會友、娛樂為主的性質。另外,花兒的傳承手法“對歌”已經改變了其傳統的模式,現在主要以專門的演唱社團進行演繹,結果就是花兒會最原始的傳承效果以及影響傳播力都有所削弱。
因此,如何保護和傳承花兒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筆者認為花兒是一種公共文化資源,保護它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個人民的意識要求。政府在實施一系列保護措施時,同樣要取得傳承群體的認同。這樣保護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其次就是要精心保護花兒傳承的文化空間。甘肅花兒如同其他民族的歌會一樣,有其傳唱的特殊場所(文化空間),即每年一度的花兒會。其中以蓮花山、松鳴巖、二郎山花兒會最為出名。這三個享譽中外的花兒會已經進入國家名錄,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甘肅花兒是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我們要遵循它的保護原則,要防止商業團體對其過度地開發,不能借各種文化節、旅游節、文化產業的開發名義,破壞花兒傳承的生態環境。
六、結語
通過文獻閱讀以及課堂學習,筆者對各個地區的花兒、不同類型的花兒以及不同民族的花兒做了一個較為系統的梳理。這讓筆者對這個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感受花兒獨特的魅力以及它所處的特有生存環境。花兒會與宗教信仰的聯系為花兒會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也讓筆者對其源起以及流變有了更大的興趣,由于可獲取的資料過少、資歷有限,因此在本文中并未過多闡述。花兒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一,它的傳承與保護值得人們去深思并投以實際的措施。
參考文獻:
[1]周亮.花兒的文學性與音樂性關系及傳承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0.
[2]周亮.花兒傳播途徑及分布區域分析研究[J].科學·經濟·社會,2010(4):188-192.
[3]盧翱.“河州花兒”的演唱習俗與傳承——以甘肅臨夏松鳴巖“花兒會”為例[D].濟南:山東大學,2008.
作者簡介:項丹雅,上海大學音樂學院音樂與舞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