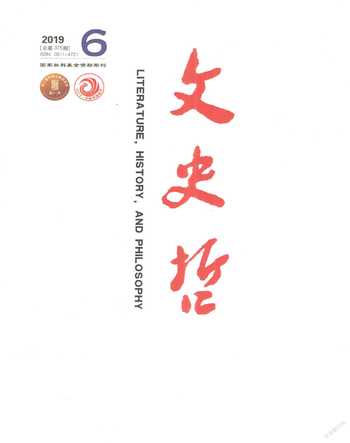反思“五四”:中西古今關(guān)系再平衡
任劍濤 陳衛(wèi)平 譚好哲 方朝暉 魏建 劉悅笛
編者按:自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以來,如何把握中西古今關(guān)系這一命題貫穿了百年中國現(xiàn)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們所關(guān)注的重大理論問題。本期推出的這組筆談,從政治學(xué)、哲學(xué)、文學(xué)、歷史等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jìn)行了新的探索。任劍濤先生認(rèn)為,風(fēng)雷激蕩的“五四”徹底終結(jié)了帝制復(fù)辟圖謀,從根本上拯救了現(xiàn)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國現(xiàn)代建國的政治理想與現(xiàn)實(shí)路徑;陳衛(wèi)平先生辨析了“五四”與全盤反傳統(tǒng)、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革命四個方面的關(guān)系,以期在社會科學(xué)知識體系中重建“五四”敘事;譚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學(xué)革命”確立了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性新文學(xué)直面現(xiàn)實(shí)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啟蒙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反思和總結(jié)中國文學(xué)的百年歷程,必須重視“人生論”文學(xué)觀及其人道主義思想內(nèi)核的精神啟蒙價值和文學(xué)范式意義;方朝暉先生將中國文化心理特征概括為此岸取向、關(guān)系本位、團(tuán)體主義,認(rèn)為中國的現(xiàn)代性迄今仍沒找到自己的恰當(dāng)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對這一深層心理結(jié)構(gòu)了解不夠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為例,通過這部最能體現(xiàn)“五四”抒情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績之代表作的研究,總結(jié)了“五四”文學(xué)研究的歷史教訓(xùn);劉悅笛先生從世界文明的大脈絡(luò)當(dāng)中重新審視“五四”,認(rèn)為20世紀(jì)以來的“中國啟蒙”,在結(jié)合本土傳統(tǒng)后,可以為世界文明提供一種新的發(fā)展范式。六篇筆談從各自不同的視角,為肯定“五四”的價值,提供了新的向度與新的思考,對于相關(guān)研究將有啟發(fā)和推動作用。
關(guān)鍵詞:五四運(yùn)動;共和;“五四”知識敘事;文學(xué)革命;中國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中國啟蒙”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6.02
“五四”與拯救共和
任劍濤
(清華大學(xué)政治學(xué)系教授 北京100084)
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到1919年“五四”,接近八年時間。這八年時間,現(xiàn)代共和政體在中國經(jīng)歷了令人驚心動魄的起伏歷程:曾經(jīng)讓國人高度心儀的共和國建構(gòu),僅僅過了數(shù)年,便成為過街老鼠,遭到全方位攻擊,陷入四面楚歌的狀態(tài)。風(fēng)雷激蕩的“五四”,徹底終結(jié)了帝制復(fù)辟圖謀,從根本上拯救了現(xiàn)代共和。“五四”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國現(xiàn)代建國的政治理想與現(xiàn)實(shí)路徑,帝制中國自此才徹底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
一、瘸腳的“第一共和國”
1911年,辛亥革命發(fā)生,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世界上第三個實(shí)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大國【參見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上),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6年,第Ⅶ頁。】。這是中國人踏入現(xiàn)代世界門檻后,在政治上可以感到非常榮耀的事情:整個亞洲,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尚未能在建立現(xiàn)代共和國上有如此成就,它們大多仍然徘徊在古典帝國的陰影中。尤其是在接近歐洲的中東,奧斯曼帝國還在上演“帝國的絕響”,此時的中國與土耳其,可謂亞洲國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土耳其在地理意義上被認(rèn)為是亞洲國家,在歷史意義上被認(rèn)為是歐洲國家。這與土耳其特殊的地理、歷史與文化相關(guān)。此處是在前一意義上斷定土耳其的洲際歸屬的。】。
辛亥革命不是中國人熟悉的王朝循環(huán),而是徹底終結(jié)王朝邏輯,開啟中國現(xiàn)代共和政體進(jìn)程的偉大革命。革命的“低烈度”與共和確立的“大業(yè)績”為人所稱道【參見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上),第1頁。】,但現(xiàn)代共和豈是那么容易在專制土壤中扎下根來的,對于一個歷史長達(dá)兩千余年的古代帝國來講,帝制建構(gòu)和皇權(quán)思維根深蒂固,除卻不易。人們對共和政體的理論認(rèn)知與實(shí)踐嘗試,似在暗昧之中摸索。這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方面。先看后者。革命后的共和建國,在革命者一端,還難以將革命建國轉(zhuǎn)化為國家建設(shè),而共和運(yùn)轉(zhuǎn)中的制度擔(dān)當(dāng)者,也不知手中權(quán)力的存在目的與運(yùn)用技藝。因此,共和政體不僅沒有展現(xiàn)其績效合法性與運(yùn)作說服力,而且亂象叢生。
于是,兩幅畫面展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一幅畫面由革命者呈現(xiàn)。當(dāng)其時,對共和政體運(yùn)轉(zhuǎn)作出變質(zhì)斷定的革命領(lǐng)袖孫中山,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開始頑強(qiáng)從事新一輪革命運(yùn)動。孫中山的激進(jìn)化,使革命自身的正當(dāng)性嚴(yán)重遮蔽了革命之共和建國的目的性。這讓中國陷入了更為長久的革命泥淖。1914年組建中華革命黨,1915年回國斗爭失敗滯日,1917年在廣州聯(lián)合軍閥組建軍政府而后分道揚(yáng)鑣,且對俄國革命心有戚戚焉,1918-1919年系統(tǒng)建立建國理論,生命的最后階段終于確立激進(jìn)共和進(jìn)路、極左建國理念,——孫中山本是最忠于共和建國理念的領(lǐng)袖人物,這從他確立的革命最終目的就是憲政上可以得到印證,但孫中山對革命手段的一味崇信,讓他與共和建國的目標(biāo)不是愈近而是愈遠(yuǎn)。
另一幅畫面由當(dāng)權(quán)派呈現(xiàn)。關(guān)乎民國共和政治的國家性質(zhì)之議會的運(yùn)轉(zhuǎn)情況,令人憂慮。由于議員們的共和政治素質(zhì)較低,民國初年的議會政治簡直就是一團(tuán)亂麻: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派議員們年輕氣盛、容易沖動,在與前清舊派人物的政爭中,并不占優(yōu)勢。加之年輕議員中的留學(xué)人員大多出自日本,學(xué)習(xí)技術(shù)的居多,學(xué)習(xí)法政的很少,他們對歐美國家的議會政治并不熟悉,因此不知道如何有效實(shí)踐議會政治【民國初年的共和實(shí)踐情形,可參見朱宗震:《真假共和——中國憲政實(shí)驗(yàn)的臺前幕后》(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8-103頁。】。
與此相關(guān),現(xiàn)代共和政體所依賴的政黨政治,在民初也處于一哄而上的無序狀態(tài):在完全缺乏現(xiàn)代政黨生態(tài)的情況下,一時之間,政黨叢生林立,三百多個政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這些政黨展開的政治競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其目的不在為共和政體有效運(yùn)作而妥協(xié),相反是各自為政,莫衷一是。與其說它們是為了共和的共同目標(biāo),不如說是為了排斥性的政黨利益。革命黨之間為了權(quán)力而明爭暗斗,不知合作為何物。舊派人物的組黨,就更是赤裸裸地為了謀求權(quán)力。袁世凱與北洋軍閥政府對政黨的扶掖,內(nèi)心都對國民黨的建國意圖深懷拒斥,雙方都不明白為合作而黨爭的現(xiàn)代共和精神。至于這些政黨的現(xiàn)代屬性,也是參差不齊:國民黨其實(shí)是現(xiàn)代政黨與會道門的混合體,其他各有名目的政黨基本上是搖擺不定的派別或一時的利益共同體,甚至不過是議會機(jī)構(gòu)或政府中的老鄉(xiāng)會而已。由這些政黨組成的議會,有時候其實(shí)就是一個政治取鬧的場合。
中華民國剛剛建立時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在各省擁兵自立、參議院缺乏政治意志、孫大總統(tǒng)名義擁權(quán)、清政府尚未完全退出舞臺的情況下,根本就沒有全國范圍內(nèi)的政治與法律約束力。緊接其后為保證袁世凱忠于共和而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shí)際上是一紙空文。當(dāng)袁世凱自己制定《中華民國約法》時,明明白白就是為了自己集權(quán)。曾經(jīng)熱鬧非凡的政黨政治,就此徹底失去了法律保障。試想,袁世凱仰仗兵權(quán)而成為總統(tǒng),他怎么可能誠心誠意地跟國人玩分權(quán)制衡的政治游戲呢?共和國缺乏法律護(hù)航,本身就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加之國人自古至今信從人治而非法治,這對仰仗依法治國的共和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亞洲“第一共和國”因?yàn)楣埠蜋C(jī)制的瘸腳,本身就存在自陷危機(jī)的嚴(yán)重風(fēng)險。恰如孫中山痛心疾首所指出的那樣:“綜十?dāng)?shù)年以往之成績而計(jì)效程功,不得不自認(rèn)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墮廢,乃生無數(shù)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渾,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孫中山:《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7頁。】共和政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讓其很難在中國生根開花:先天不足,是其與千年君主制相比,缺乏生長發(fā)育的土壤;后天失調(diào),是指它降生之際效用有限、失信于人。這似乎注定了中國建立現(xiàn)代共和政制的一波三折、艱難困苦。
二、企而望歸君主制
再看前者。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quán)專制,告別了古代帝國,但并不等于就徹底終結(jié)了皇權(quán)理念和皇帝念想。在中國共和建國后的前數(shù)年,無論是革命分子還是保守分子,心中的皇權(quán)思維與行為定勢不僅沒有隨共和國的建立而蕩滌干凈,相反,他們對新政制的建構(gòu)心里常存帝王意欲。孫中山建立同盟會,要加盟會員對自己行磕拜之禮以示忠誠,便是標(biāo)志。至于保守分子,心中念茲在茲的是皇權(quán)與帝制,完全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兩者合力,讓君主制隨時隨地、變換形式回到中國政治現(xiàn)場。
人們可以從兩條線索清晰地觀察到這一態(tài)勢:一條線索是掌握共和國權(quán)力的權(quán)勢集團(tuán)對皇權(quán)專制揮之不去的依戀。袁世凱的復(fù)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們常以復(fù)辟鬧劇看待袁世凱稱帝的舉動,其實(shí)這就無視了這一事件的深刻歷史內(nèi)涵:兩千年之久的帝制,豈是一場革命、一段啟蒙,就可以讓其灰飛煙滅的?袁氏的復(fù)辟,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度不適應(yīng)中國的國情,它讓國家權(quán)力的權(quán)威性流失。就袁本人而言,他對限制其權(quán)力的共和制度十分不滿,且對乾綱獨(dú)斷的皇帝專權(quán)心生艷羨;就袁身邊人而言,基于對大位的覬覦,也對袁氏勸進(jìn)有加;袁本人極迷信,方術(shù)之士對袁誘以帝制能破短命宿命,讓袁益信復(fù)辟帝制勢在必然。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的幻滅,并沒有讓國人的皇帝迷夢徹底破滅。1917年6月,張勛率辮子軍進(jìn)京,“襄贊復(fù)辟大業(yè)”,擁戴末代皇帝溥儀復(fù)辟,通電全國改掛龍旗。雖然張勛復(fù)辟只有短短的12天,但已經(jīng)足以說明帝制重來不是黃粱大夢。革命領(lǐng)袖孫中山為此發(fā)布“討逆宣言”,北洋政府為之組成討逆軍。此所謂“逆”者,是與共和大潮相對而言的。對長達(dá)兩千年之久的皇權(quán)專制來講,共和恰恰是逆轉(zhuǎn)“大勢”的事情。因此,以帝制扭轉(zhuǎn)共和,在“第一共和國”的六年歷史上,竟然兩次出現(xiàn),不能不使人意識到帝制土壤之深厚、共和危機(jī)之深重。
陳獨(dú)秀在袁世凱復(fù)辟失敗后即指出:“袁世凱之廢共和復(fù)帝制,乃惡果非惡因,乃枝葉之罪惡,非根本之罪惡。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quán)之思想之學(xué)說,實(shí)為制造專制帝王之根本之惡因。吾國思想界不將此根本惡因鏟除凈盡,則有因必有果,無數(shù)廢共和復(fù)帝制之袁世凱,當(dāng)然接踵應(yīng)運(yùn)而生,毫不足怪。”【陳獨(dú)秀:《袁世凱復(fù)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年12月1日)。】此話可謂一語中的:中國的共和基礎(chǔ)之磽薄,專制傳統(tǒng)之深厚,讓人們習(xí)于帝制,疏于共和。僅靠國家高層精英發(fā)動的一場革命,權(quán)力不過仍然在高層流轉(zhuǎn),帝制忽而來去,便在意料之中。既然共和無以證明自己推動中國善治的效用,那么人們熟知的帝制便成為自然的替代選項(xiàng)。
另一條線索是頗有政治抱負(fù)的學(xué)者如康有為對君主制改頭換面的招魂。康有為的帝制主張可分為兩個時間段來看,一是民國肇建之前,康有為基于戊戌變法情結(jié),而對帝制深懷信念。“保皇會”的建立,是這一時期康氏保皇之針對光緒皇帝濃厚的個人情感的體現(xiàn)。二是在民國建立以后,康有為敏銳意識到共和體制生米已經(jīng)煮成熟飯,難以帝制取而代之,但他看清楚了共和建國對政體決斷沒有拿捏準(zhǔn)分寸的現(xiàn)實(shí),于是以自己考察了數(shù)十個國家的個人經(jīng)歷為據(jù),強(qiáng)調(diào)指出中國必須實(shí)行一種自具國家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他認(rèn)為,既然英國實(shí)行君主立憲制度而致秩序穩(wěn)定、國家富強(qiáng),那么中國也完全可以在千年君主制傳統(tǒng)上建構(gòu)同樣穩(wěn)定有序、促成富強(qiáng)的君主立憲制度【參見任劍濤:《政體選擇的國情依托:康有為共和政體論解讀》,《政治學(xué)研究》2017年第3期。】。這種退而求其次地為君主制招魂的做派,反映出帝制思維的樹大根深。
再從國際社會看,由于中國建構(gòu)現(xiàn)代民族國家已經(jīng)處在一個列強(qiáng)環(huán)伺的環(huán)境中,因此,強(qiáng)國對中國的共和政制建構(gòu)發(fā)揮著極大的影響力。像袁世凱復(fù)辟帝制的時候,他的美國顧問古德諾,應(yīng)袁要求分析共和制與君主制的利弊。作為美國著名的政治學(xué)家,古德諾認(rèn)為君主制優(yōu)于共和制。這不啻給袁復(fù)辟帝制以一劑政治學(xué)理論的強(qiáng)心針。加之英國公使朱爾典、美國公使芮恩有意無意的操弄,給袁世凱復(fù)辟帝制以明顯有加的鼓勵。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在中日之間為袁復(fù)辟帝制的奔走,就更是大大鼓勵了袁的復(fù)辟行徑。
在共和中國初期,立憲政治運(yùn)作的不暢,與君主制復(fù)辟的內(nèi)外動力,相互寫照,呈現(xiàn)出共和中國草創(chuàng)時代君主制強(qiáng)勁地卷土重來的政治情勢。何以君主制對共和制會有如此“優(yōu)勢”呢?簡而言之,一是因?yàn)榫髦茪v史悠久、深入國人政治記憶深層,而共和制短暫、國人對之記憶不佳;二是君主制給人以有力收拾社會政治局面的印象,而共和制收拾亂局明顯乏力;三是君主制的政治理論更有說服力,而共和制并沒有建構(gòu)起同樣有力的政治理論,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吁求,很難在民眾長期疏離政治的情況下被廣泛認(rèn)同,更難付諸行動。
民國初期的八年,可以說是君主制與共和制展開拉鋸戰(zhàn)的一個特殊階段。共和制遠(yuǎn)未在中國扎下根來。相反,共和的自我保衛(wèi)戰(zhàn),一直在艱難地進(jìn)行著。倒是君主制的兩次復(fù)辟,讓人們意識到,它的政治理念與制度功效并沒有隨帝王肉身的消逝,真正遠(yuǎn)離現(xiàn)實(shí)。共和政制能夠在民國初年的精英博弈中獲得廣泛支持嗎?能夠在君主制與共和制的政治思想之辯中贏得國民認(rèn)同嗎?能夠聚集起共和政制所需要的社會政治資源和觀念能量嗎?能夠真正讓國人信從共和政制的現(xiàn)代政治效用嗎?如此設(shè)問,令人惴惴。
三、“五四”拯救共和
在五四運(yùn)動以前,共和建國已經(jīng)被共和自身的敗績搞得聲名狼藉。在兩次君主制的短暫復(fù)辟中,共和政制自證其政治效用的任務(wù)已經(jīng)變得非常緊迫,但始終限于上層精英圈子政治游戲的共和建國,已經(jīng)很難為共和國提供什么新的動力了。孫中山試圖在革命者與軍閥之間打開合作通道,但軍閥與孫中山同床異夢,以至于讓孫中山再次陷入絕望狀態(tài)。孫中山也意識到向社會尋求共和建國的強(qiáng)大聲援之必要與重要,但他沒有伸向社會的強(qiáng)有力政治之手。到20世紀(jì)20年代,他提出所謂新三民主義,才找到政治革命之外的社會革命渠道,但這已經(jīng)是“五四”后話了。
1915年《新青年》的創(chuàng)辦,在社會政治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先于孫中山伸張了捍衛(wèi)共和必訴諸社會運(yùn)動的新理念。在今天中國“告別革命”的精神氛圍中,這一認(rèn)知被認(rèn)為是肆意擴(kuò)大革命范圍,因此讓革命日益遠(yuǎn)離其初衷的悲劇性變化,但從后發(fā)國家建立共和政制的世界史來看,這種悲劇性的轉(zhuǎn)變具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歷史既定性。一個后發(fā)現(xiàn)代國家之所以后發(fā),就是因?yàn)樗e累的現(xiàn)代國家轉(zhuǎn)變資源的短缺,內(nèi)部驅(qū)動轉(zhuǎn)變的能量十分有限。因此,在建構(gòu)共和政制的過程中,不得不一方面聚集共和建國的政治精英資源,另一方面努力改良堅(jiān)硬的專制政治土壤,以便共和政制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于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不得不同時進(jìn)行:以社會革命為共和建國開墾社會土壤,以政治革命為民權(quán)政治代替專制政治鳴鑼開道。非以前者,不足以為共和國聚集必要的社會資源;非以后者,不足以為共和國奠立國家權(quán)力基礎(chǔ)。這樣的悲劇性處境,不是那種限制革命以保證其不至于破壞社會秩序,而僅僅改變國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主觀意愿、竭力吁求就可以改變的。后發(fā)現(xiàn)代國家的共和建國,一定會走一段彎路,甚至這段彎路可能會非常漫長。法國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一再印證了這一點(diǎn)。
在1916年這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diǎn)上,陳獨(dú)秀明確指出,需要以國民運(yùn)動取代黨派運(yùn)動,以便開辟中國的“優(yōu)秀國民政治”【陳獨(dú)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號(1916年1月15日)。】。這一斷言,顯然也有針對民初黨爭政治缺陷的意味。他認(rèn)為,像法國、美國和日本那樣建立起現(xiàn)代國家,主要應(yīng)歸功于國民運(yùn)動。“國民之運(yùn)動,非一黨一派人之所主張所成就。凡一黨一派人之所主張,而不出于多數(shù)國民之運(yùn)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于國民之根本進(jìn)步。吾國之維新也,復(fù)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斗。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其結(jié)果也,不過黨派之勝負(fù),于國民根本之進(jìn)步,必?zé)o與焉。”【陳獨(dú)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號(1916年1月15日)。】由此可知,新青年與新國民實(shí)際上是兩詞一意,而新國民一定是關(guān)注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行動主體。這就直接觸及了現(xiàn)代共和的基本精神。
在皇權(quán)專制傳統(tǒng)深厚的中國建構(gòu)現(xiàn)代共和國,需要認(rèn)識清楚專制與共和截然不同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專制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zé),專在主權(quán)者之一身;共和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zé),則在國民之全體。專制國本,建筑于主權(quán)者獨(dú)裁之上,故國家之盛衰,隨君主之一身為轉(zhuǎn)移;共和國本,建筑于人民輿論之上,故國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轉(zhuǎn)。為專制時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職,在格君心之非與諫止人主之過。以君心一正,國與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國之政治,每視人民之輿論為運(yùn)施,故生此時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職,則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國民總意(General will),為引導(dǎo)國政之先馳。”高一涵因此全力吁求“國家之自覺”【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這種將共和與專制政體清晰劃分開來的認(rèn)識,難能可貴,其中雖然包含高一涵對君主制與共和國混合政制認(rèn)識的缺失,但對中國來講,由于從來不存在君主制與共和制的混合政制傳統(tǒng),以尖銳對立的眼光看待二者,有其合理之處。尤其是在民國肇建后的八年間,專制君主制的復(fù)辟,讓人們只能從對立的角度看待兩種政體的關(guān)系,因此愈益顯出高一涵這一政體劃分的重要現(xiàn)實(shí)針對。在民國初年反對君主國、捍衛(wèi)共和國的斗爭中,清醒認(rèn)識君主制與共和制在中國的截然差異,確實(shí)是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的政治問題。
訴諸國民運(yùn)動以捍衛(wèi)共和國,豈止陳獨(dú)秀、高一涵之輩的向隅之思,被稱為“五四”幕后推手的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顯然不是所謂激進(jìn)分子,但確實(shí)是“外爭國權(quán)”的積極推手。他們所爭的“國權(quán)”,當(dāng)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權(quán)。從政體論視角看,當(dāng)然爭的是中國之作為一個現(xiàn)代“共和國”的國權(quán)。這是從國際社會的大視角看中國建構(gòu)現(xiàn)代國家問題必然得出的結(jié)論。五四運(yùn)動,無論是從5月4日到6月3號的“小五四”,或者是起自1915年到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運(yùn)動之“大五四”,正是國民行動起來,徹底突破此前精英主導(dǎo)的中國共和建國模式;國民行動起來,一起來捍衛(wèi)共和國的標(biāo)志性事件。
民國肇建后的八年,捍衛(wèi)共和國,始終是新生中國的頭等大事。即便共和國的實(shí)際政治運(yùn)作弊端叢生,那也只是共和政制前行中出現(xiàn)的一時缺陷,而不是國人回頭求諸君主制的理由。袁世凱之成為孤家寡人、郁郁而終,張勛復(fù)辟前后不過12天,已經(jīng)足以說明君主專制不再具有整合偌大中國的政治能量:它已經(jīng)是被徹底終結(jié)的傳統(tǒng)政體形式,不可能具有與現(xiàn)代民主政制相結(jié)合的混合政體活力。曾經(jīng)擔(dān)任民國政府總理、袁世凱“時間最長的朋友”唐紹儀,在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就明白無誤地指出,袁世凱稱帝已經(jīng)“違背了自己就任總統(tǒng)時的誓詞,再也無法獲得中國人民的信任了”。在他看來,“即使我們再發(fā)動一百場革命,也必須保留共和制度”。在唐紹儀眼里,君主制已經(jīng)被歷史葬送,而共和制需要捍衛(wèi),一個基本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對中國而言是最好的體制”【鄭曦原編:《共和十年:〈紐約時報(bào)〉民初觀察記(1911-1921)·政治篇》,蔣書婉等譯,北京:當(dāng)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第111、112、116頁。】。盡管他對中國傳統(tǒng)政制具有悠久的共和傳統(tǒng)的闡釋有待商榷,但他致力于從傳統(tǒng)中挖掘共和制的資源,以捍衛(wèi)新生的共和國,就足以證明為君主制聚集資源的嘗試,已經(jīng)讓渡給為共和制聚集資源了,哪種政體的現(xiàn)實(shí)活力更足,已經(jīng)不在話下了。
“共和制對中國而言是最好的體制”,可以說是世情、國情、民情注定的,也可以說是世運(yùn)、國運(yùn)與時勢所決定的。五四運(yùn)動之所以如火如荼展開,就是因?yàn)楣埠蛧膬?nèi)外交困,讓國民有了一個現(xiàn)代建國的自覺。對所有后發(fā)的現(xiàn)代建國來講,建國不是高層精英的圈子事務(wù),而應(yīng)當(dāng)是國民們的共同事務(wù)。因此,國民對國家建構(gòu)事務(wù)的覺醒,是其現(xiàn)代建國具有深厚社會力量支持的標(biāo)志。中國的共和建國起自晚清,但被少數(shù)人絕對自私的權(quán)力所阻:他們已經(jīng)意識到立憲共和對國家權(quán)力穩(wěn)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效用,這是晚清立憲變革的權(quán)力動力,但他們又為眼前的權(quán)力利益所宥限,因此很難突破當(dāng)下掌權(quán)的權(quán)力天塹,晚清的立憲改革因此必然失敗。袁世凱、張勛者流,也因?yàn)闆]有意識到共和政制的大趨勢,因此必然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唯有意識到共和制是動員中國民眾投入建國大業(yè),從而為現(xiàn)代建國夯實(shí)社會基礎(chǔ),開創(chuàng)中國前無古人的共治局面,且認(rèn)準(zhǔn)這是遠(yuǎn)遠(yuǎn)勝于一個人與一群人治國理政的現(xiàn)代政治形式,這一趨勢具有人為力量不可逆轉(zhuǎn)的性質(zhì),中國才算確立了現(xiàn)代建國的根本。而“五四”恰恰發(fā)揮出催生相關(guān)力量的作用。就此而言,唯有“五四”,才發(fā)揮出此前所無、此后罕見的拯救共和的巨大作用:“五四”之前,共和是需要自辯的政體形式;“五四”之后,國人對現(xiàn)代共和政制不再懸疑。“五四”之后,形式上君主復(fù)辟嘗試的不見于史,對之作出了有力證明。
當(dāng)然需要指出,“后五四”建構(gòu)并捍衛(wèi)共和的路徑出現(xiàn)了歷史性分岔:激進(jìn)共和壓倒立憲共和,將中國引上一條激進(jìn)政治的不歸路。但這是“五四”之后中國政治諸因素激烈碰撞的偶發(fā)性結(jié)果,并不必然證明中國只能邁進(jìn)在激進(jìn)共和的革命道路上。只要中國政治進(jìn)入正常軌道,全民共和而非貴族共和的現(xiàn)代共和建國路徑,就會堅(jiān)韌地展示給人們。“五四”之隨時叩擊國人的心門,理由在此。
“五四”:在多元闡釋中重建知識敘事
陳衛(wèi)平
(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海200062)
今年是“五四”百年紀(jì)念。如何認(rèn)識和評價“五四”,是中國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新中國建立,直至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根據(jù)毛澤東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有關(guān)論述,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知識體系中形成了大體統(tǒng)一的“五四”敘事。改革開放以來,對于“五四”的認(rèn)識和評價意見紛呈,出現(xiàn)了多元闡釋的情形。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知識體系中重建“五四”敘事,需要辨析以下四個問題。
一、“五四”與全盤反傳統(tǒng)。通行的歷史教科書以及有關(guān)新文化運(yùn)動的論著,都認(rèn)定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把“五四”稱之為全盤反傳統(tǒng)激進(jìn)主義的觀點(diǎn),從海外傳入中國大陸,如今已成描述“五四”的慣用說法,而“打倒孔家店”則是全盤反傳統(tǒng)的激進(jìn)主義標(biāo)識。其實(shí),因“打倒孔家店”而視“五四”為全盤反傳統(tǒng)是沒有說服力的,道理很簡單,儒學(xué)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全部。事實(shí)上,“五四”對于非正統(tǒng)儒學(xué)和先秦諸子(包括孔子)都有肯定。這在以往的知識敘事中常常被忽略了。更值得指出的是,在至今能夠檢索到的“五四”文獻(xiàn)中,沒有出現(xiàn)過“打倒孔家店”,有的只是胡適稱贊吳虞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適:《〈吳虞文錄〉序》,吳虞:《吳虞文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4頁。】。就是說,認(rèn)定“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是沒有史料依據(jù)的。從胡適的序可以看到,所謂“打”的本意是指猶如清掃大街的“清道夫”,掃除孔門儒學(xué)這條大街上的“孔渣孔滓”,使其成為新文化重建的重要地基,因?yàn)榕c渣滓相對的是精華。這意味著清掃“孔渣孔滓”的目的是為了重新認(rèn)識孔子及儒學(xué)的精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義》(此文早于《〈吳虞文錄〉序》兩年)一文中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tài)度。這種新態(tài)度可叫做‘評判的態(tài)度’”,于是“對于舊文化的態(tài)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diào)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xué)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由此達(dá)到“再造文明”的目的;強(qiáng)調(diào)“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tài)度,科學(xué)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不難看出,所謂的“打”,胡適用學(xué)理化語言來說,就是“評判的態(tài)度”。我們不能因“打”或“打倒”的字眼頗有激憤色彩,就給“五四”戴上全盤反傳統(tǒng)的帽子。
事實(shí)上,主張“打孔家店”的胡適在五四時期的論著中,依據(jù)“評判的態(tài)度”,對孔子和儒學(xué)有不少肯定:如《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在評價孔子為人、為學(xué)時,說孔子“有志于政治改良”,是“積極的救世派”,其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為人是“何等精神!”;“孔子的教育哲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又注重標(biāo)準(zhǔn)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孔子的正名論是“中國名學(xué)的始祖,正如希臘梭(蘇)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xué)的始祖”,“孔子論知識,注重‘一以貫之’,注重推論”;孔子“所反對的利,乃是個人自營的私利”等等【胡適:《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19年,第70、76、71、93、104、110、119頁。】;再如《清代學(xué)者的治學(xué)方法》一文指出:“我們平心而論,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合有一點(diǎn)歸納的精神”,“陸王的學(xué)說主張真理即在心中”,體現(xiàn)了“獨(dú)立自由的精神”,而“清代的‘樸學(xué)’確有‘科學(xué)’的精神”,因?yàn)闃銓W(xué)家“有假設(shè)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jù)來證實(shí)假設(shè)的是非”等等【胡適:《清代學(xué)者的治學(xué)方法》,許嘯天編輯:《國故學(xué)討論集》第二集《學(xué)的討論》,上海:群學(xué)社,1927年,第7、13、14、31頁。】。可見,胡適的“打”絕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與“平心而論”的評判相聯(lián)系。
尤其要指出的是,當(dāng)時所要“打”的“孔家店”是以“孔教”為主要對象的。因此,胡適《〈吳虞文錄〉序》既稱贊吳虞“打孔家店”,又稱贊他和陳獨(dú)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胡適:《〈吳虞文錄〉序》,吳虞:《吳虞文錄》,第2頁。】。攻擊孔教是由于袁世凱和張勛的復(fù)辟帝制始終與尊孔相聯(lián)系,而與此呼應(yīng)的孔教會試圖在憲法中將儒學(xué)和孔子確立為國教和教主,維護(hù)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李大釗的《孔子與憲法》、陳獨(dú)秀的《憲法與孔教》等,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無疑,“打”這樣的“孔家店”具有歷史的正當(dāng)性,即把人們從封建意識形態(tài)(孔教)中解放出來。從文獻(xiàn)梳理來看,把“打倒孔家店”作為“五四”的標(biāo)配,定型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初期。這是非難和贊同“五四”的兩方面人士的“共謀”:前者以此鞭撻“五四”要徹底毀滅傳統(tǒng)文化,后者覺得這樣更能表達(dá)批判的徹底性。不過,后者并不由此而認(rèn)為“打倒”意味著全盤反傳統(tǒng)。全面抗戰(zhàn)前夕,由馬克思主義者主導(dǎo)的“新啟蒙運(yùn)動”最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diǎn)。它以“重提五四精神”為號召,認(rèn)為其真正的精神是既要“打倒孔家店”,也要“保衛(wèi)中國最好的文化傳統(tǒng)”【陳伯達(dá):《思想無罪——我們要為“保衛(wèi)中國最好的文化傳統(tǒng)”和“爭取現(xiàn)代文化的中國”而奮斗》,《讀書月報(bào)》1937年第3號(1937年7月5日)。】,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張申府:《什么是新啟蒙運(yùn)動》,《實(shí)報(bào)·星期偶感》1937年5月23日。】。因此,今天重建“五四”的知識敘事,應(yīng)當(dāng)去掉枉加在“五四”頭上的“打倒孔家店”;同時,不能把“五四”的攻擊孔教定性為全盤反傳統(tǒng)的激進(jìn)主義;比較恰當(dāng)?shù)谋硎鰬?yīng)當(dāng)是:“五四”批判孔教表現(xiàn)了批判封建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徹底精神。
二、“五四”與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現(xiàn)在說的“五四運(yùn)動”,通常包含了“新文化運(yùn)動”,這在五四時期已是如此。近些年的論著中,時常出現(xiàn)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造成中華文化命脈“斷裂”的說法。這種說法夸大了“五四”批判傳統(tǒng)中的某些片面性。事實(shí)上,“新文化運(yùn)動”的提出,標(biāo)示著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達(dá)到了新高度。這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新文化運(yùn)動明確地舉起了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旗幟。“新”與“舊”相對,中國近代以來就有“新學(xué)”和“舊學(xué)”之別,前者指外來的西學(xué),后者指本土原有的中學(xué)。所謂新學(xué)與舊學(xué)之爭,蘊(yùn)含著推動中國文化形態(tài)由傳統(tǒng)轉(zhuǎn)向現(xiàn)代的意味。把新文化與“運(yùn)動”尤其是“五四運(yùn)動”相聯(lián)系,主要涵義有兩點(diǎn):一是形容這樣的文化轉(zhuǎn)型猶如“五四”那樣,是聲勢浩大的全方位的大變動;一是描述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主體具有進(jìn)行運(yùn)動時的主動性和能動性。陳獨(dú)秀1920年寫的《新文化運(yùn)動什么》就表達(dá)了這兩點(diǎn):“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nèi)容,是包含著科學(xué)、宗教、道德、美術(shù)、文學(xué)、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yùn)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xué)、宗教、道德、文學(xué)、美術(shù)、音樂等運(yùn)動”;“新文化運(yùn)動要注重創(chuàng)造的精神。創(chuàng)造就是進(jìn)化,世界上不斷的進(jìn)化只是不斷的創(chuàng)造”【陳獨(dú)秀:《新文化運(yùn)動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1920年4月1日)。】。從這兩個方面可見,“五四”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自覺地把全面推動文化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作為自己的使命。這在此前是未曾有過的。
其次,新文化運(yùn)動明確指出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建設(shè)以創(chuàng)造性的會通中西為內(nèi)涵。如上所述,“五四”前基本上把新學(xué)、舊學(xué)與西學(xué)、中學(xué)相對應(yīng),因而舊學(xué)向新學(xué)的轉(zhuǎn)型似乎就是以西學(xué)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tài)。新文化運(yùn)動則對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內(nèi)涵有了新認(rèn)識:不能簡單地將新學(xué)等同于西學(xué),將舊學(xué)等同于中學(xué),因而中國文化的新形態(tài)應(yīng)當(dāng)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也不是模仿西洋,而是中西結(jié)合的新創(chuàng)造。陳獨(dú)秀、胡適、魯迅常常被一些論著作為毀壞中華文化命脈的代表人物,其實(shí),他們都認(rèn)為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必由之路是融合中西的新創(chuàng)造。陳獨(dú)秀指出,新文化運(yùn)動的創(chuàng)造精神,意味著“我們不但對于舊文化不滿足,對于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于東方文化不滿足,對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chuàng)造的余地”【陳獨(dú)秀:《新文化運(yùn)動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1920年4月1日)。】。這里的四個“不滿足”,表明創(chuàng)造會通中西的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再版(對舊文化不滿足),也不是西方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翻版(對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不滿足),同時也是面向未來的(對新文化不滿足)。胡適的《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和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也有類似的意思。
再次,新文化運(yùn)動開始把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展開于眾多文化領(lǐng)域。它沒有把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停留在抽象的討論上,而是貫徹于具體的文化領(lǐng)域。這在五四時期首先表現(xiàn)于“整理國故”即國學(xué)研究方面,因?yàn)樵u判傳統(tǒng)文化是新文化運(yùn)動的重要課題,胡適把“整理國故”作為“新思潮”的題中之義【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1919年12月1日)。】,就反映了這一點(diǎn)。1919年胡適倡導(dǎo)以科學(xué)方法“整理國故”,他說的科學(xué)方法是西方實(shí)證科學(xué)方法與清代漢學(xué)家方法的會通,即把后者“‘不自覺的’(Unconscious)科學(xué)方法”變?yōu)椤白杂X的科學(xué)方法”【胡適:《論國故學(xué)——答毛子水》,《新潮》第二卷第一號(1919年10月)。】。由不自覺變?yōu)樽杂X,也就是對后者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樣的方法論上的中西會通,可以說是建設(shè)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在國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具體化。“古史辨”是當(dāng)時“整理國故”的重頭戲,其核心人物顧頡剛便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明自己深受胡適中西會通的科學(xué)方法的影響【參見顧頡剛:《古史辨·自序》(1926年1月12日-4月20日),《古史辨》第一冊,《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店,1926年,“自序”第30-36頁。】。“古史辨”疑古的觀點(diǎn)現(xiàn)在看來并非全對,但它奠定了古史研究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基礎(chǔ)。由此可見,“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知識體系、學(xué)科體系、話語體系,正是新文化運(yùn)動把建設(shè)中西會通的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深入到具體文化領(lǐng)域的產(chǎn)物。因此可以說,這些體系及其代表性成果是中國文化新形態(tài)的反映。顯然,它們所展示的不是中華文化命脈的斷裂,而是中華文化生命力在與世界潮流同步發(fā)展中得到煥發(fā)。
三、“五四”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五四時期,一批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將其作為指導(dǎo)思想,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對此,通常的知識敘事以李大釗發(fā)表于1919年《新青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作為標(biāo)志,認(rèn)為它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其實(shí),這樣的知識敘事沒有真正揭示出此文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意義。
李大釗此文的重點(diǎn)是在“觀”字上,即“我”觀馬克思主義。這有兩方面的指向:一是指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nèi)容是什么;二是指應(yīng)當(dāng)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果僅就前一方面而言,近些年的相關(guān)研究表明,此文要遜色于稍晚于它兩三個月發(fā)表的胡漢民所著的《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這是合乎事實(shí)的。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節(jié)譯了《神圣家族》等八本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論述,是當(dāng)時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最集中、最完整、最詳盡的介紹。更重要的是它回應(yīng)了九種對于唯物史觀的非難,表現(xiàn)了作者對于唯物史觀的理解頗有深度。如文章指出,批評唯物史觀忽視倫理的精神力量是對唯物史觀的誤解胡漢民:《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建設(shè)》第1卷第5號(1919年12月)。。這很可能是針對李大釗的,因?yàn)槔畲筢摗段业鸟R克思主義觀》就有同樣的誤解,李大釗以為人類理想社會的實(shí)現(xiàn),“不可單靠物質(zhì)的變更”,需要有“改造人類精神”的“倫理運(yùn)動”,因此“近來哲學(xué)上有一種新理想主義的出現(xiàn),可以修正馬氏唯物論,而救其偏蔽”【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5日,本期雜志延至1919年9月出版)。】。由此可以看出,就介紹唯物史觀來說,較之李大釗,胡漢民在學(xué)理上更勝一籌。
然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后一方面的“觀”,那就是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看待馬克思主義。通常的知識敘事涉及李大釗上述“修正”唯物論的意見時,往往將其視為李大釗馬克思主義理論尚不成熟的表現(xiàn)。這固然不錯。但是,李大釗接受而又“修正”馬克思學(xué)說的態(tài)度則是成熟的,因?yàn)檫@表明他沒有把馬克思的學(xué)說看作不容置疑的神圣教條。這種態(tài)度更凸顯在他提出了把馬克思學(xué)說運(yùn)用于中國,絕不能將其照抄照搬:“馬氏的學(xué)說,實(shí)在是一個時代的產(chǎn)物,在馬氏時代,實(shí)在是一個最大的發(fā)見。我們現(xiàn)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huán)境造成的學(xué)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yīng)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fā)見。”在肯定馬克思學(xué)說具有“特別的發(fā)見”的同時,又指出不顧時代歷史條件,把馬克思學(xué)說原封不動地“整個拿來”,以為可以“去解釋一切歷史”,“應(yīng)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是行不通的【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5日)。】。李大釗在略早于此文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中也指出,社會主義理想要“盡量應(yīng)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shí)境”,“變作實(shí)際的形式使合于現(xiàn)在需要”,于是,它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zhì)情形,有所不同”【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事實(shí)上,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前后的三次論戰(zhàn)(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社會主義的論戰(zhàn)、關(guān)于無政府主義的論戰(zhàn)),就是以如何把馬克思主義運(yùn)用于中國“實(shí)境”為核心的,由上引的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可見一斑。李大釗關(guān)于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應(yīng)用于中國的“實(shí)境”,“變作實(shí)際的形式”,也包含著與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他認(rèn)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是以為“俄羅斯之文明”能夠成為“東西文明調(diào)和”的“媒介”【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diǎn)》,《言治》季刊第3冊(1918年7月1日)。】。他還指出:“民族文化者何?即是民族生存活動的效果”,然而,“一個民族都有一個民族的特性,即各民族都有其特別的氣質(zhì)、好尚、性能”【李大釗:《史學(xué)要論》(1924年5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18頁。】。他說不能把馬克思學(xué)說原封不動地“整個拿來”,包含著必須注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特性。因此,他從中西文化的融合來闡釋社會主義理想。他說:“各民族之相異的特殊理想都可認(rèn)為真識,而不是完全的真理。若用哲學(xué)的眼光,把他們這些真識合而為一,乃為完全的真理。”【李大釗:《人種問題》(1924年5月13日),朱文通等整理編輯:《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頁。】社會主義理想正是如此。他指出:“現(xiàn)在世界進(jìn)化的軌道”是走向“達(dá)到世界大同的通衢”,而這不僅以西方近代個性解放為思想資源,也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大同思想相聯(lián)系,“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tuán)結(jié)。這個性解放的運(yùn)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tuán)結(jié)的運(yùn)動。這兩種運(yùn)動,似乎是相反,實(shí)在是相成”【李大釗:《平民主義》(1923年1月),朱文通等整理編輯:《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158頁。】。可見,“五四”的意義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所接受,還在于同時具有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自覺。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為什么“行”、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的歷史出發(fā)點(diǎn)。對此應(yīng)當(dāng)在重建“五四”知識敘事中予以突出。
四、“五四”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在突破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的凝固化框架之后,比較突出的傾向是以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作為考察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于是,原先知識敘事中將“五四”視作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定性變得模糊不清。這里的問題癥結(jié),在于沒有看到中國近代的社會革命和走向現(xiàn)代化是同一歷史進(jìn)程的兩個方面,它們同時起步,又交織在一起。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興起,是以中國如何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為出發(fā)點(diǎn)的。近代民主革命中前后相繼的政治變革或社會變革,都是以反省前一個政治變革或社會變革為何沒有使得中國現(xiàn)代化走上坦途為切入點(diǎn)的。戊戌維新是如此,辛亥革命是如此,“五四”也是如此。因此,這樣的反省包含著社會革命和現(xiàn)代化兩方面的內(nèi)涵。“五四”的醞釀、興起和發(fā)展,在社會革命方面反省辛亥革命的失敗,認(rèn)識到了發(fā)動廣大群眾進(jìn)行直接斗爭的必要性。陳獨(dú)秀在1916年說,“共和立憲而不出于多數(shù)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并將之歸為“吾人最后之覺悟”【陳獨(dú)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李大釗指出,十月革命表明皇帝、貴族、軍閥、官僚等在“群眾運(yùn)動”的力量面前,“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fēng)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五四”由文化運(yùn)動發(fā)展為群眾運(yùn)動,由此成為了新民主義革命的開端。這在以往的知識敘事中已經(jīng)有了很多論述。“五四”以民主和科學(xué)為旗幟,是從現(xiàn)代化方面反省辛亥革命失敗而來的,陳獨(dú)秀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中說:“國人而欲脫蒙昧?xí)r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dāng)以科學(xué)與人權(quán)并重。”【陳獨(dú)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認(rèn)為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必須以科學(xué)和民主作為價值指引,為中國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樹立了明確的價值原則。這是辛亥革命所缺失的。
“五四”精神哺育下誕生的中國共產(chǎn)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lǐng)導(dǎo)者,又以實(shí)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化為使命。應(yīng)當(dāng)說,后一方面在以往知識敘事中非常薄弱。事實(shí)上,毛澤東關(guān)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jīng)典著作,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都再三強(qiáng)調(diào)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中國由“農(nóng)業(yè)國轉(zhuǎn)變?yōu)楣I(yè)國”的現(xiàn)代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shí)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xiàn)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chǎn)力的,還是解放生產(chǎn)力的。”【毛澤東:《論聯(lián)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頁。】從發(fā)展現(xiàn)代生產(chǎn)力出發(fā),毛澤東指出,“從農(nóng)業(yè)基礎(chǔ)到工業(yè)基礎(chǔ),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wù)”;“如果我們永遠(yuǎn)不能獲得機(jī)器,我們就永遠(yuǎn)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并認(rèn)為是否這樣看待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區(qū)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xiàn)選編(1921-1949)》第21冊,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第484頁。】。因此,他在1948年提出,必須批判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的思想”,當(dāng)時新華社發(fā)表《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問答》對此作了系統(tǒng)闡述【《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的問答》(1948年7月27日新華社信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1948年),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659-665頁。】。重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知識敘事,無疑應(yīng)當(dāng)對此予以重視。
因?yàn)樯鐣锩同F(xiàn)代化訴求是中國近代歷史進(jìn)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兩個方面,所以某些在以往“五四”革命敘事中被忽視或被否定的人物和思潮往往具有某種合理性。如五四時期及以后出現(xiàn)的“科學(xué)救國”“教育救國”“實(shí)業(yè)救國”,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于科學(xué)和民主的價值原則的肯定,表現(xiàn)了對于推動中國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歷史擔(dān)當(dāng)。還有五四時期形成氣候的自由主義思潮和開始崛起的現(xiàn)代新儒家思潮,前者對于民主價值的維護(hù),后者反思科學(xué)在現(xiàn)代社會的異化,都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如自由主義者1922年在《努力周報(bào)》發(fā)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把政治監(jiān)督、個人自由和社會福利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內(nèi)容【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bào)》第2期(1922年5月14日)。】,盡管這里存在空幻的色彩,但反對軍閥和政客操縱政府,是符合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要求的。開創(chuàng)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的梁漱溟說:“今日科學(xué)發(fā)達(dá),智慮日周,而人類顧有自己毀滅之慮。”【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成都:路明書店,1949年,第143頁。】這不僅是指科學(xué)造就了人類能夠相互大規(guī)模殘殺的武器,更是指科學(xué)導(dǎo)致西方對于物質(zhì)世界“風(fēng)馳電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淪喪苦悶”【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梁漱溟全集》第1卷,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8頁。】,把如何克服科學(xué)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負(fù)面結(jié)果的問題加以凸顯,有助于正確把握作為價值原則的科學(xué)。因此,在重建的“五四”知識敘事中,對于“五四”在中國近代歷史進(jìn)程的意義,應(yīng)當(dāng)指出它既是新民主義革命的開端,同時又首先確立了現(xiàn)代化的價值原則。
“文學(xué)革命”與中國現(xiàn)代“人生論”文藝觀的確立
譚好哲
(山東大學(xué)文藝美學(xué)研究中心教授 山東濟(jì)南250100)
一
以倡導(dǎo)“文學(xué)革命”而著稱史冊的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是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標(biāo)志性歷史節(jié)點(diǎn),自此以后,中國文學(xué)正式走向“現(xiàn)代”之路,這個現(xiàn)代是時間維度上的,更是精神維度上的。自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開始,中國文學(xué)就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東方殖民擴(kuò)張與西學(xué)東漸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之下開始了現(xiàn)代性歷史轉(zhuǎn)型,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興起,特別是“文學(xué)革命”的發(fā)動則自覺地將這種轉(zhuǎn)型推向了一個高光時刻。因此,在五四運(yùn)動百年紀(jì)念活動中,萬萬不可忘記“文學(xué)革命”對于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引領(lǐng)作用,更不可忘記“文學(xué)革命”對百年來中國文學(xué)的范式塑造意義。
在學(xué)界,人們經(jīng)常會把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與歐洲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相提并論,就二者都是推動社會歷史由古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偉大思想文化運(yùn)動而言,這種提法有一定道理。然而,二者在運(yùn)動的表現(xiàn)形式上卻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近代的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是借了復(fù)興古希臘羅馬文化和藝術(shù)的形式傳播人文主義的新思想,而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則是以徹底反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姿態(tài)引領(lǐng)運(yùn)動潮流的,在這一點(diǎn)上,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倒更像是17、18世紀(jì)歐洲特別是法國以理性之光驅(qū)散黑暗,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新思想激烈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宗教愚昧的啟蒙運(yùn)動。啟蒙運(yùn)動著力于人的啟蒙和解放,最終使歐洲諸國走進(jìn)現(xiàn)代文明國家前列。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也著力于人的啟蒙和解放,力圖在對現(xiàn)代文明的追求中使民族和國家強(qiáng)大起來,所以說它從直接的起因上看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巴黎和會”引發(fā)的一場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yùn)動,而從深層思想文化層面上看則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yùn)動。如果我們從社會轉(zhuǎn)型和思想啟蒙的角度來看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以及百年來的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歷程,必須首先承認(rèn),五四新文化以及新文學(xué)運(yùn)動中的確有許多文化和文學(xué)觀念不是從我們自身的文化和文學(xué)傳統(tǒng)中內(nèi)生出來的,而是從近現(xiàn)代的西方國家中引進(jìn)過來的,或者是在西學(xué)東漸的沖擊中新生出來的,屬于與傳統(tǒng)國學(xué)相對而言的西學(xué)或新學(xué)范疇。而在這其中,貫穿百多年、在不同時期起起伏伏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就是藉由五四“文學(xué)革命”才確立下來的一種嶄新的現(xiàn)代性文學(xué)觀念。
具有現(xiàn)代意識、以現(xiàn)代人學(xué)觀念為基礎(chǔ)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雖然在以梁啟超為主要代表的近代文學(xué)革新運(yùn)動中就已初露先聲,但主要是在五四“文學(xué)革命”運(yùn)動時期才真正確立起來的。在1918年12月發(fā)表的《人的文學(xué)》一文中,周作人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文學(xué)”主張:“我們現(xiàn)在應(yīng)該提倡的新文學(xué),簡單地說一句,是‘人的文學(xué)’,應(yīng)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xué)。”【周作人:《人的文學(xué)》,《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此后不久,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學(xué)》一文中提出了“平民文學(xué)”這一口號,作為人的文學(xué)的補(bǔ)充,把人具體化為平民也就是普通民眾,并且像陳獨(dú)秀在《文學(xué)革命論》一文中論國民文學(xué)一樣把平民文學(xué)與貴族文學(xué)相對立;同時,他還在此文中以及1920年初所作的《新文學(xué)的要求》里,將他所推崇的文學(xué)觀稱為“人生的藝術(shù)派”。周作人的文學(xué)主張,在當(dāng)時獲得了廣泛的響應(yīng)。比如,文學(xué)研究會的代表人物茅盾(沈雁冰)在1921年的《文學(xué)和人的關(guān)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xué)者身分的誤認(rèn)》一文中也主張“人是屬于文學(xué)的。文學(xué)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xiàn)人生”,“文學(xué)到現(xiàn)在也成了一種科學(xué),有他研究的對象,便是人生——現(xiàn)代的人生”【賈植芳等編:《文學(xué)研究會資料》(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頁。】。在1922年《文學(xué)與人生》的演講里,他又說:“西洋研究文學(xué)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標(biāo)語:是‘文學(xué)是人生的反映’。人們怎樣生活,社會怎樣情形,文學(xué)就把那種種反映出來。”【賈植芳等編:《文學(xué)研究會資料》(上),第88頁。】胡適后來在評價《人的文學(xué)》時說:“這是一篇最平實(shí)偉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們那個時代所要提倡的種種文學(xué)內(nèi)容,都包括在一個中心觀念里,這個觀念他叫作‘人的文學(xué)’。”【胡適:《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建設(shè)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導(dǎo)言”第20-21頁。】胡適的話并非溢美之辭,“人的文學(xué)”或曰“人生論”的文學(xué)觀,的確是中國現(xiàn)代新文學(xué)先驅(qū)者們普遍追求的一種具有時代主旋律性質(zhì)的文學(xué)觀念。
在“人的文學(xué)”或“人生論”文學(xué)觀念的引領(lǐng)之下,五四時期的作家紛紛轉(zhuǎn)向?qū)ι鐣松年P(guān)注和反映,涌現(xiàn)出了大量易卜生式的“問題小說”和“問題劇”,并且產(chǎn)生了“表現(xiàn)自我”的自覺文學(xué)追求,出現(xiàn)了郭沫若的《女神》與郁達(dá)夫的“自敘傳”抒情小說等將時代精神與個人生活、個人情緒、個性表達(dá)有機(jī)融合的優(yōu)秀作品,創(chuàng)造了中國新文學(xué)的華麗開篇。今天,當(dāng)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diǎn)上回望“五四”的時候,依然不能不高度重視“人生論”文學(xué)觀的張揚(yáng)與確立對百年來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及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如果說五四“文學(xué)革命”從文學(xué)的載體形式上確立了白話文在此后中國文學(xué)書寫中的正宗地位的話,那么對人的發(fā)現(xiàn),對人生論文學(xué)觀的張揚(yáng),則為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歷史品性的塑造奠定了精神底色。百年來中國文學(xué)的寬廣歷史向度的形成,深邃人性深度的呈現(xiàn),及其對于人性解放、民族復(fù)興和歷史進(jìn)步所產(chǎn)生的巨大精神推動作用,都與“人生論”文學(xué)觀的歷史展開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可以說,“人生論”文學(xué)觀作為一種新的文學(xué)觀念,不僅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中,而且也在此后——比如20世紀(jì)80年代——的思想啟蒙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當(dāng)代中國的文學(xué)發(fā)展中依然是有其積極思想意義的構(gòu)成力量。
二
在國內(nèi)學(xué)界,有學(xué)者把“立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和“文學(xué)革命”的一個基本時代主題加以言說和分析。這一時代主題的產(chǎn)生有其歷史語境。在中國社會由古代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過程中,人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即由依附于傳統(tǒng)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不自由的臣民向具有獨(dú)立個性和民主權(quán)利的自由公民的轉(zhuǎn)變是一個根本的方面,而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包括“文學(xué)革命”的發(fā)動正是與此相表里,或者說正是因應(yīng)這一歷史要求而加以展開的。
揆諸歷史,立人的問題從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之初就已經(jīng)提出來了。19世紀(jì)中葉以后,面對西方堅(jiān)船利炮的銳利打擊和思想文化的強(qiáng)烈沖擊,在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面臨生死存亡的關(guān)頭,梁啟超、王國維他們那一代人就從保國保種、延續(xù)中華文明的角度提出了以教育、文化的革新改良國民性也就是“新民”的歷史任務(wù)。按照他們的邏輯,面對外來強(qiáng)權(quán)的侵略欺侮,中華民族國將不國、種亦難保,怎么辦?那就要“變法”,走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路,也就是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就得有與民主共和制度相匹配的民眾,要把中國人從天子的臣民變成具有民主權(quán)利的平等、自由的公民。然而,問題是傳統(tǒng)封建社會里不會自動生長出這樣的公民,因此必須以具有現(xiàn)代意識和現(xiàn)代內(nèi)容的新教育和新文化來培育出這樣的公民,于是便有了以新教育、新文化來改造國民性、新一代之民的“新民”說的產(chǎn)生。梁啟超鼓吹“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王國維倡導(dǎo)新式教育和“美育”,其主旨都在于此。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啟超等人那里,雖然其變法的根據(jù)來自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民權(quán)思想,但對民族和國家命運(yùn)的憂思是占了主導(dǎo)位置的,因而其思想觀念中對“共和”或“群治”的看重遠(yuǎn)遠(yuǎn)超出個人自由或個性解放,盡管“群治”包含了個人之間的平等這一前提在內(nèi),但梁啟超那個時代的思想家側(cè)重點(diǎn)其實(shí)還是在人國之立的“群”和“共”的方面,卻也是不爭的事實(shí)。
與梁啟超等人思路有異的是魯迅先生。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幾篇文章里提出了以文藝“立人”的思想。先是在《科學(xué)史教編》中,他一方面描述了科學(xué)昌明對西方社會發(fā)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防止偏倚科學(xué)一極而使“精神漸失”“人生必大歸于枯寂”的狀況,在科學(xué)之外還需要文藝,因?yàn)槲乃嚲哂小爸氯诵杂谌钡墓δ堋爵斞福骸犊茖W(xué)史教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5頁。】。在《文化偏至論》里,他指出19世紀(jì)末葉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重物質(zhì)、重眾數(shù),當(dāng)時一般維新人士也極力推重這二者,而他則不以為有當(dāng)。他認(rèn)為過于重物質(zhì)會壓抑精神的發(fā)展,而共和民主政治對“眾數(shù)”的追崇也可能流入借眾以凌寡的民主空名,將古代的獨(dú)夫治國頓變?yōu)榍f無賴之尤的“眾數(shù)”政治。為此,魯迅提出:“誠若為今立計(jì),所當(dāng)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人既發(fā)揚(yáng)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7頁。】他還指出,不能發(fā)揮精神的輝光于人生為無當(dāng),“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義也”【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5頁。】。在此文中,魯迅還根據(jù)對法國大革命及其后來發(fā)展的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特別是對中國的歷史積習(xí)的分析,明確指出:“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8頁。】而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又為圖“國民精神之發(fā)揚(yáng)”而別求新聲于異邦,滿懷激情與敬意介紹了西方國家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派”。他不僅盛贊摩羅詩人們“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fā)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101頁。】,更期望中國文學(xué)能有“精神界之戰(zhàn)士”應(yīng)時而生,作至誠之聲,致國人于善美剛健,作溫煦之聲,援國人出于荒寒。由這些文章可見,魯迅雖然也追求國家的富強(qiáng),但他認(rèn)為這全然要以國人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dú)立為前提,立人是立國的前提,這使他的思想超出了梁啟超一輩。不過,由于魯迅當(dāng)時還在留學(xué)時期,文章都發(fā)表于日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只在留日學(xué)生間傳播,所以其思想影響不廣。只是到了五四時期,類似魯迅的這種思想觀點(diǎn)才經(jīng)由《新青年》雜志的鼓吹逐漸蔓延而成為時代的強(qiáng)音。
長期以來,人們以德、賽二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xué)來概括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精神。王元化先生則認(rèn)為“獨(dú)立的思想和自由之精神”才是五四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思想成就“主要在個性解放方面,這是一個‘人的覺醒’時代”【《王元化對“五四”的思考》,王元化:《清園近思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8年,第73-74頁。】。就陳獨(dú)秀等新文化運(yùn)動先驅(qū)們的言論來看,這個判斷有其根據(jù)。比如說,陳獨(dú)秀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的《敬告青年》中就以成就近世歐洲“解放歷史”的“人權(quán)平等之說”為依據(jù),把“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作為對中國青年的第一個啟蒙要求,說“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陳獨(dú)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1915年9月15日)。】。他還曾在1915年的《青年雜志》上,先后發(fā)表了《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和《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兩文。在前文中,他將歐洲文明和法蘭西文明歸結(jié)為人權(quán)說、生物進(jìn)化論、社會主義三個方面,而把人權(quán)說放在首位,特別推崇法蘭西人以《人權(quán)宣言》為代表的“平等、自由、博愛”的思想,并視之為近世文明的靈魂【陳獨(dú)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1915年9月15日)。】。在后文中比較中西民族的思想文化差異時,他認(rèn)為其中一個差異在于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擁護(hù)個人之自由權(quán)利與幸福是西方社會的向往與追求,由于有了思想言論的自由,故有個性之發(fā)展,有個人之自由權(quán)利,故有個人平等【陳獨(dú)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一卷第四號(1915年12月15日)。】。此后,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陳獨(dú)秀又對于肩負(fù)個人、國家、民族新生責(zé)任的青年們的思想動作,提出了他的期望:一是要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二是要尊重個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三是從事國民運(yùn)動,勿囿于黨派運(yùn)動【陳獨(dú)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五號(1916年1月15日)。】。由陳獨(dú)秀的這些言論來看,五四新文化的鼓吹者在一開始,就像以上所述的魯迅先生一樣,其實(shí)是把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礎(chǔ)上的個人獨(dú)立、個性發(fā)展、個人自由也就是人的覺醒和人性解放置于民族、國家和文化改良的首要的或核心的位置上來加以看待的。這樣一種富有人性底蘊(yùn)和人生情懷的文化觀念當(dāng)然不能不在文學(xué)觀念上表現(xiàn)出來。可以說,“文學(xué)革命”論包括以“人的文學(xué)”主張為代表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正是由此而發(fā)生的。
三
五四“文學(xué)革命”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xué)”主張是建立在現(xiàn)代人道主義觀念之上的,有其特定的人性內(nèi)蘊(yùn)。周作人指出,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他之所以提出“人的文學(xué)”,意在“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fā)見‘人’,去‘辟人荒’”,“希望從文學(xué)上起首,提倡一點(diǎn)人道主義思想”。他還明確說他所謂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而“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xué)”。他認(rèn)為,“人的文學(xué)”對于人生的描寫包含理想與寫實(shí)兩方面:“(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dá)的可能性。(二)是側(cè)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周作人:《人的文學(xué)》,《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1918年12月15日)。】在兩類描寫中,他更重視后一類,認(rèn)為這類描寫數(shù)量最多,也最重要,可以因此使人明白人生實(shí)在的情狀,與理想生活相比較,找出差異與改善的方法。所以,他所謂“人的文學(xué)”著眼于文學(xué)的人性內(nèi)涵,注重個人權(quán)利與個性的張揚(yáng),目的在于促成人生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發(fā)展。同是在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雜志的“易卜生專號”上發(fā)表的《易卜生主義》,欣賞易卜生的寫實(shí)主義“肯說老實(shí)話”,“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shí)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xì)看”,又贊揚(yáng)他在揭露社會弊端的同時,“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它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fā)達(dá)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1918年6月15日)。】。這其實(shí)表達(dá)的是與周作人一樣的人生論的文學(xué)觀。
可以說,以人道主義為精神底色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是五四時期最具時代特征的代表性文學(xué)觀念,也是那個時代文學(xué)中最為深沉、最具感召力的內(nèi)在精神構(gòu)成力量。對人生問題的關(guān)注,不僅表現(xiàn)在五四文學(xué)革命的倡導(dǎo)者們身上,也幾乎體現(xiàn)在那個時代所有新文學(xué)家的創(chuàng)作中。在一篇關(guān)于“五四”的反思文章里面,胡風(fēng)先生指出:“借用‘人底發(fā)現(xiàn)’這一個舊的說法來形容‘五四’底歷史意義,雖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錯的。”以此而論,“當(dāng)時的‘為人生的藝術(shù)’派和‘為藝術(shù)的藝術(shù)’派雖然表現(xiàn)出來的是對立的形勢,但實(shí)際上卻不過是同一根源底兩個方向。前者是,覺醒了的‘人’把他的眼睛投向了社會,想從現(xiàn)實(shí)底認(rèn)識里面來尋求改革底道路;后者是,覺醒了的‘人’用他的熱情膨脹了自己,想從自我底擴(kuò)張里面叫出改革底愿望。如果說,前者是帶著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傾向,那后者就帶有浪漫主義的傾向了,但他們卻同是屬于在市民社會出現(xiàn)的人本主義底精神”【胡風(fēng):《文學(xué)上的五四——為五四紀(jì)念寫》,《胡風(fēng)評論集》(中),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第122-123頁。】。這就是說,五四時期的文學(xué)其實(shí)都是人生論的,而且都是以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為思想基礎(chǔ)的。
人生論的文學(xué)觀不僅體現(xiàn)了五四時期“文學(xué)革命”論在更為宏大的層面上對中國文化與社會之革故鼎新的追求,而且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性新文學(xué)直面現(xiàn)實(shí)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啟蒙的優(yōu)良精神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是由五四“文學(xué)革命”造就的嶄新傳統(tǒng),它不僅截然劃出了中國現(xiàn)代性新文學(xué)與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精神分界,而且使中國現(xiàn)代性新文學(xué)進(jìn)入“世界文學(xué)”之林,獲得了與世界各國現(xiàn)代性文學(xué)進(jìn)行交流與對話的資格。中國百年來那些最為優(yōu)秀的文學(xué)家和文學(xué)作品,如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dá)夫、巴金、老舍、曹禺等優(yōu)秀作家,以及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的諸多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新寫實(shí)主義文學(xué)”等等,無不成就于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視與人道主義精神的內(nèi)在浸潤。然而,這樣一種優(yōu)秀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卻在后來的發(fā)展中被導(dǎo)向兩個不同方向,一個是導(dǎo)向純粹抽象的人性論方向,一個是導(dǎo)向摒棄人性的階級論方向,比如20世紀(jì)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以“新月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作家與“太陽社”和后期“創(chuàng)造社”等為代表的“革命文學(xué)”、無產(chǎn)階級文藝派作家的對立就是如此。糟糕的是,這兩種傾向,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中依然存在。比如,在20世紀(jì)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相當(dāng)長一段時期內(nèi),主流文學(xué)就連文學(xué)要表達(dá)人性、人情這種觀念都不容許存在,就連從無產(chǎn)階級作家高爾基那里發(fā)展出來的“文學(xué)是人學(xué)”的觀點(diǎn)都一度成為修正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而遭到批判和禁絕,而在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的某些所謂文化反思小說和尋根文學(xué)創(chuàng)作,則往往完全剝離掉人的階級性以至一切社會屬性,而把人生描寫導(dǎo)向抽象的人性論以至人的動物性本能方面。這兩種傾向都是對五四時期“人生論”文學(xué)觀的背離,并由此而對文學(xué)的健康發(fā)展造成需要加以深切反思的負(fù)面影響。
令人欣慰的是,“文學(xué)是人學(xué)”命題在改革開放的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重新得到認(rèn)可。人重新被置于文學(xué)舞臺的中心位置,從而使得當(dāng)代文學(xué)獲得蓬勃發(fā)展的強(qiáng)勁生命動力,這從一個重要側(cè)面象征著對于五四時期人生論文學(xué)觀這一新文學(xué)正統(tǒng)的重新接續(xù)。尤其需要指出的一點(diǎn)是,當(dāng)巴人、王淑明、錢谷融等人在1957年分別發(fā)表《論人情》《論人性與人情》《論“文學(xué)是人學(xué)”》,把人作為文學(xué)的中心、核心加以論證時,都是以人道主義作為其文學(xué)人學(xué)的思想基礎(chǔ)的。比如錢谷融就不僅在《論“文學(xué)是人學(xué)”》中強(qiáng)調(diào)了“文學(xué)是人學(xué)”命題中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而且在撥亂反正的新時期文學(xué)初期發(fā)表的《〈論“文學(xué)是人學(xué)”〉一文的自我批判論綱》里再次明確指出:“文學(xué)既然以人為對象,當(dāng)然非以人性為基礎(chǔ)不可”,“作家的美學(xué)理想和人道主義精神就應(yīng)該是其世界觀中對創(chuàng)作起決定作用的部分”【錢谷融:《〈論“文學(xué)是人學(xué)”〉一文的自我批判論綱》,《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可見,面向人生的文學(xué)書寫,是不能割裂開其與人道主義的內(nèi)在血脈關(guān)聯(lián)的。因此,當(dāng)我們在今天反思和總結(jié)中國文學(xué)百年來的發(fā)展歷程的時候,必須充分重視以“人的文學(xué)”主張為代表的“人生論”文學(xué)觀及其人道主義思想內(nèi)核的精神啟蒙價值和文學(xué)范式意義。只有對濫觴于五四“文學(xué)革命”時期的這樣一種重要文學(xué)觀念加以充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而對百年來的中國文學(xué)的優(yōu)長在什么地方,失誤在什么地方加以歷史的、實(shí)事求是的分析和研判,才有利于繼承新文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中國文學(xué)未來的發(fā)展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chǔ)。
從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反思“五四”
方朝暉
(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 北京100084)
五四運(yùn)動向我們提出的一個最深刻的問題是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一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現(xiàn)代性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恰當(dāng)定位,其根本原因就是因?yàn)槲覀儗τ谥袊幕纳顚有睦斫Y(jié)構(gòu)了解不夠深刻。換言之,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理解還是不夠深。導(dǎo)致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理想化接受有關(guān)。20世紀(jì)以來中國人從自由主義那里學(xué)到了什么?他們學(xué)到的東西有的好、有的壞,但我認(rèn)為其中最壞的東西之一就是制度決定論(甚至是政體決定論)。
迄今為止,歷史的教訓(xùn)依然不能使很多人清醒過來,依然深深地迷戀著某種理想的、來自西方的社會制度。事實(shí)上,在人類任何一個文化當(dāng)中植入一種制度的前提是要認(rèn)識到,這個文化的心理基礎(chǔ)是否真的適合于它。盡管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都可能變化,不可能一成不變,但是我們?nèi)绻皇菑恼軐W(xué)建構(gòu)的立場,而是基于純經(jīng)驗(yàn)的判斷和分析,即可發(fā)現(xiàn),文化心理基礎(chǔ)有時是非常強(qiáng)固、最難動搖的。這不是說文化心理的所有層面都難以改變,而是指有些方面,比如在此岸取向、關(guān)系本位和團(tuán)體主義這三個方面,迄今為止中國文化與三千多年前沒有大的變化。
一
我曾多次指出,過去三千多年來,中國文化建筑在一個基本預(yù)設(shè)——此岸取向的基礎(chǔ)上,并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關(guān)系本位和團(tuán)體主義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這是我們今天理解中國現(xiàn)代性的重要前提,也是本文反思“五四”的主要視角。
(一)此岸取向,認(rèn)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是真實(shí)而唯一的,對于死后生命是否繼續(xù)存在持不確定立場。數(shù)千年來,中國人以“天地”為最大,一切生命,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了的,都逃脫不了天地的范圍。至于天地之外是否有天地,六合之外是否有六合,中國人非但存而不論,實(shí)際上并不相信。正因?yàn)椤胺ㄏ竽蠛跆斓亍保省芭c天地準(zhǔn)”“彌綸天地之道”就成了最高學(xué)問(《易傳·系辭》)。此后,孟子欲“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董仲舒欲“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玉英》),張載則欲“為天地立志”張載:《張子語錄·語錄中》,張載著,章錫琛點(diǎn)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20頁。。因此,一切的學(xué)問探索,一切的人生追求,都以天地為最后歸宿。
人們也許會說,中國人不是也十分重視道、天道、天理等所謂“形而上”的超越存在嗎?誠然,中國人當(dāng)然有超越日常經(jīng)驗(yàn)、實(shí)現(xiàn)精神不朽的終極價值追求,但這種價值追求從根本上講是屬于此岸、服務(wù)于此世的。中國人并不會在“這個世界”之外去尋找“道”,他們所謂“道”本指此岸世界的正確道路,或者說,是為了引導(dǎo)人們行走于此岸。《莊子·知北游》中如下一段話極能說明“道”不離此岸:
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后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此外,《中庸》也極論“道不遠(yuǎn)人”,所謂“道不遠(yuǎn)人”,實(shí)指“道”之所以為“道”,是因?yàn)樗砹巳藗惾沼贸P兴?dāng)遵行的道路。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此岸取向?qū)е铝酥袊嗽缭谙惹鼐托纬闪司d延幾千年的天道觀,導(dǎo)致中國人以“天人合一”為最高理想。因?yàn)橹袊说氖澜缰挥小斑@一個”,所以最擔(dān)心的就是這個獨(dú)一無二的世界不安寧、不太平,因?yàn)檫@是他們安全感的終極保證。也正因如此,他們不僅在信仰上追求天人合一,也在世務(wù)中崇尚天下一家,在政治上向往九州大同。由于世界只有“這一個”,人們對這個世界紛擾混亂的擔(dān)憂極為強(qiáng)烈,所以諸子百家皆以治國平天下為宗旨,即所謂“皆務(wù)于為治”(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像公孫龍子、惠施等人那樣關(guān)注一些抽象、無關(guān)乎實(shí)用的思辨問題,在中國文化中就發(fā)達(dá)不起來。
作為中國文化之前提預(yù)設(shè)的“此岸取向”,在《易經(jīng)》的“陰陽之道”以及五帝的“絕地天通”中已經(jīng)成型,在十三經(jīng)及先秦諸子處則得到了清晰淋漓的展現(xiàn)。它實(shí)際上規(guī)定了中國文化后來兩千多年的基本路徑。它的獨(dú)特之處,只有通過與希臘文化、猶太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印度文化進(jìn)行對比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而它對中國文化的深遠(yuǎn)影響,可通過其所造就的關(guān)系本位而非個人本位、團(tuán)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等得到理解。
(二)關(guān)系本位。由于中國人的世界只有“這一個”,由于死后生命形態(tài)不夠確定,導(dǎo)致中國人以此生此世為人生最高目標(biāo);于是,應(yīng)對人在此世所遭遇的關(guān)系和處境,成為每個人或集體的主要任務(wù)(關(guān)系本位也可理解為處境本位)。在人遭遇的所有關(guān)系中,人倫關(guān)系最為基本,而人倫關(guān)系以人情和面子為基本機(jī)制。面子是正常交往的底線,人情是積極交往的動力。數(shù)千年來,在人情和面子的基礎(chǔ)上安頓人倫,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和政治事業(yè)中最重要的任務(wù),此即《中庸》所謂“五達(dá)道”。
關(guān)于中國文化的關(guān)系本位(或稱關(guān)系主義),目前已經(jīng)有大量人類學(xué)、文化學(xué)、心理學(xué)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啟示【較有代表性針對東亞的研究參Richard E. Ni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較系統(tǒng)的評述見A.Fiske, S.Kitayama, H.R.Markus, R.E.Nisbett,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 Gilbert, S. Fiske, and G.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San Francisco: McGraw-Hill, 1998), 915-981.】。
關(guān)系本位決定了中國人的關(guān)系世界呈現(xiàn)出親疏、遠(yuǎn)近、內(nèi)外有別的“差序格局”(費(fèi)孝通語)參見費(fèi)孝通:《差序格局》,《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29頁。。由此可以解釋為何梁啟超說儒家一切道德皆以私德為基礎(chǔ),為何五倫三綱成為社會安定的基礎(chǔ),為何禮大于法成為中國制度的需求,為何儒家會在中國長盛不衰,為何儒道釋互補(bǔ)成為中國人信仰世界的主流,等等。
關(guān)系本位重視人與人以“血?dú)庑闹浴保ā抖Y記·樂記》)為基礎(chǔ)的心靈感通與心心相映,與個人主義主張人與人相互獨(dú)立、靈魂屬于彼岸、生命不屬于也不能交給任何世人或集體等完全不同。個人主義是西方現(xiàn)代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基礎(chǔ),是西方民主、法治得以良好運(yùn)行的文化心理土壤,但這一土壤在中國文化并不深厚。
(三)團(tuán)體主義。由于“天道遠(yuǎn),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天道、天理無法對終極救贖給予明確的承諾和絕對的保證,中國人覺得在世俗生活中能夠?qū)崒?shí)在在給自己帶來安全感的東西,要么是私人關(guān)系,要么就是由私人關(guān)系構(gòu)成的親近團(tuán)體。親近團(tuán)體(primary groups)乃是關(guān)系的另一種形式,通常由共同血緣、身份、家鄉(xiāng)、工作等因素構(gòu)成。中國人需要在這種關(guān)系性親近團(tuán)體中找到安全感。這在文化心理學(xué)上稱為文化團(tuán)體主義(collectivism)。
自20世紀(jì)70年代末以來,由于歐洲學(xué)者格特·霍夫施塔特(Geert Hofstede)的開創(chuàng),以及后來以美國伊利諾斯大學(xué)心理學(xué)家特里安迪斯(H. C. Triandis)及其一大批弟子或同道(如 Kwok Leung, M. H. Bond, etc.)的跟進(jìn),人們對文化團(tuán)體主義經(jīng)過多年的研究,已經(jīng)積累了一大批成果。其中霍夫施塔特甚至將世界各國的團(tuán)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指數(shù)量化,構(gòu)成了一個系統(tǒng)的數(shù)據(jù)庫【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abridged edition (California: 1980/1984).系統(tǒng)性評價參D. Oyserman, H.M. Coon, and M. Kemmelmeier,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svol.128(2002): 3-72.】。大抵來說,我認(rèn)為文化團(tuán)體主義將以所在集體為個人安全感的主要來源,個人自我歸屬感也落腳于集體或團(tuán)體;而個人主義正好相反,以個人自身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寄托,個人自我歸屬感也落腳于個人而非集體或團(tuán)體。
中國文化中的團(tuán)體主義導(dǎo)致中國人的世界里盛行圈子意識、地方主義、小團(tuán)體主義和幫派主義,也塑造了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這種關(guān)系性團(tuán)體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同黨”而加以批評,因?yàn)樗菀籽葑兂蔁o理性的情緒化爭斗,從而斷送公道和正義。這種團(tuán)體主義,是與費(fèi)孝通所謂的西方文化的“團(tuán)體格局”完全不同的。后者以個人本位為基礎(chǔ)、以自愿性契約為前提,因而個人不需要將自己的生命整個地交給任何團(tuán)體或組織。相反,個人退出團(tuán)體以及不受所在團(tuán)體(包括國家、組織、單位等)約束的自由被視為至關(guān)重要。
可以說,家族主義所以在中國文化中興盛,正是因?yàn)橹袊嗽诓钚蚋窬只A(chǔ)上更能接受“愛有差等”的社會組織方式,以及與此相應(yīng)的團(tuán)體生活。中國式團(tuán)體主義對于我們理解為何西式民主在中國文化中遇到了巨大障礙,容易變質(zhì)變味,提供了極有意義的視角。
二
鴉片戰(zhàn)爭180年來,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體制已天翻地覆,現(xiàn)在我要問:這些重大變化動搖了中國文化的上述三重深層結(jié)構(gòu)了嗎?我的回答是沒有。
五四運(yùn)動100年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文化視野、世界處境已今非昔比,但是我要問:這些重要改變意味著中國人能在民主、自由、法治中安身了嗎?我的回答是不然。
只有從上述三重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出發(fā),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千年有效的制度和價值。只要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沒有改變,其主流價值和最有效的制度形式也難以改變。這不是說我們今天不需要學(xué)習(xí)西方制度和價值,而是要認(rèn)清什么是中國文化中最有效的制度和價值。雖然今天的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已與古代迥然不同,我們不可能、也無需完全回歸古代政治及制度,不可能、也無需完全照搬古人價值及生活,但我們必須正視前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及其在塑造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的制度和價值方面無與倫比的作用。
民主、自由當(dāng)然是好東西,當(dāng)然有普世價值。不過我們要清楚,普世價值不等于核心價值。民主、自由在西方是核心價值,在中國是普世價值,而不是核心價值。核心價值是指對于特定文化有特別效用的最重要價值。同樣的道理,“三綱五常”也有普世價值,但未必能成為其他文化的核心價值;相反,“三綱五常”不僅在古代中國是核心價值,而且在未來中國能否仍成為核心價值尚待檢驗(yàn)。
中國當(dāng)然需要民主,從某種意義上講亟需真正的民主制度,但如何在中國文化中建設(shè)民主,如何讓民主實(shí)踐在中國不至于演變成無理性的對抗和一發(fā)不可收的混亂,是一個考驗(yàn)當(dāng)代中國人的嚴(yán)峻課題。為此,社會肌體的發(fā)育成熟、社會自組織的健全運(yùn)行,無疑是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建設(shè)民主政治與賢能政治相結(jié)合的政治制度,從基層開始培育健全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是未來建立民主的必要條件。為了通向未來的理想政治,今天中國應(yīng)當(dāng)從“仁政”做起,從民主政治與賢能政治的結(jié)合做起,從培育民主生活方式做起。
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中國文化中幾千年來盛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由此導(dǎo)致權(quán)力無法約束,導(dǎo)致中國無法進(jìn)入現(xiàn)代。這種觀點(diǎn)永遠(yuǎn)認(rèn)識不到,在以人情、面子為基礎(chǔ)的中國文化中,最有效的制度絕不是一刀切式的法治,而是禮治。禮治與法治一樣,都是現(xiàn)實(shí)的文化生活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不是誰發(fā)明出來強(qiáng)加給整個社會的。而正因如此,它才會對一個社會有效。如果從禮治的角度看,古代中國有與當(dāng)時相適應(yīng)的發(fā)達(dá)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與同等條件下人類其他社會相比并不遜色。
讓我們來面對一個自由主義最關(guān)心的問題:“自由”如何在中國文化中落地生根?自由主義者很自然地認(rèn)為這是制度問題,只有確立相應(yīng)的制度才能保證個人的基本自由和權(quán)利。這一思維由于把自由當(dāng)作不言而喻的至上目標(biāo),然后思考自由的保障,所以對自由的思考從一開始就變成了如何人為地創(chuàng)造一套制度強(qiáng)加給中國社會的問題,而這套制度如何才能在中國文化找到基礎(chǔ)反而受到了忽略。然而,自由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只是通向人性價值的手段。只有從更高的價值標(biāo)準(zhǔn)出發(fā),才能找到自由賴以落實(shí)的制度條件。把手段當(dāng)成目的,結(jié)果是手段的問題被忽略,于是一系列相關(guān)的后發(fā)性問題得不到正視。
自由主義者總是說,缺乏制度安排,一切都是一場空。但是,解決問題的途徑絕不是簡單地強(qiáng)調(diào)某種理想的制度,而是要從社會動力學(xué)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才能找到個人正當(dāng)自由、權(quán)利不被剝奪的基礎(chǔ)。從過去幾千年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看,我曾提出今天這個基礎(chǔ)在于“行業(yè)與社會自治”。個人自由需要現(xiàn)實(shí)的社會基礎(chǔ)來保證,在古代,家族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承擔(dān)了此一任務(wù)。其道理在于:個人只有在自我組織和管理有效的團(tuán)體中才能保證自身,因?yàn)閭€人作為單獨(dú)的個體無法抗衡強(qiáng)大的國家。從今天的角度看,行業(yè)與社會自治應(yīng)該說代表了在現(xiàn)代條件下保證個人必要自由和權(quán)利的社會力量。
我之所以提出行業(yè)與社會自治作為個人自由的社會基礎(chǔ),不僅與我個人對西方市民社會研究有關(guān),更是因?yàn)榭紤]到過去數(shù)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習(xí)性,即前述的文化團(tuán)體主義。現(xiàn)代歐洲市民社會運(yùn)動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只有社會自身能組織起來,才可能制衡國家,對權(quán)力的濫用構(gòu)成制約。但是,社會如何才能自我組織起來,尤其在中國文化中組織起來?過去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證明,在中國文化中,社會自治基于兩件事:一是禮樂教化,二是賢達(dá)治理(或稱賢能治理)。
為什么孔子制禮作樂?為什么中國文化需要禮教?因?yàn)檫@是中國文化中使社會實(shí)現(xiàn)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根本有效之道。這絕不是個人自由這么簡單的事情。人有了自由,固然可用來追求自身的價值,但也可以用來相互爭斗。尤其是人與人構(gòu)成一個共同體時,其整合之道絕不是“自由人的聯(lián)合”這么簡單,而是必須訴諸人們共同能接受的價值和權(quán)威。我們看到,自由主義的契約精神和法治權(quán)威在中國文化中缺乏根深蒂固的土壤,無法讓大家在一種崇高的精神信仰中凝聚起來。相反,過去幾千年來歷史地形成的禮教傳統(tǒng),確曾發(fā)揮過把人們有效地組織起來的作用。當(dāng)然,如何在當(dāng)代中國情境下恢復(fù)賢達(dá)治理、重新制禮作樂,是一項(xiàng)尚待摸索的艱巨任務(wù)。
正如歐洲市民社會運(yùn)動所揭示的,有效的個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過社會共同體的力量來保證的。如果說,這個社會共同體在古代是家族,在今天將會主要是行業(yè)。行業(yè)自治是社會自治的最重要內(nèi)容之一。為了實(shí)現(xiàn)行業(yè)自治,除了禮樂教化與賢達(dá)治理之外,頭等大事絕不是設(shè)計(jì)出一個制度,而是要確立行業(yè)價值。前面說過,行業(yè)與社會自治的價值基礎(chǔ)并不是個人自由,而是生命的尊嚴(yán)與價值,以及共同體的安寧與繁榮;具體落實(shí)到每個行業(yè),可以發(fā)現(xiàn)各行各業(yè)都有自身獨(dú)立和獨(dú)特的價值,而它們體現(xiàn)了個人需要通過合乎行業(yè)邏輯的方式來展現(xiàn)生命的尊嚴(yán)和價值,促進(jìn)共同體的繁榮與進(jìn)步。對行業(yè)價值的漠視,將行業(yè)價值看成從屬于政治價值,是霸道政治的現(xiàn)代表現(xiàn)形式,是與儒家王道政治根本對立的。
因此,實(shí)現(xiàn)行業(yè)與社會自治本是一項(xiàng)長期而艱巨的任務(wù),也許需要幾代人,特別是社會精英持久耐心地去做才能實(shí)現(xiàn)。這絕不是像一些自由主義者想像的那樣,喊幾句口號而就能完成的。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生活在自己想當(dāng)然的情緒和日益無望的憤怒中,而最現(xiàn)實(shí)最具體的社會自治的建構(gòu)卻不在他們的視野內(nèi)。
三
今天,我們在認(rèn)可自由主義的重要意義的同時,一定要同時警惕其在中國所表現(xiàn)的烏托邦傾向。這種烏托邦的最大誤區(qū)就在于,認(rèn)為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理想制度,是全人類所有文化的共同目標(biāo)。于是接下來的任務(wù)就是在各個文化中落實(shí)一套他們心目中的制度。這種烏托邦本質(zhì)上建筑在制度決定論,甚至政體決定論之上,輕視不同文化在塑造制度和價值上的深刻影響。
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學(xué)者已認(rèn)識到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性,并努力試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自由主義之間尋找溝通的渠道或連結(jié)的橋梁。他們目前的最大困擾可能是為傳統(tǒng)文化價值與自由主義價值之間的矛盾而糾結(jié),其最壞的結(jié)果則是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dāng)成了實(shí)現(xiàn)自由主義的工具。
誠然,中國人今天需要借鑒和學(xué)習(xí)西方制度和價值,但在未來數(shù)十年,甚至數(shù)百年的漫長歲月里,他們恐怕仍將需要從自身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出發(fā),以中國數(shù)千年來形成的重要制度和價值為基礎(chǔ),重建真正適合于中國文化的制度和價值。為此,一定要放棄制度決定論或制度烏托邦的思維定式,認(rèn)識到制度多樣性、文明多元性才是現(xiàn)代性的必由之路。只有放棄自由主義的決定論,才有可能找到中國現(xiàn)代性的正確定位。
比起研究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tǒng)如何結(jié)合來說,也許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國文化中的治道是什么,中國文化中有效的制度是什么,中國文化中制度的基礎(chǔ)在哪里?這些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可能是次要的、工具性的方面,也許恰恰具有首要的意義。比如我曾經(jīng)提出,“風(fēng)化效應(yīng)”是中國文化中極其重要的社會整合機(jī)制,所以儒家經(jīng)典才一再強(qiáng)調(diào)移風(fēng)易俗是重塑社會的極重要途徑。當(dāng)“風(fēng)氣”凝定成好的禮俗之后,即可形成一種制度,其作用遠(yuǎn)大于任何人為的制度設(shè)計(jì)【方朝暉:《“三綱”與秩序重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244-276頁。】。賢能政治之所以比民主政治更有效,也是因?yàn)樗侵袊幕写_立引導(dǎo)風(fēng)尚和潮流,從而有效整合人心、保證規(guī)則或制度有效運(yùn)作的最重要手段。
100年前的五四運(yùn)動,以及180年來的近代史,摧毀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基本信念,顛覆了中國人對自身文明的千年信仰。這是迄至今日中國現(xiàn)代性遲遲不能走上正軌的主要原因。今天,我們對于中國文化在社會整合方式及其制度、價值上的迷茫,究竟出自我們自身怎樣的思想誤區(qū),是一個亟待搞清的大問題。
“五四”文學(xué)研究的幾個歷史教訓(xùn)
魏 建
(山東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山東濟(jì)南250014)
無論是新文化運(yùn)動的“五四”,還是愛國學(xué)生運(yùn)動的“五四”,距今都跨過百年了。今天,我們高舉五四旗幟,弘揚(yáng)五四精神,是很好的紀(jì)念;同時,我們認(rèn)真反思“五四”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也應(yīng)該是紀(jì)念“五四”的重要內(nèi)容。后者,也許是五四先驅(qū)更希望于我們的。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的“五四”,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歷史教訓(xùn),例如看待問題有簡單化、絕對化的弊端,典型的例證就是五四先驅(qū)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無論我們給五四先驅(qū)的全盤反傳統(tǒng)找到多少開脫的理由,那也只能是為了開脫。縱使我們這些五四之子為先驅(qū)們說一萬句好話,人家一句“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了”,這一句頂我們一萬句。更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是,當(dāng)年是否把孩子和一部分臟水潑掉了,卻把一些更臟的污泥濁水留下了?對此,我們至今都沒有認(rèn)真研究過。
100年了,盡管我們幾乎不停頓地一直在研究“五四”,但我們與五四新文化以及五四文學(xué)之間還存在相當(dāng)?shù)母裟ぃ阂环矫媸钦J(rèn)識不足,一方面是闡釋過度。認(rèn)識不足好理解,闡釋過度就有些復(fù)雜了,主要表現(xiàn)為兩極化傾向,贊美者把它夸大了,拔高了;貶損者把它丑化了,貶低了。比如說,當(dāng)我們把儒學(xué)和“五四”聯(lián)系起來的時候,有的人把儒學(xué)看成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一劑毒藥,有的人則看成是實(shí)現(xiàn)“中國夢”的靈丹妙藥。其實(shí)都不是!儒學(xué)就是儒學(xué),沒有夸大者說的那么好,也不像貶損者說的那么壞。具體來說,我們對于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的研究還存在很多嚴(yán)重的問題,除了剛才說的簡單化、絕對化之外,還表現(xiàn)為“五四”研究成果的同質(zhì)化等。這些同質(zhì)化的研究成果,談到“五四”的優(yōu)點(diǎn)和缺點(diǎn),說的都差不多,甚至幾十年陳陳相因。已有成果的研究局限還表現(xiàn)為:宏觀研究有余,微觀研究不足;大膽假設(shè)有余,小心求證不足。所以,我想以《女神》為例,通過這部最能體現(xiàn)“五四”抒情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績之代表作的研究,總結(jié)“五四”文學(xué)研究的一些歷史教訓(xùn)。
一
我要談的第一個歷史教訓(xùn)是,以往對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的研究長期受制于“五四”當(dāng)事人的自述。例如,研究《女神》的人大都受制于郭沫若有關(guān)《女神》的創(chuàng)作回憶。郭沫若說是怎么回事,研究者也跟著說是這么回事。這樣的研究成果不像是研究者在論述,而像是對郭沫若有關(guān)回憶的復(fù)述、轉(zhuǎn)述和闡述。得出的結(jié)論不是論文作者研究出來的,而是郭沫若給定的。郭沫若給定了多少內(nèi)容,研究者們就“研究”出多少內(nèi)容。例如,郭沫若有一段自述,經(jīng)常被《女神》研究者引用:“當(dāng)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運(yùn)動發(fā)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郭沫若:《序我的詩》,《郭沫若全集》第19卷《文學(xué)編》,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2年,第408頁。】根據(jù)這段自述,幾十年來,研究者們得出了一系列同質(zhì)化的研究結(jié)論。“當(dāng)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這是郭沫若給定了惠特曼的《草葉集》與《女神》的聯(lián)系,而《草葉集》在風(fēng)格上與《女神》中的一些名篇確有相似性,也就肯定并強(qiáng)化了這種聯(lián)系;接下來,“正是五四運(yùn)動發(fā)動的那一年”,這句話給定了十分精確的時代背景,于是,研究者們大談《女神》與1919年五四愛國運(yùn)動的關(guān)系;郭沫若自述繼而強(qiáng)調(diào)了“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就把詩人“小我”與民族“大我”聯(lián)系起來了,于是,研究者們就隨意地、理直氣壯地把《女神》中的個人抒情提升到為民族代言的高度;郭沫若接下來說的“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雖然沒有明說,研究者們似乎都明白“噴火口”和“噴火的方式”給定是什么,根據(jù)上下文,研究者們幾乎眾口一詞,都把“噴火口”理解為詩歌創(chuàng)作,把“噴火的方式”理解為郭沫若詩歌的創(chuàng)作手法。郭沫若只說了這五十多個字,卻給了研究者們太多的東西,既有時代背景又有創(chuàng)作動機(jī),既有個人情感又有民族內(nèi)涵,既有思想內(nèi)容又有表現(xiàn)手法,……這樣,郭沫若給定的結(jié)論就演變成了研究者們大同小異的研究成果,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然而,自古詩無達(dá)詁,對詩歌的理解出現(xiàn)見仁見智的歧異才是正常的,像《女神》研究這樣長期出現(xiàn)同質(zhì)化的研究成果,反而是極不正常的。
從表面上看,郭沫若的自述是在幫助研究者回到歷史現(xiàn)場,結(jié)果卻是導(dǎo)致了研究者對《女神》的誤讀,形成歷史遮蔽,甚至形成歷史歪曲的研究結(jié)論。如上所說,強(qiáng)調(diào)了惠特曼《草葉集》與《女神》的關(guān)系,無形中就遮蔽了其他外國作家和外國文學(xué)作品對《女神》的多元影響,例如比惠特曼影響更大的泰戈?duì)枴⒏璧碌热说挠绊?強(qiáng)調(diào)《女神》與1919年五四愛國運(yùn)動的關(guān)系,距離歷史真相就更遠(yuǎn)了,因?yàn)椤杜瘛分械脑S多詩篇原創(chuàng)于1919年五四運(yùn)動以前,即使五四運(yùn)動以后郭沫若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大都與國內(nèi)這場愛國學(xué)生運(yùn)動沒有什么關(guān)系;研究者們更大的誤讀表現(xiàn)在,把《女神》中的個人化寫作曲解為代言式寫作,比如,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把《女神》中的“鳳凰涅槃”,解讀成象征著民族的新生,象征著國家的新生。許多研究者還找到郭沫若事后很多年才表達(dá)過的類似言論,這就算坐實(shí)了。不僅研究者這么說,教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課程或講新詩的老師大都這么說。僅從郭沫若自述來看,并非如此,因?yàn)楣暨€有與之相反的更私密的自述;從創(chuàng)作動機(jī)的角度來說,也不是這樣的。《鳳凰涅槃》起初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私人化寫作,屬于個人抒情。郭沫若曾與宗白華詳細(xì)地講了這首詩如何表達(dá)了他與日本戀人安娜之間的感情。他非常希望把過去的自己燒掉,換一個新我。這是《鳳凰涅槃》投稿寄出去五天后,郭沫若在給宗白華信里寫的創(chuàng)作動機(jī)。信中說:“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xiàn)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來,把我現(xiàn)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毀了去,從那冷凈了的灰里再生出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2年,第87-88頁。】
與之同樣的情況,以往學(xué)界對五四文學(xué)革命發(fā)生的研究,也是依據(jù)胡適的回憶,依據(jù)陳獨(dú)秀的自述,可是他們的回憶和自述明顯包含著給定的結(jié)論,導(dǎo)致了研究者的誤讀,從而形成歷史遮蔽,甚至形成歷史歪曲的研究結(jié)論。即使他們的回憶和自述不乏符合歷史事實(shí)的材料,但研究者們是否看過“五四”先驅(qū)對立面是怎么說的?是否看過其他原始文獻(xiàn)檔案呢?比如說《新青年》,我們依據(jù)胡適回憶和陳獨(dú)秀的回憶,都覺得《新青年》當(dāng)時很了不起。事實(shí)上,《新青年》的發(fā)行量一直不大,創(chuàng)刊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停刊半年多以后復(fù)刊,過了不到一年又停刊了。為什么?都是因?yàn)殇N路不好。通過查閱原始檔案和文獻(xiàn)就會發(fā)現(xiàn),以往學(xué)術(shù)界把《新青年》的作用夸大了。看的原始檔案文獻(xiàn)越多,越會發(fā)現(xiàn)當(dāng)事人的很多自述并不可靠,至少需要借助更多的旁證來參考。
二
我要談的第二個歷史教訓(xùn)是,以往對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的研究總是受制于一個又一個僵化的,或是大而無當(dāng)?shù)难芯靠蚣堋R酝难芯砍晒蠖既狈r值中立的學(xué)術(shù)立場,帶有明顯的研究預(yù)設(shè),或是為了肯定“五四”,或是為了否定“五四”,更有甚者就是為了別的目的,拿“五四”說事。這表現(xiàn)在每個時代的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研究各有某種固定的闡釋框架。例如《女神》,從聞一多開始直到今天,《女神》研究者都要談“五四”的時代精神,幾乎沒有人回避這個問題。“五四”時代精神成了一個闡釋《女神》的框架,當(dāng)然我們需要研究框架,但我們不需要制約學(xué)術(shù)研究的框架。如果研究者都用這個框架,而且是一個僵化了的研究框架,難免形成同質(zhì)化的研究成果。對于《女神》研究來說,不同時期談“五四”時代精神,研究者分別賦予了它不同的含義。最初是聞一多的含義,那個時候就是指20世紀(jì)現(xiàn)代的精神,還包括青春的精神、科學(xué)的精神等含義,后來被賦予了愛國的、反帝反封建的含義,再后來被賦予了啟蒙的含義,近年來又被賦予了現(xiàn)代性的含義。這些不同的含義形成不同的研究規(guī)約,多是為了印證當(dāng)下的某一種流行的理論學(xué)說,拿《女神》作為佐證。《女神》是這樣,其他的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研究成果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順便說一下。目前網(wǎng)絡(luò)上,特別是微信上流傳的郭沫若的材料有很多是偽造的。這些偽作可分為如下幾類:第一類,假題目,真內(nèi)容。如流傳的郭沫若歌頌斯大林的詩:《斯大林是我親爺爺》《斯大林是我親爸爸》《斯大林元帥,你是我的爸爸》等。這一類偽作的作品題目是假的,但詩作的內(nèi)容基本是真的。1949年是斯大林70歲壽辰,郭沫若寫了一短一長兩首詩為斯大林祝壽:短的一首題為《斯大林萬歲》,長的題為《我向你高呼萬歲》。偽作的制造者用假題目替換了真題目《我向你高呼萬歲》,詩作內(nèi)容與《我向你高呼萬歲》的內(nèi)容大部分相同。有些見過《我向你高呼萬歲》這首詩的內(nèi)容而沒有記住題目的人,最容易被欺騙。第二類,假題目,內(nèi)容半真半假。如偽作《斯大林是我親爺爺》《斯大林是我親爸爸》《斯大林元帥,你是我的爸爸》等還有另外的造假版本,作品題目是假的,在真實(shí)的作品《我向你高呼萬歲》中加一點(diǎn)偽造的詞句。如原作中有這樣兩行:“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篡改者把作品題目改成《斯大林是我親爸爸》,同時在詩中加上“你是我親爸爸”這句話,變成:“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你是我親爸爸/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一般的讀者沒有見過真實(shí)的原作,只看到詩中有“斯大林……你是我親爸爸”,題目又叫《斯大林是我親爸爸》,便信以為真。第三類,真題目,內(nèi)容半真半假。例如《我向你高呼萬歲》的某些偽作版本,題目是真的,內(nèi)容多數(shù)是真的,只把其中個別句子改成:“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你是我爸爸/……我向你高呼萬歲!”或改成“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你是我親爺爺/……我向你高呼萬歲!”等等。這一類偽作因?yàn)榇鄹某潭茸钚。钊菀鬃屓伺俪烧妗5谒念悾}目偽造,內(nèi)容篡改,體裁造假。如流傳很廣的所謂郭沫若詩歌《獻(xiàn)給敬愛的江青同志》,源于郭沫若的一次講話。當(dāng)時江青在場,郭沫若的確說了一些奉承江青的話。造假者從講話稿中選了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再加上偽造的題目“獻(xiàn)給敬愛的江青同志”,就改編成一首詩了。盡管詩中的某些詞句確是郭沫若說過的,但這首詩是假的。第五類,假題目,假內(nèi)容,即完全是無中生有之作。如網(wǎng)上和新媒體上流傳的《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完全是杜撰的“作品”。造假者為了讓人相信是真的,還偽造出處。這些出處因?yàn)椴淮嬖冢圆椴坏健R话闳瞬幻髡嫦啵眠@些偽作傳來轉(zhuǎn)去可以理解,難以理解的是一些文史研究專家也參與制假造假和以訛傳訛。有些知名專家將偽作摻到郭沫若一些真實(shí)的作品中作為例證引用,讓人誤以為真。他們何以如此?有些是成心要對郭沫若污名化,有些則出于其他研究目的的預(yù)設(shè)。
三
我要談的第三個歷史教訓(xùn)是,以往的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研究往往受制于某些簡化了的研究“定論”。關(guān)于五四文學(xué)是什么,五四文學(xué)革命是什么,迄今為止,讀者看到的多是被簡化了的,并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的結(jié)論。這與其說是研究結(jié)論,不如說是一個歷史的傳說。在這樣的傳說中,五四文學(xué)革命被簡化成如下的樣子:一個人首倡——胡適;兩篇發(fā)軔之作——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和陳獨(dú)秀的《文學(xué)革命論》;“一校一刊”的推動——北京大學(xué)、《新青年》;其發(fā)展線索是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對于歷史真相來說,以上這些內(nèi)容不是正確與錯誤的判斷問題,而是某幾棵樹與森林關(guān)系的認(rèn)知問題,因?yàn)檎麄€五四文學(xué)革命比這些內(nèi)容要豐富很多很多。“五四”是一個非常復(fù)雜的歷史事件,這里面包含了很多內(nèi)容,可惜被后人簡化成干巴巴的幾條。尤其是那些被簡化的“第一”,仔細(xì)閱讀原始的文獻(xiàn)檔案,大都經(jīng)不起推敲,比如說在許多文學(xué)史研究論文和著作中把胡適1916年創(chuàng)作的《兩個蝴蝶》(原名《朋友》)說成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首白話新詩,讓研究古代文學(xué)的人笑掉大牙,因?yàn)橹袊糯缇陀邪自捲姟?/p>
以往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個“定論”——五四文學(xué)革命起源于美國,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一幫美國留學(xué)生發(fā)起了這場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劃時代的“文學(xué)革命”。“美國起源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界成為深信不疑的學(xué)術(shù)“定論”。然而,“美國起源”只是一種可能,同時還存在其他的可能,如“日本起源”。我曾以胡適文學(xué)革命時期的活動為參照,對比同時期郭沫若等人在做什么參見魏建:《〈女神〉研究的三大教訓(xùn)》,《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9年第3期。。我為什么這么做呢?因?yàn)檫^去都是聽胡適等人的回憶,聽他告訴我們五四文學(xué)革命是怎么回事,卻沒聽聽其他人怎么說。且不說所謂復(fù)古派,就說郭沫若,他可是新文學(xué)家。郭沫若曾說:中國新文壇是留日學(xué)生創(chuàng)造的麥克昂:《桌子的跳舞》,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9年,第53頁。。細(xì)想一下,除了胡適,其他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先驅(qū)大都是留日學(xué)生:陳獨(dú)秀、周作人、李大釗、錢玄同、魯迅。這些人只是“定論”中的先驅(qū),郭沫若說的創(chuàng)造中國新文壇的留日學(xué)生首先是他們創(chuàng)造社作家。很多人以為創(chuàng)造社是1921年以后成立的,相比五四文學(xué)革命滯后了好幾年。仔細(xì)閱讀歷史文獻(xiàn)就不是這樣了。胡適和美國留學(xué)生討論文學(xué)革命的時候,幾乎同時,郭沫若和郁達(dá)夫、成仿吾、張資平等人,也在討論文學(xué),——當(dāng)然是新文學(xué)。再仔細(xì)查看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胡適他們主要討論的是語言文字,白話能不能入詩等問題;郭沫若他們討論的是新文學(xué)的純文學(xué)問題,早就超越了一般白話文問題了。總之,以往對五四新文化/文學(xué)的研究,把《新青年》一派當(dāng)成主流,嚴(yán)重背離了“五四”的歷史事實(shí)。“五四”的歷史事實(shí)是什么?不是《新青年》派一家獨(dú)大,而是百家爭鳴,多元共生。
作為“大啟蒙”的“五四”:走向“啟蒙就是救亡”的歷史大勢
劉悅笛
(遼寧大學(xué)文學(xué)院特聘教授 遼寧沈陽110031;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所研究員 北京100732)
“中國啟蒙”不僅具有本土價值,而且具有全球價值,它可以為世界啟蒙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中國范式”【劉悅笛:《如何認(rèn)識新文化運(yùn)動百年的全球意義》,《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19年第4期。】。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給中國帶來的乃是一種“大啟蒙”,它的歷史貢獻(xiàn),就在于讓中國要走在富強(qiáng)、民主、科學(xué)和自由之康莊大道上。所謂的中國啟蒙,既不可能走全盤西化之路,但卻要借鑒與吸納來自西方的第二次啟蒙的普遍要素;也不能徹底回到傳統(tǒng)本位中去,但卻要讓來自中土第一次啟蒙的傳統(tǒng)得以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換,從而可能在第三次啟蒙當(dāng)中找到本土發(fā)展之途,并將這種既自本生根又具有全球化潛質(zhì)的模式,應(yīng)用于未來世界之中。
一、五四運(yùn)動:到底是不是“啟蒙運(yùn)動”?
在紀(jì)念五四運(yùn)動八十周年之際,著名歷史學(xué)家余英時曾有個斷言:“五四”既不是文藝復(fù)興,也不是啟蒙運(yùn)動。按照他的觀點(diǎn),把“五四”作為文藝復(fù)興是“自由主義詮釋”,而把五四作為啟蒙運(yùn)動則是“馬克思主義詮釋”,這兩套界定歷史的方案都形成了歷史錯位。由此,“不能輕率地把文藝復(fù)興與啟蒙運(yùn)動兩種概念,視為隨機(jī)援引來比附五四運(yùn)動的兩種不同特征。相反地,必須嚴(yán)肅地視它們?yōu)閮煞N引導(dǎo)出各自的行動方針、且又不相容的方案。簡言之,文藝復(fù)興原本被視為一種文化與思想的方案,反之,啟蒙運(yùn)動本質(zhì)上是一種經(jīng)偽裝的政治方案”【余英時:《文藝復(fù)興乎?啟蒙運(yùn)動乎?——一個史學(xué)家對五四運(yùn)動的反思》,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fù)興,亦非啟蒙運(yùn)動》,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1-12頁。】。然而,這種看法不僅割裂了文化思想與政治之間的本然關(guān)聯(lián),而且,將兩套方案置于“政治動機(jī)”的視角之內(nèi)來加以考量,有失歷史定位的公正性,五四運(yùn)動致力于啟蒙中國民眾的本然特性,不能被政治立場抑或語言游戲所推翻。
這可以從五四運(yùn)動的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種詮釋者那里得以明證。當(dāng)1933年7月胡適在美國芝加哥大學(xué)所做名為《中國的文藝復(fù)興》的赫斯克爾講座(The Haskell Lectures)當(dāng)中強(qiáng)調(diào),五四運(yùn)動也是“一場以理性對抗傳統(tǒng),以自由對抗權(quán)威,張揚(yáng)生命和人之價值對抗壓制生命和人之價值的運(yùn)動”時【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 44.】, 其實(shí)也是在肯定五四運(yùn)動所本有的啟蒙性質(zhì);當(dāng)張申府在1936年開啟的新的一場“新啟蒙”運(yùn)動當(dāng)中,確定“凡是啟蒙運(yùn)動都必有三個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并要求“思想的自由與自發(fā)”與“民族的自覺與自信”得以相互結(jié)合時【張申府:《什么是新啟蒙運(yùn)動》,《實(shí)報(bào)·星期偶感》1937年5月23日。】,也就是將啟蒙的特性與五四運(yùn)動的本質(zhì)結(jié)合了起來。實(shí)際上,“使中國的文藝復(fù)興與啟蒙運(yùn)動分開來的正是那場變革的本質(zhì)特征——它的向度和目標(biāo)”【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fù)興》,魯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4頁。】,但事實(shí)是二者恰恰是歷史地糾結(jié)在一起的。
在“五四”詮釋史上,對于文藝復(fù)興與啟蒙運(yùn)動較早采取兩面看的評價,來自李長之1942年的長文《五四運(yùn)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他認(rèn)為五四運(yùn)動“并非文藝復(fù)興”,“乃是一種啟蒙運(yùn)動”【李長之:《五四運(yùn)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bào)·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一方面,“文藝復(fù)興的真意義乃在新世界與新人類的覺醒”,這就是如今對文藝復(fù)興的世界的發(fā)現(xiàn)與人的發(fā)現(xiàn)的雙重評價,這種評判符合歷史,但是將之與“五四”比附,顯然哥白尼那種發(fā)現(xiàn)新世界的覺醒在中國并不存有,“新人類的覺醒吧,這也是基于一種新的形上學(xué)或?qū)τ谌松鷨栴}一種深摯的吟味”,這更不是五四時代的精神所能容【李長之:《五四運(yùn)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bào)·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所以五四運(yùn)動談不上文藝復(fù)興,把胡適譽(yù)為“中國文藝復(fù)興之父”也是張冠李戴。另一方面,啟蒙運(yùn)動則是要“在一切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種精神運(yùn)動”,“因?yàn)槭羌兇饫碇侵髁x之故,所以這種啟蒙的體系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義與目的實(shí)效”,這的確是以理性為內(nèi)核的啟蒙運(yùn)動的缺陷所在,但即便如此,“啟蒙運(yùn)動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實(shí)效的,破壞的,清淺的。我們試看五四時代的精神,像陳獨(dú)秀對于傳統(tǒng)的文化之開火,像胡適主張要問一個‘為什么’的新生活,像顧頡剛對于古典的懷疑,像魯迅在經(jīng)書中所看到的吃人禮教(《狂人日記》),這都是啟蒙的色彩”【李長之:《五四運(yùn)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bào)·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這個判斷無疑是接近歷史真相的。
盡管五四運(yùn)動曾被李澤厚先生評價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的一場運(yùn)動,但卻恰以感性化的形式提出了所謂“啟蒙的理性任務(wù)”,作為一場參與政治的愛國運(yùn)動,富有激情這是歷史必然,但是要看其主要訴求到底是什么。歷史學(xué)家張灝也曾揭示出“五四”“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歧性”,“五四”“思想中一個很重要成分就是以啟蒙運(yùn)動為源頭的理性主義。但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很強(qiáng)烈的浪漫主義。理性主義是強(qiáng)調(diào)理性的重要,浪漫主義卻是謳歌情感的激越”【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fù)興,亦非啟蒙運(yùn)動》,第35頁。】。1936年在京滬發(fā)動的另一場“新啟蒙”運(yùn)動,它所倡導(dǎo)的就是一種“新理性主義運(yùn)動”,但是從整體觀之,20世紀(jì)中國的啟蒙缺憾仍是理性之不足。具有悖謬性的是,歐洲啟蒙運(yùn)動的綱領(lǐng),恰是讓人們?nèi)ジ矣谶\(yùn)用自己的理性,這來自德國哲學(xué)家康德的啟蒙箴言。于是乎,一種內(nèi)在的巨大矛盾就形成了:啟蒙思想本身倡導(dǎo)理性化,啟蒙運(yùn)動卻激情四射,這也是啟蒙的內(nèi)在缺憾所在。
二、重詮五四:從“小啟蒙”到“大啟蒙”
五四運(yùn)動有廣、狹兩種含義:“五四運(yùn)動有廣、狹兩種含義:狹義的‘五四’是指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發(fā)生的學(xué)生愛國運(yùn)動;廣義的‘五四’則指在這一天前后若干年內(nèi)所進(jìn)行的一種文化運(yùn)動或思想運(yùn)動。這一文化或思想運(yùn)動,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兩年以前(民國六年)的文學(xué)革命,其下限則大抵可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為界。”【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tǒng)及其現(xiàn)代變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82頁。】這是余英時先生的看法,但實(shí)際上,我認(rèn)為,這種廣義與狹義的“五四”都可以被歸入“小五四”,而與之相對的“大五四”則是指由此所形成的一種曠日持久的思想解放進(jìn)程,此即從人類“大啟蒙”的視角返觀新文化運(yùn)動的世界意義。
所以,需要繼續(xù)區(qū)分“大啟蒙”與“小啟蒙”的不同。我們所謂的“大啟蒙”就是要破除啟蒙的異化現(xiàn)象,讓啟蒙理性不再以理性為絕對中心,這就需要用東方智慧來平衡西式啟蒙的偏頗。“大啟蒙”恰恰是要找回人類的情感,以人情來對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類獲得一種完整的“情理結(jié)構(gòu)”【劉悅笛:《為“大啟蒙”辯護(hù):中國啟蒙的世界價值》,《社會科學(xué)報(bào)》2019年4月4日。】。因此,未來的全球社會需要一種“大啟蒙”,這種啟蒙既反對理性中心主義,又不流于唯情是舉主義,而是走向了一種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啟蒙通途,中國啟蒙在這里就有個全球用武之地。
所謂“小啟蒙”,指18世紀(jì)那場歐洲的啟蒙運(yùn)動所帶來的一系列跨文化的啟蒙,五四新文化就是其影響在東方的余緒之一。這場啟蒙的核心,就是倡導(dǎo)理性、科學(xué)、人文主義和進(jìn)步,這是東西方的共識。進(jìn)入到20世紀(jì)之后,當(dāng)今世界則直面再一次啟蒙,那種“小啟蒙”的缺憾則被顯露了出來,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理性而塑造的科學(xué)所帶來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見,如今一味追求進(jìn)步從而忽視理性的邊界,正讓人類付出“自然與文化”的雙重代價,同時,一種冷酷無情的“科技理性”正在塑造著全球民眾的生活,并且對人類的世界產(chǎn)生了禁錮與反制,這是我們不得不加以警惕的。
20世紀(jì)以來的“中國啟蒙”就是一種“大啟蒙”,它盡管是一種后發(fā)的啟蒙,但是結(jié)合本土傳統(tǒng)后,卻可以為世界文明提供一種新的發(fā)展范式,因此,如何賦予啟蒙以“中國性”的定位,也就成為了關(guān)鍵之舉。
盡管事實(shí)如此確證,但是如今仍不乏有論者持反對意見,臺灣“中央大學(xué)”哲學(xué)研究所李瑞全教授就與筆者商榷:“有說五四運(yùn)動是一種中國式的‘啟蒙’或‘大啟蒙’,如劉悅笛,《為‘大啟蒙’辯護(hù):中國啟蒙的世界價值——從人類理性視角紀(jì)念五四運(yùn)動百年》一文所持的論點(diǎn),其中所寄望于中國傳統(tǒng)中的‘情理合一’之說作為人類第三次啟蒙的范式,有回歸儒家義理,或與本文旨意有相通之處(但實(shí)有很不同的詮釋和意向),在此不能備論。至于該文以五四運(yùn)動為參加了西方第二次啟蒙,實(shí)有嚴(yán)重疏漏不一致之處。如以所引西方學(xué)者平克所提出的,‘啟蒙’包括:理性、科學(xué)、人文主義和進(jìn)步四方面來說,‘五四’如上論正是反傳統(tǒng)、全盤西化與科學(xué)主義等既違反理性,亦缺人文主義精神,正不足以言是一啟蒙運(yùn)動,不能以口號中標(biāo)示科學(xué)與民主即為啟蒙運(yùn)動”【李瑞全:《從返本開新論當(dāng)代新儒學(xué)對五四運(yùn)動的回應(yīng)》,《鵝湖月刊》第44卷第2期(總號第518,1999年4月)。】。李瑞全教授繼續(xù)認(rèn)定:“至于說五四運(yùn)動是一種‘啟蒙運(yùn)動’也可以說是無根之談。因?yàn)椋酥兴^追求科學(xué)與文明,實(shí)是一種盲目的崇拜:西方來的就是科學(xué)的,文明的。傳統(tǒng)的自然都被打?yàn)榉纯茖W(xué),反文明的。此種鼓吹式的‘文化口號’不但是膚淺的,實(shí)是違反理性的。因?yàn)椋渲胁]有針對傳統(tǒng)社會和西方社會文化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理性批判反省。全盤西化在文化發(fā)展上基本上就是違反科學(xué)與理性的構(gòu)想。因?yàn)椋幕皇且路皇敲摿伺f的換上新衣就成為新的‘文化人’。文化是人類生命發(fā)展中已成為每個人生命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東西,已貫徹于一切的生活價值與行為習(xí)慣的表現(xiàn)之中,甚至常是超乎自覺之外的日常生活模式和習(xí)慣,猶如日日呼吸的空氣,幾乎無從置換。五四運(yùn)動對于國人維護(hù)國家主權(quán)和政治上要求民主的表現(xiàn)固然有推動社會政治上的理性表現(xiàn),但對于啟發(fā)每個人的理性思維和批判反省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反之,更多的是由于接受不同的理論變成主張這即是唯一真理,使原來可以是理性的理論蛻變?yōu)橛^念的‘意識形態(tài)’或‘意底牢結(jié)’(牟宗三先生語),形成一不容許自我反省批判的唯我獨(dú)尊式的思維,此正是反啟蒙的一種表現(xiàn)”【李瑞全:《從返本開新論當(dāng)代新儒學(xué)對五四運(yùn)動的回應(yīng)》,《鵝湖月刊》第44卷第2期(總號第518,1999年4月)。】,這種將“五四”視為“非啟蒙”乃至歸于“反啟蒙”的論調(diào),顯然偏離了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本來軌跡。
歷史事實(shí)是,在1919年的群情激昂的“小五四”之后,新文化與新思潮始被廣為接受,五四運(yùn)動的引領(lǐng)者之一胡適反思性地在當(dāng)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fā)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門見山地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xué)理”“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并將這四個基本點(diǎn)作為新思潮和新文化運(yùn)動綱領(lǐng)【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但是四者的地位卻是不同的,需要進(jìn)一步加以解析。實(shí)際上,無論是拿來主義還是整理傳統(tǒng),最終都是為了中華文明的再造。胡適在1927年《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中寫道:“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不過如此’”,是為了“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hù)人們不受鬼怪迷惑”【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現(xiàn)代評論》第五卷第一一九期(1927年3月19日)。】。由此觀之,所謂“整理國故”也不是那種單純的復(fù)古,而是要求用科學(xué)的精神去對傳統(tǒng)加以梳理與研究,從而將“傳統(tǒng)復(fù)興”與“現(xiàn)代啟蒙”得以結(jié)合起來,這是胡適主張所包孕的深層意味。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乃是具有世界價值的,它始將中國這個始終未中斷傳統(tǒng)的文明古國帶到了“啟蒙之境”,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啟蒙將人類啟蒙拓展到了一個“大啟蒙”的階段。當(dāng)然,啟蒙在中國乃至世界至今都尚未完成,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正在進(jìn)行時,我們始終在路上。
三、啟蒙轉(zhuǎn)型:從“救亡壓倒啟蒙”到“啟蒙就是救亡”
2009年,筆者曾提出“啟蒙與救亡”的發(fā)明權(quán)問題,但現(xiàn)在根據(jù)史實(shí),李澤厚率先提出這個思想無疑【劉悅笛:《“救亡壓倒啟蒙”,本無可爭議》,《社會科學(xué)報(bào)》2017年9月28日。】。我曾經(jīng)指出,作為對中國近代史的內(nèi)在發(fā)展邏輯的一種言說方式,啟蒙與救亡的變奏同時也成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題之一。該學(xué)說的發(fā)明權(quán)之爭,并沒有必要如此被關(guān)注,哪種理論對歷史和現(xiàn)實(shí)更有闡釋力才是更為關(guān)鍵的。毫無疑問,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更有歷史闡釋力,且產(chǎn)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我曾給出的結(jié)論如下:“其一,李澤厚明確提出了‘壓倒說’,從他早年認(rèn)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題始,就已經(jīng)明確認(rèn)定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其二,李澤厚試圖將這種‘壓倒說’貫穿到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闡釋當(dāng)中,而顯然舒衡哲沒有如此恢弘的視角和闡釋的野心。”【劉悅笛:《“啟蒙與救亡”的變奏:孰是孰非》,《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10期。】
救亡與啟蒙的歷史邏輯,的確就是李澤厚最早揭示出來的。我們可以換個說法,“反帝”壓倒了“反封”,其實(shí)就是救亡壓倒啟蒙,反過來說也沒錯。因?yàn)楦鶕?jù)解析可以看出,救亡的反面就是“反帝”,啟蒙的反面則是“反封”,李澤厚的言說恰好是反帝與反封的一種“反說”而已。漢學(xué)家們也有近似的說法:“盡管啟蒙哲學(xué)家們有意無意地開創(chuàng)了一個革命的時代……受到啟蒙的中國‘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卻卷入了由于一場革命而帶來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機(jī)之中”【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fù)興》,第335頁。】。李澤厚在發(fā)表于《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文章《二十世紀(jì)初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中就曾論證過,“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首要命題”,反帝壓倒反封,才是“救亡壓倒啟蒙說”的雛形【李澤厚:《二十世紀(jì)初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啟蒙與救亡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實(shí)質(zhì),我認(rèn)為,其實(shí)是給中國提出的兩難選擇:到底是“國家富強(qiáng)”,還是“個人自由”,二者哪一個才更為重要?這是由于,啟蒙要求自由,進(jìn)而強(qiáng)調(diào)個性的自由解放,但國富的訴求卻壓制了啟蒙,而且國富也并不等于民強(qiáng),在中國的特定歷史語境當(dāng)中,二者恰恰也構(gòu)成了一對矛盾。
李澤厚的著名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首刊于1986年8月的《走向未來》創(chuàng)刊號,最初收入1986年12月三聯(lián)版的《走我自己的路》,直到1987年6月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才正式收入,由此明確了“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著名說法。這是大家公開所見的事實(shí),然而,據(jù)李澤厚本人的回憶,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早,寫作時間應(yīng)該是1985年8月,那是在廬山開完中國哲學(xué)史會議回來后寫成的。而且,這篇文章最初也不是給《走向未來》的,當(dāng)時《走向未來》還是剛創(chuàng)辦的民間刊物,本來是應(yīng)《北京社會科學(xué)》雜志之約而寫的,目的是為了紀(jì)念文革結(jié)束十周年,但交出后被雜志壓了太久,后來才給了《走向未來》,而且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對于這場發(fā)明權(quán)之論爭,我曾給出了兩個判斷,必然性的判斷乃是“變奏說”與“壓倒說”,無疑都是來自李澤厚,漢學(xué)家舒衡哲(Versa Schwarcz)所論的則是“啟蒙與救國”之關(guān)聯(lián)。關(guān)鍵是我給出的那個或然性判斷——“非常可能的是,這個說法本來在李澤厚和舒衡哲的內(nèi)心都是一個‘模糊的共識’,在他們于20世紀(jì)80年代早期見面的時候,啟蒙與救亡的說法被相互激發(fā)了出來”【劉悅笛:《“啟蒙與救亡”的發(fā)明權(quán):歸李澤厚,還是舒衡哲?》,《中華讀書報(bào)》2009年9月16日。】,如今根據(jù)更多的歷史材料研究,應(yīng)該說“相互激發(fā)了出來”這一判斷不準(zhǔn)確,并不能成立。
遙想當(dāng)年,“啟蒙壓倒救亡”說提出時,“反傳統(tǒng)”的力量在當(dāng)時思想界其實(shí)是位居主流的,而且在青年學(xué)生中影響非常巨大,其中的諸多誤解至今仍未加以澄清,所以,如今重溫李澤厚先生《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的價值就有以下五個方面:首先,李澤厚的文章所論“救亡壓倒啟蒙”,實(shí)際上是一種歷史性的描述,而非價值性的判斷,但諸多論者的誤解在于,他們更多視之為一種價值性的判斷而非歷史性的描述;其次,“五四”并不是“救亡壓倒啟蒙”,這就不同于諸多論者所接受的那樣的理解,在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這才是當(dāng)時的歷史實(shí)情,此后,啟蒙才被救亡所壓倒,那是后話,該文第一節(jié)的標(biāo)題就是“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jìn)”,而后來者們往往忽視了這個表述;再次,李澤厚文章延續(xù)“文化運(yùn)動”與“政治運(yùn)動”之分,這種區(qū)分早已確立,由此李澤厚認(rèn)定,“啟蒙性”的新文化運(yùn)動開展不久,便與“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yùn)動合流了,這種提法其實(shí)不同于“大五四”與“小五四”的新近提法,而且也較新提法更加可靠;第四,李澤厚文章從“救亡——戰(zhàn)爭——革命”的現(xiàn)實(shí)角度,闡明了后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動因,這在他2006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當(dāng)中得以全面展開并集中論述【參見李澤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香港:明報(bào)出版社,2006年。】;最后,李澤厚的這篇文章從社會體制結(jié)構(gòu)與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兩方面來論證其所說的“轉(zhuǎn)換性創(chuàng)造”,這種返本開新的建構(gòu),仍是以中國儒家作為主體的,而且這種對于傳統(tǒng)的轉(zhuǎn)換,不僅關(guān)涉到現(xiàn)實(shí)發(fā)展,而且關(guān)系到中國未來命運(yùn)。
2015年,秦暉先生發(fā)文認(rèn)為壓倒啟蒙的并非救亡,應(yīng)為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其中的內(nèi)在邏輯應(yīng)該是:一面是從“小五四”“愛國進(jìn)步”到“民族主義”,另一面則是從“大五四”“科學(xué)民主”到“自由主義”【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diào),及其何以被“壓倒”》,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394.html。】。此文反對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我認(rèn)為乃是內(nèi)在偷換了概念,其實(shí),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壓倒,不就是救亡壓倒啟蒙嗎?現(xiàn)如今,中國人所直面的乃是另一番歷史境遇,這就是“啟蒙就是救亡”。這是由于,救亡圖存的大業(yè)早已實(shí)現(xiàn),但是,“大啟蒙”的事業(yè)在中國卻并未完成。
李澤厚在紀(jì)念五四運(yùn)動七十周年的《啟蒙的走向》一文當(dāng)中,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認(rèn)定:“如果說,過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壓倒啟蒙,那么在今天,啟蒙就是救亡,爭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就是使國家富強(qiáng)和現(xiàn)代化的唯一通道。因之,多元、漸進(jìn)、理性、法治,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與科學(xué)的五四精神的具體發(fā)揚(yáng),這就是我所期望的啟蒙在今日的走向。”【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擴(kuò)而來理解,如今中國的現(xiàn)狀就是“啟蒙就是救亡”。然而,這個救亡,已經(jīng)不是當(dāng)年“圖存”“保種”那種狹義的救亡了,而是關(guān)系到中華文明“再造”的廣義救亡了。因此,與這種廣義救亡相對的啟蒙,也就是一種“大啟蒙”了。
從救亡壓倒啟蒙,再到啟蒙就是救亡,這也是符合歷史發(fā)展邏輯的,其中情與理之間也形成了歷史性的巨變。按照李澤厚的闡釋,“救亡壓倒啟蒙后,激情與革命的結(jié)合成為巨大的行動力量”【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如此一來,本為理性所點(diǎn)燃的“激情之火”卻不斷燒灼著“理性本身”,而在狹義的救亡重任完成之后,中國社會的確需要回歸五四時代所倡導(dǎo)的理性,“今天要繼續(xù)五四精神,應(yīng)特別注意發(fā)揚(yáng)理性,特別是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學(xué)的體現(xiàn),即如何寓科學(xué)精神于民主之中。從而,這便是一種建設(shè)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設(shè)。不只是激情而已,不只是否定而已”【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這其實(shí)也應(yīng)對著從啟蒙到革命再到改良的中國社會的宏觀轉(zhuǎn)型。
四、視角多元化以后:如何定位“五四”?
隨著反思“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深入,五四形象變得愈加復(fù)雜,這的確值得重思,特別是以啟蒙為核心的思考始終沒有中斷過,但是其中的歷史發(fā)展一定有反復(fù)的過程。“在1919年五四運(yùn)動隨后的幾十年當(dāng)中,中國啟蒙先行者們被迫去對其加以重思與評估,甚至有時一度放棄了知識解放的視角。政治暴力和反帝運(yùn)動創(chuàng)造的環(huán)境,向主張緩步革命的知識分子提出了緊迫挑戰(zhàn)。他們作為文化先覺者的自身形象也遭到質(zhì)疑。五四知識分子們終而改變了自身的觀點(diǎn),開始重新看待已啟蒙的思想家與未被喚醒的民眾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而開始去改造國民的心靈慣習(xí)”【Vers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 】, 歷史的發(fā)展也確實(shí)是一波三折的,但啟蒙的核心卻始終并未改變。
如今,對“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歷史描述、闡釋、反思與判斷被再度呈現(xiàn)出來。出于不同的歷史觀,學(xué)者們通過觀察與研究,對于歷史有了不同的描述,然后有了不同的闡釋,進(jìn)而作了不同的反思,最終給出了不同的論斷,使得歷史面目本身變得愈加模糊了。當(dāng)我們試圖揭開“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真實(shí)面紗的時候,豈知面紗之后還有層層面紗,“五四”的真面目竟如剝洋蔥一般,層層剝離下來卻不見真核也。難道看待這段已經(jīng)百年的歷史,人們真的失去共識了嗎?真如后現(xiàn)代撕裂般之公說公有理、婆說更有理?為了主觀學(xué)術(shù)創(chuàng)見,同時客觀投合“反西化”,皆可置歷史本身于不顧?我們的歷史觀,果然成為了滿天繁星而彼此距離甚遠(yuǎn)之“星叢結(jié)構(gòu)”?
無論將之視為五四“政治”運(yùn)動,還是“新”的文化運(yùn)動,這兩種運(yùn)動似乎難以割裂開來,正如歷史本身的復(fù)雜糾葛一般,“五四”乃多種歷史力量相互角力的場域。胡適并不贊同“五四”只是倡導(dǎo)民主與科學(xué),恰如今日之簡化解讀一樣,這場運(yùn)動的思想譜系仍需全方位透見。他首先就覺得,陳獨(dú)秀先生抨擊新思潮兩大罪案,有些簡單化且比較激進(jìn)。因?yàn)榘凑贞惇?dú)秀的主張,要擁護(hù)民主(德先生)就要反對舊倫理與舊政治,要擁護(hù)科學(xué)(賽先生)便不得不反舊藝術(shù)與舊宗教,要同時擁護(hù)科學(xué)與民主這兩位先生就要先反國粹和舊文學(xué),這其實(shí)也是為何運(yùn)動從文化興起的緣由。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在哪里呢?其實(shí)就在于胡適所論“新思潮的意義”的最后一點(diǎn)上面,亦即“再造文明”。“五四”之后,中國文明的再造,并不能在中國傳統(tǒng)內(nèi)部封閉發(fā)展,而是形成了中西之間的互動。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胡適將“五四”視為“中國文藝復(fù)興”的看法的確有窄化之嫌,但胡適的觀點(diǎn)還是容納了更為多元性的理路。胡適所說的“研究問題”,就是要解決社會、政治、宗教與文學(xué)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進(jìn)而所說的“輸入學(xué)理”,則是介紹西方的新思想、新學(xué)術(shù)、新文學(xué)與新信仰,這兩方面被胡適視為“評判態(tài)度”的兩種趨勢。然而,千萬別以為胡適就是一位徹底的全盤西化派,他同時也主張整理國故,而不是將傳統(tǒng)徹底加以拋棄。如今,面對“五四”的態(tài)度,既有繼承“五四”者,也有斷裂“五四”者,前者希望將“五四”傳統(tǒng)接續(xù)下來,后者則認(rèn)定“五四”乃是中國文明發(fā)展的歧途。實(shí)際上,“五四”就是個既破又立的雙向歷史過程,這就是所謂“不破不立”;“五四”更曾如此大刀闊斧地扭轉(zhuǎn)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方向,進(jìn)而融入全球文明的大格局之內(nèi),這就是所謂“大破大立”。
總而言之,我們試圖從“大啟蒙”的角度看看新文化運(yùn)動的意義,其中一個視角轉(zhuǎn)換就在于:從世界文明的大脈絡(luò)和大維度當(dāng)中來重新審視“五四”,而不是以往那種僅僅從中國文明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待“五四”,這其實(shí)是一種從內(nèi)在視角到全球視角的轉(zhuǎn)換,因?yàn)椤拔逅摹辈⒉皇莾H僅被視為中國文明內(nèi)部的一次歷史轉(zhuǎn)折,而且同時也帶來了對于世界文明的積極貢獻(xiàn)。
【責(zé)任編輯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