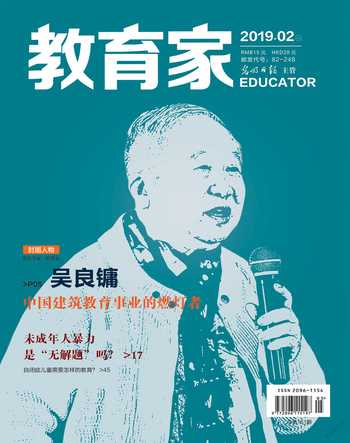李祖文:對兒童閱讀的追問與思考
作為一名語文老師,如果不談兒童閱讀,好像自己out(落伍)了一樣。有人甚至說,兒童閱讀就是還語文教學的詩和遠方。但是許多老師經過多方嘗試和努力,不僅沒有讓兒童愛上閱讀,反而適得其反,收獲了這樣一個現實:繁榮了童書市場,枯竭了閱讀欲望;繁榮了推廣層面,枯竭了閱讀興趣。理想很飽滿——讓孩子們從小熱愛閱讀、熱愛文字、熱愛圖書,現實卻很骨感——好書人手一本,效果卻參差不齊。面對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我們有必要對兒童閱讀發出如下追問。
追問一:到底是“兒童為中心”,還是“成人為中心”
看到這個問題,很多家長和老師會天然覺得自己做到了“以兒童為中心”。事實是這樣嗎?兒童如何讀,你要聽我安排;讀完你要探討什么,我來幫你確定;為什么要讀這本書,因為它可以給你帶來好處……這種情況下,其實很多成人在兒童閱讀中扮演的是決策者的角色。兒童是讀書的主體,如果以兒童為中心,那么他們有讀“差書”的權利,有讀多少的權利,有討論什么的權利,也有無目的閱讀的權利。而這些正是成人常常忽略的問題,以至于成人忽視了兒童在閱讀中的主體作用,甚至打消了他們的閱讀積極性。
追問二:到底是“思辨性的閱讀”,還是“引導式的閱讀”
“思辨性的閱讀”容易將整本書的閱讀帶入一個“死角”;“引導式的閱讀”在兒童不同的閱讀階段進行不同角度引導,鼓勵兒童一次又一次的反復閱讀。老師們經常是讀到《獾的禮物》《一片葉子落下來》,就情不自禁要探討對于“死亡”的認知;讀到黑鶴、沈石溪的動物小說就要談談“環保與愛護動物”……在兒童閱讀層面,我們倡導的是“引導性閱讀”,至于更深層次的思辨,可以留待合適的時機,讓孩子自然綻放、自然思辨。
追問三:到底是“策略的學習”,還是“知識的獲得”
“策略的學習”為“知識的獲得”服務。我們可以用任務單、閱讀單作為工具,關注孩子們的困難與問題,讓孩子記錄下自己讀書時在哪里卡殼了,哪里沒讀懂,想對書中某個人物說什么……對此,教師也好,家長也好,要與孩子一起追根究底,解答他們的困惑和疑問。
追問四:到底是“童書演奏”,還是“圖文搭配”
“童書演奏”是源于我國港臺地區的一種閱讀方式,就整本書而言,既有封面又有扉頁,既有插圖又有文字,用“整本書”的思維,編者將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所有信息散落在書中的各個角落。“童書演奏”的方式在整本書閱讀時可以呈現這樣的態勢:不同的“樂器”在“樂曲”的不同演奏階段介入兒童的不同閱讀狀態,一首動聽的“樂曲”如同讀書納入不同孩子不同程度的感知后,共同“譜寫”的閱讀之歌。這就讓很多不同進度的孩子,都能從自己的視角解讀圖書的用意,而不必強迫孩子向著最快最好的目標邁進。“圖文搭配”,則是將書看成簡簡單單的圖是圖、文是文,即只是為了搭配得好看,跟整本書傳遞信息的理解不一樣。而讀一本書,我們就是要還原“整本書”的“本色”,跟隨一本書的講述節奏,感知這本書要傳遞的知識與內涵。
追問五:到底是“閱讀的樂趣”,還是“閱讀的績效”
我們要求兒童在閱讀時記錄下很多東西,如好詞佳句、讀后感,還要做與這本書相關的練習題,甚至續寫故事、將原文轉化為圖畫。但是成人閱讀時卻并不會如此嚴格地要求自己。閱讀大抵分為三類:知識性閱讀、實用性閱讀、消遣性閱讀。因閱讀的目的不同,所以閱讀的方式與要求就不同。當我們進行某一種目的性閱讀時,使用一些輔助的工具加以幫助無可厚非,作為成人,我們有必要要求兒童每本書都要如此嗎?這值得教師和家長深思。
追問六:到底是“親子閱讀”,還是“同伴閱讀”
從“從眾”心理角度分析,我們的閱讀目的或者閱讀品位,跟我們所在的群體有極大的關聯。“親子閱讀”可以輕松地將閱讀的主體與責任交予家長;“同伴閱讀”則需要我們跟進相應的讀書會,協調不同家庭的關聯,有一定難度,但是效果同樣顯著。
追問七:到底是“書香校園”,還是“校園書香”
“書香校園”,這個稱謂不是隨便起的,在各地均有嚴格的參考標準。如是否有領導小組、工作計劃和規章制度以及讀書活動;是否有專門的圖書閱覽室、讀書櫥窗、宣傳口號,還要考核具體的人均藏書擁有量;是否有參加各級各類評選、教師與家長參與;要求學生每天的閱讀時長,還有教師關于讀書的論文發表情況等。但“書香校園”真的飄蕩著“校園書香”嗎?“閱讀”能稱之為“特色”嗎?閱讀不是本來就應該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嗎?換言之,我們創設“書香校園”不應該拘泥于一種形式,而是要讓孩子們真正地在校園書香的浸潤下,喜愛閱讀,做一個快樂的小書蟲。
我們可以在音樂教室擺放關于音樂的書籍,在美術室擺放關于美術的書籍,在實驗室擺放關于科學的書籍,甚至在學校各個樓層擺放上關于體育的書籍。我們的書籍到兒童的手里,其實就差最后一米,書籍就應該放到兒童“伸手可及”的地方。兒童閱讀要真正回歸兒童本位,實現真正的兒童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