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霍巴利王》“腦洞大開”的背后真相
徐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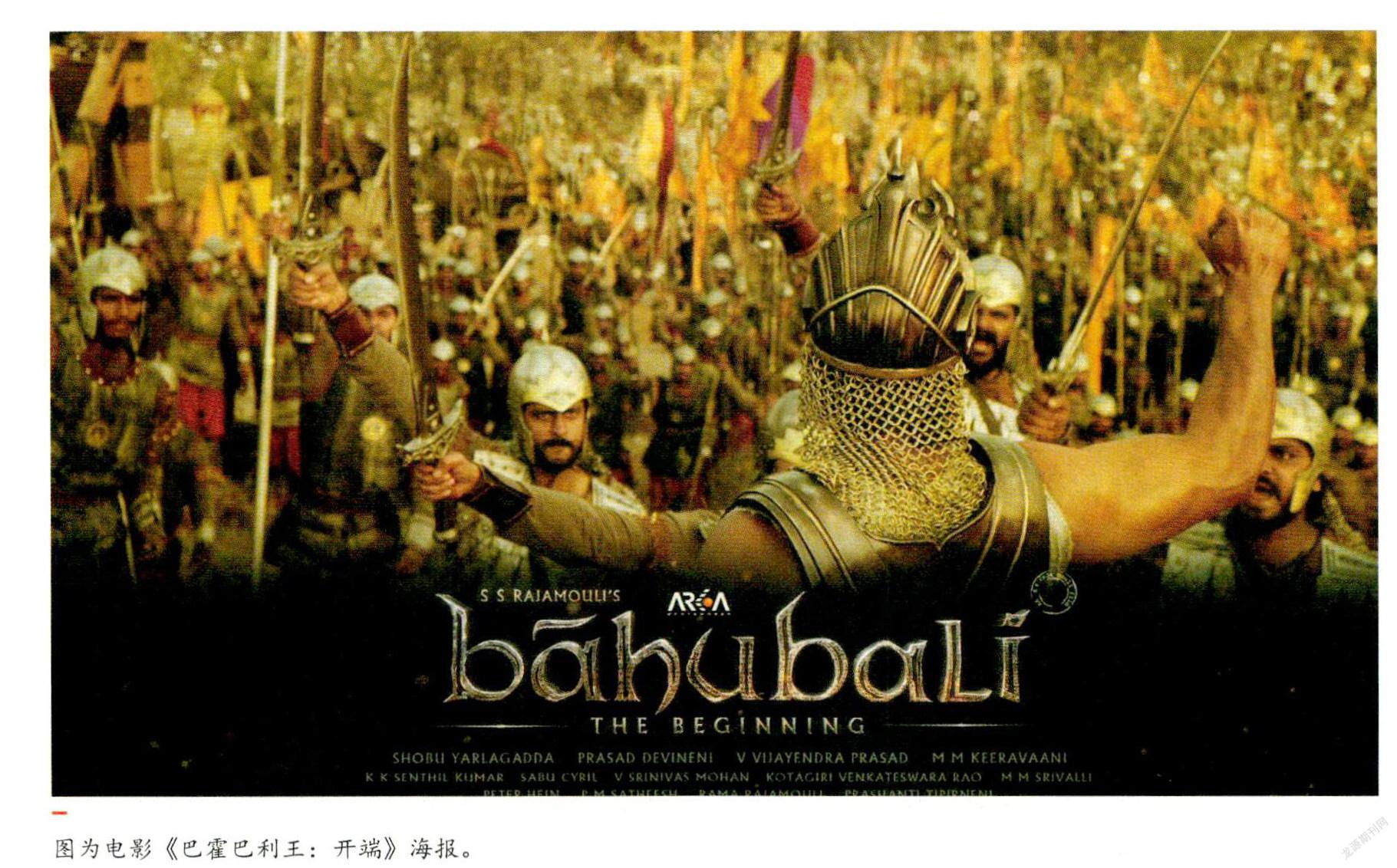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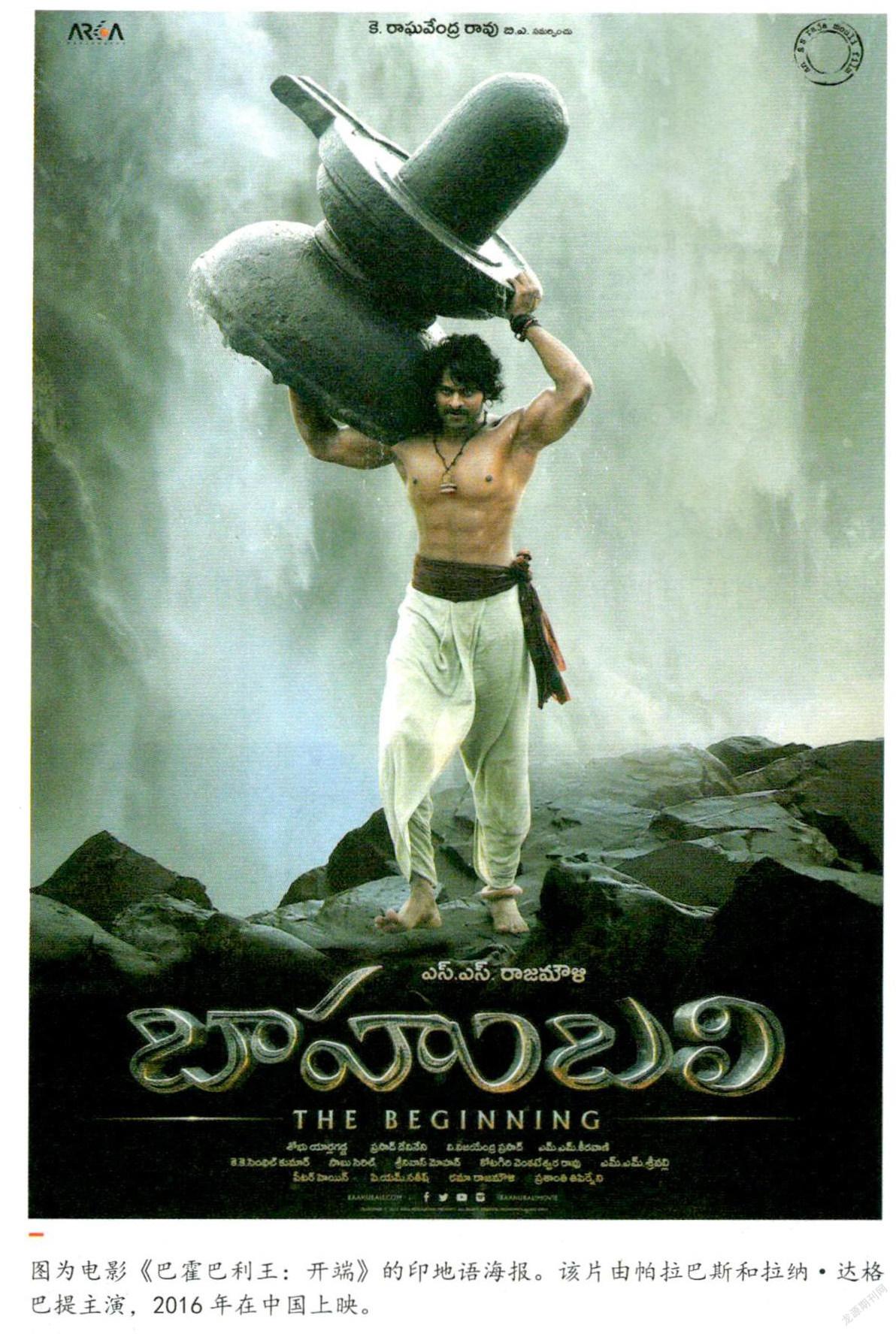
我們對于這部史詩片所承載的印度傳統(tǒng)與文化知之甚少,卻習(xí)慣在自己所處的文化背景中或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理解它。
在全球化的時代浪潮中,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然而對于中國人來說,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現(xiàn)象:我們對地球另一邊歐美文化的了解遠遠超過毗鄰而居的南亞鄰國印度,這片南亞次大陸成了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對待印度電影,中國觀眾更樂于接受那些取材現(xiàn)實、聚焦當(dāng)下,具有情感共通性的作品,而對于那些歷史題材、史詩題材的作品,往往由于缺少相關(guān)的知識背景而產(chǎn)生理解上的偏差,甚至是誤讀。《摔跤吧!爸爸》以近13億票房成為當(dāng)之無愧的印度引進片票房冠軍,然而在印度本土以及海外更多地區(qū),打破多項紀(jì)錄、口碑爆棚的作品則是《巴霍巴利王》系列,該系列的下部在印度本土上映時票房是《摔跤吧!爸爸》的近三倍。盡管如此當(dāng)它雄心勃勃地進軍中國市場時卻折了戟,上下兩部分別以700多萬和7000多萬票房收場。
從跨文化視角來看,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我們對于這部史詩片所承載的印度傳統(tǒng)與文化知之甚少,卻習(xí)慣在自己所處的文化背景中或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理解它。《巴霍巴利王》系列通篇充滿了各種神話和宗教隱喻,這些印度觀眾耳熟能詳、了然于心的典故,對于中國觀眾來說卻像隔著兩國的喜馬拉雅山一樣難以逾越。《巴霍巴利王》被中國觀眾詬病最多的便是“腦洞大開”的“開掛”和“歌舞”。那么,這些“腦洞大開”背后的深層緣由究竟是什么呢?
“化身”思想與偶像崇拜
在印度的宗教和習(xí)俗中,神靈往往具有多種化身。他們常常化身為各種形象拯救世界于危難之中,久而久之,印度就形成了非常濃厚的偶像崇拜情結(jié),他們認(rèn)為英雄都是神靈的化身。當(dāng)人們崇拜某個英雄時,就不知不覺地賦予英雄某種神性,將其神格化,且對英雄的渲染無所謂過譽。
《巴霍巴利王》的故事框架脫胎于史詩著作《摩訶婆羅多》,書中描繪了婆羅多族的兩支后裔班度五子和持國百子為爭奪王位繼承權(quán)而展開的一系列斗爭。
電影的主人公大多能在史書中找到對應(yīng)的人物原型。初代巴霍巴利的人物原型是班度五子,作為神之子,他們分別具有智慧、天生神力、正義、勇敢等品質(zhì)和能力,巴霍巴利王身上也具有這些“神性”。“巴霍巴利”的梵語本意即是“大臂者”,他力大無窮、以一敵百,同時機敏過人、足智多謀,擁有“照亮夜空的智慧”。他為人親厚、心胸闊達,受到百姓的尊敬和擁戴,他是一切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是人亦是神。二代巴霍巴利可以看作濕婆的化身,他劇中的名字就是“Shiva”,即濕婆,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毀滅之神、舞蹈之神。林伽(男根)是濕婆最主要的象征,因而Shiva能夠徒手舉起巨大的林伽,會歡快地跳起坦達羅舞,還能在與叔叔決戰(zhàn)中節(jié)節(jié)敗退的情況下,伴著鏗鏘有力的坦達羅頌,以自己的血祭林伽爆發(fā)出巨大的能量反敗為勝。
勇敢且獨立的提婆希那公主也是若干史詩里女中豪杰的集大成者:不屈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選擇心儀之人時,她是“安巴公主”;忍辱負(fù)重、風(fēng)餐露宿時,她是復(fù)仇女神“黑公主”;大仇得報之時,拎著敵人頭顱,挺拔英姿又猶如“迦梨”女神附體,令敵人聞風(fēng)喪膽、落荒而逃。從殺伐果決的希瓦伽米太后身上,我們又能看到“貞信”太后的影子,沒有合適的王位繼承人時,曾憑一己之力統(tǒng)治整個國家,國泰民安、富庶繁榮。除此以外,還有像“毗濕摩”一樣忠心耿耿的卡塔帕,猶如“沙恭尼與難敵”附身的奸詐狡猾的巴拉父子,史詩人物的靈魂就這樣鮮活地注入到電影角色當(dāng)中。
歌舞段落的想象空間與敘事功能
《巴霍巴利王》上下兩部在中國大陸上映時,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刪減,尤其是歌舞段落。在中國觀眾眼里可有可無甚至略顯尷尬的歌舞,卻是印度電影中靈魂般的存在,是這個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國度得以緊密連接的文化認(rèn)同載體。印度觀眾習(xí)慣在歌舞中互動、狂歡、盡情釋放,獲得被稱為“Darshana”的宗教體驗(可理解為觀看者“信徒”與被觀看者“神”之間的雙向觀看),因而歌舞也是印度人民寄托情感的重要載體。
印度的宗教與哲學(xué)傾向于將現(xiàn)實世界視為虛無,稱作“摩耶(maya)”,中文譯作“幻”,世界萬物均為假象,唯有“梵”為真實存在,故而相比于注重寫實,印度人民更加熱愛且擅長幻想,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也常常帶有一定的魔幻風(fēng)格。
《巴霍巴利王》下部中美輪美奐的天鵝船歌舞段落,應(yīng)該會給中國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當(dāng)天鵝船騰空而起,船帆變作翅膀,在天際與云馬共同馳騁時,我們?yōu)橛《热嗣裉祚R行空的想象力與無與倫比的創(chuàng)造力感到驚嘆的同時,也被不屬于自身既有審美習(xí)慣與經(jīng)驗的陌生感所裹挾。
同樣的情節(jié)給中印兩國觀眾帶來的觀影體驗大為不同。對于印度觀眾來說,天鵝船并非“腦洞大開”的產(chǎn)物,而是出自他們自幼耳熟能詳?shù)摹读_摩衍那》。書中羅摩歷盡千辛萬苦終于戰(zhàn)勝十首魔王羅波那救回妻子悉多,夫妻二人乘著財神俱毗羅的云車,回到了家鄉(xiāng)阿約迪亞,而史詩中云車的造型就是能飛的天鵝,在諸多神話插圖以及影視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云車的原型。羅摩和悉多被世人稱為愛情的典范,而影片中也借此隱喻了王子與公主的結(jié)合像羅摩和悉多一樣珠聯(lián)璧合、佳偶天成。
除了拓寬想象空間,歌舞還在影片中承載了敘事功能。《巴霍巴利王》下部中被刪減的一段歌舞,表面看起來是一首頌神之歌,實則是女主向男主表明心意,借“神”喻人。歌詞里的克里希那是印度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的化身之一。他的少年時代是在一個牧牛人的家里度過的,他和牧牛少女拉妲兩小無猜、情投意合,給后人留下佳話。克里希那與拉妲的愛情超越了神與人的界限,是印度人心目中的“至上之愛”。
印度古典戲劇理論《舞論》中把藝術(shù)作品的“味”分為8種,首當(dāng)其沖的便是“艷情味”,而“艷情味”對應(yīng)的“常情”便是愛情,因而愛情是印度人格外鐘愛的主題,是藝術(shù)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婆希那公主借歌詞中拉妲對克里希那的愛慕之情,含情脈脈地表達了對心上人的一往情深,而王子也心領(lǐng)神會,遙寄相思。這首歌從情感到意境都對男女主角感情的遞進起到了重要作用。刪減后的版本呈現(xiàn)給中國觀眾的是公主對智勇雙全、力挽狂瀾拯救了自己國家的王子一見傾心,產(chǎn)生了突兀感,而完整版中這段歌舞做了很好的鋪墊——原來公主從他還是那個“傻小子”時便已芳心暗許,從而令電影敘事節(jié)奏流暢、結(jié)構(gòu)完整。
《巴霍巴利王》是印度神話史詩的現(xiàn)代傳承,并且巧妙地融入了歌舞段落。在跨文化視角下,我們得以看清這部電影的“靈魂”。當(dāng)整個世界變得更加扁平,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尤為重要,中國觀眾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tài)和平等的視角對待他國文化,客觀看待文化多樣性。加強多元文化之間的互聯(lián)互通,不僅是減少文化折扣的有效手段,也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