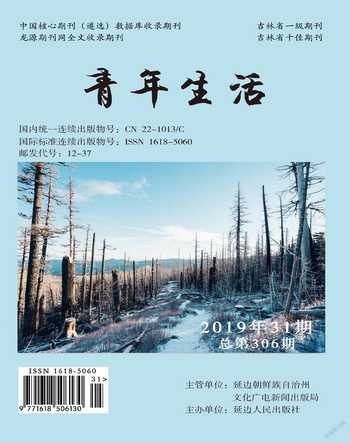人性本質中的“善”與“惡”
繆志鵬
摘要:對于人性問題的探討,從古至今都是社會熱議的話題。人性問題的核心是: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性善”、“性惡”兩方給予了絕然不同回應。站在新的歷史角度,回溯人性本質中的善惡起源及思想內涵,思考人類本質中的善惡,啟示人類對人性本質的追求。
關鍵詞:性善論;性惡論
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這樣的辯論,也不是第一次提及,它就像一個邏輯的黑洞,永遠都有理論可以支持其中的一方。孟子說,人性善。《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提出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荀子則反之,提出了“人性本惡”的理論,荀子說“好惡、喜怒、哀樂,夫是之謂天情”。性善論,性惡論就此展開了長達千年的爭論。
一、性善論、性惡論的歷史起源及思想內涵
(一)性善論的歷史起源及思想內涵
春秋戰國時期,時局動蕩,紛爭不斷,在這樣的歷史時代,提出性善論,并不僅僅是對人性本質的思考,還有對安定祥和,國強民富的一種精神價值追求。孔孟性善論的提出具有現實的針對性,符合歷史的發展訴求。
早在孟子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了對人性本質到底如何的探討,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美好期冀。孔子提倡“仁”、“義”,從“仁義”中探討人性本質的根源。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此處孔子雖說“仁”卻也是在對人性的思考,提出“克己”,從本質上克制自己,改變自己本身的壞毛病,使得自己符合禮儀的要求和規范,達到“仁”的境界。孔子提出的“仁”是一種先天內在的精神,是人類本性中的東西,是一個自在的品行,強調了人性本善。《中庸》中提出“天命謂之性”也在主張性善。
在經過早期對人性本質的初步探討之后,到了戰國初期,社會時局更加動蕩,對“善”的追求和渴望更加強烈。諸侯混戰,各個國家未來蠅頭小利盡相追求自身利益,戰爭成為家常便飯,忽略了國家建立最初的本質,向極了餓狼,全部撲向戰爭所帶來的盈利,整個社會猶如野獸橫沖的牢籠。在這樣的時局之下,孟子提出了對社會的美好期待,希望天下是太平的,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在對社會有著深刻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性善論”就成為了孟子追求的美好愿望。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孟子曾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人性是本善的,在看到別人遇到危險時,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救人,這樣的救人行為并不是因為利益關系,血緣關系的存在,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善”,因為這樣的“善”救人于危難之中。孟子在論述“人性善”的過程中,也發現人雖然“本善”,卻也大量存在不善的行為,孟子認為,這是因為受到外界環境和后天自身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是自身內心對善的曲解,導致了部分人后天為惡,孟子認為,在私利和外界因素的影響之下,我們應該放棄私利,學會克制自身,維護我們內心本存的善。
(二)性惡論的歷史起源及思想內涵
性善論的存在必然帶來對性惡論的思考。性惡論主張“人性本惡”。荀子提出“性惡論”時,已經處于中國“百家爭鳴”的末期,荀子借鑒諸子百家對人性的論述,結合當時社會時局現狀,綜合形成了性惡論。
戰國末期,中國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人類的生產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農業,商業,手動業發展迅速,人員交流逐漸頻繁。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之下,人們潛藏在內心的“惡”慢慢顯露。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劇烈動蕩,經濟繁榮昌盛,社會對思想的管控力度空前減弱,思想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代。性惡論就產生在這樣一個文化,思想大繁榮的時代。道家提倡崇尚自然,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強調融入自然,保持內心的清靜。法家主張法治,認為人是好利貪欲的,提倡通過強權來保證社會規范的建立,雖然法家沒有直接的提出人性善惡的理論,但影響了“人性惡”思想的提出。在文化大繁榮的同時,社會經濟也進入了高峰,牛耕,灌溉技術的發展,使得生產力大幅提高,經濟貿易成為生活的日常,廣泛的貿易,使得大量的人口脫離原來的土地,活躍與各地,由此展開的土地,財富爭奪成為必然,人民對利益的追求之心被成功喚醒,人民貪欲的心就此展現。荀子自身的生長環境和他所處的特殊時代,喚醒了沉睡在人類心中的“惡”,促成了改理論的形成。
荀子認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其偽也”。人是天生好逸惡勞,喜聲色的,如果所有的東西都不加以節制和制止的話,就會出現戰爭,禮儀道德將淪喪,天下將大亂。所以人們要學習禮儀,知仁義,克制自己,利用外界的規矩教化于人,避免我們沉入“性惡”的深淵。“人性本惡”,區別圣人和小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學習禮儀規范,從而規避我們心中本來的惡性。因此,我們的人性是惡的,最后的善是由于外界的學習而掌握的,從而證明了人性本惡。
二、史前人類本質中的“善”與“惡”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第一編《歷史對今天的啟示》中對人性的本質進行了論述。書中這樣說到“歷史記載表明,人類生來既不愛好和平,也不喜歡戰爭;既不傾向合作,也不傾向侵略。決定人類行為的不是他們的基因,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教給他們的行事方法”。斯塔夫里阿諾斯承認人性是本善的,認為人性惡是受到外部社會的潛在影響,是外界因素致使人性出現“惡”。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經過研究得出結論說“人性是一種巨大的潛能,會因社會影響而具有多種表現形式......侵略性不是人類與生俱來或不可變更的特征,而是一種鼓勵侵略的社會環境的產物。”
史前人類的男女社會分工就表明了史前人類本質中“善”的部分。在史前社會,男女共同承擔著這個部族的生產生活。男性主要負責獵物的捕獲,部族安全的防御,女性負責采集,照顧孩子。由于沒有足夠的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較低,女性和男性在勞作方面并沒有太大的差別,男性和女性都是平等的食物供給者,在男女社會地位方面是保持平等的,兩者在社會生活形態中表現出極其的公平。隨著農業社會生產工具的發展,技術得以提高,先進工藝的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分化,男女平等地位就此打破,徹底的破壞了女性在社會上的獨立地位,女性成為了男性附屬品的歷史就此開始。“人性本善”在農業社會的影響和驅使之下逐漸表現出“惡”。
史前人類數量屈指可數,是整個自然中較少的一個種群。一定的區域就能滿足社會生活的全部需要,太大的區域對于一個群體的生活并沒有太大的好處,可能還會給族群的生活帶來災難。史前人類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控制周圍的世界,沒有強大的力量和其他物種展開保護領地的爭奪,太多的土地對于史前人類來說,是無用的。史前生產力的限制,最終形成“人性善”的結果。
在“善”的對立面必定存在“惡”。史前人類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善”,但也在形成“善”的過程中伴隨著“惡”的產生。在認識到“人性本善”的同時,我們也在太平洋的部分島嶼發現了“人性本惡”部落的存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芬圖人是一個兇猛的部落,他們在接觸外界的過程中一直是以武力的方式,整個部落兇殘勇猛。在非洲的草原部落中,我們也能發現同樣現象的存在。
在“善”與“惡”之間,史前人類在歷史發展的80%的時間中,一直還是以“善”的形式存在著的。“善”與“惡”本就是一個邏輯的黑洞,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孟子,荀子在對人性進行善惡的論述中,主張不同,思想不同,最終結果卻都是殊途同歸,走向“善”。孟子沿襲了孔子“性相近”的主張,孔子提倡“習相遠”,兩者從不同角度出發,以孔子的思想為指引,最終都回歸到共同的思想淵源上。荀子提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孟子說“仁義禮智,非有外爍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無論是孟子性善的主張還是荀子對惡的論述,歸根結底都是希望人們從善,到達禮儀教化的規范,追求道德上的善。
三、對性善論、性惡論的思考
“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爭論兩千余年未有結果,最終勝負難論。就事實而論,性善論、性惡論之所以會爭執長達千年而未有結果,主要是因為人們并非是在認識人性,而是在主張人性,缺乏從根本上對人性善惡認識,只是根據主張的不同形成對立的人性觀,并由此提出去怎么看待人性,沒有回歸到人性善惡的辨別上,只是在爭論誰對誰錯的漩渦中徘徊。
因此,人性無論是歸結為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都無法完美的詮釋、演繹人的心理和行為。我們更應該從實踐出發,分析論證。《全球通史》一書就說,其實自然間本吳善惡之分,有善惡之分的是我們人類社會,善惡的區分主要看我們怎么去定義善惡,不能拋棄對善惡的定義來看,如果沒有原始的定義,我們對善惡的一切評判都是無力的。
客觀看待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我們會發現,兩者師出一門,在孔子提出對人性的思考以后,并沒有給出具體的回應時,對于人性善惡論述之爭就此開始。細致分析對人性兩派的主張我們就可以看出,兩者是相互補充、批判的,缺一不可,是不可以獨立存在的。
“性善論”與“性惡論”在幾千年的爭論中,相互補充,促進這對方的進步,在到達自己觀點發展的同時,也推動了另一個理論學說的升華。
“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爭論對當今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物質得到充分滿足的時代,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我們的精神世界卻沒有同步的更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性善論”與“性惡論”符合了當代社會對于精神世界建設的需求,達到了理論和現實的無縫契合。在“性善論”與“性惡論”都追求最終的善的基礎之上,法律無法約束的社會道德等方面,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觀點將在人們的內心筑起高墻,推動整個社會精神世界的發展,從“性善論”提倡保持內心的善與“性惡論”提倡的要學會克制自己的欲望,規避先天的惡開始,帶動社會道德與經濟發展的同步,實現全面和諧社會的倡導。
發揮禮法對人的主動積極作用之下,社會也應該在“性善論”與“性惡論”的爭辯之中,尋求社會禮法制度的建立。在法治社會完善的同時,我們還有法律條文之外未涉及的社會管理部分。回歸到“性善論”與“性惡論”的終結,完整社會禮法的建立勢在必行。結合社會法治強有力的治理和根植于內心的禮法規范,形成內外聯動的約束力,社會將會得到極大的進步。我們的社會建設,要加強道德建設,健全人們的人格,制定出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規范,不斷的提升人的素質,劃出社會參與人員的最低底線,形成完備的體系。
人類從歷史中走來,我們無法預知人類的最終命運,但站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至少能回溯我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展望我們的未來,從歷史中得到啟示,用于不斷豐富我們的智慧。
注釋:
《孟子·告子上》
②《孟子·公孫丑上》
③《荀子.性惡》
④( 美) 斯塔夫里阿諾斯.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 21 世紀( 第七版) [M].吳象嬰,梁赤民,等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3-44.
⑤ A.Bandura,Agression(Prentice Hall,1973),pp.113,322.
⑥《荀子.性惡》
⑦《孟子·告子上》
參考文獻:
[1]荀子著,方勇 李波譯.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 21 世紀( 第七版)[M].吳象嬰,梁赤民,等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3-44.
[4]高信奎.荀子人性論思想研究[J].河北:河北經貿大學,2018.
[5]張子申 潘多英.淺論“性惡論”與“性善論”之比較[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日報,2014年01期.
[6] 楊英法.荀子“性惡論”與孟子“性善論”比較研究[J].北方論叢,2012年06期.
[7]蔡雯雯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比較研究[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5年2月第31卷03期.